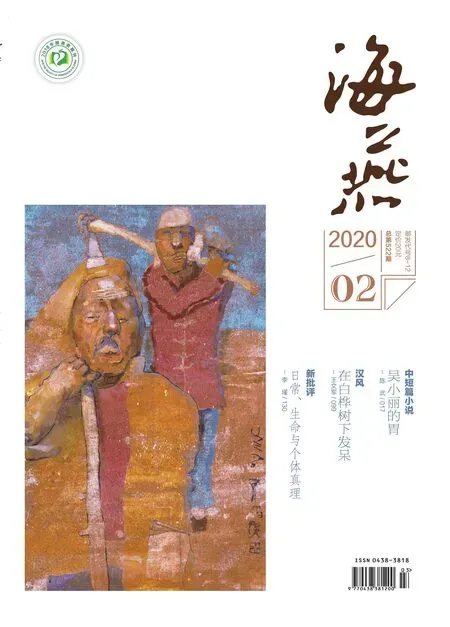沉甸甸的谷穗(外一篇)
文
有时候,我们自认为自己是“老师”,可是很多地方还不如学生,尽管学生那么尊重自己;有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是家长,在某些地方却不如自己的孩子,这你得承认。生活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彼此学习,才会得到更多。有时候面对比自己小的,比自己矮的,就要弯下腰来“轻声细语”。
说来不怕你们笑话,我下乡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谷穗长啥样子,只是看过书本上的。1975年我下乡,也才17岁,还是懵懂的少女,对很多事物都觉得新奇,不仅什么农活也不会干,我个子较矮,瘦弱,甚至连个镐头都拿不动。也不知道遇到了哪位“贵人”,让我去村学校教书,可能看我干不了农活吧,可怜我。这个学校因小学、初中在一起,所以叫“学校”而不是小学。我担任三年级某班班主任,兼教初中语文。
九月末的一天,突然雷声大作,紧接着蚕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的下了起来。学校紧急通知,让我领着全班同学去帮助农收,说是公社给的紧急协助任务。我也不知道干啥,就跟着“大部队”走,准确地说是一路“急行军”。大家都没带防雨工具,人人淋得像“落汤鸡”。一路跑到目的地,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才发现我们抢收的是马路泥坡下种的一大片谷子。三年级的学生个个都像是“小老虎”,麻利地跑下泥坡,就去抱已经有人割好捆好的谷子。我好不容易下了泥坡,还摔了一个大跟头,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一个学生看到了赶紧把我拽起来。暴雨紧密地打在脸上,相撞的急雨激起一层薄薄的雾,我都看不清楚地里有多少忙碌的人。朦胧中我也去抱捆好的谷子,却发现谷子那么沉,试了几次才抱起来。
抱谷子容易,爬坡上去就难了。我一次次从半坡上“呲溜”下来,反复多次也上不去。身边的学生一个个都是干活的好手,那么沉重的谷捆在他们怀里、肩头看似那么轻盈,那么滑的泥坡,他们竟然上下自如。没想到,自己还不如一个个10岁左右的孩子,辛亏当时疾风暴雨和大家都非常忙碌,要是全校师生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笑料。女校长看见我“不行”,就招呼我负责去割谷子。
抹一把脸上的雨水,弯下腰面对一大片谷子,我这才仔细地看清楚谷子长啥样。原来,谷穗那么长那么沉,它们低垂着头,感觉是那么饱满。如果此时不及时抢收,谷穗则会烂在地里,这可是他们一年中的口粮啊。金黄色的谷子,在暴雨中它们的“身躯”被打得东倒西歪,我好不容易“拢”一把,却又发现镰刀割不断它,因为穗秆已经淋湿。其他老师们都是“刷刷刷”地割,我是“嚓嚓嚓”地划。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割了两捆,可我发现我都不会捆谷子,怎么捆都是一提就散。一个男孩子看见了,跑过来“三下五除二”帮我捆上,我低下头冲着这个学生感激地笑着说:谢谢你。

我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和谷粒,大家都一样,看到每个人依然那么干劲十足,尤其是这帮孩子,个个都是“画面”,我也感到这没什么。一看他们都是农活的“熟练工”,可能以前学校经常参与这样的“紧急任务”吧。在这次抢收中,我都觉得自己是来给大家添麻烦的,是给班级“拖后腿”的,不仅校长老师们关照我,学生们更是体贴我,瞬间感觉自己这个城里人都不如一个乡村的小学生。这次“任务”完成以后,我希望改变一下自己,开始学着熟悉一些农作物,业余时间也会主动去干点农活。
一个休息日,恰好是艳阳高照的日子,正赶上村里打谷子,我就跟着一起去了。打谷场上,脱粒机一直响个不停,有人负责脱粒,有人在筛谷子,用木锨扬谷子,一片丰收喜悦的山区景象。我掂一掂木锨不怎么沉,也想跟着学扬谷子,就是把脱粒机脱下来的谷粒壳米分开。看别人轻轻一扬,沉淀的橙黄的米就自动往“小山”上堆,而谷壳随风而去。看他们扬谷子那么轻松自如,我也跟着一起操作,可同样的动作,我发现怎么扬风都是往我自己身上吹,弄得我跟个“土人”似的,眼被谷壳迷得睁不开,不仅呛得咳嗽,还眼泪直流。当时大家都笑了,不过他们笑得那么淳朴,那么可亲,还一口一个“老师”的称呼我,也许因为我是他们孩子的老师。有老农主动走过来手把手教我,我试了多次以后,总算是得心应手了。
这个故事过去40多年了,今天想起来依然感觉十分温暖。现在,每每我喝到小米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那段难忘的日子和那次雨中抢收的镜头。从农田到餐桌,谷穗给了我多少书中不知道的东西,不一样的生活体验,那金黄和沉淀给了我多少值得珍藏的记忆。几十年来,我从不浪费一粒粮食,因为每一粒都来得如此不易,它们不仅带着土香、泥泞和汗水,还有等待、喜悦和渴望。浓浓的米香,雨中的思绪,我会把这份美好的情愫化成内心和生活中的诗篇。
美丽的乡村,就像一个人生的“田间课堂”,可爱的孩子们,他们如此质朴,个个都是我生活中最好的“老师”。
“长寿秘诀”
我下乡那会儿,村里有一个老爷爷,他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一生也是谜一样的。之所以这样说,是这个老人给全村人甚至更远地方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他是全村乃至公社最长寿的老人,他的长寿之道大家一直在研究探讨,最后好像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要说对这个老人的印象,大家一定对“修仙”者非常熟悉,他特别像深山老林里独居的老者。村里的人都知道他100多岁,有人说他108岁,可你问他,他永远告诉你自己99岁。老人独自一人,独门独院,和蔼可亲,胡须白长,削瘦,不仅生活能自理,而且走路脚下生风,还耳聪目明,不拄拐杖。老人家和我们青年点隔着一条河沟,非常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和这个老人聊天,感觉他就像自己的祖父。
那年我17岁,在乡村当民办教师。休息的日子,我就去陪老人聊天。刚开始,我不敢进老人的院子,那里总有种阴森森的感觉。一天,青年点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老人院子里有棵枣树,他家枣非常甜,他摘枣给我吃,我说这样好吗?他说没事没事,你看我的。说着我俩去敲院门,发现没有动静,朋友说老人耳背听不见。院门用手轻轻一推就开了,原来院门是虚掩着的。
进了院子,一棵高大的枣树近在眼前,一颗颗饱满硕大的红绿相间的鲜枣特别诱人,那枣子沉沉地低垂着头,似乎一下子就能伸手可摘。朋友个子高,却发现自己伸手也不可及,连蹦带跳也无济于事。他去老人的柴垛边上找棍子打,一眼还真瞄见了一个竹竿,他又惊又喜地跑过去。我半天不见他回来,扭头一看,发现他在轻声招呼我过去。我走过去,发现柴垛旁是一间很暗的小屋,我们顺着上了锁的门缝望去,看见里面有一口红漆漆的大棺材,奇怪的是棺材上一尘不染,非常光亮。
四周静寂,似乎只能听见自己的喘息心跳声。我们没敢久呆,轻手轻脚地往外走,刚一转身,发现老人笑嘻嘻地站在屋子门口,招呼着说:“进来吧。”我们不好意思了,跟着老人身后进了门。我进了屋,发现老人的生活极其简朴,屋里是土炕,炕上铺着陈年的席子,一个人的铺盖干净整齐地叠着,但成了老人休息时的“靠椅”。地下一张桌子,桌子上一套旧式茶具,看着有点像古董。老人说,我们一进院子他就瞧见了,他不反对我们摘枣,但是“那个地方”绝对不准去。我们笑着,点点头,说知道了知道了。老人从里屋端出来一小筐鲜枣,红红的,说:“吃吧,孩子,我老了咬不动了,这是我刚摘的。”说着抓了两大把给我们吃,还把枣筐放在炕上,说让我们这些城里来的人吃个够。那枣特别甜,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脆最甜的枣,就是那种能“甜掉牙”的感觉。
我们和老人唠嗑。我问:“爷爷,你自己过呀?”老人点头算回答了。我又问:“你孩子呢?怎么没见他们来过呀?”老人停顿了几秒钟,慢慢地说:“他们都忙。”我接着问:“平时你自己做饭吃啊?”老人说是呀。我还是好奇:“你一个人在家里不闷吗?你这么大年纪了身边没人陪能行吗?”朋友拽了一下我的衣角,嫌我多嘴。没料到老人笑眯眯地告诉我,他不闷,白天眯着眼睛倚在被子上,困了打个盹,上山拾草拾柴、出去卖菜。我惊讶了:“你老人家还卖菜呀!”老人说:“我屋后有块地,种的茄子辣椒西红柿呢。”我恍然大悟,进院子时没看见菜园子,原来屋后还种着菜呐。
从那以后,我就留意河沟对面的老爷爷了,有时候老人背个筐去村子热闹的地方卖菜,有时候拿个麻袋去搂“菠箩叶子”,有时候穿得利利索索不知道去哪里,一走就是几天不回来。我们这里离村口很远,成年人都要走半小时,我每天去学校教书走这路都很累,可感觉他来回一点也不打怵。有时候我去老人家,想帮着老人扫一扫院子,帮助挑担水或者干点啥,可老人说什么也不让我干,说自己能行,不麻烦人。我问:“爷爷,你几天没回家了,去哪里了?”老人开心地说:“去儿子家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老人的儿子早死了,他可能是攒了卖菜的钱去看孙子了,孙子在城里,非常忙,没有功夫过来看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不太信。
熟悉了以后,老人告诉我,那屋里的棺材他准备快半个世纪了。几十年前,老伴去世,他就开始准备了,换了好几个,这个是最好的棺木,沉得四个人都抬不动。他每天临睡前都要去那里看一看,亲手擦一擦,回来后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感觉自己很舒服。这习惯保持了几十年了,多少次都差点快“住”进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反而越活越精神。他还说,其实自己也想开了,听天由命,命不由人,活一天就认真点活,要对得起老天给的“命”,只要自己能动,就一定要动一动。你看,我现在自己还能缝衣服呢。我这才发现,原来老人床头有个不起眼的小针线篓呢。
后来我离开了乡村,几年后我突然想起什么,再去“故地重游”,却看见爷爷家的院子里满是落叶,好像一年四季没人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