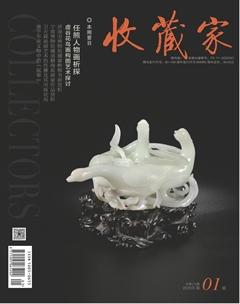谈谈中国古代权杖的发现
张明华



权杖,昭示身份、政权和神威的象征。在人们的印象里,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古埃及、西亚、安纳托利亚、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古埃及法老有权杖,西方的一些王室、军事首长、各宗教领袖们有权杖,近现代尚存的原始部落也有花样多多的权杖(图1)。中国的皇帝、藩王、官吏等的权力象征,一般都是等级森严、质地优良、形制繁多、大小不一的玺印。南宋匪山一战被元军大败后,丞相陆秀夫眼见回天无力,为免受辱,不忘把象征治国大权的玉玺栓在宋幼帝赵昺身上,背着他一起跳海自尽。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打垮蜀国藩王之后,因掠得的“蜀王金宝”是明朝皇室权力的象征,为了宣泄自己对明王朝的刻骨仇恨,对明王朝权力的鄙弃和蔑视,以赢得民心,将其暴力地凿碎成10多块(图2)。传统戏曲中县太爷升堂时,他的公案上总有那么一颗用布包裹着的大印,包龙图宁可丢掉官印(官位),也要判殺皇亲国戚中祸国殃民的人渣。有趣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有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电影名字也是“夺印”。确实,我国用印的历史相当久远,也有极其丰富的出土与传世资料。不过,考古发现及研究证明,中国不但有用权杖的历史,而且至少已有6000年之久,大概在商代开始逐渐显现以玺印示权的迹象,直至现当代。当然认识它们是有一个过程的。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嵌绿松石龙凤纹冒镦青铜柄扉棱玉戈(图3,玉戈复原时刃口上下似是颠倒了)、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距今4000~3800年四羊首青铜器、1986年在四川凉山新庄遗址出土顶托马鞍形装饰、周身刻满图腾状纹样的青铜杖等,应该都是权杖。还有不少同时代或稍晚的玉戈、戚、钺、斧等利刃形器物(图4、图5)。它们并非砍伐、杀戮的实用器,精美孱弱造型当属权杖无疑。质地与形式上的不同,应该是用途分工上的区别而已。当然,最形象、最精彩的无非是1986年在四川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杖(图6)了。长143、直径2.3厘米,重463克;上面錾刻五齿高冠人头像,乌、鱼、箭翎等纹饰。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应该是鱼凫王所执掌的权杖。那么,我国是否还有更早的权杖存在?答案是肯定的。突破始自1986年。
这一年浙江省良渚文化取得重大收获,考古队员们在反山良渚大墓的一件玉斧形器旁,意外发现了一些米粒状玉饰片,在其延伸线的末端,出现了一件用途不明的“舰形玉器”。经对残存遗迹的研判,米粒状小玉片应该是已朽柄体上贴嵌的装饰物,而凿有卯口和销孔的舰形玉器应该是镶在柄尾上的玉饰(图7)。由于玉质斧形器之前从未发现过有柄的征迹,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整个发掘工地,也引起了考古界的重视。我和同事们闻风赶去时,那件玉斧形器、几十颗米粒状的小玉片和“舰形玉器”,已从墓中起取,被纹丝不差、按1:1的比例,移到了一块底衬米厘格纸的画板上,其组合关系让人一目了然。我突然发现这件舰形玉器十分眼熟,它几乎同我们先前在上海福泉山良渚大墓发现的一件完全一样(图8)。上海的那件会不会也是玉柄尾饰?有没有复原的可能……一连串的问号,一种大有希望的发现,使我热血沸腾,归心似箭!
刚下火车,我便迫不及待地钻进库房,捧起这件“舰形玉器”仔细观察,果然没错!窄长椭圆形的体型,顶凿小小的卯孔,横向穿一销孔,这就是一件玉柄尾饰。再核查原始的考古发掘平面图,它的位置离开玉斧形器50厘米左右,与浙江反山一件情况接近,客观地反映了柄体的长度。我并不满足于此,我想,福泉山既然能复原一件,会不会还有二件、三件?于是,我将福泉山所有出土斧形玉器的良渚墓葬重新整理了一遍,将规格、形制、结构接近的玉器挑出来,从位置上、从功能上分析,居然有了更重要进展。先是新发现了一件马鞍形柄尾饰(图9),又在形式接近的玉器中发现几件底部有扁长卯孔,但没有横销孔的原来被称为“倒靴形玉器”(图10)、“僧帽形玉器”的奇特玉器,出土时它们都在玉斧形器上部约10厘米左右的位置上,而且其中两件恰巧分别与有柄尾饰的玉斧形器三位一体,配成两整套(图11)。良渚玉斧形器还有柄首饰!这又是一项重要突破!
为了更全面地、规律性地证实这一点,笔者几乎搜齐了江浙地区当时已经发表的所有资料。有趣的是,更早就有报道的江苏寺墩等多处遗址的平面图上,就已清晰地反映出这一情况,只是由于连接柄首、尾饰的柄体已经朽蚀殆尽,墓中的叠压文物太多,致使早已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宝贝不被认识。其实只要用虚线将它们连起来,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新的完整组合(图12)。不久,这一发现进一步发酵。浙江同行来沪,我正在撰文总结,便无私奉告这一规律性发现,他们回去居然完整复原了五套,没过几天再次来沪时,当面告诉了我这一喜讯。一时间,海内外博物院等收藏单位那些类似的、长期被误读的不知名器,由此得以正名,台北故宫玉器专家还专门寄来了复原成功的照片。玉斧形器三位一体的造型,由于酷似江苏澄湖古井出土良渚文化陶罐上的斧钺形刻画(图13),从而为“斧”字的祖形找到了四五千年的依据,结合各地良渚文化玉石陶器上出现的不少字形的刻画,也为良渚文化古文字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实证(图14)。
1986年,我草成《良渚玉钺研究》(当时大家都称“玉钺”)一稿。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给予了我极大鼓励,他亲笔致函,并重要提示:“‘玉钺一词文献少见,但有‘玉戚一词,戚即钺,也是斧柯之物,文字家谓戚是钺属而小,古代舞用‘朱干玉戚。文中所载的玉钺都不甚大,秘(柄)饰又甚豪华,作舞蹈的道具也未尝不可。用途未必局限于军事权力,如表示先人在部落或氏族中的地位,如权杖一类的性质。也是可以考虑的。总之,看司题要宽一点。”经检索,我发现先秦文献上“玉钺”一词确实难以寻觅,“玉戚”倒是屡见不鲜。从功能上、形制上、出土依据上认识,“玉戚”一词名副其实!这一规律性的组合发现与功能上的认定,在考古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新华社为此专门播发了消息(新华社上海11月11日电:《考古发现玉戚出土。这种王权的象征物,证明太湖地区4000年前就形成国家》,1987年)。1989年,当拙作《良渚玉戚研究》在《考古》第7期上正式发表时,又得到了时任《考古》主编、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来信高度赞扬。
《礼记·祭统》有“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的记载,显然,这里的舞并非娱乐之舞,而是出征前巫师(首领或王)手执红漆的盾牌和豪华型玉戚的巫舞。浙江反山“戚王”上雕刻有象征通天的乌纹和巫师御虎蹻的“神微”,这象征巫师的挥戚讨伐所向,是正义的,是受上天的意志决定的,对方是该死的天敌。由于原始社会的军、政、神、医等各种大权,一般均由地位至高无上的巫师(首领或王)一人承担,因此,形制取自刃具(生产工具和兵器)的豪华型玉戚,应该是象征军政大权的权杖。资料证明,原始部落里的权杖形式、质地、功能并非单一,良渚社会的权杖是否仅玉戚一款?
2010年,上海的考古隊员在福泉山遗址以北不远处的吴家场良渚墓地的207号墓中,出土了两件大型象牙器。一件79厘米,残损严重,置墓主左侧。另一件长达97厘米。片状,弓弧形,顶端斜梯状僧帽形,若玉戚的玉冒,下端榫卯结构插入椭圆形象牙镦。全器满饰10组繁缛细刻羽冠人兽纹,象牙镦上有两组鸟纹和兽面纹。长大、精彩、繁复程度,前所未见(图15)。笔者认为,前及豪华型良渚玉戚以利刃形式呈现的权杖,应当是军政大权的象征,那么,扁薄、孱弱、稀贵材料制作的象牙器,应该是良渚先民意识形态的象征物。象牙器上的羽冠人兽纹形象地表达了头戴羽冠的巫师,驾驭虎蹻与天地鬼神沟通的图案,那么这件象牙器应该就是良渚大巫师(首领或王)行使神权的权杖。其实,上海在1982年第一座良渚大墓中就已经出土了这种象牙器,由于朽损严重,无法辨识其全貌。近悉,浙江良渚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残留发现。良渚文化象征军政权威的玉戚与象征神权象牙器的出现,为良渚首领的角色、社会性质的认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良渚玉戚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以后盛极一时的玉戚、斧、钺、戈式权杖的演变和延续的祖型。象征神权的象牙器的后继者或替代者的面貌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分化到了道家等中国宗教之中,因笔者缺乏研究未敢置喙。至于良渚之前的权杖,其实早已出土,只是因为其石头质地而让我们犹豫不决。
20世纪90年代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发现了两套精致的骨牙雕冒镦组合石钺(图16),上海青浦崧泽遗址136号墓出土了一件骨镦石斧(图17)。前者与马家浜文化相当,距今6500~5500年,后者属崧泽文化,距今五六千年。从形式上发觉,明显与良渚豪华型玉戚有渊源。作为生产工具?如此贵重精致的装饰,没有必要,且没有使用痕迹。石头与玉确实是有区别的,但以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玉,石之美”者来认识,在先民眼里只要是美的石头都可归玉。不要说先民,即使是今天的非专业人员,在工艺品古董市场上,有多少人能够精准分辨得了玉与石的?因此,这些非生产、实战性装饰的精美石斧(钺),均应属礼仪性质的权杖。综上所述,中国在先秦时期早已有自己精彩、悠久的权杖使用与发展史。至于我国历史上由权杖转换成玺印的课题,目前少有专论者。
印学专家孙慰祖认为,“从目前可以确认的实物来看,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铭铸有文字的铜玺。”(孙慰祖《印章》,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016年7月新华社报道,陕西省考古人员在澄城县柳泉九沟村出土了一件表义性文字的四神“玉玺”,古文字专家周晓陆教授鉴定,这是西周早期墓葬中首次出现随葬的玺印,是我国印史上目前所见最早的玉质印章,也是最早的龙纽“玉玺”。古代认为四神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星象方位,四神又各司其责,各具神功。显而易见,有青铜簋和表示极高地位的龙钮四神玉印的执掌者,是西周时期一位通神握权的大角色。战国时期官、私印玺并存,其中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和氏璧”的故事流传至今。秦代曾专门建立了掌管符玺的官署,以“符玺令”主持其事。秦始皇执政时曾将“和氏璧”改制成“传国玉玺”,并昭天下“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虽然由璧改玺在技术上存疑,但反映了当时由戚钺之类的器物改性的权杖,开始被玺印所替代的一种强势导向。结合秦始皇最著名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的铁律政策,在中国,明确由玺印替代权杖的制度,也应该始自秦始皇执政时期。至西汉,玺印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分“玺、章、印”三大阶层,并且分别与玉、金(银)、铜三种质料和螭虎、龟、鼻三种钮式相对应(图18)。此后历代印玺的制度多有变化,更加丰富(图19~21),特别是明清以来,除了严格的象征权力的官印王玺国宝,在民间甚至发展演化成了一门繁花纷呈的篆刻艺术。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