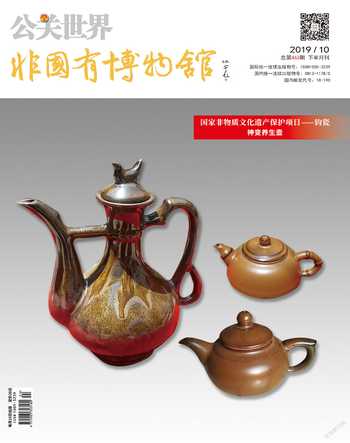五千年良渚,四代人80年的发现
王仁湘

经过四代考古人八十多年的努力探寻,一座5000岁的良渚古城展露在世界面前,中国古文明一角的光辉闪耀于世人。今天世界拥抱着良渚,良渚古城遗址被接纳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员,世界由良渚的发现看到了文明中国初始出现时那一角的绚烂。
良渚自发现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考古不断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这也不断更新、提升着我们对良渚的认识。良渚考古发现大体可以归纳为三大时段,即陶器、玉器与大型墓葬、城址与大型水利工程,这三大发现认知时段。
最早是良渚考古的奠基阶段,此刻我们特别怀念前面两代学者,他们大都已经作古,没有等到今天申遗成功的开心结果,但他们却奠定了良渚考古的坚固基石。当这些先行者已然成为历史,从他们的足迹里我们又看到了历史延伸的方向。
第一代学人发现了良渚。施昕更(1911-1939),浙江余杭良渚镇人,原名兴根,后更名为鑫赓、昕更。八十多年前,施昕更还是一位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工作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自己的家乡良渚采集到了一些古老的黑陶片和石器,他没有想到一个重大的发现由此开启了序幕。这位良渚人对良渚遗址进行了几次田野考古发掘,而且很快将发现公诸于世,这也是世人了解良渚的开端。
施昕更
施昕更是发现良渚第一人,他也是一代考古人的代表。那是上世纪30-40年代,考古平台上活跃的有一拨“10后”,他们大多是施昕更的同龄人。如良渚考古的关键推手1909年生人的苏秉琦和1910年生人的夏鼐,这二位与1911年生人的施昕更,差不多就是同年人了。他们是第一代开拓者,是良渚的发现者和认知者,也是后来中国考古学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在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中,良渚文化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架构。夏鼐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论,他于1959年命名“良渚文化”,十分重视良渚发现的价值。这两位施昕更的同龄人,在他们活跃的年代里引领着良渚考古的方向。
夏鼐
从那开始的20年,一批30年代出生、逐渐成长为著名考古学者的后来者,开始研习考古学。他们是1932年的严文明、1933年的俞伟超、1934年的张忠培,还有两位是1932年的牟永抗和1930年的黄宣佩。美籍华裔学者1931年的张光直,也曾为解读良渚作出重要贡献。
这又是一拨鼎鼎大名的同龄人,是第二代良渚的发现者与解读者。健在的严文明先生仍然一直关注良渚考古,还动情地作长诗歌唱良渚。其他的几位都已经先后作古,他们大都见证了良渚大墓、精美玉器和城址與宫殿址的发现,不断亲临考古现场指导,陆续发表研究成果,使得良渚的面貌越来越清晰起来。黄宣佩和牟永抗,还有略小一些的1943年的王明达,都是在考古一线成长起来的学者,他们主持了若干重要发掘项目,也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牟永抗
上世纪70-90年代,良渚一系列重要发现再次引起学界和公众关注,许多大型墓葬出土大量精美玉器,良渚研究涌起新的热潮。新鲜、神秘、精致、完美,良渚玉器带来的信息让人们着迷。随之成长起来一批批学者,他们接过前辈学者的接力棒,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激情满满的学者,还提出了“玉器时代”的概念,觉得非如此不足以描述良渚带来的前所未知的世界。
良渚因玉器而彰显精彩雅致,良渚人的精神世界就珍藏在这些精致的玉器里。良渚人的信仰,他们的虔诚与情怀,都包容在这些神秘的玉器里。
又是20年过去,再一个20年来临,一拨拨50-60后、70-80后为良渚考古而生,这是以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任所长刘斌为首的团队,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登上良渚考古平台。
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它包括了正年轻和已然不太年轻的两代人,可以看作是良渚考古第三代和第四代。是他们最大限度打开了折叠着的良渚,将那从未见到的甚至是不曾想象到的文明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所说的良渚第三时段玉器与古城的发现,正是主要由这两代学者辛勤探寻的成果。
刘斌
这一阶段良渚考古的大收获是城池与水利工程的确认,这也是国家形态文明的确认。良渚这么庞大的城池与水坝的设计筑造,是强大国家机器才能实施的工程。这一阶段还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与谷物分配一定纳入到了良渚的国家大政。
后浪推前浪,新人追前人。披星戴月,风雨兼程。我们欣喜地看到良渚第四代考古人已经登台整齐亮相,新的发现在向他们召唤。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