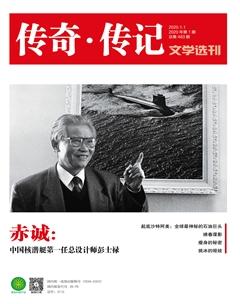挑冰的哑娃
菊韵香

惹祸的奶牛
深冬的一天,郑顺顶着飕飕直往脖子里钻的冷风,踩着弯弯山路刚到小村里的孤松岭,就遇上了一桩麻烦事:同住一条街巷的胖婶和刘老栓打起来了!
郑顺是应届大学生,大一就入了党,此次到孤松岭是来当村官的,给村党支部书记当助理。虽然村官不是官,但在两年任职期满后再考公务员,会享受至少5分以上的加分照顾。到那时,凭本事在大城市考个吃香升职快的热门岗位,那必是抡大刀的切豆腐——不在话下。
美滋滋地想着,郑顺进了村。一打听才得知,村支书因病住院差不多已有小半年,眼下主事的是村主任老亓。说来不巧,老亓也去了临镇女儿女婿家,没在村里。不过,他打电话回来,让哑娃拾掇出村委会的一间旧屋子,暂做郑顺的住处。
“你叫哑娃?多大了?”放下背包,郑顺感觉有些饿,就拿出一盒快餐面,边冲泡边问。
哑娃是个哑巴。老亓在电话里说,这小家伙是个弃婴。当年在山坳里捡到他时,哑娃小身子瘦得跟猫崽子似的,眨巴着小眼睛东瞅西瞅,不哭也不闹。大伙猜测,他可能有病,不然,一个男娃,谁肯舍弃?老亓把哑娃抱回了村委会,还口头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家养一天,挨家挨户轮;谁敢薄待他,可别怪我翻脸,扣你粮补!
转眼工夫,小家伙渐渐长大了,不会说话,脑瓜也不甚灵光,大伙就给他取名叫哑娃。
哑娃朝郑顺比划了个12岁的手势。
郑顺正要再问亓主任啥时能回来,院外突然传来一声急喊:“出事了,刘老栓和胖婶打起来了,谁劝跟谁瞪眼呢!”
村支书和村主任都不在,只能由郑顺这个助理出面了。郑顺将泡面推给哑娃:“小家伙,你吃吧,我去看看。”说完,他拔腿奔出屋,跟着来报信的村民赶去了刘老栓家。
“他們为啥打架?”郑顺问。
“因为胖婶家的牛偷嘴,惹大乱子了。”村民说。
这大乱子还真是“大”,大到郑顺听着都想乐:胖婶家养了一头奶牛,快要下奶了。一眼没照顾到,奶牛跑进隔壁刘老栓家,将脑袋扎进了水坛子。水坛子肚大口小,奶牛喝饱了水,拔不出脑袋,使劲一甩,啪,水坛子磕墙上碎了。听到动静,刘老栓急了,抓起挡门棍砸上了牛屁股。而这一幕,恰好被出院找牛的胖婶瞧在了眼里。
你打我的奶牛,还不如打我呢!胖婶奔上前,不依不饶,和刘老栓撕扯成一团。
当郑顺风风火火赶到时,腰身粗实的胖婶双手一使劲,就将刘老栓给摁倒在了地上。
“都住手,别打了。”郑顺分开看热闹的街坊,挤到了胖婶跟前,“我叫郑顺,是新来的村支书助理。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他打我家奶牛。这牛万一不出奶了,他赔得起吗?”胖婶扬起巴掌就要抽刘老栓,却僵在了半空。
郑顺搭眼一瞧,糟糕,刘老栓晕了过去,嘴角吐得满是白沫!
人命关天,容不得耽搁。郑顺赶忙背起刘老栓就往村外跑:“谁家有车?快帮我送他去医院!”
解乏的热水澡
孤松岭是个地处偏远的山中小村,虽有几条出山路,可都弯弯绕绕像极了羊肠,别说开轿车,就算驾马车赶牛车都费劲,稍有不慎,准保折个儿。赶上紧要事,就像今儿个这般,也只能背着出去。
背着跑着,还没到上岭,郑顺已累得迈不开步,大颗大颗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助理,我要是昏迷不醒,住院抢救,谁交钱?”
“甭管谁交,救命要紧。实在没钱,我出。”
“那可不行。这钱要胖辣椒出,不然我就再晕过去。”.
胖辣椒,是胖婶的绰号。郑顺还想接话,却一下子回过味来,站住了:“刘叔,你醒了?”
“不醒能聊天吗?”刘老栓拿余光扫,瞄见胖嫂等几个街坊也跟了上来,忙贴着郑顺的耳根说,“还是把我背回去吧,别花那冤枉钱。我在家里躺着,照样能吓唬她。”
敢情,刘老栓是在装晕!郑顺哭笑不得。待紧张劲儿一散,一股子浓浓的汗臭味扑面而来,熏得他脑瓜子直发懵。
这老家伙,至少得有个把月没洗澡了!
接下来,一连数日,郑顺得空就往胖婶家和刘老栓家跑,摆事实讲道理,调解矛盾。毕竟,这是他来孤松岭经手的第一件纠纷,必须处理得漂漂亮亮,打响头炮。哪知,胖婶性子倔,不肯低头,刘老栓更是一根筋:“哼,当着街坊四邻的面,她胖辣椒骑在我身上,太丢份。想让我跟她和解,除非她答应我一个要求。”
劝来劝去,郑顺累得下巴差点脱臼,这天晚上总算劝刘老栓松了口:“让她供我家一个月水吃,不然没完。”
这还叫事儿?“好,我替胖婶应下了。”郑顺长出了一口气,回到村委会,连烧了几壶开水,兑了一大木桶,然后往里一坐,泡起了澡。
白天忙得腿软脚跟疼,天气又冷,晚上泡个热水澡再钻进被窝,可真是舒服。郑顺正闭目享受呢,村主任老亓来了:“听说,胖婶和老栓吵架了?”
“解决完了。明天跟胖婶通个气,就没事了。”郑顺说,“亓叔,你稍等一会儿,我也给你兑桶水,泡泡澡。哦,这木桶是从杂物间翻出来的,好像有几年没用了。”
老亓微微皱了下眉,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摆摆手走了。次日一早,天色还没亮呢,老亓又来了。
“亓叔,有事?”郑顺揉揉惺忪的睡眼,起身开了门。
老亓也不多说,带着他走出了村委会。
时值深冬,寒风吹来,冻得人直打哆嗦。郑顺刚要问老村主任这是要去哪儿,前方影影绰绰出现了一个人影。
个头不高,身子瘦巴巴的,手里提着一把镐头,肩上挑着两只木桶。
是哑娃。
郑顺倍感好奇,深一脚浅一脚地跟了上去。
刨冰的哑娃
这一跟,便是四五里地。只见哑娃翻过岭,走进一道山洼,放下扁担,往手心里啐了一口唾沫,叮叮咣咣地刨了起来。
他刨的是冰,一下又一下,格外卖力。等把木桶装得满满登登,哑娃又抱起一大块冰,这才挑起扁担,晃晃悠悠原路返回。
郑顺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他吃的水,洗脸洗澡用的水,竟都是哑娃起大早,一块一块刨出来挑回去的!
“昨天我回来,问哑娃,新来的助理咋样,哑娃比比划划说,好着呢,还给了我一碗面吃,真香。从小长到大,哑娃还是头回吃快餐面。他还比划说,助理哥哥是从城里来的,爱干净,我得天天给他挑水,让他洗脸洗澡。”
多么朴实纯真的孩子。郑顺听得眼窝一热,心里酸酸的,又暖暖的。
“孤松岭最缺的,就是水。”老亓接着说,“你看,周遭山岭上旱得光秃秃的,就长了一棵松树。幸好老天怜悯,给了这么个山洼,夏秋蓄的雨水,冬天结成冰,供村民们吃用。刘老栓和胖婶吵架,不是心疼坛子,是心疼那坛子水呢。”
“那为啥不打井?”郑顺问。
老亓带郑顺走向了村东,又从村东绕到了村西。大半个村子走下来,郑顺也瞧出了名堂。老亓说:“此前,孤松岭没少打井,有的都钻到了百米深,到头来,钱没少花,却只留下十几个不出水的井窟窿和叽叽呱呱的埋怨。如今,村里的账上还欠着万把块钱的打井费呢。不怕见丑,村里人还找风水先生来看过,说整个孤松岭的地下,覆盖着一块王八盖子般的巨石,把水脉盖住了,甭管用啥钻头,根本打不透。要赶上大旱年景,别说洗脸,就连吃水都成难题。所以啊,村里的年轻人能走的都走了,只剩下些老弱病殘,守着这个穷窝儿。前些日子,住在村北的赵老二,盼了半辈子,总算有人来给他说媒,不料女方张口一提彩礼,赵老二就傻了眼。”
“女方要多少钱?”郑顺问。
“人家不要金银不要钱,就要一口井!”
怪不得刘老栓会提出那般条件,敢情水比油金贵。可既然答应了,就得兑现。第二天,郑顺也起了个大早,抢在哑娃前头挑上水桶,去山洼刨冰。可他在城里长这么大,哪曾挑水走过山路?扁担上肩,木桶悠来荡去,一步没踩稳,出事了——
骨碌碌,郑顺连人带桶,从岭上滚了下去。好不容易停住,脑袋却磕上石头,郑顺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郑顺悠悠醒来了。不等睁眼,就闻到一股浓浓的汗臭味,直往鼻子里钻。
是刘老栓。刘老栓正背着他,跌跌撞撞地往岭上跑呢。身前身后,跟着老亓、胖婶、哑娃和七八个乡亲。
“都怪你,不要老脸,要水。助理要摔出点啥事,我看你咋交代?”胖婶气哼哼地训斥道。
“我闺女上大学,眼看要放寒假了,我这个当爹的,还不是想多备点水,别难为着闺女吗?”刘老栓辩白说,“你也有责任。要不是你家那头牛偷水,哪会出这些乱子?”
“你知道我为啥养奶牛吗?我儿媳妇快生了,孤松岭水少,也浑,我得让他们娘俩喝上奶啊。我发誓,只要助理好起来,他在村里待一天,我也让他喝一天;待一年,喝一年,一分钱都不要。”
“别吵了。来,我再背他一段路。”老亓说。
刘老栓已累得气喘吁吁,刚放下郑顺,哑娃就弓腰背起他,颠颠地跑。
“哑娃,我没事。咱回去,我再给你泡面吃。”郑顺说。
哑娃听到了,顿时激动得“啊啊”叫起来,哭了,又笑了,笑得满眼是泪。
春到孤松岭
寒冬过去,春天来了。
当冻土开化的时候,几个勘探技术员走进了孤松岭。紧接着,一支打井队也开了进来。
勘探和打井的费用,是郑顺垫付的,那是他准备在城里买房的钱。
井址就选在了村委会哑娃住的屋子前。整整钻了大半个月,打下了800米深,终于出水了!清亮亮的水花喷涌而出,溅得围观村民满身满脸都是。
没人能分清那是水还是喜泪。
最欢喜的是哑娃,郑顺给他封了官——井长,专门负责给全村村民供水。
两年后,郑顺任期届满,离开了孤松岭。就在村民们对这个小伙子念念不忘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郑顺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公务员招考的笔试和面试。但他没去大城市,也没挑热门岗位,而是选了孤松岭村支书的职位。
也难怪他会放弃在城里买房,原来,两年历练,他的心已悄悄留在了孤松岭。
不,郑顺早立下了一个新目标:有了水,还要有树,我要和亓主任、哑娃、刘老栓他们一起,变荒山为青山,把孤松岭改造成——
青松岭!
〔本刊责任编辑 周 雨〕
〔原载《乡土·野马渡》
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