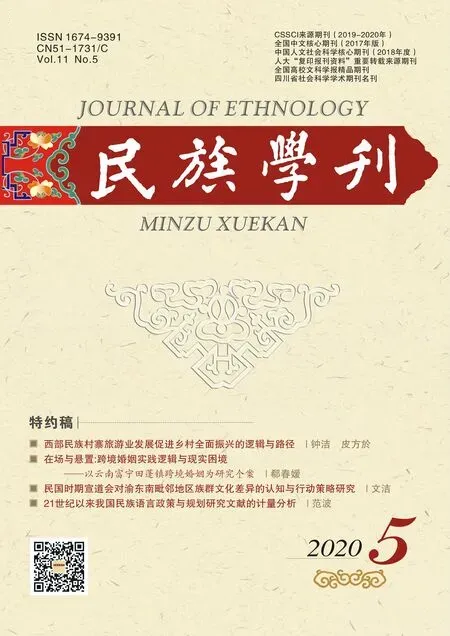从古歌到民族史诗:《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综述
覃 琮 吴絮颖
《密洛陀》是以口承为主的瑶族史诗,主要流传在布努瑶支系,流传区域覆盖滇、黔、桂、湘交界地带,以桂西北的都安、巴马和大化三个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都安县、巴马县、大化县)及其周边区域为主要流传地,涉及十几个乡镇,近五十万人口。 布努瑶民间把密洛陀称为“杂密”,把世代传下来的关于密洛陀神话、传说和故事统称为“密洛陀古歌”。 古歌主要讲述人类创世祖母密洛陀和她的两代儿女工神、武神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以及瑶族先祖及其南迁的故事,是一部集创世、英雄和迁徙为一体、拥有很多分支歌的完整群系统的复合型史诗,叙事宏大,内容庞杂,被誉为布努瑶的“百科全书”。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零星调查到80 年代以来的全面搜集整理和出版,《密洛陀》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人们希望通过《密洛陀》来了解这个偏安于桂西北石山地区、最晚近被外界所知道的瑶族支系。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密洛陀》搜集整理的历程以及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今后对这部史诗进行更深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挖掘它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滋养包括瑶族在内的现代人的心灵,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
一、《密洛陀》的搜集整理
(一)《密洛陀》搜集整理的进程
《密洛陀》的最早记录,发现于民国时期桂岭师范学校校长刘锡蕃所著《岭表纪蛮》一书,其云:“桂省西北之苗瑶于盘古大帝外,兼祀伏羲兄妹及迷霞(女性)、迷物(女性)、含溜(性别不详)诸神”。[1]这里所说的“迷霞”“迷物”,从名称和性别上看,应是“密洛陀”的音译。
不过,《密洛陀》真正意义上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从20 世纪60 年代才开始的。 先是广西民间文学调查组的农冠品、黄承辉到都安县采风,在七百弄乡(今属大化县)收集到了三千多行的《密洛陀》,油印成资料在社会上传阅。 受此影响,中央民族学院的刘保元、盘承乾等人也前去七百弄等地采录。 莎红和黄书光(广西民族学院教师)等人则顺藤摸瓜到巴马县东山乡采访,获得七份有关《密洛陀》的原始材料,莎红整理了其中的“创世”部分,发表在1965 年《民间文学》的第1 期,引起世人关注。
这一时段的《密洛陀》搜集整理比较零散,参与者中大多数不是土生土长的布努瑶人,存在着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碍,特别是不懂《密洛陀》宗教语,①造成工作艰难、进度缓慢,还引起了许多误讹。[2]“文革”期间,《密洛陀》被斥为封建余毒,不少巫公、歌手惨遭游斗、毒打,相关搜集人员也因此遭殃,有的还被关进了牛栏,《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工作被迫中断。[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思想开始得到全面纠正。 进入80 年代,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事业慢慢复苏。 198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研会向原河池地区文化局下达相关通知,《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重新启动。 此后,以蓝怀昌、蒙通顺、蒙冠雄、蓝永红、蓝正录、蒙有义为代表的一批布努瑶学者逐渐成为搜集整理甚至研究的中坚力量。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至2002 年,包括1981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莎红版《密洛陀》单行本,一共出版了五个版本的《密洛陀》。这些不同版本的《密洛陀》,分为以下两大类:一类是文学版本,即汉语意译的版本,共有四个版本;另一类是科学版本,即在整理和翻译《密洛陀》时,要有瑶文(布努语)、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道工序,或最少要有三道工序,即国际音标、直译和意译。 目前,科学版本只有2002 年张声震主编的《密洛陀古歌》一版,有三道工序。
(二)不同版本的《密洛陀》的比较
莎红版《密洛陀》是第一个汉译本,由巫公、歌手吟唱,自己先逐句用汉语译出,莎红再做整理,材料原始可靠。 为更好地表达“创世始祖”之意,莎红在瑶、壮和汉语的对译过程中,把布努瑶民间的称谓“杂密”译成“密洛陀”。 “杂密”本意是“话密洛陀”,又隐含“母道理”之意。“密洛陀”一词中,“密”即“母亲”,“洛陀”意为“古老”,两部分合起来即为“古老的母亲”。 这个译名,既蕴含“至尊的创世之母、伟大的母亲神”之意,又符合“密洛陀”是“一切道理之母”的丰富内涵,后一直沿用至今。 这是莎红的一大贡献。 但是,因为顾虑到当时的民族政策,有关原始材料中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章节全部删去,同时,不会讲汉语的巫公、歌手的传唱材料无法收集,所以这个版本内容不全,只分为“造天地、造森林、造房子、射太阳、杀老虎、找地方、造人”七个部分,九百多行。 此外,莎红是壮族诗人,因而这个版本被认为“渗入后来的成份太多、在运用俗语方面有不准确的地方。”[4]
1986 年的潘泉脉、蒙冠雄、蓝克宽搜集整理的《密洛陀》(以下简称潘版),后被编入第七册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 年)。 这个版本的《密洛陀》,古歌源于当时保存相对完整的七百弄乡。 除“开头歌”外,共分为二部十八章。 第一部创世歌十章,记录从密洛陀出世到为密洛陀做“补粮做寿”,分为密洛陀出世、造天地、卖种子、造动物、惩罚动物、找地方、造人、判是非、射太阳、补粮做寿,古歌展示更加具体形象,出现了一些新的材料。 第二部也叫创世歌,计有分家、西天学法、报仇、逃难、智斗财主、抗暴、为了后代、酒歌共八章,反映的是布努瑶来到广西,特别是来到都安以后的传说和故事,既表现瑶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壮族土司土官和朝廷皇帝)的斗争,也表现了瑶民与壮、汉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 这些内容是莎红版本所没有的。
第三个版本是1988 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密洛陀》。 这个版本由蓝怀昌、蓝京书、蒙通顺搜集整理(以下简称蓝版),歌源主要来自巴马县的东山乡、都安下坳乡的隆石、加文、崇山等地,计有序歌和三十四章,主要内容为造神、造天地万物、惩杀日月妖兽、造人类、分族分家与逃难迁徙、祭祀六个方面,内容基本完整,南方民族史诗复合型特点已清晰可见。 由于蓝怀昌、蓝京书、蒙通顺三人都是文学出身,文学造诣较高,而蒙通顺的祖辈、父辈们又都是当地有名望的巫公、歌手,这些便利的条件使全书在瑶、汉的对译过程中遵循史诗讲究对偶、对仗的语言特点,大量运用比拟、夸张、复叠的表现手法,文学性强,艺术想象丰富,极富感染力,是文学版本中的珍品。
第四个版本是1999 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密洛陀》,这个版本由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整理,实际上是2002 年《密洛陀古歌》科学版本出版之前的文学版本,因为蒙冠雄是《密洛陀古歌》项目的重要负责人和参与者。 这个版本共有三十四章,一万两千多行,从内容版块上与蓝版《密洛陀》大体相同,但章节安排与故事情节有较大差异。 比如,蓝版《密洛陀》用了五章(第二十九章至三十三章)来叙述布努瑶来到都安后分家逃难以及各姓氏世系的历史,而这个版本只编排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各奔一方”。 这个版本有几大贡献:一是首次区别了《密洛陀》和《祖宗歌》《族谱歌》三部古歌,澄清了以前的许多不解、误解;二是为古地名作了注解,特别是宗教语喃唱古歌时提到的古地名;三是附录了演唱者的名单,介绍他们的生平简历和艺术特长;四是对《密洛陀》史诗中提到的44个神祗按冥界(五位)、神界(十四位)和阳界(二十五位)进行了分类和附录,初步厘清了神谱关系;五是配有《造神界》《造神童》《造天地》等35 幅插图,图文并茂,生动形象。 因此,这个版本,原始材料更加翔实可靠,被瑶族学者认为是“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融文学、史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宗教学等各学科的丰富史料于一体,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5]
科学版本,是1987 年“密洛陀古歌”成为国家民族古籍出版“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后在编译整理方面的体例要求。 这个项目是目前广西民族古籍办跨时间最长、资助最多的项目。 2002年,在历经14 年的漫长煎熬后,由蓝永红和蓝正录搜集、整理和译注的《密洛陀古歌》终于问世。 《密洛陀古歌》的歌源主要来自大化县的七百弄乡、板升乡,以及都安县、巴马县和东兰县个别乡镇,采录的歌师上百名,最后取当时宗教语保留比较完整的七百弄乡的唱本作为参照进行辨别和编译。 从编排来看,《密洛陀古歌》设篇、章、节,分有上篇和下篇,各章又分为若干节,共计八十八节。 上篇主题为“造神”,共九章:密洛陀诞生,造天地万物,封山封岭,造动物,迁罗立,射日月,抗灾,看地方,罗立还愿;下篇主题为“造人”,共五章:造人类,分家,密洛陀寿终,逃难,各自一方。 每一章(包括序歌)都采取“题解” +“古歌” +“附记” +“注解”的基本框架。 书后附有蓝永红编制的“神谱表”“曲调”和“采访歌师情表及主要歌师简介”三个附录。其中,“神谱表”按原始神(一位)、始祖神(四位,其中密洛陀是人类神)、密洛陀首批造的“工神”(十二位)、密洛陀第二批造的“武神”及女神(十位)、其他小神(五位)、人类诞生后的主要人物(八位)进行分类,彻底弄清密洛陀传说中纷繁复杂的各个神话人物关系,使史诗的神谱结构更加严密。 全书分上、中、下三册,九万多行,共计340 多万字,篇幅恢宏,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各个《密洛陀》汉译本中搜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体例最规范、内容最齐全、故事情节最生动、资料最全面的版本,被称为“一部集布努瑶古文化的鸿篇巨作”,[6]为研究《密洛陀》及布努瑶提供了极大方便。
《密洛陀》是布努瑶一代传一代的思想和智慧的结晶。 它的整理成书,饱含着布努瑶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崇敬。 为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布努瑶的地方学者、文化人、民间文化工作者不计名利,呕心沥血,前仆后继,走遍千山万弄,历尽千辛万苦,将蕴藏于民间的、散乱的古歌一点一点挖掘出来,成为今天的鸿篇巨著。 不同版本的《密洛陀》先后问世,终使布努瑶的这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黑格尔语)”走出瑶山,汇入中国民族史诗的星空长廊,成为南方民族史诗的典范文本。
二、《密洛陀》的研究
1981 年,韦其麟为莎红《密洛陀》单行本出版所撰写的序言,首开《密洛陀》研究之先河。此后,伴随每一次《密洛陀》汉译本的问世,都掀起学界不大不小的研究热潮和评介。 截止2020年6 月,史诗《密洛陀》的研究,出版专著1 本;硕士论文11 篇,其中题名为“密洛陀”的共有5篇;期刊论文93 篇,其中篇名为“密洛陀”的共计49 篇。 这些研究,主要讨论了以下议题:
(一)《密洛陀》的定位
《密洛陀》被誉为瑶族的民族史诗,但它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为什么只有在桂西北的布努瑶支系中有密洛陀传说,其他支系,包括瑶族的第一大支系盘瑶,以及与布努瑶同属苗瑶语支的其他分支、小支也无此传说? 由此,怎样认识《密洛陀》所描绘的远古社会,它对理解整个瑶族的历史文化有何作用? 进而,与另一部瑶族古籍经典《盘王歌》相比,《密洛陀》在瑶族文化中的地位如何?这些都是《密洛陀》研究必须予以回应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多年来却没有学者专门探讨,只是有所触及。 蓝芳敏从史诗、谱牒、服饰、铜鼓、语言等方面论述布努瑶的文化特征,推断桂西北的布努瑶不是“盘瓠种”,而与黔中苗族有亲缘关系,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将其标之为瑶。”[7]毛珠凡也谈到,布努瑶只信奉密洛陀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为瑶族历史文化核心的盘王神话传说,可以断定布努瑶来源以苗族为主,兼有汉族、壮族甚至侗族,而来源于信奉盘瓠(王)瑶族的不是主流。[8]谭振华指出,《密洛陀》和《盘王歌》是瑶族文学的两座高峰,分别被瑶族的两大支系所继承。《密洛陀》是“母亲之歌”,代表女神,象征母亲的慈爱。 《盘王歌》是“父亲之歌”,代表父神,象征父亲的威严。 瑶族的“民族根”恰恰是附在这两部史诗中,更体现在《密洛陀》之中,因为《密洛陀》的篇幅和体量是《盘王歌》的十倍之巨,它才是瑶族文学的巅峰。[9]
(二)《密洛陀》的创世特点
《密洛陀》是创世史诗,对它的创世特点很早就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陆桂生认为《密洛陀》突出地反映了布努瑶先民创造世界的英雄业绩,具有“人类创造了自身创造万物、人是万物之灵、反映了母氏社会痕迹、运用半人半神的表现手法”的创世特点。[10]张利群认为在《密洛陀》的“创世”史诗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互生关系、在创世精神指导下确立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性”的自然文化观。[11]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密洛陀神话揭示人类从神到人、从自然到人、从个体的人到社会的人的特征,显示出人类起源过程中人的巨大的“创世”力量及其在创造人类、创造民族、创造文明中的巨大作用,由此体现出“密洛陀”神话传说的文化人类学意蕴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意义。[12]
(三)《密洛陀》的哲学思想
对《密洛陀》进行哲学思想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多,共有10 多篇论文。 这些文章主要讨论了《密洛陀》的唯物论、辩证思想、天人观、生态观等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 陈路芳认为《密洛陀》体现了瑶族先辈以神话的形式表达了“气生万物的宇宙起源说、动物变人的人类起源说、万物异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哲学思想。[13]朱国佳从生存智慧的角度分析了《密洛陀》天人合一、群体责任意识、坚定生存信念三方面的特征,认为这是布努瑶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生存之道,其意义在于反思各民族最佳的相处之道是什么?[14]谢少万、刘小春先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诠释《密洛陀》所蕴涵的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15]再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观念出发,指出《密洛陀》包含有本体论思想萌芽、普遍联系的朴素辩证观思想、“人定胜天”以及“天人合一”的人天观,由此要看到瑶族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应当有适当的地位。[16]卢明宇以生态审美为视角,认为《密洛陀》存在万物同源、人类同根、内在价值的生态平等思想,对当今构建平等和谐的生态社会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17]
(四)《密洛陀》的文化认同
史诗是文化表达的源头,也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根谱,是最为擅长表述这种认同的文类。[18]郑威认为《密洛陀》实际上是一个记忆文本,包含有一个族群自我认同的多个要素,它对布努瑶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进行了建构和解释,并将它们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强化布努瑶的族群认同和归属意识。[19]伍君则运用神话—原型批评分析方法,结合《密洛陀》对瑶族作家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里人物形象的原始意象进行探讨,认为当代文化艺术与远古人类民族文明之间存在脉脉相承的相应的象征意义。[20]蓝芝同探讨了《密洛陀》对研究人类起源、瑶族先民逃难原因和迁徙路线、瑶族生产生活和宗教信仰等文化习俗方面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其实也隐含着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21]王宪昭对《密洛陀》的功能性母题进行了分解与梳理,发现这部创世神话史诗具有古老性、完整性、持续性和实践性,并由此发挥着民族历史的记忆功能、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承功能以及日常教化与行为规范等功能。[22]
(五)《密洛陀》的传承规律
近年来,在口头诗学的理论影响下,开始有学者探讨《密洛陀》的传承规律问题。 何湘桂通过对不同《密洛陀》文本的梳理与比较,指出《密洛陀》能够活形态世代相传,不仅源于其特定的生态环境、传承形态以及思想内涵,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创编规律和生成机制。 其一,《密洛陀》是典型的南方创世史诗叙事范型(原形和母题),即它的母题包括始祖诞生、开天辟地、造人造物、洪水泛滥、族群迁徙、农耕生产等几大部分,始终以“创世”主线为中轴,依照历史演变、人类进步的发展程序展开,通过天地神祇、先祖人物、文化英雄及能工巧匠的塑造,把各个诗章连接起来,关注更多的是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二,《密洛陀》依靠程式这一内部法则,使史诗具有程式化特点,然后不断进行积累、加工和完善,使史诗便于记忆、储存、回忆、现场创编。 具体而言,《密洛陀》的叙事程式,包括语词程式(人称地名程式、叠音词程式、数字程式)、句式程式(对称式平行、层递式、排比式)、结构程式(衬词的使用、复合大型程式)。[23]林安宁则结合歌手蒙凤立的现场演唱,分析“声音”对密洛陀史诗研究的意义,强调对史诗演述背景的叙述与记录,都是密洛陀史诗研究者要面对的共同话题。[24]
(六)《密洛陀》和其它史诗的比较
对《密洛陀》与其它史诗的比较研究,学界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密洛陀》与瑶族的另一部经典《盘瓠》的神话比较,代表作是何颍的《对瑶族神话〈密洛陀〉与〈盘瓠〉的深层思考》。 该文认为按照社会发展过程排序,《密洛陀》排于先,《盘瓠》出现于后,两则神话串连起来构成了瑶族神格观念的顺序,是瑶族长久以来“先有瑶,后有朝”观念产生的直接诱导。[25]第二,《密洛陀》与壮侗语族的神话比较,重点是与壮族史诗《布洛陀》进行比较,代表作是李斯颍的《壮族布洛陀与瑶族密洛陀神话比较》。 该文从神祇、神话母题两方面详细比较布洛陀和密洛陀神话,发现两者在世界的最初结构方式、创世的始祖内容上保持了较高的相似性,从而论证了壮、瑶是文化上互通有无的两个民族。[26]第三,《密洛陀》与汉族远古神话的比较。 蒙有义从创世神话定义、相同创世神话的比较、不同创世神话的比较三个方面揭示了瑶汉创世神话的异同及其动因和规律。[27]张利群则以女娲作为参照系来比较密洛陀,指出各民族文化表现出某种共同性和某种趋向性,从而成为一种潜在的人类意识,因此,密洛陀越是走出瑶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就越能表现出它的永久魅力和巨大价值。[28]第四,密洛陀神话的“世界比较”,代表作是林安宁《〈密洛陀古歌〉和〈古事记〉神话比较》。 该文不仅比较了《密洛陀》与日本《古事记》在神谱叙事、女神两方面的异同,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以下思考:神话研究如何从传统的中外比较走向世界比较? 其中,又如何凸显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地位?[29]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三十多年来《密洛陀》的研究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至少现在,《密洛陀》不再象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样,是学界无人问津的“研究盲点”。 自2011 年《密洛陀》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这部史诗在整个瑶族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非遗价值、学术价值、传承状况、创新性发展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学界对《密洛陀》研究日渐深入,正进入活跃期。
三、今后《密洛陀》搜集整理和研究展望
尽管《密洛陀》在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 比如,搜集整理方面,成果形式比较单一、搜集区域过于集中;在研究方面,重文本、轻田野的研究倾向非常明显,以致于目前《密洛陀》的研究,尚无法深挖它的文化内涵,更无力迈向精审深细的诗学分析。 因此,今后《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提高。
(一)全方面、立体式地进行搜集与整理
《密洛陀》是活形态的史诗,布努瑶把《密洛陀》及其分支歌与日常生产生活联系起来,形成包括宗教活动、节日活动、婚嫁、生育、立房上梁、交易、狩猎、神判与诅咒等多个使用场合,每个场合都会演唱一部分《密洛陀》或其分支歌的相关内容。 从传承形态来看,《密洛陀》是由语言叙事、仪式化行为叙事、图像叙事和景观叙事共同构成的完整谱系。 因此,仅仅是文字文本的《密洛陀》,缺乏其它材料的共同形构,势必会割裂掉史诗活形态传承的完整性和联系性。
所谓全方面、立体式地搜集和整理《密洛陀》,有两个层面涵义:其一,运用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记录手段,整理出包括语言、声音、民俗场景、歌手创编、现场演述、观众互动等在内的丰富素材。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推进的节日影像志和史诗影像志两大研究工程的逐步发现和理解,影视人类学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和技术方法在国内已经日臻成熟,影像志或影视作品的独特优势和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公众的认可。[30]《密洛陀》已入选中国史诗影像志的子课题,要利用这一契机,丰富《密洛陀》的资料素材和形式,成为研究者的一手田野资料。 其二,同样运用现代新媒体手段,搜集、记录老巫公和老歌手们的各个唱叙版本,建立数据资料库。 特别是过去较少进入的乡镇,如都安县的东庙、大兴、隆福、龙湾、青盛等地,大化县的板升、雅龙、江南等地,以及布努瑶的韦氏、罗氏等其它姓氏的版本。 根据笔者近几年的调查,散落民间的各种古歌唱本依然数量庞杂,即使邻近村落也有不同的版本。 这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因为那些参加过大还愿的老巫公,大多年过90 岁,抢救、记录和整理这些老巫公的演述版本迫在眉睫。
(二)加大对《密洛陀》的田野调查研究
由于布努瑶主要聚居在广西的“石山王国”,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巫公群体所喃唱的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语言,必须有懂宗教语的布努瑶学者协助才能整理和翻译,田野工作难度极大,导致过去《密洛陀》研究最大的缺憾就是田野调查太少,史诗的传布状况、传承群体、传承形态、创编规律、传承现状等基本资料没有被充分调查、掌握和研究。 今天,桂西北几个瑶族自治县的交通状况已大有改观,基本实现硬化公路村村通。 与此同时,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许多偏僻的瑶族村寨被整体搬迁到县城或乡镇中心居住,而这些村寨往往又是布努瑶文化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 一旦脱离原来的生态环境,《密洛陀》是否还能保持活态传承是一个问号。 因此,加大对《密洛陀》的田野调查,恰逢其时,也正当其时。
1.《密洛陀》传承形态的综合调查
语言叙事的调查,一是要调查各传承群体在不同场合唱叙《密洛陀》的各种语言,包括宗教语言、史歌语言和情歌语言等;二是要调查布努瑶在不同的场合对密洛陀的不同称呼(有10种不同的称呼)及其含义;三是要调查围绕《密洛陀》主体诗下的其它史诗、神话和传说,当务之急是尽快整理出英雄史诗《阿申·耕杲传》(阿申和耕杲是密洛陀创造的第二代儿女中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因为这是《密洛陀》史诗集群中最重要的子史诗。 仪式化行为叙事的调查,重点是《密洛陀》的各种使用场合,包括丧葬和各种祭祀场合的喃唱、世俗场合的盘唱、日常生活的“讲古”等。 图像叙事的调查,包括各种祭祀仪式中的竹卦、麻衣麻帽、纸衣纸裤、纱纸、插神枝、倒神水、火盆等构成图像。 景观叙事的调查,包括大型祭祀场合搭建的祭棚、各家各户的密洛陀神台、村寨里的雷神林、史诗提到的古地名,以及近年来与史诗内容的主题景观公园、雕像、广场、酒店、阁楼、村落、传习基地等公共文化建设和文创、物语营销等。
2.《密洛陀》传承现状的全面调查
首先,调查《密洛陀》在布努瑶聚居地各乡镇村寨的流布情况,借以划分当前《密洛陀》的主要流传区、次要流传区和外围流传区三大区域。 这既是研究要掌握的必备资料,也是为地方政府提供保护史诗对策建议的重要凭据。 其次,调《密洛陀》的“布西”、“分”歌手、“布商”和“耶把”和爱恋歌歌手四大传承群体的传承谱系,包括师承系统、传授方法、记忆悟性、熟练程度、表达技巧、吸收借鉴、相互合作等材料,借此了解和掌握《密洛陀》的传承规律。 再次,调查《密洛陀》传承群体的生活状况。 重点是巫公的生活史,因为巫公不是简单的史诗演述人,而是“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全能型人才,了解巫公的生活和地位变迁,有助于把握当下《密洛陀》活态传承遭遇的困境。 最后,调查《密洛陀》的演述场域,包括民俗背景,巫公(歌手)的素质、声音、使用的句式程序、与现场观众的互动、现场的创编、修正,仪式结束后主家和观众的评价等内容,借以掌握《密洛陀》的演述规律。
(三)拓宽《密洛陀》的研究领域
《密洛陀》是布努瑶的“标志性文化”,但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布努瑶的民间说法是“什么都是密洛陀创造的”“什么都要用到密洛陀”,由此可见《密洛陀》是与布努瑶的其它文化互渗共生的。 今后对《密洛陀》的研究应借势延宕开来,与其它相关表意文化研究互相印证呼应。
《密洛陀》的表意文化形式很多,其中祝著节和铜鼓应是《密洛陀》研究重点要拓展的领域。 祝著节原本就是为了纪念密洛陀的仙逝而过的节日,加强对它们的关联性研究是应有之义。 对布努瑶铜鼓的研究过去偏重于音乐、艺术和技艺制作,实际上这样研究还远远不够,甚至有点“本末倒置”。 因为在史诗《密洛陀》中,铜鼓是密洛陀创造的,武神们曾利用铜鼓射杀日月、抗灾,布努瑶的铜鼓是密洛陀送的,并在楠妮婚宴中跟危娘(一只母猴)学会了敲打铜鼓、铜鼓舞……因而,对布努瑶铜鼓的研究,今后应着力挖掘附着在它身上的传说、故事等文化意涵上。 此外,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挖掘《密洛陀》相关的其它布努瑶口传文化、服饰文化和美食文化等方面的内涵,促进布努瑶聚居地各县创建优质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形成《密洛陀》的非遗旅游、非遗扶贫、非遗传承保护和非遗研究的良好互动局面。[31]
不同形式的表意文化,充当着《密洛陀》活形态传承的记事、叙事、说事、演事等不同功能。但是,目前对这些表意文化形式的研究,有的基本上还没有,已有的个别研究,相互间则缺乏整体的有效呼应,这是今后《密洛陀》研究亟需整合的地方。
(四)实现与国内外史诗研究的接轨
实现与国内外史诗研究的接轨,目的是要让《密洛陀》及其研究“走出去”,汇入诗学研究的大潮流,扩大《密洛陀》在中国乃至世界史诗学界的影响力。 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在理论和方法上自觉运用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叙事学理论等当代史诗学重要学说对《密洛陀》进行精审深细的诗学分析。 具体做法就是把严格的田野作业引入《密洛陀》的研究之中,从静态的文本转向了对史诗的唱叙群体、程式、创编、演述语境、交互指涉、流布与变异、史诗与民俗信仰的互渗等议题的综合研究,形成多学科的延展观察,探索《密洛陀》的表达系统,揭示其创编和传承规律以及其作为活形态史诗的诸多体裁样式的社会文化意义,丰富、检验甚至修正以印欧语系为研究对象而抽象出来的口头诗学理论,为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添砖加瓦。 二是通过对《密洛陀》的研究探寻瑶族文化的底色,从史诗文脉之根中寻找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和新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根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文化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学理支持。
四、结语
瑶族在历史上迁徙十分频繁,因而形成现如今居住分散、语言差异极大、风俗习惯不同、支系繁多的“民族共同体”。 布努瑶是瑶族的第二大支系,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迫害和民族歧视、民族纷争等原因,长期在石山地区过着颠沛流离的游耕生活,被认为是历史上迁徙时间最长、“受苦最深、受难最重”的瑶族支系,解放前还一度被视为“末开化的特种部族”。②但在每一个苦难、困境面前,布努瑶都高唱古歌,坚信密洛陀能帮助他们走出险境、绝境,通达新的人间乐土。 正是依靠世代传唱《密洛陀》,布努瑶构筑了共同的族群记忆、精神寄托和抗争支撑,顽强地保留了民族凝聚力和族性。
作为神话、传说史诗化的成果,《密洛陀》的文本化过程,既是瑶族民间文学的发展史,也是20 世纪50-60 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映射。[32]随着民族史诗研究南北格局的确立,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和研究正进入学理反思阶段,中国史诗研究的学科化和制度化正在有序推进。[33]今后《密洛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应当充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尽快弥补短板与不足,在理论和方法上自觉与国内外史诗学接轨,彰显出《密洛陀》的学术价值和独特贡献。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和重大的课题,需要《密洛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所谓宗教语,主要是指瑶族巫公在驱神赶鬼的宗教场合唱述《密洛陀》所使用的歌唱语言。 布努瑶除日常交际语言外,还创造出三种歌唱语言,分别是宗教语言、乐歌语言和爱恋歌语言。 宗教语,布努瑶民间称之为“鬼语”,主要是用古汉语词和古瑶族词以及少量其他民族的语词混合构成其词汇的,特点是一词多音。 比如,在宗教语中,“密洛陀”的称谓是“密本洛西·密阳洛陀”。 乐歌语言只限于喜庆场合使用,主要涉及历史题材的歌,包括密洛陀歌、族史歌、开亲史歌等,语言的构成成分是古瑶语和古壮语。 爱恋歌语言是布努瑶年轻人用来唱爱恋歌的语言,民间叫“撒旺”,是乐歌语言语汇和布努瑶交际语言词汇混合在一起的歌唱语言。 三种语言中,宗教语最古老,最难掌握,所以过去一名巫公的培养,从他几岁就开始跟着长辈出门看、学、唱、做宗教法事活动,直到十七、八岁才能完全掌握这种语言和各种法事活动。 外来学者如要搜集整理《密洛陀》,必须有懂宗教语的布努瑶学者或会汉语的巫公协助才能顺利完成。
②1930 年代中期以后,广西省政府对尚未与汉族“同化”的瑶、苗、侗及少数壮族等所谓“特种部族”进行“开化”,以期实现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 在都安,“化瑶”成为“开化”政策实施的重点(彼时苗瑶不分)。 《都安县志稿·民国》(由都安县县志办整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出版)第183 页“特种教育”记载:“本县汉苗杂处,历有年所。 惟苗(大部分实为瑶族)与汉言语隔阂,不相往来,故其生活习惯,均与汉人(大部分实为已“同化”的壮族)异。 政府迭令遣子弟入校读书,以其同化,惟苗人视学校为畏途,结果很少识字兴趣。 民廿九年调查有特种部族杂居十乡,共三十二村。 令其无分畛域种族,悉施以国民教育。 惟师资缺乏,收效很少,幸得桂岭师范学校招生,政府考送特种部族优秀之人计二十五名,自行前往投考,取得肄业学位者不下廿十人,先后毕业回籍,服务乡校间及县府统计室,引起苗人求学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