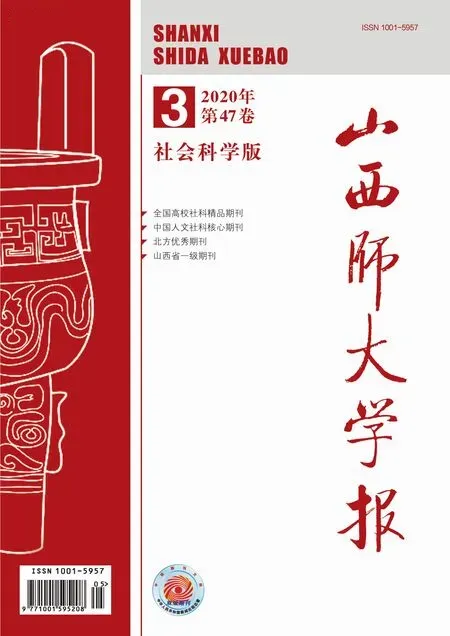略论《西游记》影视改编中现代性的植入
陈伟华, 韩冰玉
(湖南大学 文学院, 长沙 410082)
引 言
以当今的“IP”理论视之,《西游记》无疑可位于中国最具有 “IP”价值的古典文学著作之列。纵观《西游记》的影视改编历程(本文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信息全部来自视频资料。电影名后括号中的年份为出品年份,公映年份可能与该年份一致,也可能滞后),可见各版“西游记”影视剧都记录着它们所处时代的印记。从万籁鸣、唐澄执导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1961—1964)中,可见1960年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1986)中,可见1980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从刘镇伟导演的电影《大话西游》系列(1994)中,可见1990年代的游戏和反叛精神;近几年由《西游记》改编成的电影中所体现出来的“超级英雄”文化,则明显带有美国大片影响的烙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西游”,《西游记》的改编始终体现着现代性。
现代性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没有明确的分期。广义的现代性是指“意味着成为现代(being modern),也就是适应现时及其无可置疑的‘新颖性’(newness)”[1]337。汪民安在《现代性》一书中也指出,现代性的发生,就是现代同过去的断裂: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技术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现代之所以是现代的,正是因为它同过去截然不同。[2]49
20世纪初人类生活已经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重大裂痕,21世纪初随着消费文化逐渐兴起,传统与现代更是严重分化,不断崛起的新事物和新观念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视作为文化现象与文化输出,也必定在这方面有所体现。正如周仲谋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电影改编》一书中所说,改编对原著进行了解构和颠覆,但又暗合了原著的某些精神,并建构出了一些新的时代意义,而这种精神,正好与当代年轻人的思想观念相契合。[3]143在《西游记》的影视改编过程中,创作者们不断地摒弃一些传统理念,将当代社会问题和价值观植入,继而赋予《西游记》更多更深刻的内涵,让《西游记》与现实结合,寓教于乐,推陈出新,让古典“西游”在今天的荧幕上获得了一次次重生。
一、构建现代师徒伦理
(一)摒弃尊卑关系:跪拜礼逐渐消失
跪拜礼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含义,虽然它刚出现时并不带有严格的身份等级象征,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封建社会的成熟和完善,跪拜礼成为中国社会一种表现尊卑贵贱的重要礼仪。1912年,民国政府才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废除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跪拜礼。[4]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跪拜礼虽然逐渐被国人摒弃,但封建社会残余的尊卑贵贱思想依然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许多文艺创作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反封建意识融入自己的作品当中,《西游记》的影视改编也是如此。
在《西游记》的原著当中,孙悟空拜师的场景是这样的:只见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马前,赤淋淋跪下,道声:“师父,我出来也!”对三藏拜了四拜。[5]167猪八戒拜师的场景:那怪走上前,双膝跪下,背着手,对三藏叩头。[5]234沙和尚的拜师场景:那悟净才收了宝杖,整一整黄锦直裰,跳上岸来,对唐僧双膝跪下。[5]274后人将《西游记》搬上荧幕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跪拜礼逐渐退出了观众的视线。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1986)中,徒弟三人都对唐僧行了跪拜礼;程力栋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2009)中,孙悟空没跪,八戒和沙僧行了跪拜礼;张建亚(总)、黄祖权、赵箭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2011)中三人都行了跪拜礼;到了郑保瑞导演的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中,徒弟三人的跪拜礼全部消失。
到目前为止,在某些风俗中跪拜礼仍然存在,比如祭祀祖先、长辈,祭孔大典等,但这时的跪拜礼已经不再承载“尊卑和等级”文化了,而是变成了“尊敬”。《西游记》影视改编里跪拜礼的消失,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里糟粕部分的摒弃,也是对师徒关系的重新思考。
(二)师徒关系发生嬗变:从仆主依顺到相互为仇,再到平等相处
《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里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6]1860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天地君亲师”,传统文化一直是尊师重道的。《礼记·学记》有云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7]169大思想家荀子更是将尊师上升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明代大学问家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谈到对老师的态度时说:“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8]1155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不尊师长是大逆不道之罪,师父甚至可以像父亲一样对徒弟实行强权。在学徒制的师徒关系中,师徒实际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尤其是梨园里的师徒关系。看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1993)就知道,师父可以随意打骂和惩罚徒弟。在宗教里的师徒关系中,人们因共同信仰某一个教派而聚在一起,然后徒弟向师父拜师求法。悟空、八戒、沙僧虽共同信仰佛教但并没有得到唐僧的传法,保唐僧取经都是听从观音菩萨的指点,观音又是如来佛祖派来的,所以,与其说徒弟三人听从唐僧,不如说他们听从如来佛祖。一路上三人为唐僧挑担、牵马、化缘,徒弟三人更像是唐僧的保镖、马夫和挑夫,像主仆关系。
原著和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1986)里,唐僧有赶走孙悟空的权力,紧箍咒便象征着唐僧对悟空的强权。从刘镇伟导演的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1994)开始,师徒关系被彻底颠覆,徒弟从顺从开始走向反叛。《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一开场就是孙悟空想联合牛魔王把唠叨的唐僧吃掉。周星驰导演的电影《西游·降魔篇》(2012)里,孙悟空靠欺骗唐僧才从五指山下出来,并且出来以后魔性不改,想杀掉唐僧。徐克导演的电影《西游·伏妖篇》(2016)中的师徒关系更加恶化,唐僧在这部影片里已经失去了该有的师德,他对孙悟空恶言相向,并且时常鞭打悟空,最后悟空忍无可忍,不愿再被唐僧欺凌,通过反抗“师权”使得师徒关系走向平等。
在田晓鹏执导的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里,唐僧变身为江流儿——一个非常崇拜孙悟空的小孩,而孙悟空也褪去了偶像光环,被如来佛祖封印,成为连山妖都打不过的普通人。在跟山神相斗时,孙悟空是靠江流儿揭下山神的封印才打败山神,唐僧不再只是一个被保护的角色。在原著和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1986)中,唐僧虽然柔弱,但他始终是以睿智的长者身份示人,孙悟空、八戒和沙僧则像三个需要被管束的孩子,遇到大是大非的事情时,往往是唐僧来做决定。但在郑保瑞导演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2018)里,唐僧喝了子母河的水怀孕了,一心想要普度众生的唐僧顿悟他腹中的胎儿也是一条生命,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孙悟空却说:“拖家带口,如何西去?” 于是大胆地忤逆了唐僧的意图,用法术强行给唐僧等人灌下落胎水。这时候唐僧和孙悟空的角色发生了置换,唐僧变成了一个任性的“孩子”,而孙悟空变成了理性的“长者”。他们师徒四人之间更像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为了同一个目标坚定不移地朝前走,互相监督和照顾,而不是单纯的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
所以,在《西游记》的影视改编中,师徒关系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仆主依顺到相互为仇,再到平等和谐共处的变化过程。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师徒关系的演变跟社会不断发展、制度不断完善下,人们追求平等和人权的文化氛围不无关系。
二、变妖魔悟空为美猴悟空,置换或重建“西游”主题
电影是以经济物质载体而存在、以市场运作而生存的。人们可以赋予电影以种种功能,比如教育的、宣传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可以拍种种类别的影片,艺术家也可以为艺术而艺术。[9]149《西游记》系列影视剧虽改编于古代名著,但会融入当下的意识形态,揭露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积极正确地引导人们的生活,起到教益性的作用。
在原著当中,孙悟空其实是一个妖魔形象:“七高八低孤拐脸,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5]445第二十七回里还描写了孙悟空吃人肉的情节:“老孙在水帘洞里做妖魔时,若想人肉吃,便是这等:或变金银,或变庄台,或变醉人,或变女色。有那等痴心的,爱上我,我就迷他到洞里,尽意随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哩!”[5]3311949年以后,孙悟空从妖魔形象逐渐趋向于人的形象,并且被赋予了政治含义,1961—1964年摄制上映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闹天宫》借助戏曲元素使美猴王的外表色彩鲜明,真正使“妖猴”变成了“美猴”。而电影也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结局进行了改编,最后孙悟空并不是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指山下,而是高举“齐天大圣”的旗帜,仿佛彰显了“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含义,代表了反抗封建强权的胜利。
徐克导演的电影《西游·伏妖篇》(2016)充分肯定了互相尊重、平等相处的师生关系。唐僧对孙悟空非打即骂,经常叫孙悟空臭猴子,并且还体罚悟空;孙悟空对唐僧也并不尊重,常常想杀了自己的师父。影片中有一处情节:悟空让唐僧出了丑,唐僧恼羞成怒,命令悟空跪下,不跪就打死他,悟空质问唐僧:“你现在知道当众出丑是怎么回事了吗?你现在知道当众被罚跳舞是有多惨吗?你才感受到跪在你面前像狗一样被你抽打有多难受吗?没错,我就是要耍你,让你知道什么叫作没有尊严。”与其说电影在演唐僧师徒,不如说是在演当今学校里的师生关系或者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唐僧就像是某些对孩子使用暴力的老师或者家长,悟空则像是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少年。当专制的长辈遇到叛逆的晚辈,摩擦和矛盾在所难免。影片里唐僧听完悟空的质问后突然打了自己一巴掌,然后给悟空跪下道歉了。这之后唐僧和悟空的关系就变得很奇妙,唐僧让悟空不要叫他师父,唐僧说我们俩是一辈子的好兄弟,让悟空叫他大哥。师徒关系变成了兄弟关系,意味着师徒走向平等,这种创作意图符合当今对师生关系、长辈和晚辈关系的认定。
郑保瑞导演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2018)思考了堕胎的罪恶性,传达了当今社会“人本思想”的理念。原著当中,唐僧一行怀孕后,唐僧对女儿国大臣说:“你这里可有医家?教我徒弟去买一帖堕胎药吃了,打下胎来罢。”[5]654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1986)里,唐僧等人怀孕后,唐僧说:“敢烦太师指个医家,叫我大徒弟买一帖药来打一打。”无论是吴承恩,还是电视剧导演杨洁,都没有意识到堕胎的反人道主义。《西游记·女儿国》里,女儿国的君臣一听唐僧等人怀孕,拍手称快:“恭喜诸位,诸位有身孕啦!”女儿国像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那里的子民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她们看来男人生孩子符合正常的伦理观念。孙悟空去取落胎水时,如意真君反问他说:“你说你去西天,是为了普度众生,可这腹中胎儿,何尝不是众生?”如意真君的话道出了堕胎的反人性。“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大量胎儿被迫流产,如今政策放开,但堕胎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相较于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1986),这部电影思考了堕胎的罪恶性,告诉观众胎儿也是一条生命,是当今“人本思想”的深刻体现。
现代社会问题和社会观念的植入,给古老的《西游记》注入了新鲜养分,让它继续焕发生机。如果说《大话西游》这类“无厘头”搞笑影视作品是对“西游”严肃命题的颠覆和消解,那么现代观念的植入无疑是对“西游”主题的置换和重建,是创新的良好体现。
三、基于当代大众情感和美学新构故事
(一)以爱情故事引发观众共鸣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命题,通过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当然也离不开爱情。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几乎没有情感戏。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1986)中试探性地让唐僧和女儿国国王有了一些暧昧情愫。《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开启了“孙悟空谈恋爱”的先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刘仕裕导演的电视剧《齐天大圣孙悟空》(2002)里的孙悟空喜欢紫兰仙子;郑保瑞导演的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3)里孙悟空喜欢白狐狸;郭子健导演的电影《悟空传》(2016)里孙悟空喜欢阿紫。作为和尚的唐僧也并不总是清心寡欲的。在杨洁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1986)里,唐僧扮演者徐少华提议将原著里的“唐僧”形象赋予更多的人性,于是有了广为流传的“若有来生”:女儿国国王色诱唐僧时,唐僧刹那心动,并对国王说出“若有来生”的话。这种改编实际上也是对原著的颠覆,因为原著当中唐僧将“女儿国之行”完全当作一场劫难,始终清心寡欲,一心向佛。刘镇伟导演的电影《情癫大圣》(2005)里唐僧喜欢蝎子精岳美艳;《西游·降魔篇》和《西游·伏妖篇》这两部电影里,唐僧喜欢过段小姐和小善;《西游记·女儿国》里唐僧和女儿国国王更是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戏码。
唐僧和孙悟空能不能谈恋爱,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六小龄童曾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认为,《西游记》这样的名著不能恶搞,不能随意翻拍,让孙悟空和白骨精谈恋爱就是人妖不分是非颠倒,是三俗:低俗、庸俗、媚俗。[10]网上甚至还有专门讨论“孙悟空能不能谈恋爱”的帖子和辩论赛。实际上,19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氛围下,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不断开放,宽容度不断上升,在一个淡化个人英雄主义、讲究合作和全面发展的时代,孙悟空谈恋爱、唐僧动凡心就变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曾经性格单一的人物形象已经不再符合大众的审美。观众希望在大荧幕上看到更加有血有肉的人物,体会更加能引起共鸣的感情,而不只是看到耳熟能详的师徒四人斩妖除魔的故事。不管是《大话西游》里的“爱你一万年”还是《西游降魔篇》里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抑或是《西游记·女儿国》里的“我舍我的王权富贵,你守你的戒律清规”,都借由《西游记》的框架创造了一个个爱情悲剧。悲剧模式下的爱情能够容纳更多的母题和内涵,比如爱情和责任的两难抉择、取舍、放弃、成全以及牺牲。这些桥段或多或少都曾在观众的人生当中上演过,这些命题也更能打动荧幕前那些经历过“爱而不得”的人的内心,即使没有经历过,人们也乐于在电影院欣赏一段爱情传奇,而不仅仅为了看唐僧师徒如何去取经。
在这一部部“爱情西游”里面,难免会有原著被过度消费的行为。但不得不承认,爱情元素的融入让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有了更广的知名度和更长久的寿命。人们借由《西游记》的故事表达今人对爱与责任,大爱和小爱取舍的看法,只要逻辑和价值观引导不出偏差,不失为一种创新。六小龄童尊重传统文化的思想没有错,但时代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吐故纳新才能源远流长。
(二)以“娱乐化”满足大众审美需求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香港影星周星驰自电影《赌圣》开始,在华语电影圈内逐渐确立了特有的无厘头表演风格。周星驰影片的“无厘头”风格通过活跃在底层社会的无赖痞子形象,以无明确指向和莫名其妙的行为、到处耍小聪明的刁滑举动、玩世不恭和不成调调侃的嬉皮士态度,凭借离经叛道的恶搞方式反叛正统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秩序,深层次契合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大众文化精神价值和审美需求。[11]《赌圣》于1990年出品,算是开山之作。1994年两部由周星驰领衔主演的《大话西游》电影则可视为“无厘头”电影的经典之作。从《大话西游》开始,《西游记》的影视改编就一直偏向喜剧风格。即便电影中含有悲剧情节,但因其人物和台词设计上都融入了搞笑元素,所以也并不让观众感受到太多的悲剧意味。
《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情癫大圣》以及《大话西游3》是由刘镇伟导演的西游系列电影。《月光宝盒》里的孙悟空变身为土匪头目,一出场就是斗鸡眼,猪八戒由喜剧演员吴孟达饰演。他们外形上披头散发、衣衫褴褛,性格上咋咋呼呼、莽撞急躁,关键时刻还会出卖朋友和队友,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在《大话西游》里被彻底颠覆。《大圣娶亲》和《大话西游3》延续了《月光宝盒》的剧情,唐僧依然是婆婆妈妈的话痨形象,用冗长、拗口并且无厘头的台词制造笑点。《情癫大圣》一开场,师徒四人来到莎车城,以搞怪的舞蹈造型出场,莎车城全体子民站在城墙上跳民族舞来欢迎他们。
从2013年开始,国内几乎每年都会上映一到两部“西游”电影并且都会融入各种喜剧元素。郑保瑞导演的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里猪八戒由小沈阳出演,一改丑陋的猪头扮相,变身为一个爱穿红色衣衫的淫贼。徐克导演的电影《西游·伏妖篇》(2016)里一开场,师徒四人由万人敬仰的取经人变成了为生计所迫在街头杂耍的卖艺人,猪八戒的形象借助戏曲元素,在脸上涂满了油彩。郑保瑞导演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2018)主要借助人物对话和情节来融入搞笑元素,唐僧师徒怀孕更是一大喜剧情节。纵观这些电影,将猪八戒女性化、人物对话通俗化、故事情节恶搞化、加入现实里的流行语等似乎成为《西游记》影视改编的一个总体趋势。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外来文化的引入,中国社会呈现出更广的开放性和更宽的包容性,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在中国慢慢出现并流行,比如港台的流行歌曲、言情和武侠小说,比如崔健的摇滚乐、王朔的“痞子文学”等。而滥觞于《大话西游》的“大话”文化在1995年进入内地后,更是掀起了一股颠覆、解构和调侃的风潮。“在今日之中国,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大众’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载者,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要求在逐渐分裂并多元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显位。”[12]3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禁锢、80年代的迷惘,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是文化的商业化。文艺逐渐不再以政治导向为中心和全部重心,精英文化和宏大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大众也开始追求轻松幽默搞笑、能够调剂生活、缓解心理压力的文艺作品。这些变化明显地反映在1980年代末弥漫在电影界的“娱乐片”思潮中。“在不断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电影票房的巨大压力下,全国22家电影制片厂,以及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电影导演,都不约而同地放下架子,或瞻前顾后、或义无反顾地转向了‘娱乐片’或类型片创作。”[13]397《西游记》影视改编所走的“娱乐化”道路,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形成的。
结 语
1906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出品京剧电影《金钱豹》,此为孙悟空与唐僧的故事首现银幕。虽然其剧情不见于小说《西游记》,但中国电影与“西游记”故事渊源之深可见一斑。1926年,由邵醉翁、顾肯夫执导,胡蝶、金玉如等主演的剧情片《孙行者大战金钱豹》问世,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中国第一部由《西游记》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时至今日,《西游记》的影视改编之路快要走过一百年了。在这漫长的、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西游记》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被创作者们不断赋予新的思想和内涵,始终体现着现代性。观众可以从这些影视作品中听到耳目一新的台词,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师徒伦理的变化,体会到被植入作品中的人本思想,甚至可以在影视作品中找到自己的情感诉求。《西游记》作为中国老少皆宜的古典名著,是中国文学长河里的璀璨明珠,是传统文化里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为中国打造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为当今“IP”产业的繁荣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但与此同时,《西游记》的影视改编也一直是一个具有较大争议性的话题。保守派认为《大话西游》等另类的作品属于恶搞,是亵渎古典名著和传统文化,让孙悟空和妖精们谈恋爱实则是善恶不分,颠倒黑白。开明派则认为小说《西游记》本身就是对玄奘法师去天竺取经这一历史事件的“恶搞”,所以后人对小说《西游记》的各种改编也无可厚非。一千个读者有一千部《西游记》、一千个孙悟空。但无论如何,《西游记》极具现代性的影视改编确确实实使得古典名著重新焕发生机,让半文半白的古典小说在当今的消费文化语境里不至于被束之高阁,而是在一次次改编之下历久弥新。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娱乐化”泛滥现象也非常严重。影视改编对名著深度的消解、对历史的篡改、对崇高意义和宏大意义的摒弃,都会对影视作品的艺术性和生态文化造成不良的影响。《西游记》的影视改编无论改成悲剧还是喜剧,仍然应当尊重正确的悲/喜剧理念,而不是为了追求娱乐化和商业化生硬地加入不合时宜的噱头和笑料;无论融入怎样的新潮思想,都应该有着正确的价值观和适合我们国情的精神及文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