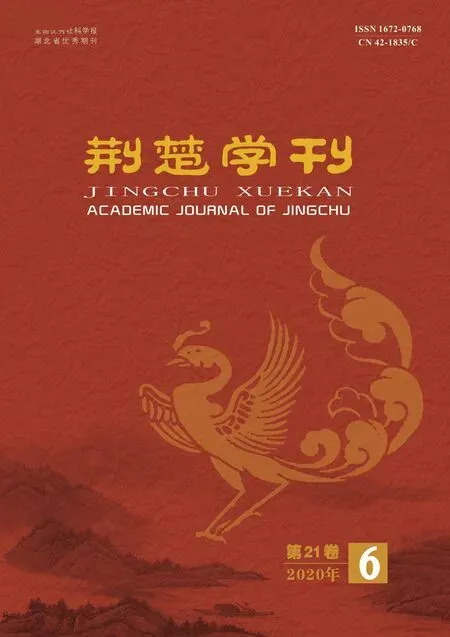汉魏时期道家对孔子形象认识的变化——以《淮南子》和王弼为考察对象
景世东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居于中国学术史的核心地位。每逢社会、学术变革时期,对孔子及其历史形象的认识往往代表着时人对传统文化和典籍的态度,也就昭示着下一阶段学术发展的方向。因为孔子思想的丰富和深邃,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其形象被多次改造,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学者视野里甚至会出现截然对立的几个侧面。汉魏时期,道家学派对儒道融合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他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也随之改变。《淮南子》(1)是汉代道家思想的典型代表之一,而王弼的玄学思想以其结构完整、论证严密,在魏晋时期玄学思潮中也颇具代表性。通过分析《淮南子》和王弼思想中孔子形象的典型表现及其差异,并以此认识背后反映的学术与社会状况,不仅可以为研究道家思想发展提供新的角度,也是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时期思想世界变迁的必要工作。
一、“体道者”——《淮南子》中孔子的形象
汉初诸子学复兴,各家多有明显的融汇百家思想的尝试,其中以儒道两家较为成功。儒家思想经陆贾、贾谊以儒统合道、法、阴阳诸家的努力后,至董仲舒时已经蔚然成风。适应汉初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黄老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1]3289,成为一时显学。而《淮南子》强调“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2]864、“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2]865,应当认为是黄老道家学派的著作。出于治世的现实需求,相较于老庄哲学中更多形而上的探讨,《淮南子》对指导实践的“外王之道”同样重视。
纵观全书,《淮南子》站在道家立场上对儒家学派、思想不乏贬损,却少有对孔子的直接批评。西汉初期,儒家思想虽然并不是王朝的指导思想,但无论在朝在野,它的影响不容忽视。与《淮南子》同期,正是董仲舒《公羊春秋》学大行其道的时候。《淮南子》从自身立场和治道出发,一方面积极肯定儒家仁义学说有助于教化的一面,一方面又对“今之儒者”背离自然情性大加鞭挞: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为义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构而多责[2]412。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颜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学也。然颜渊夭死,季路葅于卫,子夏失明,冉伯牛为厉。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2]289-290。
《淮南子》并非排斥“仁义礼乐”理论,承认礼义在规范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它所反对的,是当时儒者不知顺应自然情性而强以礼义自缚,以至于违背礼义的根本,因此对其作了严厉指责。而对于孔子本人,《淮南子》以肯定评价为主:
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2]727。
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2]829。
其余大多如此,非但少有严词厉色,反而对其品行、功业赞誉有加,直至推到“圣人”的地位。
究其原因,《淮南子》一书正处于西汉前期思潮转变的节点上,这一时期儒道交锋又交融。孔子是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自先秦以来一直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他诸子包括道家学者在内也常以“孔子曰”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淮南子》对孔子的评价,既是先秦以来孔子地位不断抬高事实的反映,也是《淮南子》试图兼融儒道、建立以道统儒思想体系的现实需要。在这种现实下,《淮南子》塑造出“体道者”的孔子形象,通过超越性的“道”来沟通孔老,将孔子改造为道家话语的代言人。这一做法不仅有利于道家思想理论的丰富,也对道家思想在治国实践的具体操作中借鉴儒家礼乐思想提供了方便。
《淮南子》中对孔子形象的描述材料受《庄子》影响颇深(2)。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庄子》书中塑造出了“非道者”“求道者”和“体道者”三种孔子形象。而通过对《淮南子》文本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淮南子》中的主要孔子形象是可与老子比肩、作为道家学说代言人的“体道者”形象。此处孔子所体的“道”,显然不是儒家主张的伦理之道,而是道家形而上的“道”,即“天地之道”。作为体道之人,孔子的言论、行事展现出了鲜明的道家特色。
《淮南子》对孔子形象的描述,首先通过“内圣”角度展开。所谓“内圣”,指的就是对“道”的理解和掌握。《淮南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是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又是支配世界运行的总规律。“道”的本体是虚无的,超然于具体事物之上又体现在具体事物之中,具备着自然转化、循环往复的特点。因此《淮南子》特别强调“反”的概念,“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泰族训》),“道”永远处于动态的向自身回归的平衡状态。于是在《淮南子》语境中,孔子表现出贵柔守静的一面。《道应训》记载:
孔子观桓公之庙,有器焉,谓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贡在侧曰:“请问持盈。”曰:“益而损之。”曰:“何谓益而损之?”曰:“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是故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多闻博辩,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贵广大,守之以俭;德施天下,守之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尝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2]502-503
孔子通过这段对宥卮特点的谈论传达出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是他认识到“物盛而衰”的道理。道的特性,是“极则反,盈则损”,具体事物的发展表现也必然符合这一规律。这种“反”的发生既然是道规定的,具备广泛性,人类社会无疑也遵守这一规律。因此这一认识引出第二层含义:孔子主张通过“益而损之”来持盈,具体表现就是以柔弱守静之道处事。即便智慧超群、品格高超,也要守之以愚、陋、畏、俭、让,因为“不盈”,所以“不危”。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持柔守静不是被迫妥协的结果,而是积极主动地选择,目的是“持盈”“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不是弱者的权宜之计,而是强者、有力者体道之后的自然行为。“孔子劲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2]461-462,这里所讲的“以强为弱”的持胜之道,正是上述理解的有力表述。
从“内圣”推而广之,由己及人,所展现的就是“外王”之道。关于孔子的“外王”之道,《淮南子》主要从教化治民和“守约治广”两个方面论述。《主术训》中有一段集中描述:
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弘,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约,故举而必荣[2]375-376。
这段话对孔子盛赞不已,乃至尊为“素王”“圣人”,这与自先秦以来孔子“圣人化”历程也是相符的。《淮南子》认为,孔子虽然“能亦多”,却“事亦鲜”,一方面与其“贵柔守静”的人生哲学相符合,另一方面却也使“专行教道,以成素王”更加凸显出来。孔子的“教道”,既包括思想层面的编撰六经、“采善鉏丑”,即所谓“论亦博”,也包括实践层面的教导弟子、教化民众。正如前文所言,《淮南子》致力于治道,自然对孔子教化治民的功绩大加赞扬:
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2]829。
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买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班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2]814。
以至于《道应训》中作者借恵孟之口称赞孔子“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2]464。
至于“守约治广”,实际是指孔子实行教化的方法。上文提到,“道”是事物运行的总规律,又每每体现在具体事物之中,“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2]557。孔子作为体道之人,理应具备见微知著的素质,相关描述《淮南子》书中多见,不做列举。孔子既然能由小见大,由近推远,那么他能够教导弟子,自然可以教导民众;能治理一国,也就可以治理天下。至于及时铲除恶政的源头,自然也是同样道理。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2]546-547,也就能够实现“至赏不费,至刑不滥”的状态,故称“其所守者有约,故举而必荣”。
关于体道的途径,《淮南子》认为孔子主张通过“反性求本”的方法。《淮南子》指出,性是人从上天得来的自然禀赋,“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2]401,与个人的形体同时形成,“夫性命者,与形俱出其宗,形备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2]47。性与道直接关联,“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2]412,“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2]272。虽然人性的本质是“无邪”“生而静”的,但会受到外部环境的污染,以至于“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2]79。“夫性,亦人之斗极也”[2]423,若要重归于道,则必须反求那个无邪的本性。《齐俗训》:
孔子谓颜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于我也亦忘。虽然,汝虽忘乎,吾犹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2]423。
孔子所不能忘的,就是指引体道途径的“性”。因为纯真本性的存在和指引,孔子才能不离于道,即“孔子知其本也”。
在具体操作层面,人如果想要“反性求本”,首先需要知晓“道”的存在,“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2]424。失去了这一前提,体道自然无从谈起。其次,求道之人需做到“去载”。“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2]561“去载”,即祛除不合于性本质“无邪”“静”的过多的欲望,达到虚、平的境地。这种祛除的实现,不是借助外力的克制,而是自己内心平意清神的结果。若是“目虽欲之,禁之以度,心虽乐之,节之以礼”,仍是对性命之情的违背。因此需要效仿达道者“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如此才能追求大道,成为体道之人。
总体来说,《淮南子》上承先秦道家学派对孔子道家化改造的努力,塑造了一个体会“天地之道”并以之指导人生和政治实践的体道者孔子形象。经过这番努力,孔子较之先秦更加具备了道家思想的特征,开两汉道家学派融合儒道的先河,儒道两家融合互补的趋势逐渐明朗起来。
二、“体无的圣人”——王弼思想中的孔子形象
汉魏之际是道家学说再次走上思想世界中央的时期。此时的经学衰微,五十年间两次禅代,旧有的秩序与观念已丧失说服力,制度异化、价值混淆、人心惑乱,整个社会经历着大剧变。随着玄学在学术史地位的确立,以王弼、何晏、郭象等人为代表的玄学家重新审视儒道经典,论述孔老优劣,辨析本末有无、名实关系,意图融合儒道,规范名教与自然关系。汤用彤先生指出:“夫历史变迁,常具继续性。文化学术虽异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渐进。”[3]23两汉时期,在今古文经学和谶纬神学的推动下,到了汉末,孔子的圣人地位已经无可动摇,被全社会承认了。即便当时学术界风气由两汉通经转为祖尚老庄,玄学家们依然重视孔子形象,孔子道家化的努力仍在继续,因此玄学家们通过改造孔子,将其塑造成一个体无的圣人,力图从本体的高度融汇儒道。孔子形象也随之玄学化,思想内涵有较大的改变。此时的玄学家一方面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发起冲锋,对孔子形象的相应表述却是散见于只言片语之间。王弼是玄学流派的核心人物,他的学说被认为“内圣之道在老庄,外王之业在孔子。以此汇通儒道,则阳尊儒圣,而阴崇老庄”[4]121,思想学说具有代表性,对孔子形象也有相对集中的认识。下文我们以王弼思想为例分析此时孔子形象的特点。
王弼首先承认了孔子的圣人形象。《世说新语·文学》: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5]218-219
当时思想界普遍将孔子视为圣人,以老子为贤人。但是,正始时期,人们重视“有无之辨”,一般认为“无”是世界的本原,强调“无”的本体地位。孔子作为公认的圣人,却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人事而非天道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就与“孔高于老”的普遍认识产生了矛盾。王弼创造性将对“无”的理解、感悟区分为两个层面,用“体无”与“言无”分别表达。“依王、何之学,孔子之所以为圣,在于体无。而老子恒言虚无,故与圣学同。留儒家孔子圣人之位,而内容则充于老庄之学说。”[6]98孔子“体无”,老子“言无”,王弼在“无”的理解上找到了儒道会通的交流基础,以玄学的内核替换了儒家的仁义学说,“表面是调和,实际老子是胜利的”[7]22。这种将孔子改造为“体无的圣人”说法,解决了孔子作为圣人“谈有不及无”的问题,是孔子形象道家化的又一重要阶段。
“无”是王弼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王弼以“无”诠“道”,是道家哲学中“道”概念在玄学时期发展的新形式。《老子指略》谈到: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万物,靡使不经也[8]195。
“无形无名者”,指的就是“道”。王弼强调,只有具备抽象性、一般性、普遍性的“道”,才能够囊括万物,才能作为具体事物的本原。而“道”本身“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9]31,因而是“品物之宗主”。王弼之所以用“无”代称“道”,“是为了说明或表明本体‘道’的抽象性、普遍性、一般性的哲学性质”[10]。显然,以“无”为本就是以“道”为本,王弼“无”本论的实质就是“道”本论(3)。
其次,王弼将孔子之“道”诠释为道家本体之“道”。在注释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时,王弼写道:“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8]624孔子所谈论的“道”,应该理解为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和基本原则,而更加侧重在人道范围,并不具备本体论的意义。王弼通过将伦理之道解释为无本论的“道”,赋予了孔子的“道”本体论的涵义,从而将孔子的思想内核玄学化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道不可体”,讨论的是“人作为万物一员,其行为之表现能否与道相符的问题”[11],强调“物与人的表现与道本身有一定的距离”[11],而并非“圣人体无”中圣人无法领会、体悟道的意思。
孔子为什么能够体“无”?王弼认为原因在于“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8]640。所谓“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汤用彤认为这即是“智慧自备,为则伪也”[9]6,并指出“圣人则藏明于内,以无为心,以道之全为体,混成无分”[3]92。万物“有”虽然各有差异,但在本体层面却是一致的,“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9]117孔子智慧超于常人,“故能体冲和以通无”[8]640。
再次,从顺任自然出发,王弼借孔子之口强调“自然无为”的治国理论。王弼在注释“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章写道:
圣人有则天之德。所以称唯尧则之者,唯尧于时全则天之道也。荡荡,无形无名之称也。夫名所名者,生于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恶相须,而名分形焉。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何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8]626!
王弼认为,孔子称许尧的原因是尧能时时全则天之道。尧以道治理天下,实质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之性而不横加干预。“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9]64。王弼讲的“道不违自然”,王中江指出,应该理解为“‘道’纯任‘万物的自然’”,并认为“道法自然”实际上是“道遵循万物的自然”[12]。《老子道德经注》第五章讲“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9]13,圣人尧“则天成化,道同自然”,顺应自然以尽物之性,“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虽不为,而使之成矣”,而不过度干涉,“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9]13,故能“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圣人体自然之心行自然之事,不以智慧自得,“是以圣人务使民皆归厚,不以探幽为明;务使奸伪不兴,不以先觉为贤。故虽明并日月,犹曰不知也”[8]626。其实孔子政治思想中本身具有一些推崇“无为而治”的思想成分,如“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等。王弼通过对孔子话语阐释发挥,突出了其中道家倾向的含义,孔老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了。
最后,在求道的途径上,王弼通过对“子曰:‘予欲无言’”章的注释提出“举本统末”的方法。他说:
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谆谆者哉[8]633-634。
王弼认为“名以定形”,而“道”却浑然而无形,那么道自然是不可名的,因而“道”具备不可言说、难以界定的特点。于是追求不可言说、不可论述的“道”,只能舍去言说来反求其本——道。
立言垂教,寄旨传辞,是历代儒家一贯的做法。汉儒谨守“家法”“师法”,“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四库全书·经部总叙》),发展到魏晋时期早已繁琐不堪,圣贤之旨湮灭不传。王弼认为,“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意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8]609。王弼的批评有着现实的依据。王弼强调“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力倡“得意忘言”说,一举廓清汉儒孜孜于末梢的治学方法,不依章句而尚“通”。“予欲无言”,乃是圣人唯恐滞泥于言象而失其本意,因而必以“不言”求返本于“无”。通过这番诠释,孔子“体无”的论述更加严密了。
综上所述,王弼以道释儒,以有无本体哲学对孔子言论加以玄学论的解释,塑造出一个体无的圣人形象。通过这种义理诠释,儒道之间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儒道融合趋势更加明显。魏晋士人讨论“老庄与圣教同异”问题时,作出“将无同”的答复自然也更容易理解了。
三、结语
孔子是代表儒家学派、儒家学说的关键人物,对孔子形象的不同认识和表述实质上反映着当时人们对儒学的认识和态度。道家学派对孔子形象的认识从“体道者”向“体无的圣人”的转变过程,也是道家学者对儒家学派态度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道家学术持续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历程中儒道融合的阶段反映。
前后孔子形象的转变,反映出道家学术走向义理探讨的发展趋势,也是魏晋时期崇尚思辨、简约的学术精神的表现。从形式上来看,《淮南子》尚延续《庄子》叙述风格,以“三言”发挥主旨;而王弼探讨“本末”“有无”,立足于本体高度,重视对“道”“名”“自然”等概念的分析,通过注经诠经方式阐释发挥文本义理,构建学术体系。从内容上看,相较于《淮南子》侧重于经验世界,王弼思想更具抽象性和超越性。陈荣灼已经指出:“先秦道家是开宗立论的草创期,成就了经典性的代表作《老子》和《庄子》。汉初黄老之学偏重外王面之发展,那末魏晋玄学则是进一步深化了其内圣面。”[13]从对《淮南子》与王弼哲学的分析来看,这一论断是切合的。
道家学派自先秦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孔子形象道家化,这是他们以道统儒、实现儒道会通的努力尝试。从庄子及其后学对孔子或批或赞开始,经《吕氏春秋》、《黄帝四经》等阶段的发展,儒道关系从对立竞争逐渐步入相融相合阶段。《淮南子》对孔子持积极肯定态度,从孔子的言谈、行事中寻找与道家思想的契合之处,并假借孔子之口阐释发挥,从外部实现儒道相通;而王弼直接将孔子认定为道家的圣人,从思想内部改造孔子,对其思想作出玄学化的解释,实现孔老的内部融合。在整个儒道融合的过程中,显然是孔子而非老子才是那个兼通儒道的代表人物。自此以后,儒道会通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显著特点,对后世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1) 关于《淮南子》的思想倾向,主要有“道家说”和“杂家说”两种说法。笔者倾向于认定《淮南子》学说为黄老学派的“道家说”。
(2) 王叔岷指出:“检《淮南》全书,其明引《庄子》之文仅一见……其暗用《庄子》者则触篇皆是。今本《庄子》三十三篇,唯《说剑篇》之文,不见于淮南。”见王叔岷:《<淮南子>引<庄>举偶》,《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366。
(3) 何石彬更进一步认为王弼对宇宙本体最本质、最准确的称谓是“无”,“道”不过是从“万物之所由”角度对“无”的体现。参见何石彬:《老子之“道”与“有”“无”关系新探——兼论王弼本无论对老子道本论的改造》,《哲学研究》,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