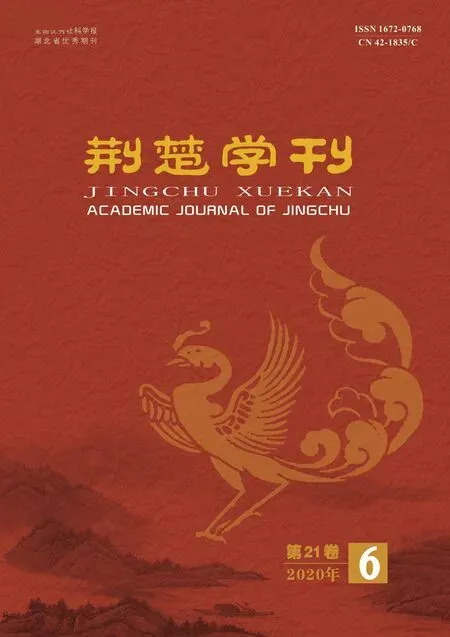论莫洛亚传记中的文人群像
叶 健
(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自文人诞生以来,人们对文人英雄的崇拜就未曾停滞过,这些作家所创造的文学经典探索了人性的各个面向,满足了我们对可能世界的无限向往。在分析莫洛亚笔下作为“文人英雄”的传主时,我们难免会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这些传主何以能够震撼世界?是什么使他们跻身文人英雄的殿堂?为什么说他们的生平经历同样是构成其作品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
众所周知,“文人英雄”是英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提出的概念,他在《英雄和英雄崇拜》这本讲演集中将历史上的英雄分为六种类型,其中塞缪尔·约翰逊、罗伯特·彭斯和让-雅克·卢梭被视为文人英雄的典范,是“新时代”的产物。他们履行一项崇高的职能:“在真正的文人身上有一种被世界承认或不被世界承认的神圣性:他是世界之光,世界的教士;像神圣的火柱在世界黑暗的历程中指引世界经历时间的流逝。”[1]257如果说“诗人英雄”具有先知一般的本领,那么“文人英雄”就是卡莱尔在一个怀疑年代树立起的精神之塔。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文人英雄们正是凭借其难能可贵的真诚品质赢得了卡莱尔的青睐。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所讨论的是文人的社会属性,而对其文学作品缺乏足够的关注。换句话说,与文学上的成就相比,卡莱尔“更加看重文人的本质或功用”[2]。
一、传主与文人英雄
事实上,文人英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既指向文人的社会意义和作品的价值,还意味着他们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卡莱尔将“真诚”视为文人英雄的重要标志,但对于莫洛亚笔下的传主而言,他们掩藏在“文人英雄”的神秘面纱下的生活细节同样值得人们去认识和了解。比如在《雨果传》中,我们时而看到文学世界中的雨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诗神,拥有不竭的创造力,享受着应有的荣光;时而看到生活中的雨果缺乏幽默感和浪漫气息,对妻子表现得严厉古板、不解风情,他需要一位理解他的女性,这便是后来的朱丽叶·德鲁埃。同时也能够看到雨果为了进入法兰西学院而苦心钻营,后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暴政而被迫流亡;甚至还看到他的子女相继离他而去。莫洛亚试图在雨果的生平经历和文学作品之间寻求平衡:“我力求时刻铭记:在一位诗人的一生中,作品与事件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我写的是一部恰如其分的传记。”[3]xvi所有这些都指引我们去体会这位伟大诗人的杰出才华与悲天悯人的胸怀。
作品与其创作者是密不可分的,孤立地看待作家或文学经典对我们的认知和理解并无裨益,只有将作品与生活结合起来,文人英雄的形象才可能完整。作品和生活是文人英雄的两幅面孔,它们看似分裂,实则是统一于传主的生平之中。一般来讲,这些文人英雄使我们感到震撼的,毫无疑问是他们的文学创造力和作品的生命力,他们的一部部文学经典是一种难得的馈赠,而这些杰作正是依靠他们的独特天才创作出来的。对于文人的天才,英国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的一番讨论不乏新意。毛姆认为,天才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所构建的世界超越了私人的领域,具有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特性,“有了这样的普遍性,他的吸引力不仅指向一类人,而是所有人。他的私人世界就是普通人的私人世界,不过更为丰富,更简洁凝练。”此外,他们对生活的感悟能力也有别于常人,“通过愉快的天赋机遇,他用人类普遍采用的健康方式,以似乎处于极高能量状态的巨大活力看待充满无穷多样性的生活。”[4]74
在毛姆看来,天才非同凡人,但这种天才能力具体为何物?他在《巨匠与杰作》一书中进行了探究并指出,正是作家的个性禀赋与强烈而持续的创作冲动,促使他们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这是基本前提。还有一种更加神秘莫测的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灵感。“当作者获得这种可喜的神力时,各种观点、形象、比喻、甚至具体事实都会向他涌来,而他感觉自己不过是个工具,就像个速记员,只需记下传授给他的东西即可。”[5]300不过,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分析并没有告诉我们灵感究竟为何物,也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作家的艺术天赋。如果说毛姆对灵感的解释带有柏拉图理念说的意味,那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番讨论则更具启示意义:“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为他们所努力要表达的主题做的一种和解。”[6]709卡莱尔在讨论但丁的意义时也表示:“他有一种伟大的洞察力,直接把握一个事物的本质,并表现出它。”[1]150而在莫洛亚看来,这就是天才的能力:“迅速发现事物并领悟其奥秘,这是天才的特性。”[7]49作家的天才和灵感就表现在他们能够揭示出隐藏在事物表面下的深刻本质,并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将其定格下来。
需要指出的是,卡莱尔所强调的是文人的“真诚”品质及其所发挥的时代价值,而莫洛亚的传记作品主要聚焦在“文人英雄”的生平和创作方面。相比之下,莫洛亚更强调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和成就,同时在更深的层面上分析了这些作家的个性特征,使读者对传主有更为立体的认识和了解。莫洛亚在每部传记的开篇都做过类似“传记契约”式的说明,他对传主的选择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些传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莫洛亚力图扭转这种局面。例如,他指出为大仲马作传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强调他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对一位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感到乐趣的作家,对这位至今我仍然喜爱其作品所表现的力量、激情与气度的作家,我仍然保持着敬重与爱戴”[8]x。但莫洛亚对传主的喜爱并不妨碍他作出客观的评价,比如他承认大仲马在艺术上处于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等人之下,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大仲马的作品在通俗文学中的地位:“在全世界,声望超过大仲马的人,恐怕并不多见。”[8]ix二是为了厘清对传主的误解和偏见,捍卫传主的文学声望和地位。比如他在《乔治·桑传》的前言中指出,有人认为乔治·桑的作品缺乏文学价值,但莫洛亚十分明确地给出自己的判断,他指出,尽管乔治·桑的某些作品的价值存在争议,但她的自传和书信作品却足以使她跻身最优秀的作家之列。
莫洛亚在传记作品中展现了传主的真实面貌,他们并非毫无瑕疵的圣人或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神,他们也存在缺陷。然而,真正使他们成为文人英雄的,正是他们与自己的命运相抗衡、与自身的平凡本性相斗争,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将自己的深刻思想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创作出伟大的杰作,这正是莫洛亚笔下的文人英雄的特质。
二、 作家与文学经典
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历程中,诞生了无数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莫洛亚不仅在传记作品中叙述了文人英雄的创作生涯,而且从作家和文学经典两个维度讨论了传主的成就。在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看来,所谓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审美价值且不受意识形态所左右的文学作品。布鲁姆提倡个体的审美选择,反对以“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新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为代表的所谓“憎恨学派”对文学经典的批判和非难,于是描绘了一个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西方文学经典的版图。事实上,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和筛选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朽的文学作品往往都具有普遍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力量,它们是认识人类情感和社会历史的精神宝库。布鲁姆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变好或变坏,“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9]24这个见解同样值得重视。
莫洛亚在传记作品中,层层剖析了传主的创作艺术和文学作品的思想,例如,他在分析屠格涅夫的小说艺术时回应了这样几种偏见。一是人们习惯于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通过抬高后两者而贬低屠格涅夫。莫洛亚认为不能以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质来要求屠格涅夫的小说,屠格涅夫所营造的狭窄的文学天地“完全符合他本人的气质”。《猎人笔记》虽然仅仅塑造了几个农民形象,但在莫洛亚看来,它比漫长的俄国历史更能展现1830年的俄罗斯[10]112-14。二是屠格涅夫小说的创作或结构问题。莫洛亚认为屠格涅夫之所以能在篇幅简短的小说里营造一种“隽永和充实之感”,得益于一种“结构严谨、十分含蓄和完美无暇的艺术”。具体而言,屠格涅夫的小说总是发生在“一个骤变的时刻”,往往迅速进入主题,避免故事情节过于延宕,只有在读者的注意力被牢牢抓住时才交待故事背景。因此,莫洛亚认为与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构相比,屠格涅夫的结构要“朴实得多,原始得多”[10]120-21。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特点,亨利·詹姆斯认为屠格涅夫是一个“做好笔记再写小说的人”[11]50。此外,莫洛亚还将屠格涅夫视为一位“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作家”,认为他的小说能够做到将外界的景物与个人的情绪混合在一起,“把大自然与人的内心激情结合在一起,把个人的遭遇重新置于云彩与太阳、春天与冬天、青春与暮年这些广泛而有节律的运动中去,这样的人便是诗人,同时也是小说家”[10]123。对屠格涅夫而言,正是凭借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和诗意的描写,最终在世界文坛享有一席之地。
我们之所以沉迷于作家所创造的文学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被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深深吸引。在分析作家的天才和艺术手法外,莫洛亚传记作品的另一特点就是在传主及其创造的文学形象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就像唐璜之于拜伦、勒内之于夏多布里昂、奥林匹欧之于雨果等。“从文学发端,作者就为自己的创造找寻原型”,毛姆认为这是文学创造力的体现,“作家并不是复制他的原型;他从原型身上提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吸引他注意的某种特征,点燃其想象力的气质倾向,从而构建他的人物。”[4]197-98作家创造的文学形象反过来又变成自己的“面具”,就像莫洛亚所说:“浪漫派作家为了更好地逃脱他们世俗的命运,于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化身,把自己的忧伤与抱负统统赋予这个化身。”[3]258在为浪漫派作家作传时,莫洛亚善于运用隐喻的手法将浪漫派传主与神话人物或文学形象建立某种关联,而这些“化身”总是能够形象地概括他们的性格特点。比如他在《三仲马传》中认为,大仲马将自己的两种性格特点赋予了火枪手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波尔多斯体现着大仲马性格中由他父亲遗传下来的那一部分”,而阿拉密斯“则代表了父子两人受恩于达维·德·拉巴叶特里的潇洒气度”[8]202。通过建立这样的联系,不仅加深了对文学人物的理解,也使传主的形象更加传神。
可以说,莫洛亚的传记实践清楚地表明他接受了福楼拜的著名公式:“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或多或少透露出作家本人的思想情感,但对传记作家而言,如果将传主创造的文学人物等同于传主本人,那就是对福楼拜名言的彻底误读。韦勒克和沃伦在讨论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方法时曾指出,“作家不能成为他笔下的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观点、美德和罪恶的代言人”。尽管我们可以将作家的作品和生平对照,而且“这种方法甚至为诗人们所欢迎,尤其是那些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写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内心情愫,或者像拜伦,甚至带着‘一颗流血的心’吟游于欧洲四处。这些诗人不仅在私人的书信、日记和自传中表现自己,而且也在他们大部分正式发表的诗作中表现自己。”[12]77-78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作家的作品就是其生活的记录或内心的真实写照,因为“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文学作品不同于书信和日记,后者与现实的关系比前者更为紧密。即使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生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决不意味着艺术作品仅仅是作家生活的摹本。”[12]77-79韦勒克和沃伦还以韦德女士的《特拉赫恩传》和穆尔的《艾米丽·勃朗特传》等例子指出他们把传主的作品和生平混为一谈,显得十分荒唐。
实际上,莫洛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传记作品表明,我们或许可以从作家的作品中管窥他们的生活。但这种了解是极为有限的,很难获得关于作家的完整认识。诚如亨利·詹姆斯所言:“我们对于那些自己甚感兴趣的作家,总希望有更多的了解,而不仅限于他们的作品。”[11]78因此莫洛亚借助于丰富的历史材料,包括传主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作家的生平,并刻画了传主内在的精神世界。与作家创造的文学经典相比,他们的生活往往具有别样的色彩。莫洛亚在《巴尔扎克传》中也写道:“生活比艺术丰富,然而生活的真实并非艺术的真实。人对生活既无法穷其究竟,也不能饱览无遗”,只是作家习惯于将生活经历改头换面地投射到文学作品中,“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把提炼过的思想通过人物体现出来,塑造出让读者感到栩栩如生而又简明概括的艺术形象。”[13]429因此,在莫洛亚看来,个人的不幸遭遇和时代弊病使巴尔扎克表现得像个悲观主义者,倾向于用黑色的笔调去描绘社会的现实,但他并没有被现实的残酷和黑暗所吞噬,反而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巴尔扎克超越了他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他们最美好的时刻可以超越人类的弱点(随即被宽恕的弱点)而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尽管他的作品中描写了那么多的邪恶,然而这一超越偏见和激情的理解使得作品成为一种力量与明达的源泉。”[13]441如果对作家的生活经历有足够的了解,就不难看到他们作品中传达出的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命运的抗争、在现实和艺术的困境中的突围等等。
总体而言,文学的创作过程总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作家的身份同样带有一种神秘性。正如小说家戴维·洛所总结的:“我们为文学创作的神秘性着迷,因此热切地希望发现作家灵感的源泉;但我们对于重要作家的私人生活,出于人的本性,还有一种简单的好奇心,尤其是如果这些作家的私人生活有些异乎寻常的话。”[14]3然而除了卢梭等少数作家外,很少有人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隐私,毛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是难于了解的,诱导他们向你讲述关于他们自己的且于你有用的特别之事是个缓慢的工程。”[4]90对作家来讲,他们需要创造一个化身来代替自己完成这个工程,因此,王尔德的观点道出了真相:“一个人谈论自己的时候最不真实。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告诉你真相。”[15]18普通人需要面具,作家尤其如此,所以在作家的文学化身中发现他们的生活痕迹也就不足为奇。作家的文学替身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超越作家个人的经验和感受,获得自己特有的生命和价值,成为永恒的文学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仅是无数文学经典得以流传的主要原因,也是莫洛亚传记作品独具艺术魅力的地方所在。
三、文人与知识分子
在叙述传主的生活与创作、分析作家作品特色之外,莫洛亚还考察了他们在一系列政治活动中的表现,从另一个侧面领略19世纪文人群体的精神风貌,因此,文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其传记作品值得探讨的一个方面。纵观莫洛亚的传记可以看出,这些传主不仅与各自作品中的虚构人物惺惺相惜,还与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们之间往往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如雪莱和拜伦的友谊,再如法国文人群体的相互交流:大仲马父子、雨果、圣伯夫、乔治·桑、缪塞、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泰奥菲尔·戈蒂耶、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或一同出入沙龙,或对各自的作品评头论足,或为了情妇和荣誉争风吃醋等等。这些文人的交流往往是不同文学观点或政治立场的碰撞,甚至成为文学创作的现实来源。
比如乔治·桑和缪塞曲折的爱情最终以失败收场,但彼此心中都无法释怀。乔治·桑对爱情不再抱有太多希望,缪塞看似把这段感情抛诸脑后,实则用文学的形式将其永远保存了下来。莫洛亚在《乔治·桑传》中写道:“缪塞不再痛苦,因此,只要艺术要求,他便能心甘情愿地再次揭开伤口。他保留的这个痛苦时期的回忆,这些爱情、欢乐,和疯狂的日子里的图景,给他的所有作品提供了养料。”[16]260因此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真正实现了内心的平静。而在缪塞死后,围绕着他们的故事又引起了一阵风波。乔治·桑根据他们曾经在威尼斯的经历创作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她和他》,将自己写成一个仁慈高尚的人,这激怒了缪塞的哥哥,后者写了《他和她》作为回应,把乔治·桑写得残酷无情,显然失之偏颇。此外,“一头雌驴也踢过来一脚:女文人路易丝·科莱,没有才能,却个性很强,写了一本题名为《他》的小册子,通篇文章充满了怨恨。”[16]554乔治·桑保存了她和缪塞的全部书信,并且指出这些书信表明《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与《她和她》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她在给圣伯夫的书信中说道:“它也许说明一方面的疯狂,另一方的热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说这是双方的疯狂所致的。但是他们的内心一点也不怯懦,一点也不丑恶,没有什么可以玷污那真诚的灵魂”[16]556。莫洛亚在文学传记中展现这些文学史背后的故事,不是出于八卦心理,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传主的内心及其文学作品的价值。
一般来讲,对文学成就的渴望是文人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而对荣誉的争夺也难免使文人产生妒忌心理或反目成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说:“只有到了不再热衷于自己时,我们才开始成为作家。”[6]438这里说的“热衷于自己”指的是以自己为中心进行创作。但在更多情况下,成为作家以后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热衷于自己,而是恰恰相反:不仅会更加热衷于自己,而且对别人的成就也难以保持平常心。比如在目睹了雨果八十岁生日的庆祝活动后,埃德蒙·德·龚古尔十分嫉妒和生气。朱尔·俄勒纳尔的一句名言可以精辟地概括这种羡慕、嫉妒心理:“别人的成功让我不舒服,如果他的成功名符其实,我会更加难受。”[17]53事实上不仅是龚古尔,雨果在年轻时取得的巨大成就还引起了很多其他文人的妒忌。法国作家安娜·博凯尔和艾蒂安·克恩圣伯夫在《法国文人相轻史》中着重描述了圣伯夫和雨果的纠葛。作者认为年轻的雨果取得的胜利与圣伯夫在文学上的沉默形成了巨大反差,很多年轻文人团聚在雨果周围,使圣伯夫与雨果的友谊“黯然失色”。于是“圣勃夫开始嫉妒,觉得自己被雨果抛弃了”,这时便将注意力渐渐转移到雨果夫人身上。作者对此表示疑问:“雨果在所有涉足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圣勃夫即使再怎么努力也难以企及。他是否想通过某种手段从雨果身边夺走点什么?”1834年,圣勃夫写文章批评雨果的作品,又发表了《情欲》这部小说表达了对阿黛尔的爱慕,至此,他和雨果“彻底撕破了脸”[17]5-7。
但在莫洛亚看来,作为雨果副手的圣伯夫对阿黛尔的纠缠并不仅仅是因为失落和嫉妒而向雨果报复,还有圣伯夫的自卑和喜欢打探别人秘密的本性。“这位朋友(指雨果)的成就使圣伯夫感到的自卑感更多于嫉妒心”[3]169,而雨果正忙于戏剧事业,对阿黛尔和家庭的关注不够,这给了圣伯夫可乘之机。当然,圣伯夫除了用空闲的时间和暧昧的感情安慰苦闷的阿黛尔外,并没有能与雨果相匹敌的才华、名誉或财富。莫洛亚还指出,两人之所以在1834年全面闹翻,与这种三角感情的纠葛关系不大,“两位老友的反目并非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由于文人的气质不合。”[3]240可见莫洛亚对“文人相轻”的见解眼光独到。
回顾19世纪的法国,两种景象相互交织:一方面文学繁荣发展,巨匠辈出;另一方面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因此以作家群体为主的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打交道。如同安娜·博凯尔和艾蒂安·克恩所指出的:“十九世纪初,在左拉发表‘我控诉’和‘知识分子’的说法出现之前,很多作家已经自认为肩负某些公共使命,即使因此招致严厉批评也在所不惜。”[17]138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也认为,法国19世纪的公共作家善于表达国家观念,而且这种观念通常既包含政治又超越政治,“在法国风起云涌的年代,许多矛盾是围绕着某位作家产生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分裂极其严重时,文学可以成为团结力量的重要来源。”[18]3-4这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来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克拉克进一步指出,在法国的文化传统中,文学家与政治家维持着相互联系、相互崇拜的关系。这种情感是特殊的,文学家希望谋求政治上的发展,而政治家也希望在文学界享有声誉。法国社会对作家普遍尊敬,但他们尊重的并不是某位作家个人,而是对作家地位的尊重,法兰西学院院士和作家甚至比百万富翁和政治家享有更高的礼遇。因此,克拉克的这番话应当引起注意:“公共作家绝不会放弃对文学的忠诚,因为这是实现抱负的平台,这些著名公共作家所具有的权威是道义上的,而非实际的;他们的‘权力’也是象征性的,因为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让大家关注某一话题并激发大家的意见。”[18]27比如雨果、巴尔扎克、欧仁·苏、左拉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的关心。
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在《自由的声音》一书中将目光对准法国19世纪的文人群体,叙述了夏多布里昂、贡斯当、基佐、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克维尔、乔治·桑、米什莱、勒南等人的政治观点,勾勒出一幅19世纪法国的自由史。在维诺克看来,这些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介入政治,“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19]8。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和历史趋势的推动下,莫洛亚笔下的传主自然也无法避免政治环境的影响,他们有的因政治和革命事件而波及到自己的创作,有的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断努力,有的甚至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前者如巴尔扎克,后者如夏多布里昂、雨果、乔治·桑等。
四、 结语
作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一员,莫洛亚并不反对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政治行动感兴趣。法国在“二战”前期沦陷后,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将军邀请莫洛亚作为流亡政府使团的成员,并要求他以使节的身份前往美国,游说罗斯福政府加入到反法西斯的阵营中,因为美国参战被普遍认为是英法取胜的唯一机会[20]263-264。莫洛亚始终把这个政治任务视为自己的使命,他在流亡美国期间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越来越清晰的判断,发表了一系列反法西斯的社会演讲。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无论在什么时候,知识分子对政治局势的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
在莫洛亚所刻画的法国文人中,夏多布里昂无疑是最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一个,他历任法国驻柏林和伦敦大使,后当选外交大臣,但最后却因不善于处理政治被国王解雇。莫洛亚总结了夏多布里昂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要想维持政治的胜利,必须足够灵活和耐心,而这是夏多布里昂所缺乏的:“一位大臣的种种最出色的天赋,如果不伴随一些次要的优点,如谦逊、耐心等,可能毫无意义,甚至是危险的。夏多布里昂没有任何卑躬屈节。他的傲慢虽然可以理解,却使一些不那么出色的人反感。他们了解他,但不希望他把心里的蔑视态度明显表现出来。突出的才华,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极大妒忌,但只有在本人不谨慎、不机灵时,才会变得有害。”[7]297从政治智慧上讲,夏多布里昂是不够“机灵”的,他的傲慢和冷漠的态度与他的政治雄心结合在一起,自然会引起政敌的报复,从中也可以看出文人参与政治总是有自身的局限性。莫洛亚在分析夏多布里昂的政治遭遇时写道:“夏多布里昂如果更机灵,更顺应实际,他本来可以领导他的同僚和亲王们,可是他却更喜欢诅咒他们。这种拒绝现实的态度,对幻想家而言十分自然,却正是他失败的原因。”[7]298翻开20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无数知识分子迷失在对政治和权力的狂热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莫洛亚的文人传记再一次向我们表明,对文人和知识分子而言,保持清醒的头脑往往比盲目介入政治行动更加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