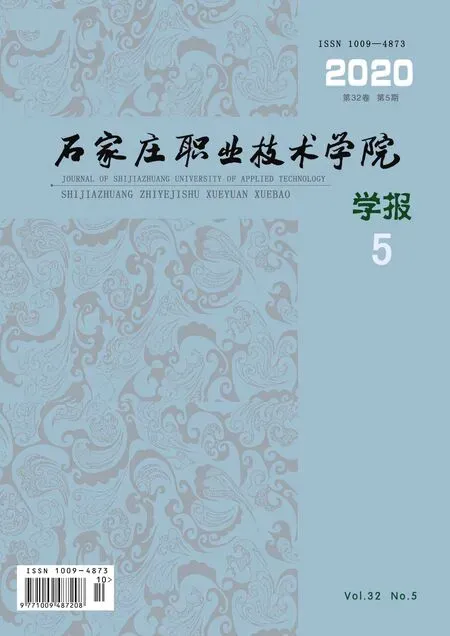“生态批评”的发展轨迹
梁 芳
(石家庄市艺术学校 英语教研室,河北 石家庄 050031)
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风起云涌,相继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等理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面临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环境保护思潮在欧美兴起,“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是一支文学批评流派,诞生于人类面临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之时,体现了西方文论“向外转”的态势,拓宽了文学批评的探索领域。
一、“生态批评”的源起
1972年,美国学者约瑟夫·米克尔在《幸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首次提出“文学生态学”概念,主张探讨“文学对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影响”[1]。后来,此类术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自然文学研究”“自然历史阅读”“环境文学批评”“绿色研究”“绿色文化研究”“生态批评”与“生态诗学”等术语纷至沓来。系列术语中, “生态批评”的接受面最广。
1978年,威廉·鲁克特尔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术语[2]。1989年,在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上,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提倡关注“生态批评”[3]13,得到时任学会主席格伦·洛夫的积极响应[3]138。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阐释“生态批评”的意义,引起了广泛关注[3]107。
两部“生态批评”著作共同构建了“生态批评”的理论纲领与原则。一部是劳伦斯·布依尔撰写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另一部是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与哈罗德·弗罗姆合著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其中,劳伦斯·布依尔的专著是“被‘生态批评’家引用最多的著作”[4],堪称“生态批评的里程碑”[5]。
英国彼得·巴里教授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中首次为新兴的“生态批评”设立一章[6], 此后,许多关于20世纪西方文论的综述性专著都将“生态批评”作为独立的批评流派专列一章, “自90年代迄今,生态批评在学术期刊、会议、项目、学位论文、专题研究里大量出现,犹如洪水泛滥。”[7]
对“生态批评”的概念一直没有确切的界定。1994年,西部文学学会曾邀请20位知名学者对“生态批评”概念进行分析,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原因在于“生态批评”是一个“巨大而且正在继续扩大的学术领域”,是一种“多种形式的考察”,“以环境问题为焦点向多种视角扩展”[8]。其跨学科特性使之不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研究方法,从而导致不同学者间批评方式差异巨大。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生态批评”空间越来越广阔,内涵也越来越复杂。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把“生态批评”界定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9]xviii。但是,“生态批评”的立场局限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表层研究,力图挖掘自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历史、精神、思想及文化根源,并以文学批评方式探寻走出生态危机的途径。
二、生态批评的发展
(一)“生态批评”的发展阶段
彻里尔·格罗特费尔蒂勾勒了生态批评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致力于研究文学再现自然与环境的两种模式——“伊甸园”或“荒野”。第二阶段力图挖掘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自然文学作品及其生态思想。如,亨利·梭罗批判工业文明,提倡回归自然与简单生活;艾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生态中心主义”与“ISB”三原则——完整、稳定、美丽;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对科技滥用的批判后来都成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或切入点。第三阶段旨在建构生态诗学,将“生态批评”提升到理论高度,出现了阿尔伯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论”、彼得·辛格的“动物权利论”以及“生态美学”“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等。[9]xxiii-xxiv
劳伦斯·布依尔教授在其专著《环境批评的未来》中,将“生态批评”发展趋势划分为两股浪潮,“第一股把环境看作是‘自然环境’,目的只是‘保护生物共同体’,认为‘自然’与‘人类’ 领域不像环境批评家所认为的那么互相关联”[10]21。第二股对此表示质疑,主张“成熟的环境美学——或者伦理,或者政治——必须考虑大都市和内地,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的关注应相互渗透”[10] 22-23。劳伦斯·布依尔教授认为 “第一股可归为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第二股可称为环境公正型生态批评”[10]138。
(二)“生态批评”的发展特点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生态批评”逐步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这一发展过程呈现出专业化、国际化与全球化的特点。
近年,一些西方高校“生态批评”专业课程不断增加,且深受欢迎。帕特里克·墨菲说:“当然不必每个人都成为生态批评家,但在现代语言学会占有职位的所有院系都应当开设生态批评课程。”[11]《环境文学教学: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源》一书,对指导“生态批评”课程与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耶鲁大学英文系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有生态文学选修课程。俄勒冈大学格伦·洛夫教授及其同事开设的环境文学研究课程有五百多名学生选修[12]。哈佛大学开设了美国文学与美国环境课程,劳伦斯·布伊尔教授的讲义被汇编为《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一书。另外,诸如弗吉尼亚、佐治亚、亚利桑那、犹他等地均被誉为“生态批评”重镇。
“生态批评”虽发轫于美国,但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7]701。20世纪80年代,“生态批评”还是新生事物,相关研究人员担心 “谁愿意听我说话”,但现在成了 “我怎样才能跟上它发展的步伐?”[13]1998年,帕特里克·默菲教授主编了一部囊括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生态批评”大型论文集《自然文学:一部国际性的资料汇编》,并提出“生态批评的发展需要对世界范围的表现自然的文学进行国际性的透视”,这部论文集是“在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14]。
英国的“生态批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其奠基人为乔纳森·贝特,1991年,他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中使用了“文学的生态批评”一语[5]9。 1998年,英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出版。劳伦斯·科普的《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被尊为英国生态批评里程碑。在英国,学者们把“生态批评”称为“绿色研究”,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1992年,“生态批评”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成立,会长为斯科特·斯洛维克。2004年,“欧洲文学、文化及环境研究学会”成立。加拿大、墨西哥、尼日利亚、马耳他、爱沙尼亚、澳大利亚、日本与印度等国的“生态批评”热度也较高。
近年来我国也涌现出从事“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与生态美学的专业学者,代表人物有曾繁仁、鲁枢元、王诺、程虹等。“生态批评”的学术团体以及研究专刊也初具规模。成立于2004年的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是我国高校第一个“生态批评”团队,由王诺教授担任学术带头人。创刊于1999年的《精神生态通讯》,是以推动“生态批评”与生态文艺学建设为主旨的刊物,由鲁枢元教授担任主编。创刊于2009年的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潘阳湖学刊》是生态学研究专刊。山东大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了由曾繁仁、鲁枢元担任主编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通讯》。上述学术团体与研究专刊均为推广与交流“生态批评”理念与成果作出了贡献。
三、“生态批评”的发展前景
“生态批评”是西方文论的一次绿色转向,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视角,开辟了新领域,注入了新活力,具有一定理论意义。首先,西方文艺理论或注重形式、文本、作家、读者或关注种族、阶级、性别、历史、精神与文化等,但“自然”缺席。“生态批评”推动了文学与自然关系的研究,突破了文本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站在地球生态圈的高度透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了久已缺席的自然在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弥补了文学研究一直以来对自然视角研究的不足。其次,20世纪以来,欧美文学研究出现了“向内心、向文本形式”转至“消解意义与价值”倾向,这既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偏颇性。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等的出现虽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但“生态批评”倡导的文学研究向自然、地球、生态意义与生态审美转向,扭转了某些文学研究脱离社会现实的晦涩化倾向,加强了文学批评对真实世界的指涉,有助于纠正当代文学研究的某些偏颇,从而拓宽西方文论探索的领域。
“生态批评”力图挖掘和批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倡导批评家为缓解甚至消除生态危机承担责任,具有一定社会意义。格伦·洛夫认为:“生态批评不仅以解读世界为目的,还试图跨越文本与现实的鸿沟,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及其同作品关系的方式来改变世界。”[15]如上所述,“生态批评”理论的社会意义不容否认,但与传统批评流派相比,还处于边缘地带,有待于在外部的质疑中成长,在内部的争鸣中成熟。
首先,“生态批评”还没有获得当代西方批评话语的主导权。美国的相关研究人员除了劳伦斯·布伊尔教授执教于哈佛大学外,几乎都就职于远离学术权力中心的西部大学;英国的相关专家也基本执教于非主流或新成立的大学。[4]248
其次,“生态批评”的反对者质疑,环境问题固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它更像一个关于“社会动员”的政治问题,所以不应把学术性的文学研究与环境危机这样的现实问题混为一谈。唐纳德·沃斯特则认为“生态批评”自有其意义:“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16]
“生态批评”还被嘲笑为是一个有助于学者出版著作和获得职位的“学术工厂的发电机”,缺乏一整套为人们广泛了解的理论预设、基本原则和批评程序。诚然,“生态批评”批判造成生态危机的人类思想、文化传统的缺陷,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要真正达到“理论上的成熟”,就不能止于批判,还必须在继承前人生态思想成就的基础上,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若干重大思想问题,进而建立新的生态哲学体系。劳伦斯·布伊尔教授也期望“生态批评”不应当仅仅是“具有颠覆性的学科”[17],更应是“具有建设性的学科,拿出影响巨大的代表性理论著述”[18],并建议“生态批评家应该好好利用中国儒家学说的资源”[19]。 因此,加强自身理论建设与东西方话语融合是全球生态批评研究人员努力的方向。
再次,“生态批评”内部还处于“争鸣”阶段,这一方面说明“生态批评”还处于建构期,达到理论成熟还有待时日;另一方面,也体现其多元性及生命力。不仅国外的“生态批评”家在方法论上有诸多不同,我国“生态批评”内部也存在一定差异。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批评不仅是对现实召唤的承诺,解救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大自然,而且要还人性以自然,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它理应成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因为它的终极关怀是重新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20]基于此,他将“生态批评”的要旨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三大方面。许多学者对此深表认同:“到目前为止,人类文明进步的取得是以自然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面对当代自然环境的失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于类似的生存竞争而导致异化,这就是社会生态失衡。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失衡同时导致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故而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都是生态批评研究的范围。”[21]
王诺认为:“生态批评的重心始终要落实在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上,落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因此生态批评在进入不同学科的交叉领域时,一定要有所节制,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轻言所谓‘精神生态’‘语言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等。”[22]有学者对此表示认同:“生态批评除了在适用范围内有所受限,还容易被一些‘庸俗’的生态批评者们‘泛化’,即将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统统都与生态环境相联系,从而 ‘变异’了文学研究的根本性质。”[23]
上述学者的观点见仁见智,其共同目的是使“生态批评”既有广阔的空间又有严密的学理。鲁枢元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分法颇具理论建构之功。王诺则提出其在批评实践中容易出现的庸俗泛化问题,但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危机的紧密联系则是毋庸置疑的。王诺的“欲望动力论批判”“唯发展观批判”“贪欲膨胀扼杀人的美好灵魂及天性”等“生态批评”切入点也的确涉及到了人类社会与精神问题。
“生态批评”既有其独特价值也有某些理论盲点,只有当人类彻底根除了自然、社会、精神与文化的重重危机,“生态批评”才可能完成其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