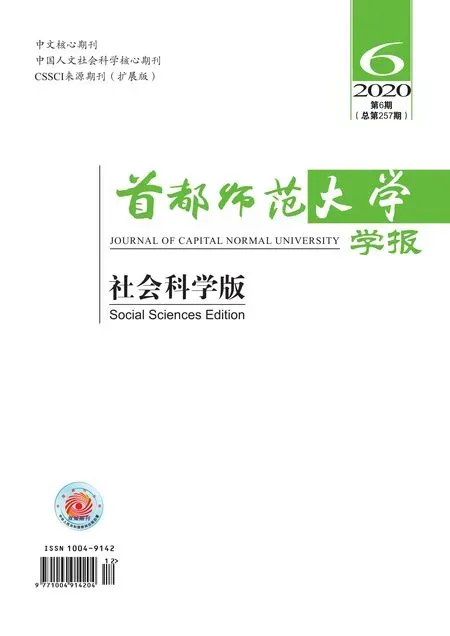职官·地理·文学
——解读李谔《上书正文体》的三重视野
马铁浩
隋代李谔《上书正文体》一文①原文载《隋书·李谔传》,无题名,宋《文苑英华》、明《四六法海》等题《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宋《四六标准》、明《隋文记》、清《古文渊鉴》《古文雅正》等题《论文体书》,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题《上书正文体》,今人多从后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对于其主题的认识,现代学者颇有分歧。或者将其置于文学观念复古的脉络之中,如郭绍虞认为“李谔所论固启唐代古文家的先声”②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7页。,罗根泽亦将“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视为“早期的古文论”③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1-482页。;或者将其视为梁代裴子野《雕虫论》的后继,认为他们皆否定魏晋南朝以来的文学发展,对齐梁绮靡文风的批评,表现出强调政治教化而轻视文学审美的倾向。对于这二种意见,钱钟书曾有批评云:“或许李谔为唐人‘古文’拥帚清道,固迂远而阔事情,又取此《书》与梁裴子野《雕虫论》齐称,亦拟不于伦。裴所重在作诗而不在文,且只陈流弊,未筹方策;李则昌言‘弃绝华绮’,‘职当纠察’。拿破仑主法国时,尝以文学不盛而申斥内务部长;使李所请见诸施行,‘公私文翰’,概归‘宪司’,‘外州远县’,‘普加搜访’,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搜幽剔隐,无远勿届,便略同拿破仑之内务部矣。”④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3-1554页。钱钟书指出李谔上书的本质是以文字狱的手段来控制文学,应当是抓住了要害。“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是否越俎代庖,最好在隋代的历史语境中去了解。李谔上书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从中可以管窥隋朝立国之初政治与文学之间以及南北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可作为这一过渡王朝的文化标本。因此,本文尝试回到历史之中,结合李谔的生平,从职官制度、历史地理、文学观念三个视角解读《上书正文体》,探索其思想主题,揭示其在南北融合时期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一、“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
据《隋书·李谔传》,李谔族出赵郡李氏,曾仕齐为中书舍人(六品);北齐灭亡后入周,拜天官都上士(正三命,相当于七品);隋文帝即位,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皆六品),赐爵南和伯,迁治书侍御史(从五品),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三品至四品),后三岁卒官。在其仕宦经历中,治书侍御史是最为重要的官职。从品阶来看,这一官职并不高,对李谔而言属于正常升迁,但由于其纠弹百官的权力,事实上成了李谔一生最受荣宠的职位。这一职位的获得,与杨坚的恩遇不无关系。本传言李谔入周后,“见高祖有奇表,深自结纳。及高祖为丞相,甚见亲待”,又言其迁治书侍御史后,隋文帝谓群臣曰:“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今此事业,谔之力也。”①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3页。可见作为北齐士人的李谔,亡国不久即趋附杨坚,充当了新朝佐命功臣的角色。按北周采用《周礼》六官制度,大司马为夏官府首领,总掌军政,周宣帝即位,杨坚以后父为大司马;大冢宰为天官府首领,“所属除御正纳言以外,不出禁卫掖庭饮食衣服诸掌”②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页。,但宇文护以五府总于天官,使其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掌权者,杨坚以大丞相秉政,大象二年十月复自加大冢宰,亦总领五府,为其禅位作准备。李谔北周时任天官都上士,当杨坚为夏官府大司马时,苦谏其不赴外职,促成了政归杨隋的政治格局;后又直接听命于天官府大冢宰杨坚,成为佐命功臣集团的重要分子。为了犒赏李谔的佐命之功,隋文帝即位后,李谔先是任职于尚书省的比部、考功二曹,后即迁官至治书侍御史,并由皇帝直接宣布其任此要职的政治资本,主要是为了说明关陇权贵。隋文帝时期,在御史大夫、治书侍御史等御史台上层官员之中,李谔是唯一的齐人。
治书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副职。《隋书·百官志》记开皇官制云:“御史台,大夫一人,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各十二人,录事二人。”③魏徵等:《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75页。与前代相比,其设官及员额稍近于北齐而稍远于萧梁。从表面来看,主要区别一是改官职名号,如改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改殿中侍御史为殿内侍御史(二者皆因避隋文帝父讳),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二是裁撤符节署,改隶门下省,称符玺局。然而实质上最大的变化却在治书侍御史。因御史大夫名号较尊,曾为汉代三公之一,故开皇年间多由三省长官兼任,而作为副职的治书侍御史,监察职责便明显提升,“台中簿领,悉以主之”④杜佑:《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67页。,代替了南北朝时御史中丞的角色,成为御史台事实上的行政长官。隋文帝实行中央集权,为了控制百官,赋予了御史台更为独立的监察权力,譬如将掌管皇帝印玺的符节署改隶门下省,又如废止北魏以来御史台长官任命属官的制度而由吏部选用,但御史之职仍然保留了皇帝亲信的性质,“仍依旧入直禁中”⑤魏徵等:《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75页。隋炀帝大业三年废此制,同书同卷云:“开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罢其制。”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96页。,是皇帝的近侍之臣。李谔正是以佐命之臣而成为入直禁中的治书侍御史,且掌握了与南北朝时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相当的权力。当然,以二人同任其职,也见出分权以使其互相牵制的用心。至隋炀帝时期,御史大夫逐渐恢复了专任,且用南方人,如曾出仕陈朝的裴蕴,大业中期之后任御史大夫,独揽司职权,与苏威、字文述、裴矩、虞世基等并称“五贵”。作为副职的治书侍御史,其权力自然便萎缩了。李谔任职的开皇年间,正是治书侍御主执御史台政事的时期。
钱钟书认为李谔上书可谓“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欲以宪纲制裁代艺苑别裁”,①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1页。视之为政治对文学的恣意干涉,那么,李谔之议是否超越了隋代御史台的权限呢?《上书正文体》曰: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②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5页。
这节文字可注意者有三。其一,李谔希承帝旨,上书迎合隋文帝“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之诏,凸显了御史台作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性质,体现了开皇时期文化领域中皇权的加强。文中所言开皇四年诏令今已不存,《隋书·文学传序》“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③魏徵等:《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云云,即可见当时御史台响应皇帝诏命弹劾百官的情形,李谔所举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得罪即其例也。④《旧唐书》卷一〇一《薛登传》载薛登于武则天时上疏,其中曰“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新唐书·薛登传》节略其辞),前引郭绍虞书已指出其“殊为颠倒事实”。皇帝强行以政令干涉文学,御史台只是将其作为弹劾的法律依据而已,这是律、令、格、式之外的特别法。隋文帝诏涉及“公私文翰”,是在西魏宇文泰、苏绰以《大诰》之体改革文弊基础上的变本加厉。钱钟书引《史通》为证,指出宇文泰“所‘革’者限于官书、公文,非一切‘文笔’”,而隋文帝诏则是“欲继周太祖志事而光大之,由‘公’文而波及‘私’著”⑤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1页。,将专制的触须延伸至私人领域。其二,文学本不属于御史管辖,但李谔巧妙地把文化问题转换为政治问题,在“选吏举人”的选官制度下弹劾文风之绮靡。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建国初即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自辟僚佐之制,将选官权收归中央,由此,文章便成为选官的重要条件。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⑥魏徵等:《隋书》卷一《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页。是科举史上的重要事件,一般认为当时已有秀才、明经的常贡科目之分,秀才科所试虽为策文方略,考核的主要仍是文学之才而非政治见识。李谔上书时岁贡之制或已实行,他批评所选吏职“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而将“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悬为理想的选官标准。从《隋书》本传所载李谔于治书侍御史任上的奏疏来看,他最为关注文化礼俗问题,这些问题似乎不便以法治之,但李谔很善于将其纳入政治的框架之内,除欲以选官革除文弊之外,其上书导致“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⑦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页。的制度化亦是一例。诏令使李谔的奏文成为制度,对世风的批评成为约束百官的铁规,皇权加强下的御史台政务,由此具有了“整风”的性质。其三,李谔沿袭了南北朝“风闻奏事”的传统,企图以文字狱的手段整顿文风。“风闻奏事”是指御史台长官不必根据任何书面告发材料而据风闻以奏劾的制度,亦偶有尚书仆射风闻弹事者,盛于晋宋至唐开元间,其后则罕闻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考证甚详。⑧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补订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80-282页。南齐时沈约任御史中丞而上《奏弹王源》,“风闻东海王源”⑨萧统编:《文选》卷四〇沈约《奏弹王源》,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62页。云云,便是文学史上“风闻奏事”的显例。李谔言“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看似担忧打击面太大而否定了“风闻奏事”之举,但令诸司搜访文章华艳者而凭具状以弹劾,与无需证据的“风闻奏事”又有多少区别呢?综上,李谔上书虽未超越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御史台的权限,变文学问题为政治问题,通过法律手段,为隋文帝的文化集权政策铺平了道路。
二、“江左齐梁”的地理蕴涵
从职官角度,可以看到李谔上书正文体,其实质是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行为。这一问题的另一面,是李谔对地方的态度。隋朝继承了北周灭亡北齐之后的版图,又于开皇九年平陈,先后融合东西和南北,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从此走向了大一统。李谔原本为北齐士人,在周武平齐后西赴长安,继而夤缘攀附,成为一统王朝的新宠,他如何认识文化意义上的南方?如何认识帝京与北齐旧地的关系?历史地理便成为审视其人其文的另一视角。《上书正文体》曰: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①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页。
这里所谓“江左齐梁”是从历史变迁层面对文学风尚的描述,李谔所指斥者既然是隋代的文风,便说明南朝齐梁的文风积淀至隋代了。因此,有必要在抽象的南朝背后,看看南朝的因子如何呈现在杨隋这个源自北方的政权之中。
李谔的时代,齐梁早已成为抽象的文学风格,而不再为具体的王朝地域所限,它衍生出北齐、北周、陈三个支脉,又绵延至隋唐,使得政治上的南朝灭亡之后,文化上的南朝犹存。隋代文学的齐梁之风有三个源头。其一,北齐的齐梁之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强力推行汉化,东西分裂后其文化昌盛之区皆在山东,至北齐形成胡汉融合之局。北齐文人模拟南朝文风,最著名者是魏收、邢劭互相攻讦对方偷师沈约、任昉文笔的故事。侯景乱后梁朝灭亡,一批文士辗转迁流北齐,《北齐书·文苑传》载十四人,颜之推、荀仲举、萧悫等八人皆自南入北者。后主时立文林馆,颜之推与北人李德林同判文林馆事,以梁朝《华林遍略》为蓝本撰成《修文殿御览》。隋代文坛的代表文人,多半来自北齐阵营,如薛道衡、卢思道、李德林、孙万寿等,他们将融合了江左、河朔的文风带入隋朝。自齐入隋的刘善经撰《四声指归》,更是保留了大量齐梁声病遗说,成为唐前声韵病犯说的集成之作。其二,北周的齐梁之风。北周所治的关陇地区,魏晋以来迭经战乱,文化残破。西魏时宇文泰执政,苏绰作《大诰》,试图改变魏晋以来的浮华之风,藉复古确立关陇的文化正统,但在攻破江陵之后,梁朝的庾信、王褒等文士羁留长安,江南文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②魏徵等:《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苏绰矫枉过正的改革很快被淡忘,宇文泰之子明帝宇文毓、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等皆成为齐梁之风的追随者。《隋书·经籍志》所载北周人文集凡八种,明帝、赵王、滕王皆宗庾信体,宗懔、释亡名、王褒、萧撝、庾信皆自南入北者。隋文帝不喜文学,而太子杨勇令魏澹“注《庾信集》”③魏徵等:《隋书》卷五八《魏澹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16页。,晋王杨广“属文为庾信体”④魏徵等:《隋书》卷五八《柳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23页。,正是受到北周宗室推重庾信的影响。其三,陈朝的齐梁之风。陈朝继齐梁而立,然因国势艰虞,建国初一改齐梁浮靡之风,文化上尚质非乐,自武帝、文帝至宣帝朝皆然。陈后主即位后,复扇淫侈之习,日与狎客江总等游宴后庭,“雅尚文词,傍求学艺”⑤姚思廉:《陈书》卷三四《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53页。,令齐梁宫体诗沦落至放荡狎邪的地步。祯明三年,即开皇九年,陈朝为隋所灭,宗室子孙多被投边裔,文士除隐居或致仕南归者如江总、徐仪(徐陵三子)、何之元、陆德明等,被迫入关者多任职于隋朝宗王府,为学士或属官,其中隶于晋王广者尤多,如庾自直、王昚、王胄、潘徽、虞绰等,此可见隋文帝灭陈之后旧陈文人仍多在南方。
在这三者之中,李谔所谓“江左齐梁”初看似无明确的地域指涉,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他似有意针对旧齐士人而发。何以云然?自开皇间追摹齐梁文风的社会阶层而言,承自北周的主要是杨勇、杨广等杨隋诸王,作为官僚中流砥柱的军事贵族则无与焉;承自陈朝的主要是旧陈士人,他们大多任职于王府,在江南杨广府邸者尤多,至炀帝即位方进入中央政治集团(至于王室子孙,多被贬黜任边郡县令,但多在隋炀帝大业中)。二者皆关涉隋室诸王,李谔必不当议及,且其针锋所对,主要是“未行风教”的地方“县令、刺史”,而这些人当时大多出自北齐。与二者相较,将齐梁之风带至隋朝的北齐阵营,主要是文人士族,他们在故国灭亡后命运发生了分歧:或在周隋易代之际选择投靠新朝,如李德林、薛道衡、裴矩、郎茂、李孝贞等,李谔亦其中一员;或选择隐居不仕,然因“隋文帝忌惮英俊,不许晦迹邱园”①李百药:《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全唐文》卷一四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7页。,“寻有诏,素望旧资,命州郡勒送”②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40页。,被迫出仕新朝,其中任地方刺史者尤多。北齐阵营入隋后的分裂,使得李谔上书无形中具有了朋党之争的意味,旧齐士人之间的拒斥,和其与北周、陈朝士人的矛盾相比,表现出更为直接的利害冲突。据曹道衡、沈玉成考证,李谔上书当在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③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卷五《李谔卒年及请正文体时间之推测》,《曹道衡文集》卷九,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809页。时间上正与隋初控御旧齐文士相合。近年有学者提出李谔上书“契合了隋初统治阶层的文化态度和对山东等地区进行文化打压的政治意图”正是充分考虑到了当时关陇与山东统一未久的历史形势。④胡政:《李谔〈上书正文体〉的再认识》,《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李谔对“江左齐梁”的批评,主要针对地方州县的刺史和县令,说明他特别强调对“外州远县”的文化控制,这与隋文帝的地方政策有关,亦反映出李谔对这一政策的积极迎合。上书中提到的因文表华艳而得罪的司马幼之,在周武平齐后与阳休之、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人同时被征赴长安。⑤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二《阳休之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63页。开皇四年为泗州刺史,开皇中卒于眉州刺史。⑥李百药:《北齐书》卷十八《司马子如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41页。按泗州在今江苏泗阳县,南北朝时处于诸国交界之境,曾先后归属北魏、梁、东魏、陈、北周,⑦魏徵等:《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邳郡”条,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2页。正是文化冲突剧烈的“外州远县”。在地方州县之间,原本尚有郡一级地方行政机构,隋文帝开皇三年,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鉴于南北朝以来天下州郡过多,上表请“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十一月,隋文帝“遂罢天下诸郡”⑧魏徵等:《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53页。。如李谔所言,次年隋文帝即“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可见其文化政策与地方政策颇有关系。炀帝时刘炫曾对吏部尚书牛弘抱怨中央对地方选官权的侵夺,云“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⑨魏徵等:《隋书》卷七五《儒林·刘炫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21页。。李谔虽与刘炫同出北齐,但却很快认同了隋文帝的集权政治,本传载其任治书侍御史时,曾上奏云“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上黩冕旒,特为难恕。凡如此辈,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10]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6页。,建议削弱地方刺史的“勾检”即监督之权。隋文帝时期尚未像后来炀帝时期一样设置专职监察地方的谒者台和司隶台,当时对地方的监察主要依靠中央委派御史或其他官员巡察州县,观《隋书·高祖纪》可知文帝遣使巡省风俗几成定制;此外地方刺史亦有监察权,可以在朝集时将地方官的考核情况汇报给中央,李谔将刺史“上陈勾检之功”称为“上黩冕旒”,无疑是维护皇权,意欲将地方监察权收归御史台。由此可见,李谔作为隋文帝特意提拔的臣僚,积极响应了隋文帝的地方政策。
三、反文学还是文学复古
李谔提到的司马幼之事件,在文字狱的历史上,也算是一个罕例。罗宗强说:“御史台而主辖文风,实别开生面。中国封建社会文网甚多,然因辞采华丽而须绳之以法者似于此仅见。”①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页。田晓菲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作者不是因为他书写的内容遭到惩罚,而是因为书写的风格。司马幼之是文风的罪人。”②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3页。这文风,便是所谓齐梁体、宫体或徐庾体。自“风”“体”来弹射文学,只关注写作的体式和风貌,而与内容不发生必然联系,使其较一般的文字狱更为苛酷,标准亦更难以捉摸。当然,隋文帝的文化控制并非泛滥无边,而是有其特定涵义,且有其产生的历史语境。
诏令云“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以“实录”作为文学的标准,且把控制范围从公文延及私著。其一,公文方面,反对以文为笔。文笔之辨是齐梁时期的重要文学命题,或云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或云诗赋铭诔为文、章表奏议为笔,大率以为文学性的文较应用性的笔地位更高。主文和主笔者的论争,刺激了二者的融合,以文为笔渐成风尚,如《文选》所录诗赋之外的文体多属于“笔”,但却以文学性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选录标准。隋文帝反对公文渲染“翰藻”,而以“实录”为其要义,但自江左之体风靡北方之后,章表奏议而染骈俪之习者蔚然成风,即如附和隋文帝之李谔,其上书竟亦不免如此。其二,私著方面的禁令,是北周改革文弊时未曾有的,与隋文帝对民间的一系列文化管控有关。据《隋书·高祖纪》,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禁杂乐百戏”,九年十二月诏“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十三年二月,“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十三年五月,“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十四年四月诏“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宜加禁约,务存其本”。③魏徵等:《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卷二《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39页。凡此种种,强力压制了民间的文化空间,至于私家文章上禁绝“翰藻”,则更是不消说的了。其三,隋文帝所谓“实录”,不是以史学的“实录”作为文学的标准,而是在文风上黜华尚实,以“质胜文则野”取代南朝的“文胜质则史”。
对于隋文帝的文学观念,不能一味从现代立场批判其专制集权,还需具有“了解之同情”,体察其何以如此。杨氏出身武川镇军阀,所建立的隋朝虽然逐步统一天下,但却是一个基于西魏—北周的政权,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民耕战一体的组织,赋予了其强悍的武力和剧增的财富,亦使其对华而不实、绚烂与腐朽共存的南朝文化充满轻蔑,将其视为以“五教”治天下的破坏性因素。宫崎市定曾把人类的不满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即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对自己和对方产生的不满”④宫崎市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张学锋、马云超等译:《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隋文帝“不悦诗书,废除学校”⑤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4页。,他对南朝文化的抵制,宏观上是军事化政权对文明的不满,微观上即表现为反文学的倾向。
李谔对南朝文学的描述,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⑥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页。。在隋文帝时代,风云月露是风俗颓败的象征。李谔希承帝旨,从反文学的观念出发,指出了一个被“江左齐梁”遗忘已久的古典世界: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①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1545页。
现代学者往往藉此将李谔视为唐代古文家的先声。固然,所谓“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的风俗批判,根源于汉代文学传统,但其标榜周、孔的目的首先是政治的,而非文学的,这与齐梁时期主张复古的刘勰、裴子野等完全不同。刘勰《文心雕龙》针对的是晋宋以来绮靡的文风,言“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0页。,故有“原道”“征圣”“宗经”之论;裴子野《雕虫论》批评时文轻艳险放,指出其症结在于“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③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四,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873页。。二者的批评都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而李谔之论则是借助于政治行为,文学复古并非其主旨,而是其反文学的手段。纵然如此,隋唐之际对六朝绮靡文风的批评,以及中唐之后的古文运动,其根源皆可追溯至李谔上书及其前后隋文帝的文化政策。相对而言,刘勰、裴子野等源自文学自身的复古之论,实际上远不如皇帝的行政干预更为有力。譬如典重法古的裴子野,曾引起萧纲的反批评,言“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④姚思廉:《梁书》卷四九《庾肩吾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使得裴氏以质救文的努力很快湮没在更趋靡丽的宫体之中;但隋文帝则可通过“宪台执法,屡飞霜简”,最终导致“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⑤魏徵等:《隋书》卷三五《经籍志·集部小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1页。宋代叶适论之曰:“隋文一朝诏令,不为偶俪,止叙事实,不尚雕彩,直露情景。《赐高丽王汤玺书》,虽对面语不能及也,文理不足而质实有余矣。李谔之言,岂其效与欠?”⑥叶适:《习学记言序因》卷三十七《隋书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57页。
隋文帝以政令的方式对南朝文学予以打击,当时文人或被动或主动,在批评或自我批评之中,呼应了官方的文化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意见,出于颜之推和王通。《颜氏家训·文章篇》曰:“自古文人,多陷轻薄……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⑦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7-238页。《中说·事君篇》曰:“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⑧张沛:《中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9-80页。颜之推和王通对南朝文学的批评,皆从文人无行的观念出发,不关涉文学本身的内容,尤其是王通,钱钟书称其“莫非以风格词气为断,不究议论之是非”⑨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正与隋朝宪台以“风”“体”来弹射文学相仿。
这种自北朝而来的崇质轻文的倾向,入唐后渐趋缓和。唐初史臣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一面将南朝文风与其王朝兴亡混为一谈,称“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一面又能超越南北之限,理性地评价南北文风之异,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0]魏徵等:《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在不否定北朝的基础上,对于南朝的文化认同,贞观时期重新拉开了大幕。隋初对文学的禁令,并未能最终打垮南朝的传统,只是留下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烙印:李谔上书反对南朝骈俪之习,却仍不免抽黄对白;颜之推云“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1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4页。,在认为学士方可明哲保身的背后,却蕴涵着文人高于学士之意;刘知幾云“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12]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而其《史通》却以骈文掎摭史籍。文学,被政治压抑的声音,它从未真正消逝,在文质之间的博弈之后,逐渐走上了“文质斌斌,尽善尽美”[13]魏徵等:《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的道路。
四、余论
千载之后的异邦,有一位好文的君主,朝鲜正祖李祘,这样评价隋文帝和李谔:“隋文,胥吏也,所好所能,在于簿书期会,遂以文词为不可用而斥之欤?《三百篇》比兴,多取风云月露,未闻以此为风雅之疵。李谔之言,又何其谬欤!”①正祖:《弘斋全书》卷一一六《经史讲义》,《韩国文集丛刊》第265册,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371页。炀帝时刘炫曾指出隋文帝以文书胥吏治天下,但径斥其为胥吏者,在中国文献中却是没有的。与南北朝时期相比,隋朝确实强化了文书治国的倾向,这是中央集权的结果。由于“大小之官,悉由吏部”②魏徵等:《隋书》卷七五《儒林·刘炫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21页。,地方直接听命于中央,文书往来便成为帝国运作的基本形态,文书的风格亦由此成为政治问题。
李谔《上书正文体》这面镜子,折射出隋文帝时代诸相:职官方面,将南北士族纳入新的皇权秩序,强化了宪司对百官的监察;地理方面,通过废郡加大了中央对地方尤其是文化昌盛之区的控制,外州远县成为重点;文学方面,对南方化的文学整体持否定态度,黜华尚实成为时代的文化精神。隋是北朝的终结,由于北朝对汉代政治和文化的继承性,三者共同表现出向汉代回归的倾向。然而,由于文化包容性的缺乏,隋初以北朝的文化身份,来强力打压南朝文化,对于这个新的统一王朝而言,显然会带来新的分裂。后来炀帝重振南方文化精神,绮靡之风又起,但由于反其父之道而行,二朝文化政策缺乏相容性,文质矛盾的最终解决,还要留待新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