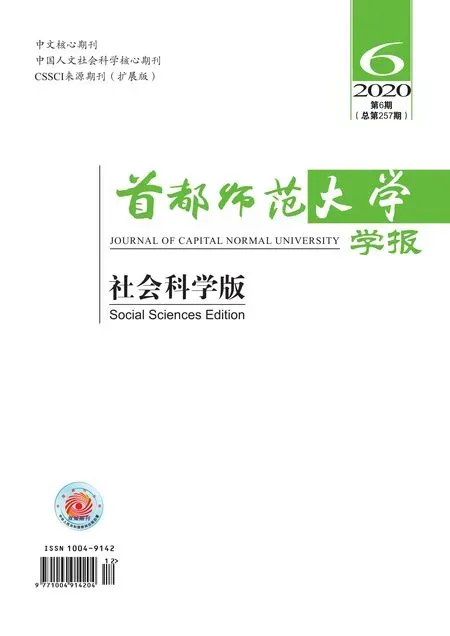从两篇近文检视近代早期天主教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全球转向
付 亮
201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两种历史学综合性论著:《牛津宗教改革插图史》(以下简称《插图史》)与《牛津近代早期欧洲史(1350—1750年)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前一种由英国宗教改革史名家马歇尔(Peter Marshall)主编。该书汇聚七位重要学者的文章,旨在提供新的宗教改革史解读,同时为2017年宗教改革爆发500周年纪念预热。①Peter Marshall,ed.,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后一种则由英国近代早期国际关系史学者斯科特(Hamish Scott)主编,54位学者参与撰写,意在体现过往40年国际学界书写近代早期欧洲史的方法与取径。②Hamish Scott,ed.,The Oxford Handbook ofEarly Modern European History,1350-1750(Vol.1“Peoples&Place”;Vol.2“Cultures&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由于专业缘故,两种著述中各有一篇文章引起笔者关注。英国约克大学迪奇菲尔德教授(Simon Ditchfield)为《插图史》撰写了《天主教改革与复兴》一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特普斯特拉(Nicholas Terpstra)则为《手册》奉献了《近代早期天主教》这篇文章。①Simon Ditchfield,“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 in Peter Marshall,ed.,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152-185;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in Hamish Scott,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History,1350-1750(Vol.1 Peoples&Pla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601-625.两篇近文处理的是同一主题——“长16世纪”的天主教(the long sixteenth-century Catholicism)②“长16世纪”这一概念乃是受法国年鉴学派之影响,强调16世纪的欧洲历史前推至15世纪,后延至17世纪甚至18世纪,以体现历史之连续性。目前,“长16世纪”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相接榫,不光包含欧洲历史,而且涵盖非欧洲地区的历史。。两文皆充分吸收、消化乃至批判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同时提出自己的书写模式,以求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块垫脚石。两文既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的考量所在,但都体现了目下近代早期天主教史书写模式的微妙转换,亦即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与全球转向(global turn)渐成风气。③近年,国际学界对近代早期基督宗教的新文化史转向已做出初步的总结和评述,参见Alexandra Bam ji,Geert H.Janssen and Mary Laven,eds.,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Surrey:Ashgate,2013;Ulinka Rublack,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此一转换颇能说明国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斩获,也可从中看出未来研究走向之端倪。因此,本文拟先梳理两篇文章所依托的学术系谱,然后将两篇近文置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之中加以分析,并就该研究领域的未来走势略作展望。
一、天主教史学系谱中的三种重要范式
(一)耶丁与“天主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范式
20世纪40年代是近代天主教史研究的一个转捩点。德国教会史巨擘耶丁(Hubert Jedin)于1946年发表《天主教改革还是反宗教改革?》一文④Hubert Jedin,KATHOLISCHE REFORMATION ODER GEGENREFORMATION?Ein Versuch zur Klärung der Begriffe nebst einer Jubiläumsbetrachtungüber das Trienter Konzil,Luzern:Verlag Josef Stocker,1946,pp.5-38.,于1949年又推出四卷本《特兰托大公会议史》的首卷,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界思考近代欧洲天主教复兴的方式。⑤耶丁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史》(Geschichte des Konzils von Trient)凡四卷五本,及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出齐,影响甚巨,是天主教改革史研究的必读书。目前,英译本只有前两卷问世,法文本只出了第一卷。由于耶丁对意大利天主教史研究影响甚大,且与意大利学者交往甚密,故坊间乃有完整的四卷意大利文译本。
在此之前,“反宗教改革”(Gegenreformation)、“天主教改革”(Katholische Reformation)这类历史概念虽然早已存在,但由于教派论争把控主流的叙述模式,故而为意识形态所左右。譬如,新教史家就坚称天主教的种种行为是对新教运动的反动,与真正的改革毫无关联,唯有马丁·路德掀起的福音运动才是基督宗教发展进程中的“拨乱反正”,也只有新教改革才接榫了古代教会的优良传统。⑥奥马利曾对受教派论争影响的天主教史研究做出精辟分析,参见John W.O’Malley,Trent and All That: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6-45.这种“穿千里靴跨越千年黑暗中世纪”的历史描述,更是被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定型。是故,“黑格尔的幽灵”(Hegel’s Ghost)始终盘旋在以兰克为代表的普鲁士新教史学的头顶。⑦关于黑格尔学说对宗教改革史研究的“后设影响”,已有学者做出精深分析,参见Constantin Fasolt,“Hegel’ s Ghost:Europe,the Reformation and the Middlge Ages,”Viator,39(2008),pp.345-386.在兰克看来,宗教改革是独一无二的“日耳曼事件”,传播理性价值观,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种表述实则体现了兰克等德国新教史家镇日期盼日耳曼民族复兴之深刻情结。⑧Luise Schorn-Schütte,DIE REFORMATION:Vorgeschichte-Verlauf-Wirkung,München:C.H.Beck,1996,pp.94-97.无独有偶,19世纪中期以来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亦催生出自己的自由主义史学。这一史学进路以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为代表,哀叹罗马教廷不仅在16世纪阻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进步历程,而且让亚平宁半岛迟迟无法统一。故而,天主教会是意大利在近代落后于英法诸国的罪魁祸首。①Benedetto Croce,“A Working Hypothesis:The Crisis of Italy in the Cinquecento and the Bond Between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isorgimento”,in Eric Cochrane,ed.,The Late Italian Renaissance,1525-1630,Glasgow:Macmillan,1970,pp.23-4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自由主义史学坚称天主教自近代以降只有“反宗教改革”的反动做法,阻碍历史进步,不具有“近代性”。
天主教学者出于护教的需要,则避开有关“反宗教改革”的内容,大半只强调天主教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活跃的敬虔活动,着重教会历史的连续性。在他们看来,宗教改革并不是延续罗马公教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骇人的断裂和革命。非黑即白可谓斯时基督宗教改革史写作的底色。
耶丁在20世纪40年代的论说,实则是当时第一篇系统超越二元对立论而提出新见解的经典之作。他对“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这两个范畴做了详细的系谱梳理,还对它们重新提炼,予以有机融合,最终提出“天主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之说。因而,解决了重要的理论问题,从而成就了“耶丁范式”。耶丁强调天主教改革早已存在,起源于15世纪勃兴的基层改革,推动者是基层的神职人员、宗教修会、宗教社团以及平信徒等。不过由于缺少教宗的领导,故只是各自发展的涓涓溪流,而无法汇聚成强大的改革洪流。②Hubert Jedin,KATHOLISCHE REFORMATION ODER GEGENREFORMATION?pp.26-27.唯有等到特兰托大公会议(Konzil von Trient,1545—1563)的召开,在耶稣会的辅助下,基层改革终于在教宗强权的引领下形成合力。天主教改革从此进入“特兰托时代”(the Tridentine Age)。③所谓“特兰托时代”,乃从耶丁的解释而来。他强调特兰托大公会议是16世纪天主教历史的最重要事件,认为天主教改革是通过这一会议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而且,他认为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是天主教历史上的“特兰托时代”,彼时的天主教发展为“由特兰托大公会议的改革理念所形塑的天主教”(Tridentine Catholicism)。耶丁对于“反宗教改革”的理解也与前人有异,他不赞成过度强调天主教会使用暴力。他坚信“反宗教改革”与“天主教改革”之间是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天主教会通过自身的改革汲取发展动力,从而间接增强了自身的防御力量,这才是“反宗教改革”的前提。质言之,“反宗教改革”是教会的自我防御,源自其发展的内驱力。值得注意的是,教宗制度、特兰托大公会议与耶稣会是“耶丁范式”的中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此范式逐渐为学界所汲纳,乃一度成为主流书写模式。故此,美国教会史学者奥马利(John W.O’Malley)把耶丁放置在16世纪天主教史学史的“经典位置”之上。④奥马利的《特兰托及其他:重新命名近代早期时代的天主教》,专门用一章的内容分析耶丁史学,此章的标题即是“胡贝特·耶丁与经典位置”。 参见John W.O’Malley,Trentand All That: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p.46.
耶丁之所以能够发凡起例,在20世纪上半期改写近代天主教复兴史之范式,乃得益于两个因素。其一,也是最重要的,是罗马教廷逐渐开放了一批关涉16世纪教会改革的重要档案。这是曾在17世纪写作名著《特兰托会议史》的威尼斯圣仆会僧侣萨尔皮(Paolo Sarpi)所无法想象的。其二,是耶丁在“二战”期间幸运地逃脱了德国纳粹的迫害,长居罗马。其间,他坐拥“书城”,爬梳前人未见之史料,为开创新局奠定了基础。
如今,借由“后见之明”可看出,耶丁虽然清晰地定义了天主教会在近代的改革行为,却没能进一步挖掘新教的冲击给天主教改革带来的具体影响。易言之,天主教改革与新教改革之间的互动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抑有进者,“教宗制度-特兰托大公会议-耶稣会”的所谓“天主教改革三动力”书写模式,既夸大了教宗的力量,也神话了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历史作用,从而一方面让“特兰托时代”之说深入学界,另一方面又客观上为“特兰托主义”(Tridentinism)的出现提供了学理。①所谓“特兰托主义”,是指罗马教廷自16世纪晚期以来有意识地垄断对特兰托大公会议的解释权,并将其一步步神话化,以强化中央集权体制,并遏制地方主教的分权做法。为应对世俗权威与社会新思潮的挑战,罗马教廷阻击、打压乃至禁止曾一度活跃的多元神学与教会学省思,而假借特兰托之名的僵化封闭的神学观与教会观乃成为天主教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特兰托主义”的细腻分析,可参见Giuseppe Alberigo,“From the Council of Trent to‘Tridentinism’,”in Ratmond F.Bulman and Frederick J.Parrella,eds.,From Trent to Vatican II: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19-37.此外,耶丁的研究仍是“教会史”(church history)的模式,只关注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典章制度,而非当今以平信徒为探讨中心的“宗教史”(religious history)取径。这是因为耶丁始终遵循德国教会史学的传统,把“教会史”视作神学的一个科目。因此,耶丁只看到了教会精英人物之“静态的”改革,而看不见“动态的”改革,亦即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学识、不同性别等多重力量围绕教会改革所展开的多网络、多维度互动。不止如此,耶丁的洞见即是其不见之处,这是因为他只看到天主教会在近代以来的改革行为,而忽视了其他内容。毕竟改革并非天主教会的唯一内容。也正因为如此,耶丁即便自认为合理地解决了问题,实则非但没有终结议题的争论,反而激发了新的讨论。
(二)普罗迪与“社会规训”范式
对“耶丁范式”做出系统性挑战的恰恰是耶丁的学生普罗迪(Paolo Prodi)。耶丁在“二战”期间躲身于罗马,为撰写《特兰托大公会议史》皓首穷经、爬梳史料,其间与意大利天主教学人多有往来,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普罗迪即是他欣赏和栽培的后起之秀。
普罗迪早岁以一部细致周详的博洛尼亚大主教帕莱奥蒂(Gabriele Paleotti)的传记成名,但研究路数并未超越乃师,仍是遵从传统的改革史取径。②Paolo Prodi,Il cardinale Gabriele Paleotti (1522-1597),2 vols,Roma: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1959-1967.20世纪80年代初,耶丁去世,普罗迪开始陆续提出酝酿已久的看法。他首先就近代教宗制度的演变提出新论,于1982年推出迄今仍颇具影响力的典范之作——《教宗君主(一体两魂:近代早期的教宗君主制)》(以下简称《教宗君主》),此书的核心观点逐渐成为当下学界公认的“普罗迪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也是普氏充分汲取近代化理论的第一部作品。因为,普氏不仅旨在修正耶丁学说,而且意在挑战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力推的微观史进路。他认为微观史是“无时间的历史”,并不能有效地揭示意大利教会与社会在近代的演变。
前文已指出,“耶丁范式”以教宗制度、特兰托大公会议与耶稣会作为天主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枢轴,而且将教宗制度作为串联和引领特兰托大公会议与耶稣会的中枢。耶丁认为特兰托大公会议之后、17世纪中期之前的几位教宗将精力集中在改革,教宗制度与罗马教廷终于从“文艺复兴教宗”(Renaissance Popes)的世俗化境地中脱身,经历革新,从而走向正轨。这种“乐观”的看法遭到了普罗迪的质疑。在《教宗君主》一书中,普氏认为,近代的教宗制度与其说是中世纪普世主义的遗留物,毋宁说是彼时欧洲在追求近代官僚科层国家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力。16世纪晚期陆续建立的审判机构和教廷部门绝不是“特兰托改革精神”可以涵盖的,实则反映了罗马教廷的中央集权趋势。而且,此种趋势与欧洲同时期其他世俗政权的大变革是合拍的。无论是世俗君主,抑或是教宗君主,都汲汲于强化自身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主教徒由中古的亲族式的集体主义走向近代个体主义,不仅是作为罗马教会的信徒,而且也逐渐被形塑为其臣民。是故,彼时的教宗制度便具有明显的近代特点。③《教宗君主》一书出版于1982年,亦即耶丁去世的两年后。此书对英美史学界影响很大,1987年乃有英文版问世,此后“普罗迪范式”益发为国际学界所重视。本文参照的是此书的2006年修订版。Paolo Prodi,Il sovrano pontefice,Un corpo e due anime:la monarchia papale nella prima etàmoderna(Nuova edizione),Bologna:Il Mulino,2006.
在《教宗君主》一书中可发现,曾经被耶丁肯定的“伟大的特兰托改革家”教宗庇护五世(Pius V)并没有如此在意改革,而是每每在教宗利益与教会改革出现冲突时果断选择前者,甚至在世俗力量的逼迫下,不惜打压基层的改革实干派,例如米兰大主教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①关于博罗梅奥在米兰大主教区的社会规训行为,普罗迪写过一篇经典文章。Paolo Prodi,“Riforma interiore e disciplinamento sociale in san Carlo Borromeo,”Intersezioni,V,2(1985),pp.273-285.与博洛尼亚大主教帕莱奥蒂。不止如此,经由此书,还可发现横行于罗马教廷的裙带关系、圣职买卖以及围绕圣俸和恩俸的多种经济问题,并非像耶丁所说的那样趋于减缓,而是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依旧大行其道。可见,普罗迪实际上有力地击中了“耶丁范式”的核心所在。
如果说《教宗君主》一书尚只是普罗迪小试牛刀的话,那么将德国的“社会规训”范式引入意大利宗教史学界以代替“耶丁范式”,可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全力开拓的事业。20世纪80年代,普罗迪接手位于特兰托的意大利-日耳曼研究所(Istituto Storico Italo-Germanico)。他坚信耶丁(研究所的开创人)的学说已然过时,学界需要新的研究视角来探析意大利天主教的近代性问题。他多次举办“近代早期时代的社会规训”研讨班,邀请新一代德国学者如莱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就“社会规训”范式和“教派化”命题(Confessionalization)②“教派化”命题创设于德国学界,受近代化理论与近代早期国家建构之学说影响甚深。Wolfgang Reinhard,“Reformation,Counter-Reformation,and the Early Modern State:A Ressessment,”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75(1989),pp.383-405.做主题演讲。普氏更是以《“反宗教改革”和/或“天主教改革”:用新的史学识见解决既有困境》这篇重量级论文宣告“耶丁范式”业已是无力的分析工具,主张采用新的诠释范畴。③Paolo Prodi,“Controriforma e/o Riforma cattolica:Superamento di vecchi dilemmi nei nuovi panorami storiografici,”Römische historische Mitteilungen 31(1989),pp.227-237.
帮助普罗迪推广“社会规训”范式的莱因哈德深受近代化理论的影响。他质疑以黑格尔学说为底色的“新教沙文主义”的预设观点,即“寒冷北方”的宗教改革是催生近代世界出现的唯一力量。他认为“炎热南方”的经历革新的天主教同样参与了近代世界的建构,拥有和新教诸宗派相似的“近代性”,毕竟两方阵营都自16世纪中期起着重以纪律和教化作为国家形塑自身教派身份认同的基础。普罗迪对此深以为然。普氏认为“社会规训”范式既能够为近代化理论提供一个长时段框架,又可以将政治史、制度史与社会史整合一处,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省视近代意大利历史中有关大众群体与宗教嬗变的发展脉络。在他看来,这是微观史所无法做到的。
普罗迪意在揭示:彼时的意大利社会经由世俗政权和教会威权的结合而被规训为近代社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改革被拉下“神坛”,不再具有近代性的独尊地位,而是与革新后的天主教成为塑造近代欧洲社会的多元力量。普罗迪在意的“社会规训”范式也的确激发了新的研究旨趣:无论是有关神职人员的戒律规范、女性行为操守与得体衣着,还是童蒙教育、婚姻生活与家庭生活,抑或是戏剧表演的规范与社会意义等,都成为考量欧洲近代化路径的切入点。④Paolo Prodi,Disciplina dell’anima,disciplina del corpo e disciplina della societàtra medioevo ed etàmoderna,Bologna:Il Mulino,1994.不止如此,在“社会规训”范式的引导下,再加之档案材料的陆续开放,主教区审判与宗教裁判所等旧题亦取得突破。譬如,主教或宗教裁判官如何在近代重建司法审判机制、如何组织近代权力机构,遂成为史家的关注所在。史家欲借此检视物质利益与属灵利益是如何在近代社会实现接榫并与所处环境交互影响的。⑤例如,Cecilia Nubola,Conoscere per governare:La diocesi di Trento nella visita patorale di Ludovico Madruzzo(1579-1581),Bologna:Il Mulino,1993;Adriano Prosperi,Tribunali della coscienza:Inquisitori,confessori,mossionari,Torino:Einaudi,1996.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普罗迪在去世前提出了“特兰托范式”(Il paradigma tridentino)一说,指出罗马天主教会的特兰托改革与新教运动都是面对近代性挑战所做出的历史回应。①“特兰托范式”可谓普罗迪几十年学术生涯的总结,近年来引发学界很多思考。Paolo Prodi,Il paradigma tridentino:Un’epoca della storia della Chiesa,Brescia:Editrice Morcelliana,2010.普罗迪于2016年12月去世。此后不久,美国的《天主教历史评论》旋即翻译刊登了普氏在2016年10月提交给“全球史语境中的新教之宗教改革:宗教诸改革与世界诸文明”会议的一篇论文。此文亦能体现普氏对近代基督宗教演变的宏观思考。Paolo Prodi,“Europe in the Age of Reformations:The Modern State and Confessionalization,”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Vol.103,Winter,2017,pp.1-19.
如果耶丁初步做到了让学界重估近代天主教革新运动,普罗迪则超越“教会史”的狭隘畛域,以基于福柯理论的近代化阐释框架从近代性的角度再度重新审视天主教复兴运动。无论是教宗制度,还是特兰托大公会议的改革精神,都被濡染了近代色彩。这是耶丁在世时无法预料的。
(三)奥马利与“近代早期天主教”范式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还,“盎格鲁-美利坚史家”(Anglo-American historians)极力推动近代早期欧洲史(early modern European history)的研究理念,大西洋两岸的英美两国允称代表。②有关近代早期欧洲史的沿革与发展,可参见付亮:《在“全球的近代早期”视野中重写转折时期的欧洲史——评〈牛津近代早期欧洲史(1350—1750年)手册〉》,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十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5-209页。尤有进者,“近代早期”也被移植到传统的16世纪基督教史的研究领域,而为20世纪80年代受近代化理论冲击而出现的“长16世纪”天主教复兴的诠释框架埋下了伏笔。奥马利即是“盎格鲁-美利坚史家”的一位代表。
奥马利早年曾有机会在波恩大学从耶丁游,但因为学术旨趣不同,最终选择宗教文化史的取径而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奥氏对“耶丁范式”与“普罗迪范式”都非常熟稔,但他认为两者只能揭示近代天主教演变过程中的部分内容,有明显缺陷。而奥马利的解决之道便是提出了“近代早期天主教”(early modern Catholicism)这一范式。③有关奥马利史学之特点,可参见付亮:《“现代早期天主教”范式的建构及其价值——论约翰·奥马利的教会史研究》,《史林》2013年第3期。
就耶丁的“天主教改革”来说,奥马利认为改革无疑是存在的,但需要做出精准的定义。倘若将“改革”视作教会戒律与牧灵职责的恢复,则博罗梅奥当然是改革家。但以依纳爵(Ignaitus of Loyola)为首的早期耶稣会士以及其他修道人士就难以用“改革家”来界定,因为他们有各自适应时代特点的属灵追求。换言之,“改革”并不等同于高标准的宗教修为与信仰使命。
就“社会规训”范式而言,其间接导致一个迷思:特兰托大公会议一方面以打击新教徒为纯粹之目的,另一方面汲汲于让天主教徒在行为和思维上整齐划一。在奥马利看来,与会的主教和神学家即便对路德及其追随者充满愤怒,但他们实则在会议的讨论上尽可能做到公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梦想恢复基督教世界,其想法虽然是一个乌托邦,但毕竟是出于与新教徒和解的目的。另外,根据奥马利的研究,会议结束后,虽然天主教势力诸如西班牙、威尼斯共和国以及教宗国,其宗教裁判所相较以前在对平信徒和教职人士的监督与规训方面更加严厉,但是,这一现象充其量只是会议的间接结果,会议本身对此并没有一贯之目的。与会主教并没有直接改造平信徒的想法,而是把改革自身作为主要目标。也就是说,他们想要主教履行自己的职责——布道、教育教职人士,尤其是履行居于辖区的职责。④对于“特兰托迷思”,奥马利的《特兰托大公会议简史》做出了精到而有力的分析和批判。John W.O’Malley,Trent:What Happened at the Council,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在奥马利看来,“社会规训”范式固然精致,在解释天主教会的某些历史方面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其一方面夸大了特兰托大公会议的作为,另一方面遗漏了重要的历史内容,譬如时人微妙的信仰动机。⑤John W.O’Malley,Trent and All That: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p.139.
随着宗教史取代教会史以及宗教史与近代早期世界史(early modern world history)相接榫,不仅男女平信徒与大众信仰在天主教复兴运动中的历史价值被开掘和重估,天主教会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历史活动以及“新世界”(the New World)与“旧世界”(the Old World)之间的多维度、多网络的互动益发受到重视。而这些内容正是“耶丁范式”和“社会规训”范式的“不见”之处。正由于坚信“长16世纪”的天主教是近代早期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奥马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近代早期天主教”这一诠释范式,初步引入全球视角,反对西方中心论,既强调天主教历史的复杂之处与多元性,亦强调非欧洲地区的原发近代性。①参见John W.O’ Malley,ed.,Catholicism in Early Modern History:A Guide to Research, St.Louis:Center for Reformation Research,1988.
如果说普罗迪将宗教史与近代化理论加以融合,继耶丁之后有力推动了“长16世纪”的天主教研究之深入,那么奥马利内在地强调天主教在近代化道路上的重要角色的同时,则指出了普罗迪天主教近代化学说的不足之处,有力地打击了“特兰托迷思”,并号召学界将天主教史研究放置在近代早期世界史的框架中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而且,奥氏学说颇契合发展迅猛的“文化转向”与“全球转向”,为后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迄当下,就范式而言,奥氏的“近代早期天主教”已成为主流。下文要论及的两篇近文可称代表。
二、“动态的”近代早期天主教与全球史视野中作为“动词”的天主教复兴
(一)特普斯特拉的“动态的”近代早期天主教
《近代早期天主教》一文的作者是加拿大史家特普斯特拉,他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意大利宗教社团史研究的专家,在这一领域建树卓然。晚近特普斯特拉又将研究取向转向宗教改革爆发后的难民与流亡史,并力图从全球和互动的角度呈现这幅历史图景,展现另一种宗教改革史。②Nicholas Terpstra,Religious Refuge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也正基于此,《近代早期天主教》这篇文章内在认同且采纳了奥马利的诠释范式。
实际上,耶丁时代的教会史研究着重对精英人物、教职人士和典章制度的分析,特重对教义信条的解读,并不关注普通人的“活生生的”信仰(religion vécu)。即便有之,也主要是从神职人员的角度出发。随着法国年鉴学派的勃兴,受社会学影响的宗教史逐渐取代教会史。尤有进者,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重要理论愈发为历史学家所重视和汲纳,由此大众宗教以及多维度、多网络的信仰互动过程渐而成为关注的焦点,由此出现了许多前人无法想象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这20年,新文化史和全球史对学界冲击甚巨,同样刺激天主教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特普斯特拉的《近代早期天主教》一文就巧妙地精炼了过往的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奥马利的解释范式,提出了对近代早期天主教的精到看法。
特普斯特拉将近代早期界定在15至18世纪,亦即教会分裂结束、教宗回归罗马以迄法国大革命爆发。他认为,这期间所有经过长期累积而最终发生变化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力量皆形塑了天主教。③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602.传统的天主教史研究往往把建制教会的腐败堕落作为天主教出现改革和复兴的背景,甚至持所谓的“天主教信仰衰落”说。晚近研究在“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的影响下,一方面持不同看法,倾向于将教职人士的腐败作为结构性问题来做持平的处理,并不做简单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则转换视角,更关注社会变迁给天主教会带来的剧烈冲击以及天主教会自身对社会演变的强大适应能力。职是之故,五种感官(触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物质文化、神圣空间以及用于强化敬虔的情感策略等内容,遂成为显学,可谓当下探究天主教徒如何在信仰分裂时代和大航海时代践行“活生生的”信仰生活的全新研究视角。学者们由此深挖天主教徒如何参与塑造所处的世界以及如何被外在世界所形塑。伴随海外传教的发展,天主教信仰在全球流布。其间它与当地文化和权威展开多维度的碰撞与互动,并出现变形和新的本地特质。这也逐渐成为学者重新审视天主教复兴运动的切入点。可以说,学者们不再狭隘地、静态地看待天主教会,而是将之细腻地视作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动态的宗教世界、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一类人群。特氏的《近代早期天主教》一文就立足于目下的学术发展脉络。
该文提出:欧洲在全球范围内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接触、碰撞、互动,从根本上塑造了近代早期时代,这也同样重塑了天主教会。天主教会正是沿着早期近代性的三大运动轨迹进行演变的。这三大运动轨迹(亦可称为三组动力源)分别是:1.从流动到固定;2.从地方到普世;3.从行动到企图。在特普斯特拉看来,倘若某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天主教徒穿越时空,来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欧洲,此人或许仍旧认得出外在的教会、教堂与教士,却无法理解那时天主教会运转的内在机理。因为300年间,天主教会一方面要面对新教诸宗派的挑战,另一方面要在全球范围内应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习俗与信仰,以求自保和发展。恰恰在应对各种挑战的过程中,它在制度上重塑了自身,在文化上重新定义了自己。①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p.601-602.
何谓“从流动到固定”?特普斯特拉指出,“流动”是中世纪的特点,而“固定”乃是近代早期开始出现的特质。其实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都没有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京城”(capital city),因为当时尚没有一个王权拥有对政府和权威的清晰的中央概念。在17世纪之前,恰恰是罗马发展成为欧洲第一个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首都。特普斯特拉充分吸收了晚近意大利学者对罗马城和教宗制度的研究成果。②例如:Antonio Menniti Ippolito,Il Governo dei papinell’ etàmoderna:Carriere,Gerarchie,Organizzazione cuirale,Roma:Viella,2007;Antonio Menniti Ippolito,Il tramonto della Curia nepotista:Papi,nipoti e burocrazia curiale tra XVI e XVII secolo,Roma:Viella,2008.他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罗马并不是天主教信仰的绝对属灵中心。即便是在“阿维农之囚”以前,教宗也经常不驻辖在罗马。正是在教会分裂结束后,人文主义教宗尼古拉斯五世(Nicholas V)率先有意识地按照古典和帝国模式将罗马打造为一个新属灵帝国(a new spiritual empire)的京城。自1450年至1650年,新的道路和桥梁在罗马城修建,贵族和枢机的官邸陆续建立,各宗教修会的教堂更是纷纷涌现。圣彼得大教堂彰显的恢弘气势,更是展现了古典和帝国模式的成功。17世纪以后,欧洲的主要王权都在努力营建宫殿,各君主皆自然选择居于京城。像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这类教宗将自身塑造为“帝王式的司祭”(imperial priests),而世俗君王如腓力二世、詹姆士一世等则把自己打造为“司祭式的国王”(priestly kings)。可以说,一套针对欧洲绝对主义王权的权力语言和权力仪式逐渐成形,并为欧洲各君主和罗马教宗所用。近代早期欧洲开始出现权力和信仰“教派化”的局面。18世纪之前,欧洲各强权以固定的、中央化的首都为基础,借助权力与信仰的结合来实现征服、控制以及统治。就罗马天主教会而言,天主教的绝对主义(Catholic absolutism)成功地将天主教信仰与国家的目标相结合。其做法较诸新教的国家教会(state churches)只有程度和细节上的差别,并无本质的不同。③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608.
就天主教的绝对主义而言,正如《近代早期天主教》一文所强调的,除了罗马教宗之外,上至廷臣枢机、教区主教,下至堂区神父和宗教修会,都是天主教会“从流动到固定”的驱动力。晚近,学界对枢机和主教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对欧洲绝对主义王权也进行了重估,特普斯特拉对此做出了精到的归纳。①譬如:Mario Rosa,La Curia romana nell’etàmoderna:Istituzioni,cultura,carriere,Roma:Viella,2013.他指出,学界已经意识到以往对欧洲绝对主义王权的理解夸大了历史事实,实则彼时的王权远没有后世学者所认为的那般绝对化、中央集权化以及威权化。故此,要准确地理解天主教的绝对主义,就不能只停留在罗马教宗及其权力,还要关照枢机、主教、神父以及各修会。譬如,就枢机而言,近代早期的枢机已不再是教廷的议事元老,而逐渐被改造为廷臣贵族。就主教来说,及至16世纪中期,主教本人愈来愈难以掌握多份圣俸,也愈发难以在罗马教廷或其他宫廷参与权力运作,而不得不居于自己的辖区来开展牧灵工作。固定于教区的主教反倒能发展主教座堂,建立神学院、医院,培养和监督神职人员。这就为近代早期天主教的信仰职业化奠定了基石。对于本堂神父而言,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文化期许更是不同于中世纪。在中古时代,一个目不识丁的神父只是粗糙地模仿前辈来操作礼拜仪式,而在私下里则保有配偶、种地过活,与堂区内的平信徒几无差别。到了近代早期,神父则要坚守独身,接受良好的教育,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在社会身份层面,都要优于自己的信众。唯有这样,方能有更大的社会威信。故而,对神父的社会期许也就更高。诚如特普斯特拉所指出的,主教也好,神父也罢,他们固定于自己的辖区,在地方生活和属灵生活方面产生的“外溢效果”(the spill-over effects)是显著的,对近代早期天主教敬虔的职业化至关重要。②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p.608-609.
不止如此,近代早期的敬虔祈祷也出现“从流动到固定”的现象,譬如“40小时敬虔”(the Forty-Hour devotion)。特普斯特拉指出,在15世纪,群体性的基督圣体巡游乃是当时重要的敬虔活动,以庆祝基督的临在。相关队伍会在城市的固定路线巡游庆祝,市政官员、神职人员、行会成员、宗教社团等都会参与进来。到了近代早期,这种流动的敬虔活动虽然仍被保留,但带有固定色彩的新的敬虔活动——“40小时敬虔”也随之出现,更加重要。基督圣体被供奉在教堂祭台上的圣体匣内,宗教社团的成员要轮流在基督圣体前持续祈祷40小时。面对新教神学家对天主教弥撒礼和基督临在说的攻讦,天主教会旨在利用“40小时敬虔”来强化集体的公共敬虔意识。③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610.易言之,基督与信徒之间的关系随着“从流动到固定”而得以在神圣空间产生新的动力。
何谓“从地方到普世”?在特普斯特拉看来,“地方”是中世纪的标志,而“普世”则是自近代早期开始出现的特征。曾经的“新教沙文主义”对15世纪评价甚低,认为这是混乱、腐化、衰败而必然要被宗教改革时代所取代的历史时段。晚近的研究业已不受这种观点影响,而寻求以更为持平的方式来解读之。换言之,唯有更准确地理解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会,才能更准确地评估近代早期的天主教之演变。譬如,如何在15世纪做一名天主教徒就是当下更为流行的课题。特普斯特拉指出,15世纪的天主教会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这在礼拜仪式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例如,米兰尊奉安布罗斯礼仪,英格兰采取塞勒姆礼仪,爱尔兰则秉承希伯尼安礼仪。此外,弥撒礼也好,圣徒崇拜也罢,甚至宗教节日,都有浓重的地方色彩,深深植根于地方的社会风俗脉络。易言之,地方的天主教信仰活动乃以亲属关系或邻里的属灵关系为集体信仰的根基。以血亲关系或属灵关系为依托的兄弟会、姊妹会非常活跃,是践行彼时天主教地方信仰的动力。如果说在宗教改革爆发前,教会上层尚能包容这类地方活动,那么随着宗教革命引发的信仰分裂,罗马教廷对于教会的地方自治和平信徒敬虔活动愈发警惕,认为它们是异端、迷信甚或异教侵入教会的门径。④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611.天主教会在与新教诸宗以及其他宗教信仰的碰撞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普世教会敬虔观。天主教会在近代早期要通过对宗教活动采用标准化模式来改革和维护教会,为此甚至不惜打压地方的多元态势。是故,教廷在16世纪后半期先后颁布了《罗马教理问答》《罗马日课经》《罗马钦定本圣经》。不止如此,1542年重建的罗马宗教裁判所与1559年确定的《禁书目录》更是控制多元声音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在限制和打击地方多元天主教(local Catholicisms)的过程中,在与其他宗派和宗教对抗的过程中,天主教会在近代早期真正成为了“罗马的”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ism)。
在“从地方到普世”的过程中,特普斯特拉指出,近代早期天主教会的普世教会理念可谓一种吊诡,其是在离心力与向心力的互动中发展的。这点在天主教会的全球传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传教士要应对所处之地的社会、文化、政治诸种力量的挑战。发展起来的本土教会在教会统治层面虽与罗马有隶属关系,但在文化层面却与欧洲大相径庭。罗马在追求普世教会理念的过程中,不只要应对欧洲的本土主义,还要因应“天主教信仰的全球表达形式”(global expressions of Catholicism)。换句话说,近代早期的天主教在亚洲、非洲乃至美洲等地,皆创造了不同的礼仪形式和信仰表达方式。凡此种种,深受本土传统的影响,是遥远的罗马所无法掌控的。特普斯特拉认为,把近代早期天主教视作“多元共存的天主教”(a variety of co-existing Catholicisms),或许更为准确。①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613.
为了实现“从地方到普世”,罗马还借助社会规训的手段来明确教派身份,是以“教派主义”乃是斯时的主流现象。对此,前文提及了意大利史家普罗迪花费巨大心血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但普氏的“社会规训”范式有一个严重问题:它过多地关注自上而下的运作,而没能深入发掘社会规训的具体效果如何以及如何定义规训是否成功。此外,普罗迪把社会规训的操作方定位在天主教君王、罗马教廷、枢机以及主教,忽视了基层教士和平信徒也有自我规训的意图和追求。晚近的研究修正和补充了普罗迪的学说。②参见Marc R.Forster,Catholic Germany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Enlightenment,New York:Palgrave,2007.特普斯特拉就在文中吸收了学界的新成果。他指出,近代早期天主教发展出了多维度的教派主义(multi-directional confessionalism)。罗马教廷企图用标准化的模式来改造和管理宗教社团与宗教修会,也的确取得了成效。但实际上,近代早期的全球范围内的宗教社团和宗教修会则有自己的应对之道,在与罗马的角力过程中、在从事跨文化的活动中丰富了近代早期天主教普世教会理念。值得注意的是,普世教会并没有、也无法取代本土教会,实则两者乃是互惠的关系,并与带有浓重攻击色彩的“胜利的教会”理念一道,形塑了近代早期天主教。③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p.613-614;p.617.
何谓“从行动到企图”?实际上,在耶丁时代,学者们受制于传统教会史理路,关注的焦点大半是修道人士的冥思体验与神秘主义的诸种表现方式。尔后,在法国年鉴学派的推动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还,公共仪式、宗教游行以及慈善组织等成为宗教史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探析大众宗教、地方宗教以及市民宗教尤有兴趣。20世纪末以来,新文化史研究卷起千堆雪。再加之“新教沙文主义”的退潮,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来审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天主教徒渐成显学。因此,学界不再满足于天主教徒表面上做了什么,而是希冀体悟他们的内在企图是什么,以及他们理解、认知乃至塑造世界的方式有哪些。简言之,在近代早期如何做天主教徒或做天主教徒意味着什么,就成为彰显近代早期天主教的绝佳视角。由此,感官研究、情感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等,被引入“长16世纪”的天主教史之中。特普斯特拉把这一学术流变揭示出的近代早期天主教的特色称为“从行动到企图”。
特普斯特拉指出,近代早期的罗马天主教会愈发关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灵修的内在状态。如果中世纪晚期关注的是“肉身慈善”的七善行——给饥饿者食物吃、给口渴者水喝、给衣不蔽体者衣服穿、给无家可归者房子住、看望病人、探访犯人、埋葬死者,近代早期则强调“属灵慈善”的七善工——让罪人皈依天主教、教导无知者、劝告有疑虑之人、安慰伤悲之人、耐心承受不义之举、原谅伤害、为生者和死者祈祷。这种从肉身向灵魂的焦点转移可谓近代早期天主教的一大特点,也是天主教教派主义重塑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内在生活的题中之意。①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618.为了改造天主教徒的灵性状态,借助艺术、建筑、音乐等物质文化和神圣空间来强化感官对信仰的回应,则是近代早期天主教的一大特色。譬如,特普斯特拉就指出,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和礼仪带有浓厚的情感维度和感官维度。巴洛克风格的礼拜空间就旨在打动人心,激发敬畏感,启发想象力,让礼拜之人欣喜兴奋。此外,近代早期天主教还利用描述行为举止的书籍、戏剧乃至舞蹈等,来强化正统的敬虔理念。不止如此,体现天主教信仰的物质文化诸如圣母像、护身符、十字架、圣体匣、玫瑰念珠等,也在全球流通,甚至带有本地特色,从而促使“敬虔消费”(devotional consumption)的历史现象出现。②Nicholas Terpstra,“Early Modern Catholicism,”p.621.诚如特普斯特拉所指出的,天主教徒利用这些物品来确立身份认同,强化内在灵性状态。
(二)迪奇菲尔德的全球史视野中作为“动词”的天主教复兴
迪奇菲尔德是英国约克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近代早期意大利基督教文化史领域非常活跃,建树颇丰。近些年,他主张学界不要再纠缠于用哪个历史范畴来解释“长16世纪”的天主教历史,建议不妨将近代早期天主教的演变视作一个动词来具体考察。③参见Simon Ditchfield,“Of Dancing Cardinals and Mestizo Madonnas:Reconfiguring the History of Roman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8,2004,pp.386-408.因此,其《天主教改革与复兴》一文,就题目而言,与60年前坊间常见的同类型著述的标题可谓无甚差别,但其内容的编排却颇具匠心,完全是耶丁时代的学者所无法想象的。这得益于作者本人多年来对文化史,特别是全球史方法的汲取和借镜。④迪奇菲尔德近年来一直在筹备有关重写近代早期天主教历史的专书,而且运用的是全球史与文化史的方法。早在《天主教改革与复兴》一文撰就之前,他就发表了一篇重新认识近代天主教的文章,颇具启发性。参见Simon Ditchfield,“De-centering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Papacy and Peopl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Archive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101,2010,pp.186-208.
对于近代以降伴随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的海外扩张而开启的天主教全球传播,带有强烈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传统观点通常认为,非欧洲地区的、本土的天主教乃是调和的且次等的混合物(syncretic,bastardized hybrids)。⑤Simon Ditchfield,“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p.184.因此,所谓“新世界”的天主教会只是被动的接收方,乃隶属于“旧世界”的天主教会,并无主体性可言。曾经的传教学研究就是典型代表。迪奇菲尔德坚决反对此说,他主张认可非欧洲地区的多元的本土天主教类型是正宗的天主教信仰。故而,他目前的研究就力图提供一种依托于全球视野的近代早期罗马天主教的新看法。迪氏的核心论点可做如此总结:罗马天主教会自近代早期开始就在朝第一个全球宗教的轨迹发展,而且这一过程至今仍未结束;“新世界”的天主教不仅生发出自己的特色,而且回流“旧世界”,给1500年至1700年期间的欧洲天主教带来巨大影响;在近代早期,“新世界”就在改变“旧世界”,而且在基督宗教进入第三个千年的当下仍在继续;所谓的“西方在世界独占鳌头说”至少要到19世纪晚期或20世纪早期方才实现;而且,所谓的“胜利”也只是就经济、政治与军事而言,宗教信仰并非如此。《天主教改革与复兴》一文就展现了迪奇菲尔德的这一思路。
也正因如此,《天主教改革与复兴》的谋篇布局与《近代早期天主教》略有不同,更是与传统的同类著述大相径庭。譬如,耶丁笔下的16世纪天主教史总是以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召开以及教宗对特兰托改革精神的推广为叙述主轴。迪奇菲尔德则别开新境,以天主教信仰的全球流布(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the Sacred)开篇,精细描述了圣母画像、宗教象牙制品、宗教版画作品以及宗教雕刻作品是如何在全球流通并实现本地化的。⑥Simon Ditchfield,“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pp.152-154.换言之,迪奇菲尔德关心的是近代早期如何在全球“转化”(translate)天主教信仰。譬如,圣母像在美洲、东南亚、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中国明朝,皆为了适应本土环境而本地化。以耶稣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尤能适应所处地区的风土人情。此外,迪奇菲尔德指出,外方传教以及宗教本体化能否有成效,端视当地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状况而定。譬如,非洲、印度、东亚和美洲虽然各自利用天主教仪式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信仰模式,但程度、规模以及历史走向都受制于各自的政治大环境。如果说海外传教在印加帝国势如破竹,那么在印度和日本则只能利用当地政治分裂的状况来渗入力量。而在儒家中国,则要面对极其强大的政权和文化力量。①Simon Ditchfield,“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pp.153-159.
天主教信仰的全球流布导致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新世界”的传教经验与方法回流且影响“旧世界”的重新基督教化。简言之,就是“新世界”改变“旧世界”。这是《天主教改革与复兴》一文的第二部分。对此,迪奇菲尔德坚信,恰恰是在应对如何在“新世界”传播天主教信仰的过程中,传教理念与传教技巧得以发展精进;而反过来,这些理念与技巧又被用来重新加深“旧世界”的信仰。譬如,那些在墨西哥、菲律宾乃至中国的传教士就传教经验和皈依体验做出了记录。大量相关书信和报告凭借迅猛发展的出版印刷技术而得以在欧洲流传,并激发想象和思考的涟漪,给欧洲信仰薄弱地区的天主教革新带来了可资借鉴的资源。“新世界”由此成为“旧世界”的老师。②Simon Ditchfield,“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pp.163-167.
在铺设了天主教信仰全球流布的大背景之后,《天主教改革与复兴》一文才在第三部分论述特兰托大公会议。特兰托大公会议无论是在19世纪充满教派偏见的传统论述中,还是在20世纪的耶丁的清晰透彻的历史分析中,都是近代天主教革新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亦即要么是反宗教改革的桥头堡,要么是天主教改革的驱动力,以至于“特兰托时代”成为史家阐释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晚期天主教史的重要概念。当下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史研究则更加客观细腻,力图呈现它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的困局、局限乃至无力。此外,意大利左派世俗史家③意大利的左派世俗史家大半对天主教持负面看法,与以普罗迪为代表的天主教史家泾渭分明。对此,可参见John W.O’Malley,Trent and All That: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pp.78-91;付亮:《意大利宗教改革史学概述》,《光明日报·理论·世界史》第11版,2015年9月12日。(“lay”historians)诸如普罗斯佩里(Adriano Prosperi)、菲尔博(Massimo Firpo)以及博诺拉(Elena Bonora)等人,着重发掘特兰托大公会议的负面因素,认为其为罗马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是教会规训信众的开端,是意大利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④参见Adriano Prosperi,Tribunali della coscienza:Inquisitori, confessori, mossionari, Torino:Einaudi, 1996; Adriano Prosperi,Il Concilio di Trento:una introduzione storica,Torino:Einaudi,2001;Massimo Firpo,La presa di potere dell’Inquisizione romana,1550-1553,Roma:Editori Laterza,2014;Elena Bonora,La Controriforma,Roma:Editori Laterza,2009.对此,目前最新的研究持不同看法,认为此说夸大了历史事实,也忽视了与会主教的核心追求——改革自身。可以说,奥马利的《特兰托大公会议简史》允称代表。迪奇菲尔德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就充分地吸收了学界已有的成果,特别是奥氏的贡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迪奇菲尔德尤能关照从全球视野省思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历史作用。他认为此宗教会议在天主教改革和复兴的全球史叙述中有如下两点重要性:其一,是会议并没有针对教宗制度提出改革决议,因此就为天主教会最终成为以罗马为主导的天主教会铺平了道路;其二,是会议把主教打造为教会的基石,不仅对“旧世界”的教会革新意义重大,而且为“新世界”提供了教牧工作的领袖。
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迪奇菲尔德重点论述了“教宗君主”(papal prince)和“教宗牧者”(papal pastor)这一二元身份。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了普罗迪针对教宗“一体两魂”的看法,亦即“普罗迪范式”。他尤其强调近代早期教宗为了扩大中央集权而不惜打压主教牧灵工作的做法。对于“普罗迪范式”,英国历史学家莱特(A.D.Wright)曾写有专书提出不同看法。⑤A.D.Wright,The Early Modern Papacy:From the Council of Trent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1564-1789,New York:Longman,2000.迪奇菲尔德吸收了莱特的看法,并通过多年对罗马教廷封圣机制的研究,纠正了“普罗迪范式”。他指出普罗迪忽视了教宗作为普世牧者的身份认同。而且,他与特普斯特拉持相同看法,认为近代早期的罗马被有意打造为普世教会的京城。不过,与特普斯特拉不同的是,迪奇菲尔德并不关注教宗在近代早期的“帝王式的司祭”之身份,而是强调教宗如何借由制造圣徒来确保和彰显自身在敬虔事务上的普世牧者之权威。①Simon Ditchfield,“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pp.171-173.至于罗马天主教会的“社会规训”行为和教派主义,迪奇菲尔德则在文章的第五部分加以论说。与特普斯特拉看法不同的是,迪奇菲尔德更看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葡萄牙宗教裁判所以及罗马宗教裁判所对社会服从的强力作用。而且,迪氏主张从全球的角度分析三大宗教裁判所及其分支的活动并重估它们与民族教会的互动。②Simon Ditchfield,“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pp.174-178.
文章的第六部分——全球视域中的主教区,是迪奇菲尔德用力较多的地方。自耶丁四卷五本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史》问世至今这几十年,主教与主教区在天主教复兴中扮演的角色是“长16世纪”天主教史研究长盛不衰的领域,相关成果可谓宏富。但由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受制于“耶丁范式”和“普罗迪范式”,主要的研究成果大多聚焦在欧洲的主教区。对非欧洲地区的主教以及他们与欧洲同侪之间的互动,则挖掘得不深。迪奇菲尔德则主张引入全球史的方法,重新审视近代早期的主教及其活动。他以米兰大主教博罗梅奥为代表,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指出,身为天主教改革旗手的博罗梅奥不仅对欧洲的主教制度改革影响巨大,而且其改革方略和教牧理念在美洲甚至亚洲同样得到认同和模仿。③Simon Ditchfield,“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pp.178-184.故此,若要研究博罗梅奥如何推动和践行特兰托改革精神,就必须引入全球视角。探究博罗梅奥这类主教的教牧构想,也是理解近代早期天主教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
三、余论:终结“特兰托迷思”与重写变革时代的天主教史
其实,如何解释或如何定位特兰托大公会议不啻是理解近代早期天主教的一把钥匙。譬如,以耶丁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学家在省思彼时天主教的演变时,就将特兰托大公会议作为出发点。因而,“特兰托时代”和“由特兰托大公会议形塑的天主教”(Tridentine Catholicism)这类诠释概念一方面巧妙地淡化了宗教改革给天主教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突出了该会议的成果给天主教带来的正面影响。此外,耶丁强调“后路德时代”的天主教不是反宗教改革类型的宗教,而是吸收古代教会的方法以完成自我改革的宗教。自我改革的精神就在特兰托大公会议上达到顶峰,为此后的教会大改革时代掀开了帷幕。虽然普罗迪放弃了“耶丁范式”,转而强调天主教的近代性(即它与新教的平行发展及相似之处),但在他的历史认识中,特兰托大公会议仍是中心,而且是天主教近代性的最大动力。不过与耶丁不同的是,普罗迪认为特兰托大公会议不是出发点,而是终点,乃是天主教会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应对时局的一个句点,自此天主教开始走入近代性。倒是奥马利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一再提醒:特兰托改革精神只是近代早期天主教复杂多元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唯一的中心。随着“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激发天主教史研究涌现新课题,我们在特普斯特拉与迪奇菲尔德的文章中即可看出,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历史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并不是唯一的中心;毋宁说,它只是多中心发展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动力。
曾经的“新教沙文主义”书写模式,将新教革命目为中北欧与南欧不同历史走向的分水岭。这种看法如今已不被普遍接受。罗马天主教和新教诸宗派以及两造与其他宗教,在近代早期彼此碰撞、激荡、影响,形成多维度、多网络的复杂互动态势,共同参与建构近代早期世界史。这是当前的主流看法。是故,学者们对新教和天主教的物质文化、感官敬虔、生活周期充满好奇。如何在近代早期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是基督宗教史家愈加感兴趣的课题。两造对信徒的迫害以及对近代国家建构的参与作用,亦是学者们极力开掘的领域。譬如,特普斯特拉近来对宗教改革时期的难民与流亡做出的研究,就极具代表性,为全球史视域中的复数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s)提供了一种新的诠解。
近些年,迪奇菲尔德一直强调没有必要再纠缠于解释概念本身,不妨将近代早期天主教的演变视作一个动词来具体考察。他说的固然有道理,但也有问题。解释概念或诠释范式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完美的,但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毕竟其反应的是学术研究在一段时期的积累后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总结出的抽象认识。没有这类概念,相应的问题也就无从说起。再加之,史学范式本就可以作为“灯塔”指引后续的研究。譬如,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普罗迪念兹在兹的“社会规训”范式,即便有档案之公开,国际学界会涌现大量的宗教裁判所研究成果从而出现“宗教裁判所转向”的学术态势吗?当然,在范式成为遮眼物的时候,也就是新范式代替旧范式之际。这是学术发展之规律。此外,迪奇菲尔德认同天主教有其“早期近代性”,当是无可置疑的。其实,“早期近代性”不正是更深层次的“元范式”吗?没有它,何谈“社会规训”?质言之,迪氏并不能跳脱对范式的选择。
总而言之,“特兰托迷思”如今已然被打破,重写变革时代的天主教史在本文论析的两篇近文中已现端倪。近代早期天主教史的“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在可预见的未来,当会更为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