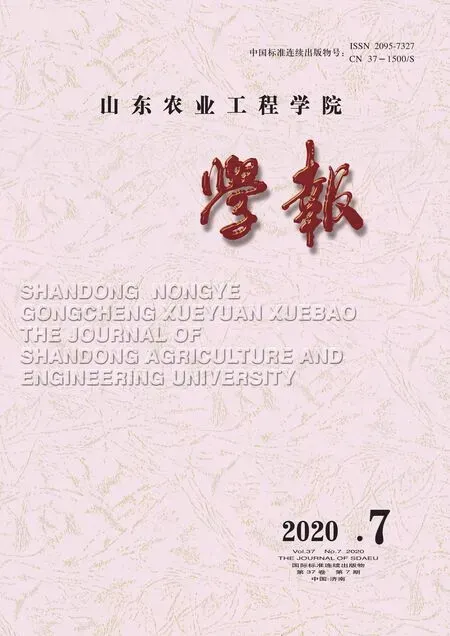福建畲族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发展研究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 福州 350202)
福建省畲族人口占全国畲族总人口52.87%,居全国首位,主要分布在福州、三明、漳州、宁德、龙岩等地。福建省作为畲族人口大省,已有500多个畲族村落,具有民族区域发展的典型性、示范性重要意义。畲族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歌曲、服饰、风俗、手工技艺,经过历史长河的不断演变与涤荡,形成了精致又丰富的畲族民族传统文化,并世世代代蕴藏于族人们久居的村落之中。
一、保护与活化畲族传统村落的重要意义
传统村落是指在其规划体系中应当拥有自然环境资源,物质空间资源,人文环境资源等条件。传统村落承载着各个历史时期、地域的迁徙变化、民族传衍的文化气息,拥有宝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发挥其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乃至经济价值,是国家应当予以保护的村落,被称为“文化的活化石”。畲族传统村落具备了景观生态与建筑方面的自然环境与物质空间条件,旅游开发与民俗活动的人文环境条件,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文化资源条件。但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等原因,畲族村落的进步与发展始终伴随着程度不均的汉文化交流与融合,所以能够完整体现畲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与精神的古村落并不多。
畲族传统村落是历史以来畲族先民创造发展出的宝贵民族文化财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丰富的历史传承、人文情感、社会经济价值、民族文化等多维度多层次的价值体现。本着党中央扶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意图,保护治理协同活化发展福建省畲族传统村落,延续村落生命,是传播和提升畲族传统文化的根本手段,对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畲族村落区域性民族文化建设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福建省畲族传统村落现状与活化发展的制约痛点
1.福建省内畲族传统村落分布不均
畲族先民历来的生活生产沿袭着刀耕火种,采食猎毛的原始方式,经历辗转、散居、迁徙,到了清代才呈现出族群逐步稳定发展的局面。在不断的多元文化介入、影响、转变之中,畲族直至今日形成“大散居,小聚居”的生活形态。这也就意味着大型畲族村落之间可能距离甚远,联系性较弱。据近年来相关统计数显示,入选首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录共339个村落,其中畲族村落有3个;入选第二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录共234个,其中畲族村落有6个;拟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共2646个,其中福建有263个,畲族村落有3个。数据统计直观体现出,能够“榜上有名”立项于名录内的畲族村落数量过少,加之“大散居”的区域生活形态,畲族传统村落在省内的分布不成体系,难见统筹规模。福建省内大多数传统村落都地处于偏僻、贫困之地,物质空间形态的缺乏对于村落发展本身就存在不利因素。所以能较为完整体现畲族传统民族文化,并且能向社会各界传播畲族历史、人文、社会等丰富畲族精神内涵,发挥传统村落价值的畲族村落更是屈指可数,更不用提活化与有效利用了。
2.中青年外迁,人口老龄化严重,村民保护意识薄弱
经过实地田野调查发现,畲族村落中的人居现状不容乐观,村中留守的大多是老龄人口,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的不良现象。在现代经济生产模式与丰富生活环境的刺激诱导下,畲民增加了外出工作的机会,其工作方式有“候鸟式”与“兼业式”两种,近年出现“外迁式”的中青年人口持续呈上升趋势。中青年脱离刀耕火种的农耕村落生活生产,长期在外,导致村中老龄化人口比重激增。除了外流人口之外的畲族村民久居村落,与外界现代化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接触少,不了解传统村落的不可再生性与稀缺性,受教育程度低,保护、发展和传播畲乡传统文化的意识淡薄。村落中许多传统风貌格局与历史建筑规划因村民的漠视而被拆旧建新、肢解殆尽,村落原真的宝贵文化特征和原生态环境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甚是可惜。
3.民间习俗、仪式逐渐减少,传承根源被阻断
习俗是民间文化的一种,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群体生活、生产实践与社会交流中逐渐形成并且世代传衍的文化事项。畲族民俗通过仪式实践形成独特风格,畲族民俗仪式有婚礼、丧礼、节日庆典、祭祖祭祀等活动,这其中畲族中青年人群是实践仪式、推动流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中青年这一主要行为实践群体的流失,直接导致畲族民间习俗活动的减少。村落是承载族人习俗仪式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根源所在,减少了习俗仪式活动,意味着村落得不到人为的活化利用,发展动向滞留不前。
4.民族手工技艺萎缩,村落遗产的制作技艺后继无人
现如今,传统民族手工业因其产效慢,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快速经济需求,早已被大工业机器发展后的时代抛之脑后。由于历史变迁、地域经济衰退、民俗与宗教活动锐减、政治激荡等原因,畲族传统民族手工技艺渐渐萎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服饰制作工艺,是综合性很强的手工服饰技艺,包括了服装刺绣、头饰制作、银质扁扣锻造等。畲族盛装服饰与村落中的世代沿袭的民间婚嫁仪式紧密结合,如此精美细致、既美观又实用的服饰制作技艺,就因为村中青年陆续离开,难以延续传统婚嫁仪式,而难以传承,后继无人。
5.建筑与景观生态环境的衰败
乡村规划发展越来越滞后的问题矛盾,随着社会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而日益凸显。传统村落的建筑、景观、生态环境、空间布局等发展问题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政策性文件指导和部署,更没有系统性的规划与执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政策指导文件中,均未对传统村落的历史古建、古民居、村落景观与环境的保存作出详细描述[1]。畲族村落中原本留存的传统民族文化符号,例如戏台、古民居、街道、祠堂等,因为时过境迁而疏于修缮;建筑材料老旧,空间使用功能退化;原有的乡镇政府漠不关心,没有引导民众了解和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村落空间环境与建筑,民众不在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导致原本承载民族文化精髓的历史民居建筑与自然生态景观无法得到延续与发展,甚至遭受到出于经济利益纷争的人为拆除与破坏,“拆旧建新”“以洋代土”的例子屡见不鲜;建筑空间与景观生态环境的保护规划已经提出诉求,却没有能够深入开展调研工作、建构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的专业人才和善于古建筑与景观环境修缮技艺的能工巧匠。
现有政策的空泛,政府引导作用羸弱,民众保护意识的缺乏,科学调研专业人才与修缮技术能工巧匠的缺失,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与资金投入的微薄,都是导致畲族村落建筑空间与景观生态环境衰败的重要原因。
6.旅游商业开发疲软、混乱
畲族传统村落数量少,知名度低,畲族旅游商业资源开发程度浅薄,各村落中旅游产品性质与种类雷同,未能形成畲村旅游商业品牌效应。宁德畲族宫、霞浦畲族文化馆、福湖畲族风情园等展览场所,存放展示了畲族人民的服装、劳动用具、祭祀用品、医药、族群文化史料等,内容详实,但是展示种类雷同,没有做好文化展示场馆重点展示内容的区分,并且展示手段太过单调,停留于图片加文字的传统静态展示内容,无法吸引游人长时间驻足观赏品位。旅游体验活动中,游客参与性太弱,没有深层次内容与畲族文化进行结合。畲族节日“三月三乌饭节”,主要的感观形式仅仅是歌舞,题材单一,活动内容无新意可言,自然吸引不了游人的目光。畲族村落中,因为汉化严重,游人目光所及的生活场景无法真实体现畲族人民的本真民族文化与特色精神。加之村落中旅游设备落后,指示牌标识系统模糊或缺失、公共卫生间数量太少使用条件差、问询咨询与导览人员服务水平低下等问题,没有足够的村落经费进行整治。住宿与购物项目不完善,村落布局与公共设施细节缺乏文化特色,村落中旅游服务业能力不足,商业开发混乱。不论从物质条件还是文化环境层面,都无法形成畲族村落旅游与商业开发的鲜明特色。
三、深化推动福建畲族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发展对策
1.建立健全政府引导的效能与机制
2015年10月,福建省文化厅授予宁德市15个畲族文化生态保护较好的村镇(单位)为第一批省级畲族文化生态保护示范点,一批具有畲族历史、文化、艺术、社会价值的畲族村落陆续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和福建省传统村落名录;宁德上水村在2013年入选国家级生态村和全国少数民族特色保护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村落;2014年5月召开的国家文物局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工作会上,福建省青水畲族乡沧海畲族村入选保护利用项目的传统村落,中央财政将在文物维修、“三防”、保护展示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2];2013年11月,“中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专家们就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等问题进行探讨,论坛主旨在呼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文化内省[3]。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地方乡镇政府能够积极配合国家、部委、省、市、县、协会等各级各类部门发挥良好的主导效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起到积极引导作用。政府引导畲族乡民了解自身的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主体地位,将自己的生存居住空间的利益与建设投入有机统一,协同参与到村落建设中来;政府引导相关政策与法规的有效制定与推行,健全管理制度与责任定岗定位;政府在保障市场的参与和有序推动新型城镇乡村建设、充分结合村落周边物质与文化资源的同时,还要平衡有效监管与合理开发的关系,在市场产生经济效应的同时,不忘保护、传播和发扬畲族传统村落文化;政府引导社会各级民众广泛参与畲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增强专家智库的渗透参与程度,呼唤各界外乡贤能之士投入畲乡建设,推动社会公益组织与民间团体力量,实践政府系统性的参与与部署行为[4]。建立健全政府引导效能与机制,从经济、法律、技术、人才、民众等各个角度多维促进畲族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协调统一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为畲族民众打造一个能够承载乡愁的魅力畲乡。
2.活态保护畲族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
畲族村落中蕴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已申报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涉及了传统医药、服饰制作、民俗、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技艺等多种类型项目。闽东畲族传统服饰技艺第六代传承人林章明在畲族传统服饰的活态保护与传承工作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村落中开办畲族传统服饰传习所,力图通过自身力量整合宁德周边县市村镇的服饰制作产业力量,选择重点培养对象传袭畲族传统服饰手工制作技艺,将手工技艺留在传统村落原生之处焕发生机活力;霞浦县溪南镇半月里畲村不久前举办了一场具有浓郁畲族特色的“婚俗活态展”,活态展上完整体现了闽东畲族婚俗的每一个环节,意在传扬民族婚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霞浦畲族婚俗第十一代传承人雷其松等一批畲族人,自发地成立畲族婚俗保护小组、婚俗研究会,建立畲族婚俗博物馆,主动活态保护畲族村落中留下的宝贵非遗文化财富。
传统村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孕育诞生、发扬光大的宝库,是畲族文化赖以生存、凝聚、发展及创新创造的摇篮。传统习俗、手工技艺、民间传说、歌舞节庆,都是畲族传统村落中最具特色的在地文化。活态保护根植于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反哺村落的活化发展和延续,激发出村落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3.畲村建筑空间形态与生态景观环境活化利用
畲村历史街道、聚落建筑形态、空间格局与功能、生态植被等空间构成要素要进行合理有序的统一规划,但并非“一刀切”“拆旧建新”,而是要贴近畲族人民活动居住的乡村实际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因村制宜”的活化原则。要保留住乡村内传统景观与建筑空间的基本骨架,围绕传统畲族人文历史的多样性与特殊性,融合自然生态要素与畲族民族艺术审美要素,对现有的街区布局形态、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建筑模式等村落空间构成要素进行合理的挖掘与整合。保留原始可用的建筑景观的结构与材料,修葺和替换已损坏的,尽力恢复原景观与建筑空间形态,还给畲民“原汁原味”的畲乡村落。在保护和修缮的基础上,坚持村落空间活化改革,替换原有历史建筑与景观的使用功能,嫁接新社会文化环境下可使用的空间,增加经济效益增长。强调活化利用村落空间的前瞻性、科学性与实际操作性,突出每个不同地区地域畲族传统村落展现的“一村一特色”。
4.合理开发生态旅游产业
福建省连江县东湖镇的天竹村与罗源县霍口乡的福湖村是目前福州市发展畲族风情生态旅游产业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传统畲族村落,以这两个村落为例,提出合理开发生态旅游产业的活化对策。
(1)生态景观设施类
天竹村在新建畲族文化馆的同时,修建了畲寨激情广场,活态开展畲民与游客的对歌交流、大型传统歌会、畲族文化庆典等。建设葡萄长廊、荷花池、油菜花园、枇杷园,为游客提供生态文化景观场所,增加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理念,吸引游客前来互动体验。福湖村建设了畲族主题公园,重点推设有关传统服饰、畲族医药、畲拳等主题的文化广场与设施空间。部分畲民改建自己的民居建筑,开设民宿,打造生态畲餐,建设饮食赏游项目。
(2)历史文化古迹类
福湖村保留了清代古建筑群落,但古建筑不仅仅只是给游人走马观花,而是嫁接了畲族服饰展示厅,将古建筑群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活化利用。不仅让人们欣赏到畲族民居建筑原始韵味浓厚的木刻石雕精致之美,历史留下的隽永之感,还能与畲族精致华彩的服饰文化相得益彰,活化了本民族服饰文化的交流展示。
(3)深度体验参与类
天竹村与福湖村,每年都回归传统,举办“三月三乌饭节”庆典活动。以畲族歌曲对唱、小说歌、畲族舞蹈、品尝畲族乌米饭为基本的参与体验项目,开发其他与非遗文化相关的深度体验旅游项目,例如畲族婚俗、打畲拳、畲族服饰制作手工艺、苎布染织缝制技艺、畲族古民居、畲族医药、畲银锻造、畲族农耕活动等等。通过节日庆典,创意化地深入挖掘畲族村落中的文化意义,加大传播力度,使游客来到村落能被畲族文化深深吸引,对畲族有深入了解,体验畲族村落生活的个性化、趣味性、特色性,从而提升畲族村落经济效益与旅游产业知名度。
5.培养畲民保护与活态发展畲村的自主意识
2016年泉州市泉港区钟厝村中也面临着青年人外流,仅剩少数老年人,畲族文化即将失传的尴尬境地。村民在村委会的号召与有力引导下,极力期盼展示和传承畲族文化,挽回民族文化精神,纷纷积极“众筹”家中具有畲族传统文化性质的老物件,在村里建立起泉港区首座村级畲族文化馆,独特的文化物件展示了盐技农耕文化、民俗风情与传统服饰。得益于这座属于村民自己的畲族文化馆,民族传统村落文化与当代文明可以有机结合,活化开创新形态的村落文化,大力提升了民族自信心。
畲族传统村落中畲民的自主保护与发展意识必须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相携而行,政府应当合理有序开展“在畲村以畲民为本”的工作导向,建立健全引导畲民共同参与保护传承与活态发展畲乡的机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多媒体等不同媒介,营造良好氛围与舆论环境,充分调动畲村民众的积极性。在充分发挥其重要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要让畲民看到科学整治村落中的生态环境、村落规划布局、历史古建保护、非遗文化传播等文化改革成效。让畲族民众从自我生存的地理空间、建筑空间与景观空间中感受并且认同改革成效,从心理上逐步相信改革成效,从而提高自身保护与活态发展畲族传统村落的主观意识[5]。
四、结束语
传统村落是历史形成的产物,它受到经济型社会发展的冲撞而出现转型和提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保守传统文化根基是固守住畲族民族魂魄的重中之重。坚持“保护传承为基,活化利用为径”的原则,在认识传统文化发展的意义之上,以民族自强意识与创新发展为基面,重视畲族村落物质与文化资源的整合,保护历史风貌与生态环境,改良利用村落规划布局,合理引导产业发展,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与基层民众的主体作用,从而实现畲族传统村落这一物质遗产活化石的活化与发展,延续美丽“乡愁”的古老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