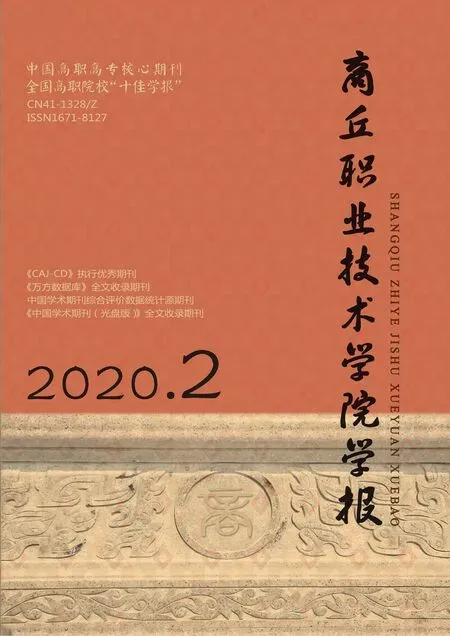王安石延请杜醇再探析
刘 岩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王安石文集内收有两篇《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以下简称《入县学书》),一般认为是王安石任职鄞县时写给宁波地区的名儒杜醇,内容是请他来鄞县县学任教。王安石请杜醇任教的举动被认为是王安石早年重视教育的重要体现,也是王安石知鄞时期的重要政绩①,袁桷、全祖望、钱大昕等人都持相同的看法。但笔者通过仔细分析王安石《入县学书》及参考宋代地方志记载,发现这两篇书信的作者及书写内容仍有可商榷之处,故略陈管见,以向方家请教。
一、关于“杜醇入鄞学”的史源探究
王安石两篇《入县学书》中的“县学”所指是鄞县县学,这个学界通行的看法当主要来自《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中“学师杜石台先生醇”条[1]。书中直言鄞县刚开始兴建学校,王安石请杜醇入鄞县县学。但作为鄞人的全祖望还不是这则信息的源头,他直言“参四明文献集”。鄞人郑真于明初辑四明地区历代先贤诗文而成《四明文献集》,共60卷,书成后并未刊行,该书在明代时已经开始散佚。到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馆臣所见《四明文献集》皆为王应麟诗文,共5卷,“故一人之作冒总集之名也”[2]。可惜的是今存《四明文献集》中并不见全祖望所参考的资料。元代鄞人袁桷纂写的延祐《四明志》卷四《人物考》“慈溪杜先生条”中存在着相同的记载,全祖望自言并没有参考延祐《四明志》,但两者的记载却是相同,那就说明《宋元学案》《四明文献集》及延祐《四明志》当出自同一处史源。今为叙述方便,现只将延祐《四明志》“慈溪杜先生条”抄录如下:
杜先生醇,越之隐君子,居慈溪。学以为己,隐约不求人知。孝友称于乡里,耕桑钓牧以养其亲。经明行修,学者以为模楷。庆历中,鄞始建学,县令王文公安石请先生为之师,其书曰:“天之有斯道,固将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余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愿先生留听而赐临之,安石与有闻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说以辞。再书强起之曰:“孟子谓好为人师者,谓无诸中而为有之者,岂先生谓哉!彼宗元恶知道!韩退之毋为师,其孰能为师?天下士将恶乎师哉?”先生始就焉。慈溪令林肇立学,又起先生为师,亦固辞,王文公作《师说》以勉之。二邑文风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谈《诗》《书》不倦,为诗质而清,当时谓学行宜为人师者也。[3]
但这段记载也并不是袁桷所写,乃其师王应麟所作。袁桷在同卷“广平舒先生”条下直言“自大隐至广平皆王先生撰”,大隐指杨适,广平指舒璘,也就是说延祐《四明志》卷四《人物考》中关于杨适、杜醇、王致、楼郁、王说、舒璘的记载都出自王应麟之手。王应麟是南宋末年的著名学者,生平著作宏富,但散佚严重。全祖望参看的《四明文献集》当为郑真收集的王应麟著作。杜醇活动于北宋仁宗时期,王应麟生活在宋元之际,那王应麟之前是否还有史源呢?限于学力,笔者并没有找到其他的记载。关于杜醇任教鄞县、慈溪的记载,延祐《四明志》当为现存最早的资料。
除了写有杜醇的传记,延祐《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儒学”载有王应麟的《重修学记》一文,言:“鄞在汉为鄮,属会稽郡;唐属明州,建夫子庙于县东;五代改鄮(贸阝)曰鄞;宋始立学,王文公安石宰县,因庙为学,教养县之子弟,风以诗书,衣冠鼎盛……昔鄞有杜先生醇,学行望一乡,鄞大夫再书然后起。”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王应麟认为王安石请杜醇入的是鄞县县学。
袁桷本人也有一篇《重建学记》收入延祐《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儒学”中,其文直言:“鄞旧有学,王文公安石为宰时,延会稽杜先生醇教之,学者辈出。”此文后面又紧接附了自己的另一篇文章,其中记载“维鄞自王文公延杜先生,以君师为端本,故后之继承,经术渊懿,蹇蹇大节,见于史传者凡数公”。更是对王安石延请杜醇入鄞县县学之事赋予了教化后世的重大意义。由于延祐《四明志》的记载,后世的鄞县方志都因袭了王安石请杜醇入鄞县县学的看法,例如以考订见长的史学家钱大昕纂写乾隆《鄞县志》,其中卷五《学校》有这样的记载:“唐以前有庙无学,宋王介甫知县事,始延乡先生杜醇入学教诸生徒,自后儒风大振。”“王安石宰县,因庙为学,乃请杜醇为师,以教养子弟。”[4]并直言材料来源于袁桷纂写的延祐《四明志》。
王安石本人得知杜醇去世时,写有一首古诗《伤杜醇》②,其诗曰:
杜生四五十,孝友称乡里。隐约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鸡豚,筠筒钓鲂鲤。岁时沽酒归,亦不乏甘旨。天涯一杯饭,风昔相逢喜。谈辞足诗书,篇咏又清泚。都城问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弃予死。古风久凋零,好学少为己。悲哉四明山,此事今已矣。
南宋李壁注解此诗言:“公为鄞县,尝有书请杜醇入县学,及在朝,又数从越人问其安否。公厚醇如此,其退之所称董邵南之流乎?读公诗,可想见其人。”[5]李壁的注解如今天所见王安石书信一样,直言请杜醇入县学。根据李壁之言的语境,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杜醇入的是王安石所在的鄞县县学。
二、对“杜醇入鄞学”的四点疑问及解释
虽然有这么多名家的记载,但笔者仍无法确信杜醇入鄞县县学这件事,在提出自己的疑问之前,有必要先说明王安石与慈溪县令林肇的关系以及理清延祐《四明志》中所记录的这件事的逻辑。王安石与慈溪县令林肇有某种姻亲关系。今王安石文集中有王安石和林肇来往的多封书信,其中一封《谢林中舍启》有言:“维家伯氏,得婚高门”“先赐抚存之教,曲加奖引之辞。”[6]1435鄞县与慈溪相邻,二人又有姻亲,所以王安石替林肇作书延请杜醇当属正常。
延祐《四明志》中所记录的这件事的逻辑是:庆历中,王安石先后两书杜醇,方将其请至鄞县县学;而后慈溪县令林肇也写书请杜醇为师,被拒绝,经王安石写“师说”给杜醇,杜醇才同意去任教慈溪县学。这段记载中涉及王安石的三篇文章,其中两篇是请杜醇去鄞县县学,一篇请杜醇去慈溪县学,即延祐《四明志》所说的“师说”。此外,王安石受慈溪县令林肇委托,于杜醇任教慈溪县学之后写了一篇记文。王安石的四篇文章现存三篇,两篇《入县学书》,一篇《慈溪县学记》,“师说”未见。
(一)杜醇任教鄞县的时间不合常理
笔者对延祐《四明志》所记载的第一点疑问是杜醇任教鄞县县学的时间。王安石在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春离京赴鄞县任职[7]163,《入县学书》当作于王安石到达鄞县后,两篇《入县学书》的篇幅都不长,因行文需要先将首篇抄录于此: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其伦也。孰持其伦?礼乐、刑政、文物、数制、事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为之师,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为君,臣不知所以为臣,人之类其不相贼杀以至于尽者,非幸欤?信乎其为师之重也。
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虽然,有鄙夫问焉而不敢忽,敛然后其身似不及者,有归之以师之重而不辞,曰:“天之有斯道,固将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余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
某得县于此逾年矣,方因孔子庙为学,以教养县子弟,愿先生留听而赐临之,以为之师,某与有闻焉。伏惟先生不与古之君子者异意也,幸甚。[6]1375
首篇《入县学书》中“得县于此逾年”可证明作文时间当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春以后,即顾栋高认为的“当任鄞之二年也”[8],刘成国教授将此文的时间定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五月或六月[7]190。而关于林肇建慈溪县学、延请杜醇的时间,延祐《四明志》卷十四“慈溪县儒学”条和之前的南宋宝庆《四明志》卷十六“学校条”都明确记载为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如此,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杜醇在短期时间内先后任职鄞县、慈溪两处县学,这对“学以为己,隐约不求人知”的慈溪隐士来说不是很奇怪吗?还有,王安石先后修书两封才将杜醇请入鄞县县学,没过多久便替林肇作书将杜醇“请”到了邻近的慈溪县学,提倡尊师重教的王安石会这样做吗?
(二)前代地方志并无杜醇任教鄞县的记载
第二点疑问是关于杜醇任教鄞县县学的记载并不见于延祐《四明志》之前的地方志。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成书时间皆早于延祐《四明志》,在这三部宋代方志中,乾道《四明图经》、开庆《四明续志》篇幅简洁,较少涉及学校、人物。胡榘修、方万里与罗濬纂的宝庆《四明志》则有关于学校、人物的详细记载。宝庆《四明志》卷八《先贤事迹上》“杜醇”条有言:“杜淳,慈溪人,经明行修,不求闻达。庆历中,县令林肇一新乡校,请公为之,不可。王文公安石再为林作师说以勉之。至今与杨公适并祠于县学。”[9]宝庆《四明志》中关于杜醇的记载只是言及他曾任教于慈溪县学,而且在南宋宝庆年间仍被学子怀念,祠于慈溪县学。同书卷十六《慈溪》“学校条”记载:“学旧在县西四十步,皇朝雍熙元年,县令李昭文建先圣殿居其中;端拱元年,令张颖记;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令林肇徙建于县治之东南一里,鄞县宰王公安石记之,贻书招邑人宿学杜醇为诸生师。”在这里,杜醇是作为“邑人宿学”的身份任教慈溪县学。同书卷十二《鄞县》“学校条”言:“唐元和九年学建于县之东南,皇朝崇宁二年移县西南,成于大观三年。”
显然,在宝庆《四明志》中杜醇和鄞县县学并没有任何关系。将宝庆《四明志》关于杜醇的记载与延祐《四明志》相比,会发现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延祐《四明志》多出来了王安石两次修书请杜醇入鄞县县学的情节。从史料的保存及利用情况来看,作于南宋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的宝庆《四明志》的条件更优于王应麟(公元1223—1296年)和作于元代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的延祐《四明志》。
(三)第二篇《入县学书》可能就是“师说”
第三点疑问是第二篇《入县学书》和王安石代作“师说”的关系。王安石有一篇“师说”是自宝庆《四明志》以来的看法,延祐《四明志》因袭。所不同的是延祐《四明志》多出了王安石为请杜醇而两次致书的记载,这也就在王安石在“师说”之外多出了两篇《入县学书》。“师说”不见于今存王安石文集,现将第二篇《入县学书》抄录于下:
惠书,何推褒之隆而辞让之过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义不辞让,固已为先生道之。今先生过引孟子、柳宗元之说以自辞。孟子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者,谓无诸中而为有之者,岂先生谓哉!彼宗元恶知道?韩退之毋为师,其孰能为师?天下士将恶乎师哉?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不曰适于义,而唯谤之恤,是薄世终无君子,唯先生图之。示诗,质而无邪,亦足见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6]1375—1376
刘成国教授认为此篇《入县学书》与替林肇作的“师说”是同一篇文章,“盖因所论乃儒家师道,发挥韩愈《师说》之旨”[7]191。但刘教授没有注意到,他这样的看法相当于否认了杜醇曾在鄞县任教。两篇《入县学书》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和目的上的一致性,如果第二篇是请杜醇入慈溪县学的“师说”,那首篇断不可能是王安石请杜醇入鄞县县学,因此《入县学书》入的应该是慈溪县学。林肇延请杜醇被拒而后王安石代书是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都明确记载的,如此,第一篇《入县学书》也不是王安石所写,当为林肇手笔,后人错归在王安石名下。但刘教授并没有顺着这样的思路推理,他最后还是回到延祐《四明志》的说法,认为“公以一县之尊,两次致书礼聘布衣杜醇,尊师重道,溢于言表,流风余韵,波及后世。”[7]191
刘教授的见解为笔者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可以抛开延祐《四明志》的说法直接看第二篇《入县学书》。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缘由,信中直言因“先生过引孟子、柳宗元之说以自辞”,今天已无法找到杜醇的辞信,但从这第二篇《入县学书》中可以推断出大概内容:杜醇认为自己“有以教人”定当“义不辞让”,但孟子有言人患在好为人师,韩愈好为师故得狂名;感谢对自己的邀请,但自身品行才干不足,也不愿惹人非议。所以王安石有针对性地论述了孟子、柳宗元的关于师说的说法,孟子关于好为人师的说法广为人知,具体可见《孟子·离娄上》。王安石说“谓无诸中而为有之者”,认为孟子指责的对象是那些实际才能不足却还以师者自居的人,并非针对像杜醇这样的君子。“彼宗元恶知道?韩退之毋为师,其孰能为师?”当是指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对师道的论述,柳宗元在文中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10]韩愈在当时经常招收后学,被时人指责为好为人师。王安石赞赏韩愈的才能和品行当是为师的楷模,对柳宗元的说法表现出不屑。最后,王安石认为君子做事首先考虑的不是毁誉,应当是事情是否符合义的标准,并以此来劝勉杜醇。
总之,第二篇《入县学书》主要是在论述前人关于为师之道的理论,借以劝勉杜醇,完全可以用“师说”名之。按照延祐《四明志》的说法,杜醇最终接受王安石的邀请入教鄞县县学。在杜醇拒绝慈溪县令林肇邀请时,王安石还会再次写一篇“师说”来劝勉他吗?
(四)鄞县县学建于王安石任职前
第四点疑问是延祐《四明志》中关于鄞县县学的记载并不符合实际。延祐《四明志》中王应麟《重建学记》一文言:“王文公安石宰县,因庙为学,教养县之子弟,风以诗书,衣冠鼎盛。”但前文已提及,宝庆《四明志》中关于鄞县县学的记载并没有涉及到王安石和杜醇。实际上,鄞县在庆历八年前已有县学,鄞县著名学者楼郁在庆历年间“掌教县庠者数年”[11],王安石有《与楼郁教授书》[6]1391传世。宋仁宗庆历年号一共使用八年,王安石庆历七年方来鄞县,如果等到王安石兴建县学,那楼郁何来掌教县学数年之说呢?
王安石另有《慈溪县学记》一文,原文过长,今抄录后半部分:
后林君肇至,则曰:“古之所以为学者,吾不得而见,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虽然,吾之人民于此,不可以无教。”即因民钱作孔子庙,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为学舍,讲堂其中,帅县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为之师,而兴于学。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无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为,其几于此矣。[6]1466
北宋朝廷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诏令天下郡县立学,后又在立学上进行人数规定,即文中所言的“县之士满二百人,乃得立学”。慈溪属于小邑,士子只得就学于孔庙。后孔庙失修,林肇到任,才用民钱修缮孔庙,“治其四旁为学舍,讲堂其中”。另外,文中对杜醇的评价是“杜君者,越之隐君子,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丝毫没有提及杜醇先前曾任教鄞县县学。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为慈溪县学所作文章与首篇《入县学书》的相似处。首篇《入县学书》中有“某得县于此逾年矣,方因孔子庙为学,以教养县子弟,愿先生留听而赐临之,以为之师,某与有闻焉”。王应麟《重修学记》中的记载当来源于此文。而王安石《慈溪县学记》载林肇“即因民钱作孔子庙,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为学舍,讲堂其中,帅县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为之师,而兴于学”。前面已经证明王安石在鄞县并没有用孔庙作学校,那如此相近的两段记载又应该如何理解?结合上文的证明,是否可推断出王安石未曾作书请杜醇到鄞县县学,首篇《入县学书》并非后人所认为的是王安石所作呢?
三、 结语
综合来看,笔者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文献记载证明杜醇没有任教鄞县,但经过分析,延祐《四明志》以来关于杜醇曾先后任教鄞县、慈溪两地的说法极可能是错误的。王安石两篇《入县学书》中所入县学也并非理所当然的鄞县县学,当为慈溪县学;第二篇《入县学书》极有可能就是王安石的“师说”;而第一篇《入县学书》则可能出自林肇之手。后人不明,将林肇的书信误归入王安石名下,成为王安石的首篇《入县学书》,而王安石本人的“师说”也变成了第二篇《入县学书》,于是成就了王安石以知县身份两次延请布衣的佳话,也造成了王安石“师说”亡佚的情况。
注释:
①详情可参看杨渭生:《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倪士毅、宋佩芳:《王安石治鄞政绩述略》,《浙江学刊》1987年第3期;范立舟:《鄞县经验》,《光明日报》2015年6月15日。
②此诗又名《悼四明杜醇》,本文所引原诗及笺注以高克勤先生点校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