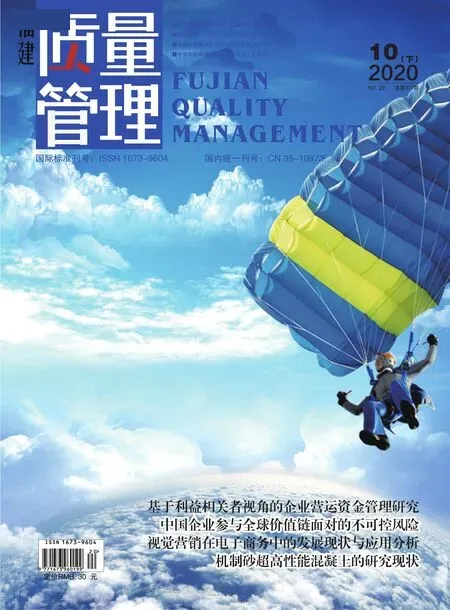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股权转让限制条款的效力
——基于司法案例之分析
莫丽琼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切入:基于指导案例96号的思考
2018年最高院发布了第十八批指导案例,其中第96号指导案例[1]是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章程限制条款的效力问题,该案例的发布引起了学界的争议与讨论。在本案中,法院认为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涉案公司章程中关于“人走股留”的章程限制性条款是否有效?法院通过三项裁判理由的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认定公司章程的限制性条款合法有效。在认定该条款效力的论证分析过程中,法院综合了三个方面的理由进行考量:第一,认为该章程是有限公司设立时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获得通过,应当合法有效;第二,从有限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司章程的限制性规定符合公司自治的理念。第三,认为案件公司章程的规定只是限制性规定并没有禁止股东转让股权。法院综合上述三项裁判理由认定该公司章程合法有效。
指导案例96号的裁判综合了三项理由对该案章程条款的效力作出判定,可以增强对于个案裁判的说服力,但作为指导案例,给出的三个裁判理由,仍有很多值得讨论和研究的空间。第一,指导案例强调该案章程为公司设立时的初始章程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对初始章程和后续章程进行区分是否有必要,初始章程一致同意受约束,后续修改章程限制股东转让股权是否有效?若无效,是只对该投反对票的股东无效还是对全体股东无效?对于这一类问题,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司法裁判。第二,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使用过于简单和泛化,公司自治的边界如何?简单引用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法理进行案件的裁判显得过于粗糙。第三,认为涉案公司章程对于股东股权转让的限制条款属于限制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而有效,此项裁判理由是否说明公司法允许公司章程进行“另有规定”存在一定的界限?禁止性的规定无效,那么限制性的规定是否均为有效?在本案中,法院综合三项裁判理由进行论证,个案上的确可以增强说服力,但三项裁判理由中何者才为认定本案结果的关键和重要理由依据,是否任意一项理由的出现均可认定该类型条款的效力,有待进一步明确。
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股权转让限制条款之司法裁判分析
笔者以“股权转让”,“《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款”,“公司章程”等筛选条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了裁判文书的检索,总共找到了一百多份判决书,通过对大量裁判文书的梳理,发现相关争议案件主要有以下三个类型:
(一)公司章程禁止股权转让或者实质上具有禁止的效果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禁止股权转让条款的效力问题,司法实践中纠纷相对较少,司法实务中对于这一类条款认定为无效条款没有太多实质上的意见分歧。在山西省朔州中院(2018)晋06民终230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公司法规定允许有限公司作出不同于公司法的规定,但应当保护股东股权自由转让的基本权利,如果公司章程的规定导致股东丧失了该权利,那么该章程条款应为无效。二审法院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章程设置不得转让全部出资的条款无效。在苏州中院(2017)苏05民终409号民事判决书中,苏州中院认为,本案公司章程中约定的限制性条款,实质上具有禁止股权转让的效果,应属无效。
(二)公司章程强制股东进行股权转让
对公司章程中对股东转让股权具有强制性要求的相关条款的效力问题,司法实践中的裁判不统一的现象更为普遍,各地法院往往出现不同的利益衡量而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
1.整体有效的裁判规则
对于公司章程强制股东进行股权转让类案件效力的判定,部分地区的法院裁判肯定了该类条款的效力。在广州中院(2018)粤01民终19159号民事判决书中,广州中院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考量,认为案件公司章程的强制转让规定有效。涉案股东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的行为,表明其对该条款的知悉和同意,该章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均产生约束力。在(2019)新29民终123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公司章程反映了股东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合意,涉案公司章程修改约定离职股东必须转让股权的内容,公司全体股东均应当受其约束。
2.整体无效的裁判规则
然而,相当一部分法院的裁判否定了该类限制条款的效力。在(2016)皖11民终259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股东享有的股权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作为财产权受物权法的保护,股东可以对自己享有的股权进行自由处分,公司章程条款不能剥夺股东的处分权。公司章程规定在股东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其股东资格就自动丧失,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在(2013)鹤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该案章程股权转让限制条款是对股东重大权益的处置方案,涉及股东的根本利益——股权利益,剥夺了股东对之前行为如认缴出资等的选择判断权。应属无效。
(三)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进行股权转让限制
对于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添加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性条款的效力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各地并未形成统一的司法裁判,往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一种观点认为通过修改章程增加股权转让限制条款无效。在(2017)云01民终2234号民事判决书中,昆明中院的观点是,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对股东转让股权添加的限制性条款应为无效。法院认为,该案中,公司通过章程修订增加了对股东的限制,该限制实质上已经具有禁止股东转让股权的效果,并且公司章程并没有为转让股东提供可供救济的替代性路径,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合法权利,应属无效。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章程修正案的设限条款有效。在(2016)苏01民终1603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从股东平等原则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条款,无论是对同意该条款还是反对该条款的股东,都应当具有约束力。在(2014)资民终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中,二审法院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人合性为由,在涉案股东蒋某对章程修改添加的限制性条款表示明确反对的情形下,法院仍然以公司章程的修改经过了法定的程序,修改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为由,认定修改后的章程条款的效力。
从以上梳理的各地法院的司法裁判来看,各地法院基于不同的利益衡量倾向,出现了不同的裁判结果,不利于各地司法裁判的统一。对于该类案件的司法裁判问题,目前依然缺乏统一的标准,司法裁判混乱的问题依然存在。
三、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股权转让限制条款效力判定的路径探讨
(一)章程效力类型化的判定方法
早在2007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就认为,公司章程修订中,因为并不要求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而是依靠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因此对于在表决中投反对票的股东而言,其并没有和公司形成合同关系,由此获得通过的章程条款并未得到反对股东的同意,所以该章程修订的条款并不应当对股东进行约束。[2]通过是否经过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对章程效力进行类型化区分来确定其适用范围。钱玉林教授支持了该观点,并且将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另有规定”区分为股权转让的程序性规定和股权处分权的规定两类,认为初始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的程序和股权处分权作出“另有规定”;但章程修正案一般只能对股权转让的程序作出“另有规定”。[3]
对章程效力进行类型化的区分,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法理基础:第一,公司合同理论。该理论将公司章程定性为合同。对于初始章程,股东加入公司时有选择的权利,若不同意章程的内容可以直接选择不加入。相对于公司成立时通过的初始章程而言,章程修订条款的通过并不要求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合同自由是公司合同理论存在的必然逻辑,自由主义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灵魂。[4]根据公司合同理论,修订新增的限制条款,在没有获得反对股东同意的情形下,反对股东不受其约束,因此有必要对初始章程和章程修正案中条款的效力范围进行区别。第二,防止资本多数决的异化。对公司初始章程和章程修正案进行效力范围的区分,可以防止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利用其控制权修改章程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笔者认为,初始章程和章程修订效力类型化的区分只是一种理论上可能的划分,对于司法实践而言,这种划分并未对法官的司法裁判提供过多的指引和帮助,裁判者往往在章程修正案条款效力的判定上存在阻碍和困难。不能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是否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这种合意机制来认定其效力问题。[5]另外,防止资本多数决滥用可采取其他手段,章程类型化并非唯一选择。我国《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可以作为规制的手段。对章程效力进行类型化的区分,排除章程修订中对该条款投反对票股东的拘束力,并不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救济手段。最后,章程效力类型化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均存在一定的争议。对于章程修订条款效力的范围问题,是只对该投反对票的股东无效,还是对全体股东无效,并未形成统一观点。将章程效力作类型化区分只会把问题更加复杂化,并没有提供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路径。
(二)人合性保护和股权自由转让的法益衡量
从上述梳理的法院判决来看,部分法院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和股东自由转让股权的角度出发,来判定章程限制条款的效力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充分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和人合性。持此观点的法院几乎均以人合性和封闭性为由,认定公司章程的限制性规定理应合法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应当维护股东股权转让的自由。支持此种观点的法院,往往以维护股权流通的价值,保护股东的转让权利为由,认定公司章程相关的限制条款无效。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限制条款的效力判定,难免会对有限公司人合性和股东转让权利的进行利益的权衡。但是不管是人合性的考量,还是股东权利保护的考虑,司法实践中都有过于简单和片面的倾向。部分法院对于人合性法理的运用,过于简单和泛化。简单运用人合性法理,易使人产生对股权转让限制措施过度包容单现象。[6]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维护固然重要,但是不能盲目运用该法理进行利益偏向的判定。另一种倾向过于强调股权作为财产权的可转让性,认为股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则其转让原则上不受限制。此种倾向依据不仅过于片面,股权转让自由的原则不应当毫无限制。笔者认为,不管是人合性的维护还是股东权利的保障,都不应当过于简单和片面。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利益衡量,来简单判定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条款有效或者无效。
四、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股权转让限制条款的边界
我国公司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公司章程该限制条款的范围和边界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均存在分歧。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如何,假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不得转让股权但又不提供其他渠道导致股东实质上无法退出公司时,该条款是否有效?笔者认为,对于该类章程限制条款效力的判断,首先应当审查其合法性,并且引入合理性的审查标准,审查公司章程设限条款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正当性匹配。
公司章程股权转让限制条款首先应当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要求公司章程股权转让限制条款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公司章程限制条款应当具有合理性。合理性来源于美国法官创造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必须符合一定的合理目的。例如为维护公司的稳健运营,允许股东随意转让其所持有的股权,不利于公司人员的稳定。[7]如果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条款具备合理性,那么该限制条款就是有效的,反之则是无效的。[8]并且,公司章程设限条款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公司章程不得禁止股权转让或者具有实质上的禁止效果
假如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进行绝对禁止,不管是在公司成立的初始章程,还是后续修订章程中,都不应当承认其效力。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章程禁止股权转让的司法裁判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否定观点,然而,学术界却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持肯定观点的认为,在私法自治的原则之下,应当充分尊重公司的自治。持否定观点的认为,公司章程自治存在一定的边界,不能以此为由禁止股东转让股权。笔者比较赞同否定的观点,即公司章程不能禁止股东转让股权或者具有实质禁止的效果。《公司法》虽然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较大的章程自治权限,但是有限公司的自治应当存在一定的范围,不能导致股东实质上丧失了其拥有的基本权利。股权作为股东享有的一项财产权,应当受到法律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因此,该类禁止转让的章程条款应属无效。
第二,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设限须符合正当性目的
对于公司通过章程修订进行相关限制的条款,既不能轻率否定该条款的效力,也不能贸然承认其效力,而是要进行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审查。修改章程更多应该是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而非出于股东的个人私利,如果章程修订中添加的限制恶意对某些股东的权利进行限制与排斥,除非该股东本人知悉并且同意,否则缺乏正当性,应属无效条款。有学者认为,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得修改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9]对于章程修正案添加的限制条款,不应当贸然将其归于无效。在司法裁判中,应当通过个案分析该章程修订条款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其次,在实体上,应当审查公司通过修改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正当性理由。为了防止公司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行损害,要事先排除一些不正当限制股东股权转让的情形。例如,如果公司章程的修改是为了恶意排除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或者股权转让限制条款只是针对小股东,仅仅是大股东压榨小股东的手段,或者仅仅是为了某个或者某些股东的利益进行股权转让的限制,那么这些限制条款不具有正当性,不应当承认其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