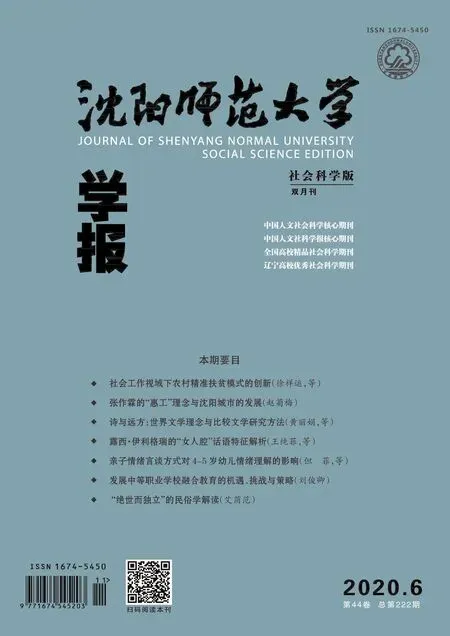诗与远方:世界文学理念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黄丽娟,赵 践
(1.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100089;2.沈阳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辽宁 沈阳110034)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关于世界文学的理念经常被引用,是他在1927 年与秘书约翰·彼得·艾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的谈话中提出的。歌德说他当时在读一本名叫《花笺记》(Chinese Courtship)的中国小说①《花笺记》于19 世纪传入欧洲。1824 年译成英文,1836 年译成德文。德国诗人歌德在1827 年2 月2 日至3日的日记中记述他读的是英译本《花笺记》。,他目视远方,感慨当欧洲人还住在森林洞穴的时候,中国人很早就找到了成百上千的真理,“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就这样,“世界文学”这个理念于7 000人口的德国小镇魏玛的一场对话中正式问世。在歌德看来,伟大的文学作品传递着人类共通的诗意精神,值得跨越国别界限传播,促进文化间的理解。
100 多年后,随着交通工具现代化,世界文学所依赖的地球似乎变得越来越小,各地的生活模式越来越趋同,失去多样性和本土传统。一位德国犹太裔美国学者面对世界局势,悲观地预测“最终某个单一的文学文化会在这个同质化的世界中绝地胜出”[2],而这与歌德百年前提出的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理念早已背道而驰。这位学者就是为现代比较文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他提倡采用语文学方法,从阐释历史时代精神与人的关系中发掘人类的思想发展谱系,用历史了解当下,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他借用圣维克多的修格(Hugh of Saint Victor)的话:“视家国独美者乃是幼稚新人,视他国为家者才强大勇敢,只有视全世界为异乡之人最为完美”[2]265,号召回到前民族国家的那种大同文化状态。奥尔巴赫认为将家、国、世界均视为他者,才是爱世界的路径。这看似矛盾和二律背反的结论其实有着深层内涵,值得品味,也是比较文学学者直到今天一直铭记并为之努力的学术立场。歌德与奥尔巴赫二人所构想的“诗与远方”的世界文学面貌可以说是“人类共同命运下的差异共存”[2]257,这也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同思想具有共通之处。
本文以歌德、奥尔巴赫的世界文学理念为起点,围绕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流变做一个学科方法发展谱系的梳理。正如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发生在欧洲反法战争时期①是在欧洲的历史转型时期,出现在欧陆各国寻求独立的过程中,如摆脱奥托曼帝国(Ottoman Empire)、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尤其是法国、俄国的过程。到了19 世纪20 年代,随着拿破仑征服欧洲,知识界开始谈论文化和民族差异,兴起反征服的文化思潮。歌德希求文学促进各国文化理解包容,法国的斯达尔夫人《论德国》《论文学》,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都开始放眼他国文学文化。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一直是古典时期以来效仿的典范,尤其在法国。在反拿破仑征服的文化抵制中,德国和意大利等开始关注自身文化、语言和文学的独异性,也就是各个民族文学的特质。,有着呼吁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特点,比较文学在诞生之时就伴随着一种焦虑感,即民族沙文主义与世界和平之间的矛盾危机,因此普遍精神和跨文化和平成为世界文学憧憬的文化景观。在历史的进程中,比较文学学者不断解读和调试种种文化危机,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也因此动态多元和兼包并蓄,充满活力,独具魅力。
一、“比较文学的危机”:从“科学性”到“文学性”的转向
1958 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教堂山分校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②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LCA 创立于1955 年,总部在巴黎,每三到四年召开一次大会。论文震惊了西方比较文学界,引起法美两国学者之间围绕比较文学理论之争。第二次大会堪称比较文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的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宣读了《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认为比较文学学科一直没有很好地定义比较文学的“主题对象和研究方法”[3],偏失了文学研究的轨迹。这篇论文如一石惊千浪,撼动了当时以法国学者为主创建的科学实证方法根基,引发了比较文学方法从注重“科学性”向注重“文学性”过渡。
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于19 世纪下半叶的欧美学界。有几个代表性事件标志着学科的初具雏形,分别是1886 年英国波斯奈特教授《比较文学》一书的出版、1870 年匈牙利梅茨尔创办《总体文学比较报》、1870 年代俄国彼得堡大学、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举办的比较文学讲座。比较文学从此正式成为高等学校常设的理论研究性课程[4]。一旦成为学科,就要对其研究进行定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有何不同?是比较的文学或文学的比较吗?是对不同国别的文学进行比较的研究吗?对此,学者们议论纷纷,众说不一,其中著名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在1903 年较有争议地指出比较文学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因为比较的方法是所有领域的研究都必不可少的,而且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尽管如此,19 世纪90 年代,在法国涌现一批比较文学学者,试图超越文学的国别界限,在不同国别文学之间搭建一座相互关联影响的桥梁。
一批法国学者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思想下发展并形成理论体系,法国一度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有戴克斯特(Joseph Texte,1865—1900)、贝茨(Lous Paul Betz,1861—1903)、布吕纳介(Ferdinand Brunetiere,1899—1906)、巴尔登斯贝格(Fernand Baldensperger,1871—1958)、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1871—1948)等,集大成者是梵第根,他在出版的《比较文学论》(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中,系统地总结了法国比较文学取得的成就,阐释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和历史。他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5],定义比较文学是两种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而总体文学是多国的文学运动和风尚研究[5]137-142。在巴尔登斯贝格和梵第根之后,承继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衣钵的是卡雷(Jean-Marie Carré,1887—1958)和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1921—2011),基亚将比较文学理解为“国际文学关系史”[6],而卡雷在《比较文学》的序言中,将比较文学定义为“一个文学史分支,是研究事实接触的精神的国际关系,如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沃尔特·斯各特与维尼生之间,在作品、灵感和不同文学的作家生活之间”[7]。法国学者形成的学派注重以科学实证的方法考察不同国别之间作家、作品的影响关系,即通常所言的影响研究,他们将文学研究扩大到了文学史+、国别文学+ 和个体作家+ 的研究范畴。
韦勒克的《比较文学危机》一文直指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弊端,指出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是在建立两种文学之间的“外贸交易”(foreign trade),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关注的是二流作家、翻译、旅行书籍、中间媒介,“人为地划分主题和方法,注重的是来源和影响,这种机械观念(彰显)的是文化国家主义的动机,无论多么宽容大度,这些对我而言,就是长久以来萦绕比较文学的危机”[3]167。其实,韦勒克所言的文化国家主义动机,指的是影响研究不可避免地追踪来源的发起者、中间的媒介、影响的接受者,从因果起落中要么强调来源方、要么强调接受方的文化优势,体现学者狭隘的国家主义和“奇怪的文化持有(cultural bookkeeping)现象”[3]167。韦勒克指出,比较文学要摒弃某一种文化的扩张主义或文化政治,“不论比较文学、总体文学还是文学,错误的观念是自设和圈定民族文学的理想。”[8]他认为,“比较文学有着无比的优势,抗拒民族文学历史的错误孤立”[3]162。
那么,韦勒克对抗死水一潭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解药是什么?首先,他强调要回归伟大的、当代的文学学术传统,视文学作品为存在差异的整体和符号结构,要综合文学理论、批评和历史这三种要素对文学作品或文学作品群进行描述阐释和评价,尤其要关注“文学性”问题。文学性是“审美的核心,是艺术和文学的本质”[3]169。他提倡对比较文学学科进行更为宽阔多维的定义,以真正的文学学术视野关注“价值和质量”。“如果说拉辛影响了伏尔泰、或者赫尔德影响了歌德的话,其意义是要知道拉辛和伏尔泰、赫尔德和歌德的创作特点,了解他们所处传统的语境,不断地衡量、比较、解释和区分,对二者进行批评”[3]168。其次,研究者要站在自我和他者双方的文化立场考察彼此影响,再借助和转向理论和批评,转向批评史。“尽管站在他者的文化立场会令学者产生失根感和精神流放,但是我们会获得唯一真实的客观性,直视客体的基本实质,去除狂热,融入紧密思考,达到解释,最后,价值判断”[3]171,这样文学学术就不会沉溺于陈旧的过去,不会成为国家信用和致谢的计算器,而是成为真正的想象行为,像艺术一样,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存留者和缔造者[3]171。
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韦勒克发表了一系列有建树的论文,不仅讨论比较文学学科和研究方法,还带动美国学界重新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超越单个国家局限的文学研究,不仅是文学间关系的研究,还研究知识信仰的其他领域,如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科学、宗教等”[9],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意义,“简单地定义,比较文学就是从一种以上的民族文学视野或者另一种甚至更多种知识学科研究文学现象”[10],形成强劲的美国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学派。1969 年《比较文学的主体与方法》(Comparative Literature:Matter and Method)中,阿尔德里奇(A.Owen Aldridge,1915—2005)将文集分为五部分,分别题为:“文学批评理论”“文学运动”“文学主题”“文学形式”和包括来源与影响的“文学关系”,总体而言,这些分类既延续和强调法国学派的跨国“文学”研究传统,还强调文学主题的重要性。1970 年,韦勒克又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从比较文学的谱系上进行了学理的追溯,重申比较文学不能局限于文学史而摒弃批评和当代文学,“批评不能与历史脱钩,因为在文学中没有中性的事实”[11],强调文学研究的三个分支历史、理论和批评之间彼此交织,“就像民族文学研究无法与文学总体脱钩或者至少在思想上不能脱钩一样”[11]20。在文末,他言道:“我反对一种方法,不是为我自己或为美国,我仅是遵从文学整体性的洞见,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划分是人为的,而且因果阐释方法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不过是无限的倒退……批评意味着关注价值意义,理解文本中吸纳的历史,批评史也需要这种理解,这意味着国际视野,目的是实现一个普遍文学史和学术的遥远理想”[11]36。
美国学派的形成与美国比较文学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密不可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大学如哥伦比亚、哈佛、耶鲁大学、加州大学等纷纷建立比较文学系,创办比较文学杂志。1949 年,《比较文学》杂志在俄勒冈大学创刊。与此同时,各大学相继成立比较文学专业或比较文学系,研究书刊也大量问世。1960 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正式成立,耶鲁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成为美国比较文学的重镇,韦勒克、列文(Harry Levin,1912—1994)、雷马克(Henry H.H.Remak,1916—2009)、阿尔德里奇等主要学者都集中在此。另外,二战后一批有着良好教育、多元文化背景、男性居多的欧洲逃亡知识分子将美国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耳熟能详的有奥尔巴赫、里奥·斯皮策(LeoSpitzer,1887—1920)、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韦勒克、乔弗里·哈特曼(Jeoffrey Hartman,1929—2016)、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等。也许是因逃亡而四海为家,也许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这些人认为学术研究不能以民族性为界限。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版了很多比较文学书籍,但由于各种批评理论的勃兴如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比较文学学者转而采用各家文学批评方法所长,变得重视理论多于文学,重视方法多于实践,形成对理论和批评过于依赖的风气。特别是20 世纪70 年代随着越战结束,社会上的嘲讽情绪和冷战思维肆虐,解构主义的怀疑风气甚嚣尘上,最时髦常用的词汇表达就是“并不清白无辜”,比较文学一经用这种理论实践,就失去了比较的根基,遇到了新的危机时刻,似乎比较的双方都是带着欺骗的面具,充满政治干预的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迎来了新的研究转向。
二、比较文学的多元文化研究:“文本化”向“语境化”的转向
在20 世纪70 年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再次面临危机。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指出,美国文学批评界陷入“当前的危机”,表现为文化的精英化、科层化、文学研究远离社会政治的现象。“文化”承载着意识形态,像一把大伞,圈定了内在与外在的边界。人文领域专研的学者钻在“文本的迷宫”[12]象牙塔中,与外部世界隔离,迷失在“误读”的解读中,批评成为装点欧洲文化价值的饰品,丧失了人文主义的意识。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也在20 世纪末期思考从前的世界文学问题,认为已经到了重新考虑人文研究课程设置的时候,改变文学研究仅仅关注西方文明的伟大作品现象,重新发明或发现美国的文化研究方法。他以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为参照,号召去除西方文明的种族中心主义思想,因为“在我们语境下更紧迫的是,任何世界文学理念都必然地要与第三世界文学的问题紧密联系”[13]。对处于西方外部的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会提供一种新的看待自我的视角,挑战自我印象。
在危机中,20 世纪80 年代比较文学研究迎来新的转向,“自1979 年以来文学研究有着巨大的重点转移,从文学的‘内在’修辞研究转向文学的‘外在’关系研究,将文学与心理学、历史或者社会学的语境关联起来。”[14]关键词由解构主义的文学文本化(texualization)转变为文化研究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将关注转向社会和社会文化的语境。在学理上,批评家抛弃解构的怀疑主义,重拾对语言的信任,认为词语具有模仿社会和反应世界的穿透力,人类书写作品彰显着权力、阶级斗争、压制女性、意识形态、族裔压迫等。即使在解构盛行的时期,比较文学研究也并没有完全被解构理论占领,如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尽管吸纳了解构主义方法,但她们重视背后的社会权力力量,挖掘被压抑和边缘化的女性声音。
那么什么是多元文化研究?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查尔斯·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1942—1998)总结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多元文化的政治表现为“认可民权运动、妇女运动以及认可包括国家和全球非西方少数族裔的文化,尤其边缘文化群体和多种再现传统”[15],是建立在语言“反应论”基础上的再现的自由,体现在:“第一,经典文学不仅再现欧洲高雅文化,还再现文学所生产的世界多样性。第二,被选到修正经典的作品应该再现创作中的多种文化。”[15]8文学研究领域拓展到从前边缘化的女性文学、族裔文学、旅行文学、传记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等,甚至进入经典文学作品未受重视的族裔文化与殖民因素。“多元”在很大意义上指的是关注文本中再现的各种形式的差异,如在文化接触中语言、宗教、种族、阶级和性别上的差异。在美国涌现出一批像萨义德、伯恩海默、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1942—)周蕾(Ray Chow,1957—)等具有两种或多种文化背景身份的批评家,将视野转向批判西方现代性主流文化。
多元文化批评改变了美国学界惯守的文学“文本化”阐释方法,是一次打破文本文类的等级秩序的一次解放风尚,发掘不同文本中再现的文化政治。在具有标志性的著作《东方学》中,萨义德条分缕析地从大量官方文件、札记、回忆录、田野调查稿本、诗歌、小说等不同类型的书写文本入手,发掘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所认识、表达和再现的东方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是欧洲文明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一种话语方式,有着自身支持的体系、词汇、学者、印象、教义,甚至有着自身的殖民机构和殖民方式”[16],是对东方的他者化。《东方学》的研究视角和批判方法“激励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文本的研究态度,促进了无数年轻的、通过其他路径政治化的学者获得新的探求方式和领域,尤其在文学领域”[17],展开从非西方文化和边缘文类中挖掘素材,进行文学研究的社会政治“语境化”批判。
与文化政治关联的“语境化”批评理论并非铁板一块,而具有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1945—)所指的跨国界“文化旅行”(travels culture)的动态特点。萨义德指出,一旦理论穿越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就会协调不同社会政治文化而改变,经过跨界移动、落地生根、适当调试、发生转化的过程,开始具有新的生命力。而比较文学学者穿越国界的旅行则有助于产生文化批判意识,这种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移置换位带来的遗产”[18],也是爱米丽·艾普特(Emily Apter,1954—)提倡的流放意识(exilic consciousness), 就像在战争期间流亡伊斯坦布尔的奥尔巴赫洋洋洒洒写下了《模仿论》一样。流亡造成了他与欧洲文化网络的疏离,流亡促成了其巨著《模仿论》(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的诞生,因为在欧洲文化学术传统笼罩下的个体学者往往要遵从研究技术伦理,而这又会束缚其文学学术视野。而奥尔巴赫空间位移让他感受到与母文化之间既认同又疏离的张力,能够以一种崭新的视野定位民族为场域单位的地点,思考欧洲与东方的边界,在与所处的其他实体地点对立中产生与共同体的确认、适应等反思。奥尔巴赫远离欧洲而他的作品又根植欧洲现实,流亡的特殊境遇促成了他对欧洲文化具体的批判。与源生文化有着血脉上的联系(filiation),但流亡促成的疏离和阻隔使其通过批判意识和学术作品带来后天联系(affliation)。
从事“语境化”批评对比较文学学者提出更高要求,要具有文化“批判意识”,维护价值和思想,进行“世俗的自我定位(worldlyself-situating)”。“批评者的个体意识不是自然轻松地成为文化之子,而是成为文化中的历史和社会的行动者”[12]15。在这种立场下,批评者的视野既有遵从所属文化环境的特点,还有一种批评的距离感,关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特殊语境与文本阐释生产的关系、文本自身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了解历史,认识社会语境的重要性,具有区分差异的解释能力”[12]15,这可能就是奥尔巴赫所呼吁的“爱世界”的方式,保持距离和批判意识,关注真实社会的世界和意识潜藏的文本,并不离弃二者中的任何一个[12]16,也就是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
三、中国语境下比较文学研究与外语学科的发展
“语境化”文化批评感召下,比较文学学者将学术视野转向文本中的西方他者,尤其是东方中国,如美国文化批评家詹姆逊、法国文学大师艾田蒲(又译艾田伯René Etiemble,1909—2002)等一些外国比较文学学者。在多元文化转向过程中,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参与到世界比较文学领域范畴。事实上,比较文学在中国20 世纪20 年代作为“学科”已经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陆续开设成“课程”,并有相应的教材成为读本。这一时期以译介法国学派为主,如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和《比较文学史》的中译本都于30年代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显著,出版的相关比较文学研究作品有:鲁迅《摩罗诗力说》、朱光潜《论诗》、梁宗岱《诗与真》等。在中国较早提出“世界文学”理念的是郑振铎,他提出“文学的统一观”。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以钱钟书的《管锥篇》为首,人文学界的诸大元老如宗白华、杨周翰、季羡林、金克木、范存忠、王元化等从各自研究的侧面,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视野,展现自己的研究观念和业绩。但真正作为学科在中国大学中持续繁荣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①1981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得以创办,此后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每3年在国内不同地区的高校举办一次。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成立,受批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培养点,90年代受批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点。。经过30多年的努力,目前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在国内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也培养出了大批后生新秀。大批西方包括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等文艺思潮的书籍得以译介和出版,奠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国内在中西文学关系和海外汉学家研究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如中德、中英、中美、中法等文学关系和海外汉学书籍,为跨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学界尤其在中西诗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创造性叛逆”的译介学和“文学变异学”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学者在世界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方法上的理论建树和方法创新,甚至有学者提出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构想,显示出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勃兴态势。
目前,在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进行了30多年后,国务院2017年对学科分类进行调整,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增设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为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打开了多语言的研究路径和维度。笔者认为,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发挥作用,填补这一学科的学术研究空间:第一,需要在学科史上与外国的比较文学学界衔接,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与世界比较文学的对话打下坚实基础;第二,需要译介世界上多语言的比较文学经典和新近成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气象、新观点、新方法;第三,需要发挥外国语言文学尤其是英语的语言优势,引领品读经典的原文理论著述,为构建中国外语人才的跨文化能力和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做出贡献。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新的全球化进程,为比较文学打开了培养多元文化主义、多语言的、跨学科、跨文明理解和全球意识的新空间,但与此同时英国脱欧、美国退出诸多联合国公约、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化燃起的某些国家民族主义傲慢情绪甚嚣尘上,比较文学学者发现跨文化理解和交流即使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研究,歌德和奥尔巴赫所感召的世界文学理念仍然是“未完成的工程”,“诗与远方”仍然如迷雾中的灯塔,吸引着比较文学学者踽踽前行,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