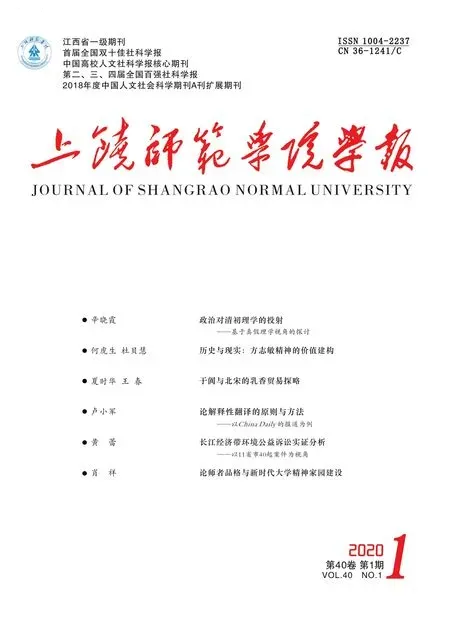革新、反叛与理性回归:北山学派的《诗经》研究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北山学派是指南宋后期到元初兴起于婺州地区的朱子学流派,以北山四先生为主,他们是朱熹弟子黄榦的嫡传。吕祖谦在时,朱熹曾到金华丽泽书院讲学,吕祖谦殁后,其弟子往依朱熹。朱熹的弟子黄榦在婺州讲学多年,一传于何基,二传于王柏,三传于金履祥,四传于许谦,人称“北山四先生”。北山学派之得名,是因学派开创者何基居于金华之北山,是以别于吕祖谦创立的金华学派。北山学派虽承朱子之学,然何基为学传承师法,谨言自守,黄宗羲在《北山四先生学案》案语中说:“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引何文定语中有:“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1]北山学派虽用功于四书,但于《诗经》研治方面亦有一定的影响,王柏和许谦尤有可表彰之处。
一、北山学派对朱熹《诗集传》的传承
婺州北山学派,所传皆以朱子之学为特色,于《诗经》研究,无不以《诗集传》为祖,它代表了宋学的最高成就,在《诗经》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毋庸讳言,其贡献和对后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诗集传》在《诗经》研究史上能取众家之长,释解经意,简明扼要。朱熹虽是理学家但于《诗》的释解不尽是讲义理,而是集众家之长,删繁就简,其书最大的特点是辞约而意明。故朱子之著《诗集传》,代表了自汉以来研究《诗经》的最高成就,使其他研究者黯然失色,王应麟在《诗考序》中云:“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学者讽咏涵濡而自得之,跃如也。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2]以前汉人注经,动辄万言,唐人作疏,亦为不简,朱熹则删繁就简,就像他在《诗经传序》中所言:“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3]
其次,《诗集传》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以大胆改革创新的新思想。在思辨学风背景下对《诗经》的研究成果,他对前人的研究有许多自己的反观理解,也有矫枉过正之失。郝经《诗集传序》曰:“时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衷,集传注之大成,乃为《诗》作传,近出己意,远规汉、唐,复《风》《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糞训诂之弊,定章名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复,而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也。其自序则至孔、孟及宋诸公格言具载之,毛、郑以下不论。其旨微矣。是书行于江汉之间久矣,而北方之学者未之闻也。”[4]朱熹不满于汉、唐的训诂音韵之学,对宋代欧阳修、苏辙、二程《诗经》亦为不满,对东莱吕伯恭父集诸家之说而为的《读诗记》亦有不同看法,故发挥义理。杨慎《升庵诗话·诗小序》曰:“朱子作《诗传》,尽去小序,盖矫吕东莱之弊,一时气信之偏,非公心也。马端临及姚牧安诸家辨之悉矣。有一条可发一笑,并记于此。小序云:‘《青莪》,乐育人才也。《子衿》,学校废也。’《传》皆以为非。及作《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疑问。’又曰:‘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先生曰:‘旧说亦不可废。’此何异俗谚所谓‘玉波去四点,依旧是王皮’乎?”[5]朱熹打破了汉宋界限,而能集之大成,虽名集传,然并未集录众家之说,只是阐发己意,发明主张,于文学亦多有阐发。
其三,北山学派对《诗集传》的接受,在继承的基础上亦有补充和新解。朱熹《诗集传》涉及到一个后世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淫诗”问题,朱熹把《诗经》中我们今人认为的爱情诗说成是不合伦常的“淫诗”,到了北山学派的王柏,竟然冒犯经典,以为传世之《诗经》并非孔子那个时代所定之本,是后儒所乱,故应删去这些“淫诗”。朱彝尊跋曰:“自朱子专主去《序》言《诗》,而郑、卫之《风》皆指为淫奔之作,数传而鲁斋王氏遂删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秾矣》《甘棠》于《王风》。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删者,鲁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变易者,鲁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渊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议,则亦无是非之心者也。”[6]从孔子到朱熹都是议而存之,提出不同的看法而已,而王鲁斋大胆革新,毅然去之而后快,在他的心目中,经典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不再是那么神圣庄严了。王柏在其《诗疑》卷一末云:“或谓《三百篇》之诗,自汉至今,历诸大儒,皆不敢议,而子独欲去之,毋乃诞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诸儒,尊尚《小序》太过,不敢以淫奔之诗视之也,方附会穿凿,曲为之说,求合乎序,何敢废乎?盖序者于此三十余诗,多曰刺时也,或曰刺乱也,曰刺周大夫也,刺庄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晋乱,刺好色,……在朱子前,诗说未明,自不当放,生朱子后,诗说既明,不可不放,与其尊汉儒之谬说,岂若尊圣人之大训乎!”[7]看来王柏比他的祖师爷走得更远,圣人孔子在他心目中是那么完美,怎么会把这些乱情之诗编入经典呢?一定是汉儒之所为,故必去之。
到了金华朱子学的最后一位传人许谦,所撰《诗集传名物钞》,在《诗》学研究上比他的前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吴师道在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序中云:“公念朱《传》犹有未备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见,要旨精义微旨,前所未发。”[8]363钱曾《读书敏求记》曰:“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十二卷,朱子之学一传为何基、王柏,再传为金履祥、许谦,授受相承。白云一代大儒,其于诗专宗朱子,泛扫毛、郑之说,未知今之三百篇,果非夫子之旧欤?”[8]363-364《四库全书总目》曰:“谦虽受学于王柏,而醇正则远过其师。研究诸经,亦多明古义,故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缺憾。”[8]364《郑堂读书记》曰:“白云受学于王鲁斋,为朱子四传弟子,以朱子《诗集传》犹有未备者,因旁搜博采,以成是书。中多引鲁斋及金仁山之说,附以己见,颇有精义微旨。又以《小序》及郑氏、欧阳氏《谱》世次多舛,一从朱子确定。正音释,考名物度数,粲然毕具,足以羽翼朱《传》于无穷矣。”[8]364从吴师道的《序》,到后世学人对许谦《名物钞》的评价,足见其在《诗经》研究史上的学术价值,从中也可以看出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许谦虽处理学时代的氛围中,但其研究《诗经》的态度较为审慎,体现出理性中的求实学风。
二、王柏的反叛性
王柏之学除受其师影响外,从家学而言,自幼的熏陶也非常重要。据《宋史》所载,王柏的祖父曾和朱熹、朱栻、吕祖谦等人交游,父亲王翰和叔伯辈,皆及朱熹、吕祖谦之门。王柏师从何基,而何基从黄榦处得朱熹之传,他亦曾多次拜访朱熹弟子杨与立、刘贵(执堂)之门。故言王柏之学与朱熹渊源深厚,有人说他是朱熹的第三代传人,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太极的认识上,他承袭了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论,在秉承经学传统时,由传入经,多与前贤所论不同,以求恢复经学的本来面目。但在追求经学之本中不能没有疑惑,有是非争论时以心解就多有辨惑。
于《诗经》研究,王柏著有《诗可言》二十卷、《读诗记》十卷、《诗疑》二卷。《诗可言》是评诗之作,类似于诗话,所评论者均为理学家之诗,且多为朱子师友之诗。王柏评诗,主张张扬《三百篇》之教化。其书虽佚,但金履祥的《濂洛风雅》多有称引。《读诗记》早佚,未见时人称引,不知其详。流传至今的《诗疑》为十篇短文,亦名《诗十辨》,即《毛诗辨》《风雅辨》《王风辨》《二雅辨》《赋诗辨》《豳风辨》《风序辨》《鲁颂辨》《诗亡辨》《经传辨》。王柏对《诗》的批评原则是“非敢妄疑圣人之经也,直欲辨后世之经而已”[9]289。他对孔子所编撰的《诗三百》没有异议,但孔子之后儒各阐其义,“及其专门之学兴而各主其传,训诂之义作而各是其说”[9]289,怀疑后世这些学者曲解了圣人之意,只是希望能还原其本。从《诗疑》十篇中可以看出他承朱子之诗学观,废《序》并遵循其“淫诗”之说,并比朱熹走得更远。在南宋的《诗经》研究中,王柏的许多特色创见集中体现在《诗疑》之中。
其一,《毛传》多不可信,《小序》亦应弃之。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认为《毛诗》流传过程中,有亦步亦趋者,有不以余力攻击者。其书《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曰:“《毛诗》者,出毛公。……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注》,郑玄作《笺》,于是《毛传》大行于而三家废矣。魏王肃又述毛非郑;王基驳王申郑;孙毓为《诗评》,评毛、郑、王肃三家同异而朋于王;陈统又难孙申郑。王、郑两家互相掊击,皆本《毛传》。自汉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别为之说者,有之,自欧阳修《诗本义》始,于经义毫无裨益,专务新奇而已。修开妄乱之端,于是攻《小序》者不一其人,攻《大序》者不一其人;若毛诗、郑笺,则弃之如粪土矣。至程大昌之《诗论》,王柏之《诗疑》,变本加厉,斥之为异端邪说可也。”[10]王柏认为《三百篇》非周公孔子之旧,年时久远,其中肯定有脱简淆乱之处,况且秦焚诗书,其祸惨烈,亘古所无。王柏在《诗疑·毛诗辨》中分析道:“汉定之后,《诗》忽出于鲁,出于齐、燕。《国风》《雅》《颂》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无脱简淆乱而尽复乎周公、孔子之旧也。”[9]289“今不知《诗》之为经,藏于何处所乃如是之祕,传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祸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圣人之旧,无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诗》《书》同祸而存亡之异遼绝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9]290经秦焚书坑儒之后,到西汉怎么会突然出现一部完整的《诗三百》,这怎么可能呢?按常理也思之难解,此王柏之所疑也。
对于《诗》之《小序》,王柏以为纰缪甚多,当予弃之。《邶风·凯风》一诗,《小序》曰:“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11]301《郑笺》曰:“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责之意。”[11]301朱熹顺承《诗序》《郑笺》之说,释解道:“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诗。”[3]23朱熹这么一说,后人便以为是此诗表达的是儿子劝母不要再嫁之意。王柏不悖朱子之意,认为:“《凯风》之诗,孝子之心至矣,其为词难矣。是诗也,寄意远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深切,可谓能几谏者也。此孝子自责之词。《序》曰‘美孝子’,何其谬哉!”[9]273-274还有许多篇章,王柏认为《毛传》的解释都太勉强或根本有误。他以为“说《诗》者不费词而诗意自见,此妙于说诗者,当以圣贤为法”[9]283,并极力推崇朱熹等理学家们的解释。
其二,《诗》的排列顺序为后儒所乱。他认为《诗经》的许多篇章内容都有错乱的现象,存在很多问题。王柏认为《鲁颂》存在篇章颠倒错乱的问题,他通过考证进一步证实了这种错误。《诗疑·鲁颂辨》曰:“愚尝即其诗而熟味之,固不敢以为非僖公之诗也。意其间有颠倒错乱之误,是盖传之者之过也。……又窃意‘土田附庸’之下,词气未终,血脉不贯;当以‘公车’以下九句接此为一章,继以‘泰山岩岩,保有凫绎’两章,于此,伦序方整,既不害其为僖公之诗,亦不妨以为伯禽之事。欲以‘鲁侯是若’为前段之终,后段自‘周公之孙’起,止‘万民是若’终,前为四章,后为四章;‘周公之孙’‘福女’为一章,‘秋尝’止‘有庆’接‘天锡公’止‘兒齿’为一章,三‘俾’自为一章,‘徂来’之下自为一章。古人作诗,章句虽重而有味,条理虽宽而实密,必不如是之断续破碎也。”[10]298-299王柏认为这种错乱现象是在《诗经》的流传过程中造成的,主要是汉人所为,不但有章节的错乱,还有篇次和章次的错乱。比如《二雅》中有些诗篇就不属于雅诗的应用范畴,而应当归之于《王风》之中。王柏的反叛不同一般,有些地方甚于他的祖师,他大胆地认为《风》《雅》《颂》的归类有误,《豳风》七诗不当在《风》诗,而应归入《雅》诗。因为从周公的教化辐射范围来说,是从西北而波及于东南。王柏以为《鸱鸮》这首诗是“周公之诗也,固已降而为风矣,但系之于豳,非也”[9]292。既然是周公之诗,就应当归于《雅》诗一类。王柏之言虽有些叛圣,但所言在理,亦不为过。
这种排列次序的错乱还表现在错简上,在王柏看来,《诗经》章次错乱的现象很多,《行露》首章就属乱入。《诗疑》言:“《行露》首章与二章意全不贯,句法体格亦误,每窃疑之。后见刘向传列女,谓‘召南申人之女许嫁于酆,父家礼不备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讼之于理,遂作二章’,而无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乱入无疑。”[9]273还有“《硕人》之诗,前三章意已足,后一章体制不类”[9]273,后面一章也是串入。再如《诗疑》:“《下泉》四章,其末章全与上三章不类,乃与《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错简也。”[9]280“《东方未明》之诗,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与上下意不贯,未必本文也。”[9]278
其三,今所传《诗》,并非圣人所撰之《三百篇》。王柏在《诗疑·经传辨》一开头就说:“自咸阳三月之炎熄而经已灰,后世不幸而不得见圣人之全经也久矣。出于煨烬之余者,率皆伤残毁裂而不可缀补。经生学士不计于缺疑而恥于有所不知,又不敢诵言其为伤残毁裂之物,于是研精极思,刳剔揍饤,雕刻缋藻,日入于诡,而伤残毁裂之书又从而再坏矣。”[9]301他认为,秦火之后,五经支离不堪,《诗》之《风》《雅》《颂》岂能幸免于难。当年项羽兵入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12],文化典籍,损失惨重。“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蹐驳,不可胜言”[13]。所以,汉初传《诗》者有齐、鲁、韩,后又有毛公,今古文派各有师法,同源而异流。故王柏言:“汉之刘歆得见闻之近,乃谓‘《诗》萌芽于文帝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以为《雅》,或以为《颂》,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其讽诵之余,追残补缺以足三百篇之数尔,乌得谓之独全哉!”[9]301王柏认为,不是孔子所编撰的《诗经》本身有问题,而是汉儒各尊师说,传授过程中字句或有异同,其他经典皆有增减出入,“安得指《国风》三十二篇为汉儒串入也!王弼之《易》,杜预之《左传》,以传附经,离其章句;郑玄《礼记目录》与刘向《别录》不同:亦咸有旧说”[9]306。《诗》在流传的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前人只是怀疑而不解,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陈鹏飞作《诗解》二十卷,就不解释《商颂》《鲁颂》,认为《商颂》有缺,《鲁颂》当废。而王柏比陈鹏飞来得更为彻底,竟为删之而后快。
其四,郑卫之音的“淫奔之诗”应予删去。《国风》中有些“淫奔之诗”,孔子的态度是“放郑声”,但孔子并没有直接删去,王柏认为这些诗是后儒串入的,不是孔子之所撰之本。朱熹把《国风》中有些情爱诗说成是“淫奔之诗”,他认为《诗经》有二十八篇诗为“淫奔之诗”,孔子未删,目的在于“垂诫后世”,警示世人,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王柏竟认为《诗经》中有三十二首属于“淫奔之诗”,应该全部删去。他认为这些应该删去的诗具体篇目为:
野有死麕(召南)、静女(邶)、桑中(鄘)、氓、有狐(并卫风)、丘中有麻(并王风)、将仲子、遵大道、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东门之埤、丰、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大车、晨风(秦)、东方之日(齐)、绸缪、葛生(并唐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并陈凤)。[9]286
所删之篇目,《诗疑》前面说是三十二篇,但后面所列之目仅三十一篇。这些“淫奔之诗”,以前学人太尊《小序》,不敢把它们归入淫奔之诗,只是附会穿凿,以求合于《小序》。王柏认为朱熹已经订正是非,“今后学既闻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为谬,真知是诗之为淫,而犹欲读之者,岂理也哉!在朱子前,诗说未明,自不当放。生朱子后,诗说既明,不可不放。与其遵汉儒之谬说,岂若遵圣人之大训乎!”[9]287当然,王柏思想比朱熹更为激进,但其实并未付诸于实施,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一点是无疑的。《诗疑》卷一曾明确地说:“愚敢记其目,以俟有力者请于朝而再放黜之,以洗千古之芜秽云。”[9]285《诗经》是古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代表着社会的上层建筑,非其他经典可以随便删改,需要朝廷出面,皇帝御诏不可。想法可以有,但要付诸实践,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王柏主张删去这些“淫奔之诗”,具有革命性的反叛精神,然出发点是善意的,目的在于卫道,是为了纯洁《诗经》,以达到更好地教化作用。后人说他非圣无法,狂妄自大,其实是误解了他的初衷。
三、许谦回归理性的趋势
许谦是北山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生于宋末,父殁而由母氏教养,历宋亡而至元,无心政治,隐居乡里,开馆授徒、著书立说,发扬儒学。受业于王柏、金履祥,四十余年都在教书,著录及门弟子千余人,为“北山四先生”之一,去世后,谥文懿,江浙行省请朝廷建四贤书院,与何基、王柏、金履祥同列学宫。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读四书丛说》二十卷、《读书丛说》六卷、《诗集传名物钞》八卷、《白云集》四卷等。《名物钞》的主要传本有明代秦氏雁里草堂钞本、《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日本《昌平丛书》本等。在文献整理方面,80年代,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集成新编》中,就收有排印的许谦《诗集传名物钞》,这是比较早的整理本。而李山的《诗集传名物钞诗缵绪》,是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献整理本,收入《元代古籍集成·经部·诗类》的第一册,也是研究许谦《诗经》研究的基础文献。近几年来,对《诗集传名物钞》作较为全面研究的是雍鹏的硕士论文《许谦及<诗集传名物钞>研究》[14],另有一些其他文章也有涉及到许谦《名物考》的研究。许谦为朱熹的五传弟子,是元代《诗经》学宗朱派的代表,由于时代的变迁,他的治学风格也与其师有明显不同,正因于此,他的《诗》学研究有着改变风气的作用。
首先,回归理性,偏重名物、音训、训诂。从学理上来说,许谦师于王柏,秉承了宋学的怀疑之风,但在经学思想上,与其师却不尽相同。由于王柏的思想过于偏激,研究《诗经》太过武断,连至高无上的经典也怀疑。夏传才在《诗经研究史概要》中言:“宋学怀疑学风由王柏发展到高峰,就跌落下来,开始向反面转折。”[15]而许谦以考证事实为基础,说解《诗经》,承朱熹之《诗集传》的权威,并有补充,所考名物音训,搜罗前儒旧说,解说平和醇正,在《诗经》古义解释上,可以补充朱熹的缺遗。同治年间,同郡后学胡凤丹为《诗集传名物钞》作序道:“为学受业于王柏,而又醇正则远过其师,研究诸经,亦多明古义。故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补集传之阙遗。至卷末谱作诗时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说则改从集传,盖渊源接受,各尊所闻之义也。”[16]47这个评价较为公允。在《诗》学史上,汉儒就致力于文字训诂之学,南北朝《诗经》释解中的有了名物研究,初唐有了陆德明对《诗经》的反切注音。许谦所处的元朝,学术氛围整体上来说比较薄弱,所以他的《诗集传名物钞》显得更有特色,他的《诗》学以朱熹《诗集传》为宗,也遵从了其师王柏的观点,在卷三《溱洧》之下把淫奔之诗也罗列出来,如“卫淫奔之诗”九篇、“郑淫奔之诗”十四篇,显示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在后面注释道:“愚窃谓《风雨》为思君子之诗,《扬之水》谓兄弟相保之诗。”[16]69再就是在书中对部分名物有所考订,比如对“芍药”的考订。还有对民俗的阐释,比如郑国三月上巳,于水边祓除不祥。许谦于《诗经》的研究中征引资料比较广泛,大量采用了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孔颖达《毛诗正义》之说,并不据守师法。在《诗集传名物钞》音训中,多引《释文》,如释《玄鸟》:“祜酤,本皆侯五反,传于酤有叶字,恐误。……《释文》:员音圆,又音云。……家说:《毛诗》诸诗注,景训大,员训益。《释文》:河,本作何若,依此训此文。则是大益维何问辞,下则应辞也。”[16]298音训时还溯其源头,有根有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诗集传》这方面的缺憾。
其次,释解《诗》中名物,泛列各家,追求事实,有考据倾向。宋人治学虽以说理为主,多是擅长论辩,作为许谦祖师的朱熹对汉儒的治学方法也不敢全然否定,对训诂也比较重视,他在《答张敬夫》中说:“秦汉诸儒解释文意,虽未尽当,然所得益多。”[17]卷三十一对汉人的治学方法也不敢小觑,他在《语孟集义序》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传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17]卷七十五他在《诗集传名物钞》卷一《广汉》之下,对汉水有详尽的考释,从《水经》郦道元之记、《汉书·地理志》到杜祐《通典》,不厌其烦,广征博引。在宋代理学大潮中,倾向于作训诂、考证者不乏其人,主要有程大昌、王应麟等人。程大昌的《考古编》和其中的《诗论》都属于考据性的著作,王应麟学识广博,所著《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诗考》《诗地理考》等,考证范围更广。元人总体上守宋,经学上少有进展。许谦虽是在朱熹《诗集传》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完善工作,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鲁颂》:“传:《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蒙、羽,二山名。《蔡传·地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阴县西南,今忻州费县。羽山,在东海郡祝其县南,今海州朐山县。费,兵媚反。朐,权俱反。前编武王灭商,封周公于鲁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留相周。武王崩,成王立,元年,周公摄政,命伯禽代就封于鲁。郑《谱》:鲁者,少昊挚之墟,国中有大庭氏之库。《疏》: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16]290于此可见《诗集传名物钞》之一斑,诸如此类的考证,书中很多,在元儒的同类《诗》学著作中,许谦之作堪称上乘。
北山学派除四先生之外,许谦门人范祖斡对《诗经》也有所研究,他著有《读<诗>记》,但成就不大,不名于当时,兹不赘述。其他门人弟子多致力于朱子四书学的研读,亦有部分在《易》学方面有一定造诣。正如百家(1)百家:即黄百家,黄宗羲第三子,撰《天文志》《历志》数种。百家承父学,其父晚年著述,多有口授,百家代书。父撰《宋元学案》未竟而逝,今所见100卷《宋元学案》为他和全祖望续成。谨案所言:“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1]2801金华朱子理学较多地保留了正统朱子之学,对理学北传以及明初理学的开启都有很大作用。
——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