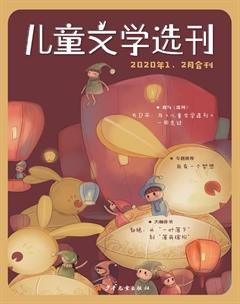日子
正是八月初热死人的天气。田埂上原本乌亮潮润的田泥早已被晒得焦硬发白,一脚踩上去,就像踩在河滩边那一颗颗硬邦邦的鹅卵石上,硌得脚生疼。田蓝提着一只装满饭菜的竹篮子,头扣一顶汗渍斑斑、早已辨不出颜色的破草帽,眯着眼走在白晃晃的反着太阳光的田埂上,她是赶着去给正在田头忙活的爹娘送饭呢。
“这鬼天气,真热!”田蓝用袖子擦了一把脸,忍不住骂了一声,但她立即缩住了话头。还好娘不在身边,要是让她听到了非挨骂不可呢。田蓝知道,这时候的天气是骂不得的,越热,太阳越大,村里人便会越发地欢喜。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早稻成熟收割的季节,有一段好好的日子,割下来的稻谷就能好好地晒它个透干。只有颗粒归仓了,村人们半年的辛劳才算没白费,大人小孩子全都吊着的一颗心才能好好地松松劲呢。所以,在这种鸡狗都热得安安静静、不肯发出一点儿声音来的大正午,爹娘却是一口气也不敢歇的。
一想到此刻正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爹娘,田蓝的心突然就有了一种收紧的感觉。“唉,也不知哥他这次到底怎样了呢。”田蓝望望眼前沉甸甸地弯着腰身、等着主人来收割的大片大片黄灿灿的稻谷,在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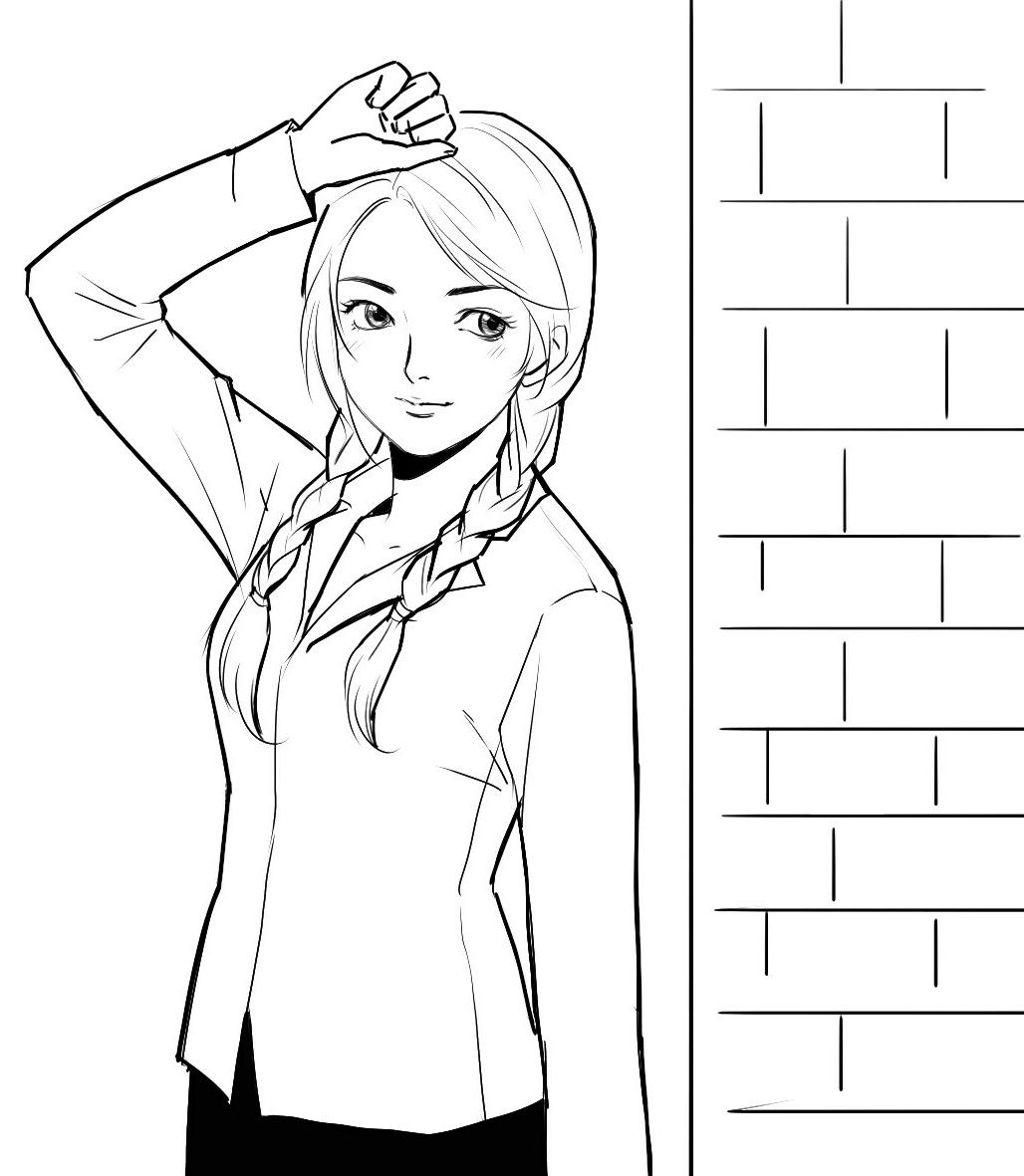
远远地望见了自家的那片田地,一半的地已经空了,割下的稻谷一排一排整齐而柔顺地躺倒在裸露着黑色胸膛的土地上。爹娘呢,却没在田地里。田蓝抬眼找时,却见娘坐在旁边空地的一棵大樟树下,正朝她挥动着手中的草帽呢。爹坐在娘的旁边,好像在吸着旱烟,一面好像还在朝她笑着。
田蓝奔过去,脚上穿着的一双旧凉鞋剪成的拖鞋发出一阵啪啪啪的声响,在干燥的田埂上拖起一股浓浓的灰尘。“爹,娘,饿了吧,快吃!”
爹娘的脸晒成了一种黑红黑红的颜色,上衣早已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两人都赤着脚,裤腿高高地卷起,小腿和裤管上溅满了点点泥星。
娘接过篮子,一边端出饭菜,一边问:“哥回来了没有?有没有晓得结果?”
问话时娘脸色平静,爹却有点儿慌神,一下子拔出含在嘴里的烟杆,睁大眼睛盯着田蓝。
田蓝心里又无端地收缩了一下。长到十五岁,她早已熟知娘的性情,娘心里越紧张,脸上就越是平静。娘是一个罕见的女人,村子里的人都这么说,田蓝当然更是这么认为。娘心里有一种东西,一种奇怪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家里的一切都靠这种东西支撑着,田蓝和哥哥田亮的命运也被这种东西支撑着,甚至支配着,丝毫动弹不得。
“他还没回来呢,你们不用着急,我哥那么用功,会有好消息的!”田蓝用草帽使劲给爹娘扇着风,说道。
娘不再说话,埋头吃饭,爹却忍不住叹了一口氣。娘看他一眼,眼光锥子一般。爹立刻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低下头去。
爹总是这样,不太像爹,倒更像是娘的又一个孩子。田蓝将目光调转开去,望向收割了一半的寂静无声的田野。正午的太阳正发出最灼热的光芒,威力无穷,不可仰视。劳作的农人三三两两聚向近旁的树阴处,吃饭,小憩,以迎接即将开始的又一轮极耗体力的劳作。
突然,田蓝的目光被娘弯腰夹菜的动作吸引住了。娘屈腿坐在地上,身子略略地倾向一侧,她伸筷子夹菜的时候,腰身自然地向前舒展着,一眼看去,竟呈现出一幅说不出的优美动人的图景。天哪!这不就是秦文所说的“线条”吗?田蓝一下子看呆了。
升入中学以后,班上的女同学开始神神秘秘地在背地里谈论“线条”。被大家公认的“线条”理论专家是文娱委员秦文。有时在路上走着,迎面走过来一位女子,秦文便会贼眉鼠眼地做手势,提请大家“注意观察”。等人家刚刚走过,她就会迫不及待地发表评论,有时是说“胸部不挺,缺乏女性魅力”,有时是说“腰部太硬,难觅弱柳扶风的韵味”。
有一阵子田蓝对秦文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因为“弱柳扶风”一词。她问秦文:“你从哪儿学来这么好的词呢?真好!”
秦文看她一眼,说:“《红楼梦》。”
田蓝傻乎乎地问:“《红楼梦》?是一篇文章吗?”
秦文笑笑,说:“就算是吧。”田蓝知道自己肯定错了,但秦文的神态令她不好意思再发问。秦文的爸爸就是她们这所学校的校长。作为校长的女儿,秦文有时会有一点儿小小的傲气。但平心而论,秦文确有傲的资本。据说她从小就极爱读书,并且过目不忘,而这些,都是受她的校长爸爸的熏陶和影响。
有时在校园里走,远远地望见秦校长依然年轻挺拔、极富魅力的背影,田蓝心里总会莫名地想起自己爹爹那劳苦而衰老的、在田地里永不停歇地劳作着的身影。原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有这样大的不同的啊。那么,若干年以后,自己和秦文之间是不是也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大的不同呢?会吗?
就像爹没法跟秦校长相比一样,娘也是没法跟秦文的妈妈相比的。秦文的妈妈是乡文化站的干部,皮肤白皙,衣着时髦,可惜她却过早地发福了,哪里像娘呢,至今保持着这么好的一副身段!
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注意过呢?田蓝呆呆地望着娘的腰身“弱柳扶风”一般(她坚信这就是“弱柳扶风”)在眼前轻盈地动来动去,心里突兀地跳上来一个想法:娘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极其出众的女孩,是一个美女!当初她怎么会嫁给爹的呢?爹比她足足大了十岁,还是那种老实得话都不肯多说半句的人!
“发么子呆?回家去!兴许你哥也回来了。”田蓝被娘的话一声喝醒,本来热得发红的脸一下子更红了。她有些愧疚地望望爹那黑瘦黑瘦、布满皱纹的面孔,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想法。娘为什么不能嫁给爹?爹是多好的一个人哪!隔壁花婶总说爹“心善得跟观音菩萨一样”,爹真的是一个好人!
“我暑假作业快做完了,你们歇歇,我留下来割禾。”田蓝说。
“你这死姑俚想气死我!就要升初三了,还割禾!还不给我回去!”
“是啊是啊,就要升初三了,回屋里念书去,禾我跟你娘割就行。”
哼,爹从来都是这样,只会帮衬着娘说话!
田蓝提着爹娘吃剩的空碗往回走,只觉心里头堵得慌。抬眼看着,哪家的田头地里没有小孩子在帮着干活呢?特别是在这赶时如救火的收割季节。可偏偏她家,只看见两个老的忙死忙活的身影。两个孩子呢?一个到镇上的学堂看高考分数去了,一个则被成天关在家里念书——为着一年以后能顺利考入师范学校。这是娘给田蓝定下的硬性目标。
“蓝姑,送饭去啦?”抬头一看,是花婶,提着一个竹篮子,也是去送饭吧。
田蓝点点头没说话。
“你哥回来了没?分数晓没晓得?”
田蓝摇摇头,仍没说话。
“你哥回来了叫他到地里帮着点!那么多地,两个老的哪忙得过来!你呢,也帮着点,大姑娘家,别太不晓事!”
田蓝急起来,说:“我是要留下割禾的,我娘她不让!”
花婶叹口气:“你娘那个性子,真是作孽!也不晓得图个啥?乡下人就这个命,她一天到黑拼死拼活的,两个伢崽倒养得像城里的娇少爷娇小姐,图个啥呢?”
田蓝低下头,心里又开始难受起来。
在他们兄妹两人念书的事情上,娘从来都有着一种固执的,甚至是可怕的决心。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决心,但却坚硬无比,似乎任何时候都能触摸到它那铁榔头一样的冰冷的质地。谁也不知道这种决心从何而来,村里人有羡慕的,有不理解的;当然更有说风凉话的。娘一概不理不睬,我行我素。这是娘身上唯一的与这块士地格格不入的地方。
哥哥田亮已经念到了高中毕业,这是十几年来村子里出现的最高学历了。花婶的两个儿子,都只念到小学毕业呢,现在已成了田里的好帮手了。可娘还不满足,她一定要哥哥拿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给她看看。至于田蓝,娘一再地跟她说她应当考上师范,穿上秦文姑娘穿的那种连衣裙,到县城里去念书。
娘是在一次到镇上赶集时见到秦文的。那时田蓝、秦文,还有同班的几位女孩一起在集市上闲逛,娘看到秦文时眼睛一亮。秦文松松地编两根辫子,穿一件雪白的直拖到脚腕儿的连衣裙,清纯美丽得如同一个小仙子。在田蓝喊过“娘”,另外几个女孩子依次喊过“阿姨”后,娘一把拉起秦文的手,说:“这姑娘真俊!叫个什么名字?”
秦文礼貌地笑着,说:“叫秦文。”一边轻轻抽出自己的手。
田蓝站在一边,赶紧说:“娘,她是我们校长的女儿。”
娘一愣:“校长的女儿?秦校长?”
秦文奇怪地看着她:“你认识我爸爸?”
娘笑了:“秦校长啥人不晓得?他是我们这块儿的名人嘛。”
打那以后,娘就总是夸奖秦文长得好,懂礼貌,不愧出于知书达礼的人家。这些话田蓝却不是很爱听,因为秦文从娘手里轻轻抽手的动作一直令她有一種心痛的感觉。
田蓝是晓得娘认识秦校长的,因为为哥哥复读的事,娘曾到学校去找过秦校长。当时田蓝曾为娘的举动感到过震惊。娘一个大门不出的乡下妇女,居然要去找校长求情!娘翻出压在箱底的簇新的蓝竹布衣裳,换上干干净净的镶有一道耀眼白边的圆头黑布鞋,对惨白着一张脸的哥哥说:“只差两分,不要紧,再读一年就好了,再读一年一定能上。我去找你们校长,求求情,让你再复读一年。”
哥说:“我不读了,你别去,谁会听你的!”
娘说:“校长也是人,讲人情的,我好好求他,总会有用的。”
田蓝和哥哥都没料到,娘求情居然真的求成了!并且,还听说秦校长同意免收补习费!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可是,娘却死活不同意,说人家校长同意复读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怎么还能不交钱!我们乡下人种田种菜都有回报的,老师辛辛苦苦给你补习,不给报酬怎么说得过去!田蓝和哥哥都觉得无话可说。因只差两分,哥哥田亮也不甘心就此放弃,就交了一笔补习费,跟班继续学习了。
一年一晃就过去了,不知这次究竟会怎样呢?哥他究竟能不能考上?别过花婶后,田蓝心绪不宁地继续往家走,远远地望见自家的门大开着,田蓝快步跑起来了。
“哥——”田蓝冲进屋,叫了一半,噎住了。只见哥哥田亮怕冷似的蜷着身子,双手抱头,坐在堂屋一侧的一张竹椅上。田蓝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她扔下竹篮,冲过去使劲摇着哥哥的肩膀:“哥,考上没?到底怎样啊,考上没?”
“差两分,又差两分……”哥无生气的声音像是从阴冷的地狱传来的一般。
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围着桌子悄无声息地吃着晚饭。田蓝有一下没一下往嘴里扒拉着饭粒,一边偷眼瞅爹娘的脸色。娘的脸在灯下显出一点点的惨白,爹的一张脸则似乎更黑更瘦了。
爹咳嗽两声,期期艾艾开口道:“考不上就算了,跟爹种田,也是一样的。”
娘不说话,甚至眼皮都没抬一下。爹便闭了嘴,屋子里重新静下来,只剩下碗筷碰撞的轻微的声响。
哥丢下吃了一半的饭准备起身,被娘叫住了:“亮伢子,听我说,俗话说得好,事不过三。我们再考它一年,我就不信真是这个命!”
一家人全张大了嘴巴望着娘。
哥扭着一张脸,似要哭出声来:“不!娘,您别再逼我!”
娘起身离座,进到里屋,摸索了一阵,拿了一个小布包出来,里面是破旧肮脏,但被娘抚得平平整整的一叠钱票子,十块五块的,一角两角的。“钱的事你不要挂心,卖谷,卖菜,卖蛋,卖猪,都有钱来。亮伢子,听娘的话,再读一年,事不过三!”
望着汗渍斑斑的一叠票子,田亮像是被毒蜂狠蜇了一下,他大叫一声:“不!我不要家里的钱!我不想再补习,我能种地,能挣钱,别再逼我!”田亮跳起来,推开凳子,飞快地冲出家门,冲进了已漆黑一片的夜色之中。
“哥——”田蓝丢下碗筷,紧跟着冲了出去。
经过了整整一天日头炙烤的大地在夜的怀里终于渐渐平息了性情,重新变得宽厚而平和。风已略带凉意,唯有夏虫仍在不甘寂寞地鼓噪不休。
田蓝陪哥哥坐在村东头的河滩边上,看月亮在水里波光粼粼的样子,听水流默默流向远方的声音。
远远地传来了一阵拖着旧布鞋走路的踢踏声,是爹过来了吗?田蓝抬眼看时,正是爹含着烟杆走了过来。
爹坐在哥的身边,吸了两口烟,说:“我给你们说个故事。”
田蓝和田亮同时抬起了头:爹居然还会说故事。
二十多年前,我们这儿除了山,除了田地,什么也没有。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更没有学堂。
上边派了一队文化人来扫盲,内中有一个小伙,个儿高,精神,嘴甜,会说话,姑娘媳妇人见人爱。山那边呢有一个姑娘,十六七岁年纪,模样俊,手灵巧,远近闻名,方圆几十里的小伙人人爱慕。他们一个教,一个学,两人很快就对上了象。
扫盲结束,文化人返城,小伙给姑娘留下了一大堆课本,他们相约:半年后姑娘到城里报考高级小学。小伙正是高级小学的先生。
不久,山外一户家道殷实、很有名声的人家进山求亲,他们的小儿子在一次集市上看到过姑娘,发誓非此女不娶,许下的彩礼照花了姑娘爹娘的眼睛。他们满心欢喜,一口应允,换了帖子,定了日期。没想姑娘却死活不依。直闹了半年,姑娘打点行装,准备进城赶考时,她的爹娘才知晓真情。
爹娘拗不过姑娘以性命相胁,与姑娘约定:只此一天,看她运气如何,赶上车是她的命,赶不上车呢,也是她的命,那就回家好好嫁人,永不反悔。姑娘咬咬牙应承下来。
第二天,她摸黑起床,挑了被褥衣物,以及先生给她的课本,赶几十里山路,来到山外的馬路边。
这是贯穿邻省和本省唯一的一条通道,每天有一趟长途班车经过,时间一般在晌午前后。这里没有站,想要搭车,就得横下一条心站在路中央。碰上人不多,司机心肠又软,就有可能行得通。姑娘跟她爹娘赌的就是这个运气。
姑娘想好了,只要车来,她就连人带行李一起躺在路中央,下跪,磕头,都行,只求带她走。没想到,姑娘一直等到天黑透了,除了附近公社的几辆手扶拖拉机,连班车的影子都没见着。
姑娘回到家已是半夜,没等爹娘开口,她就跪下了,哭着要求再给她一次机会。爹娘本意是指望女儿好的,便退一步,答应了她。
姑娘不敢睡,稍歇了歇,带上干粮,挑上行李,又翻山越岭来到了马路边上。真是老天无眼,一直到天断黑,仍是不见班车的影子。
姑娘回到家大病一场,病好后就嫁了人。
事后她才听说,前一阵子因下大雨,邻省暴发山洪,冲断了路面,班车停开了两天。这两天,正是她在路边苦苦等车的当儿。而到第三天,车也就通了。
田蓝田亮听得眼睛发直,爹的声音落下去好久,田蓝才想起问:“爹,那姑娘就是我娘?”
爹点点头。
“那,您就是山外那富有人家的小儿子?”
爹仍是点点头。
“怪不得娘老是说事不过三、事不过三……”哥哥田亮喃喃自语,田蓝则感到有凉凉的东西涌出眼眶,流到了脸上。娘,娘,你少女时代真的如此执着过,运气又偏偏这么不好的吗?
父子三人重新沉默了下来。任凭夏虫伴着流水声在空中划过。良久,田蓝惊醒过来,轻声问:“那后来呢?”
“后来,有了你哥,再后来,又有了你。我和你娘拼死拼活做,日子却不知怎的好不起来了。再后来,我们这儿通了车,接着又办了学堂。这个学堂办得可不易,是费了好大劲才办起来的,出力最大的就是那个扫盲队的小伙子。”
田蓝突然觉得心头电光一闪,她脱口而出:“秦校长?那个扫盲队的人,他就是秦校长?”
爹吧嗒吧嗒吸烟,不再吱声。田蓝、田亮愣在那儿,也不敢再开口。许久,爹站起身,在鞋帮上磕磕烟斗,磕出一些闪着亮光的烟灰,说:“你娘是个好人,心善,能干,要强。她总跟我说,她这辈子最大的心事,就是指望着有一天,能给你们兄妹俩办行李,送你们上车,看着你们坐上车进城去念书。亮伢子,你真不想念书就跟你娘说清楚。别怨你娘逼你,她有时心里不舒坦。”
爹说完,不再理会仍坐着发呆的兄妹俩,自顾拖着布鞋走了。
田蓝躺在床上,努力地闭着眼睛。可是,没用,她的脑子里像在烧着一锅滚烫的开水。娘平静而惨白的脸、爹木讷而劳苦的身影、穿着白色连衣裙的秦文以及她从娘手中抽出的手,依然有着年轻挺拔背影的秦校长……一个个人物和场景像走马灯一样在田蓝紧闭着的眼前晃来晃去,她头痛欲裂。
她真心地祈祷睡神快快来临,带她进入梦乡。她知道,等明天,一觉醒来,她就会结束自己以前在爹娘的庇护下一直过着的稀里糊涂的日子,而拿起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份日子来,不管方式如何,也不管成功与否,她都必须这样做。
哥哥他一定也是在这样想着的吧!
选自《儿童文学》1997年第10期
谢倩霓,《少年文艺》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已经出版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你是我的城》《晚霞中的红蜻蜓》《慢慢地知道》《梦中的橄榄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