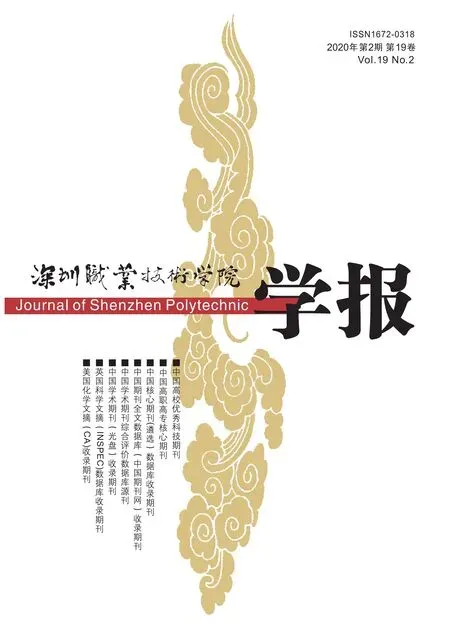从战“疫”看职业教育的初心、使命和关怀*
徐平利
从战“疫”看职业教育的初心、使命和关怀*
徐平利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广东 深圳 518055)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让我们重新审视“职业”和“职业教育”。战“役”凸显职业教育“爱与奉献”的初心,以及灾难来临时职业教育的使命担当和终极关怀。职业教育培养具有技术之魂的“平民英雄”,终极关怀是构成美好生活的职业幸福感,职业教育应在这个意义上深化改革。
抗疫之战;职业教育;初心;使命;终极关怀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然而至,弥漫全球。1月25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1]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全国打响了。战“役”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科学、务实之战,在“前线”大显身手的更多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应用型人才”。此次战“疫”凸显了职业教育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职业教育的初心、使命和终极关怀。
1 职业教育的初心是爱与奉献
1.1 重新审视“职业”与“职业教育”
在危机面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职业”这个词。职业,它不只是词典上“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的干巴解释。职业社会学理论家安德鲁·阿伯特在他的经典著作《职业系统》中说:“职业支配着我们的整个世界。它们治愈我们的身体,衡量我们的收益,挽救我们的灵魂,而我们对它们的态度却十分纠结。”[2]从冲锋陷阵的医生身上,我们重新找回了职业当中的“天职”和“神圣”之义,即职业不仅是人的生存位置,也是人的生存权,职业是神圣的,不仅标注资源与占用,也表示责任和义务。在汉语中,“职”字本身包含了职分、标记、功业、贡献、关键等意思,这些意思都说明,一个人从事“职业”是一个人存在的标识(表示有身份,并且是稳定的),也是一个人建功立业的机会,每一个从业者在他的职业中都有关键作用。
在危机面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职业教育”这个概念。职业教育也是“天职教育”,这是一种“神圣的教育”,它在培养对“天职”负责的“体面劳动者”,具有何等伟大的“意义!职业教育是最贴近实际的,但是当“实际”真的来临之时,职业教育在哪里?我相信,职业教育工作者绝不是好龙的叶公,但是当恐惧、慌乱、歧视、冷漠等等事件发生的时候,职业教育是不是应当有所反思?
我们的确需要反思我们的职业伦理教育。如果我们是职业院校教师,会在课堂上大讲一番怎样的职业伦理呢?职业伦理的根系不是扎在课堂上,而是在有血有肉的生命当中,很可能是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件当中!比如,当职业院校引入企业文化的时候,当“诚信”文化面对“忠诚”文化的挑战时,职业伦理做何选择?突发事件来临,特别是在灾难面前,职业教育的忧患与担当在哪里?
我们必须给予职业教育以意义赋值。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有技能有素养的就业者,而且要培养为意义人生不懈奋斗的乐业者,培养在突发事件面前沉着应对的奉献者。原始的生命冲动在每一个生命里面都是公平的,一个人无论居高位还是处底层,他的原始生命冲动同样在不断促使他去追求“意义人生”。
1.2 大众解放、生命救赎以及爱与奉献
职业教育是为了平民大众的就业和乐业的教育。我国伟大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对职业教育有个定义:“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3]它既指出了职业教育的本质——为了底层大众的解放,为了自由和爱,也指出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性特征——首先解决就业问题,然后解决乐业问题。黄炎培是从底层大众需要来定义职业教育的,他的出发点是对大众的爱与奉献,这是职业教育的“初心”。可以肯定地说,离开了职业教育的“初心”,职业教育的行动将失去活水的泉源,必然会干枯败落。因此,黄炎培的定义具有生命意义和救赎精神。
上个世纪,黄炎培用行动诠释了职业教育的爱与奉献的真谛。同样是在上世纪,为了启蒙巴西民众,伟大的职业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振臂高呼:“教育即是政治!”[4]这也是教育家发自肺腑的爱与奉献的职业教育之声。早在两个世纪以前,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就用不畏艰辛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爱与奉献才是职业教育的生命之根。当年,德国职业教育之父凯兴斯泰纳让职业教育在德国安营扎寨的时候,正值德意志民族知耻而后勇的时代,他坚定地指出:“职业伦理和社会精神是德国职业教育的最重要任务!”[5]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校企合作”和“就业技能”。
可惜,当我们骑着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战马驰骋畋猎的时候,当我们驾着工具主义职业教育的战车高歌猛进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感受到“令人心发狂”的喧嚣,也许我们在职业教育的功利性之路上走得太远,已经忘记了出发时的“初心”是什么。
现代职业教育是在两个世纪以前,由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为穷人举办“工业学校”开始的。裴斯泰洛齐举办学校的基本出发点是:大众解放、生命救赎以及爱与奉献。当时,裴斯泰洛齐亲身经历了贫穷、愚昧和不公带给底层大众的苦难,他相信教育是拯救穷人的最好武器,但他觉得以前的穷人学校和教育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帮助穷人,他很想按照他在“新庄”(诺伊霍夫)的实践经验开辟新的教育道路,这就是“职业”教育之路。他说:“成千上万的儿童被迫在街上流浪,他们需要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应该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我要尽可能多地接收这些可怜的孩子,教他们读书,教他们编织。他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家,他们要走在正道上!”[6]裴斯泰洛齐的学校能够培养谋生的技能劳工,但是他的根本目的是出于爱、奉献和生命的救赎,他不愿意看到孩子们流离失所,更害怕他们滑向败坏的深渊,他要培养孩子长大后从事幸福职业的能力。他说:“要把孩子在各方面都教育得很好,首先就要看他长大以后将从事何种职业,要以这个为基础,使孩子学好为他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日后幸福所必需的一切。”[7]
1.3 爱心回归技术身体
在这次战“疫”行动中,全中国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凝聚合力,“爱与奉献”的情怀和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让我们从救赎的意义上深入思考,职业教育并不是仅有种属关系的教育学概念,而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我们总是说,职业教育要转型升级,我们一直强调职业教育文化育人。那么,当疫情突然而至的时候,职业教育何去何从?我们总是说,校企合作“难难难”,现在企业真的是很难,职业院校能做些什么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仅仅是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日常工作吗?当我们讲“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的时候,我们会对学生说什么呢?仅仅说“就业就是求谋生”吗?当我们用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去衡量职业教育质量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之囊里还有没有更多指标?
面对“校企合作”实效性不强的事实,有些职业院校和机构工作者常常抱怨企业的主动性不强,也抱怨政府没有尽到强力约束企业的责任,但是很少反思自己的合作心态。反躬自省才能无所愧疚,当我们从职业教育的“初心”出发的时候,当我们把校企合作的效益机制建立在“爱与奉献”的文化精神上的时候,我相信,职业教育一定是高一层次的“引领者”。
20世纪上半叶,很多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以救国救民的大众情怀举办职业教育,他们属于“引领者”,他们具有救赎精神。比如,晏阳初面向平民举办职业教育,首先是“成为劳工”的职业教育,然后是“劳工解放”的职业教育,他号召知识分子们摘掉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民眼镜,虚心做农民的学徒;黄炎培特别强调,职业教育的第一信条是“劳工神圣”;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举办生活的职业教育;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事业,仍然举办面向农民的职业教育,他脱掉北大老师的上衣,深入乡村举办贫苦民众的学校;企业家卢作孚开办企业的职业教育,其特征是穷人、慈善、免费、思想启蒙,“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是为社会服务”[8]。
当爱和奉献的信念在每个寻求者身上生根发芽的时候,社会结构将变得合理。职业教育这颗生命之树在未来将枝繁叶茂,一定能绽放“爱之花”,生机勃勃地结出甜美的果实。有一首歌唱得好:“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人类是美好生活的追寻者,当爱心回归技术身体的时候,人类在孤独与恐惧以及浮躁和焦虑面前就会有强大的生存调适能力。因此,从现在开始,自我革命,做好准备,迎接职业教育的新生命。
2 职业教育的人才目标是“平民英雄”
2.1 职业教育的使命
如果说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那么当企业不得不大面积裁员的时候,职业教育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说职业教育学是与大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学科,那么当大众生活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时,职业教育学能否做出一些改变呢?
战“疫”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连开会议做出指示,他说:“要稳定居民消费,发展网络消费,扩大健康类消费。”[9]还说:“越是发生疫情,越要注意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特别是要高度关注就业问题,防止出现大规模裁员。”[10]此时此刻,最需要职业教育挺身而出,因为职业教育有救赎的使命。
1862年7月2日,美国内战正酣时,林肯总统签署了刺激美国农业经济的“大职业教育法案”,即著名的《莫里尔法案》;1917年2月2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急关头,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了解决美国移民就业问题的职业教育资助法案,即《史密斯-休斯法案》。
同样,中国的职业教育正是在国家多灾多难的时候走上历史舞台的。1866年12月23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福建船政学堂拔地而起。1917年5月6日,正当教育救国运动高涨之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黄炎培先生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和“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持元气,支持抗战”的16字工作方针,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被称为“职教派”。
如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身处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机器换人”仿佛一种不可控的力量,在知识、资本和市场竞争的作用下步步逼近。这就是一种大事件的来临,职业教育如何面对?一些人欢喜地等待着,一些人悲伤地等待着,那么被机器取代的人力资源何处去?如果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弱化了,那么构成人力资本的教育何处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不安。毫无疑问,如果失去了生命力和使命感,所有的疑问和行为都令人恐惧,这种恐惧不是困难当前,而是对远方不确定的孤独无助。
职业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现象,它不是几个超人坐在屋子里冥想和设计出来的,也不是上层精英对底层大众在教育资源方面的施舍,当然更不是精英教育的剩余物,作为一种生命现象,职业教育是自由与爱相结合的孩子。美国哲学家杜威是职业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他关注的重点不是职业教育的经济贡献度,而是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生命体的终极关怀。据此,职业教育具有劳力解放、平等人权和公义救赎的使命,未来职场可能会“大洗牌”,但职业教育应当带来劳动者的“乐业生活”。彼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创造与众不同的作品,人人乐而为之,人人尽职尽力,人人谦和而友善,人们彼此分享和交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美好生活的意义。
2.2 培养“平民英雄”
每逢国家有难,必有英雄站出。什么是英雄?辞典上的解释是“才能勇气过人的人”。毫无疑问,在危难时刻,所有愿意担负使命并且挺身而出的人都是英雄,包括敬畏真理、实事求是、敢于直言、无所畏惧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平民英雄。在此次全民战“疫”中,有学识有胆识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是英雄。同样,许许多多的涂抹了厚厚的爱与奉献底色的医护人员、普通民众也是英雄。80后快递小哥汪勇就是平民英雄,他的职业是快递员,但在危难时刻主动站出,担负了接送医护人员的使命。他建立服务群,招募志愿者,第一时间帮助医护人员解决各种生活问题。虽然普通,但是伟大,就像汪勇自己所说:“我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人啊!”[11]再比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创作歌曲声援武汉,志愿者深入社区疏导宣传,党员干部带头捐款援助战“疫”……他们都是平民英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威廉·詹姆斯说,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大师,也培养大众英雄,任何一个普通劳动者都可能成为英雄,因此职业教育必须扎根于爱与奉献的土壤,“无法踏实的脚掌无法固定在任何地方”[12]。
胡适曾经从哲学的角度定义教育,他说教育“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13]。在职业教育活动中,教师只做个传授“就业知识”的“教书匠”可行否?肯定不行。那么,再加上一点“能思想”的元素可行否?还是不行。所有教师都必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14。因此,如果我们说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平民英雄”,那么英雄必须实实在在扎根大地,必须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世上绝没有虚妄的英雄。而且,英雄还必须要有“行善去恶”的精神,世上也绝没有是非不分的英雄。
“平民英雄”来自于普普通通的平民大众。平民大众可能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可能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平民大众只要“行善去恶”,只要脚踏实地和躬身力行,就能引领美好。在战“役”期间,武汉之所以成为一座英雄的城市,正是因为这座城市有许许多多在不同岗位奉献的“平民英雄”。一些人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平民大众的“低层次教育”,所以看不起职业教育,然而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都是英雄的平民大众,何来“低层次”?因此,职业教育应当有英雄品质和使命担当,职业教育的英雄形象是高大的。
2.3 工匠精神与技术之魂
在全民战“役”期间,口罩和防护服的需求量极大,而且供应刻不容缓,许多企业发扬“工匠精神”,攻坚克难,迅速调整设备和改造技术,高效率高标准投入生产。生产工人表示,能够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全民战“役”中是非常自豪的,这正是“工匠精神”的体现。这里,工人们表达了关于“工匠精神”一种思想,即深层意义上的“工匠精神”还包括技术之魂,这种“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叫“道”,它在战“役”中所显示的就是爱心与奉献、使命和担当。
道之不存,人被物化;道之所存,物自芬芳。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15]意思是,人之有道,顺其自然,循道化物而却不会被物化。因此,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工匠精神”也应当居高而临下,居道而临技。如果职业教育培养人才与私利联结,如果人的精神变成了咄咄逼人的物欲,那会是什么结果呢?我们看到,战“役”中也出现了极个别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不良商家。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而是精神,是美,是诗!因此,当技术仅仅作为一种雄性攻击武器的时候,试图用技术自我救赎是不可能的;当技术用作绳索捆绑了精神的时候,精神沦落了,诗和美消失了,一切都将被粉饰为焦虑的表演者和浮躁的看客。如果意义不在、精神萎缩,私利和物欲成了“技术人”的信仰,职业教育就是“低层次”的。最终,当技术有机会反戈一击时,忙碌于“五斗米”的从业者不可能有高贵的灵魂。
因此,职业教育应当特别重视这种“技术之魂”的铸造。有“魂”的工匠不仅是技术大师,也是实实在在的“平民英雄”。
3 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是职业幸福感
3.1 职业幸福感与美好生活
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越来越细,而且“职业本身就是文化改造的一个手段”[16],因此人的职业生存方式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无论以什么职业方式生存,现代人越来越重视职业幸福感体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幸福感体验如何,体现了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美好生活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做出了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必须日益重视人民群众的职业幸福感体验。
美好生活与职业幸福感息息相关。美好生活可以表现为个体的生活状态,但更多用来描述全体国民的生活状态。与之相对,职业幸福感可以用来描写群体的职业感受,但是它更多表现为个体在职业劳动中的情感体验。总体来说,美好生活与职业幸福感是相互作用的,没有个体的职业幸福感就没有社会的美好生活;没有美好生活的社会大环境,也很难有个体的职业幸福感。从美好生活与职业幸福感的相互性特征可以看出,任何个体的幸福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他人和全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各国共同战“疫”更说明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每个人的职业伦理和职业幸福感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现。我们不要把职业幸福感片面地理解为某种职业的“工作过程体验”,它是延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持续性情感体验。比如,战“役”最前线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各级行政官员、快递员等等,这些职业人冲锋陷阵,他们的情感体验是什么?在家或在宾馆隔离且每天上网翻看战“疫”进展的其他职业人的情感体验是什么?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有关职业的情感体验,是否幸福呢?肯定是复杂的,有人张皇失措,有人沉着应对,也有人煽风点火,还有人跟风传谣。
消费行业的有些职业人,特别是小微企业老板,显得很焦虑,他们痛苦地表示“撑不过三个月”,等等。许多租客愁闷的是,无法上班却要继续付房租。在此情况下,有的房东决定免房租,有的却没有免房租。被免租的很高兴,没有被免租的很郁闷。有的“房东”本身也是贷款经营、资金紧张的小公司……各种各样的情形都在影响职业人的幸福感体验。美好生活与职业幸福感是互动的,任何人的工作和行为都与其他人息息相关,某个职业的情感体验一定会影响其他人,进而影响全社会美好生活的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了职业幸福感是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这个命题。
3.2 职业幸福感与职业教育改革
“职业教育的归宿就是人类的幸福生活本身,职业幸福感就是生活幸福感,不能给人生活幸福感的职业教育一定是失败的教育。”[17]今天,教育融通生活,技术融通美好,精细分工和深度融合共生共长。职业教育跨进了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精彩世界,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深度融通。职业教育带来美好生活,职业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18]。
战“役”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把职业教育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具有时代紧迫性。我们必须加快职业教育改革的步伐,增强职业教育的人文精神的力量,让职场人有能力面对技术升级,有责任应对灾难危机,有爱心帮助他人。换句话说,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有技术之魂的“平民英雄”。当工匠精神振作起来,当爱与奉献归回心灵,技术就是一个正义的诗人、一个智慧的勇士;技术可以戳穿作恶的伎俩,可以揭露欺骗的面具。
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也是清醒剂,我们可以从中更加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职业教育改革不仅是健全体系,而且是转变思想,要明确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绝不放弃职业教育的理想追求。在制度治理的改革中,推进教育与培训并进、线上与线下并进、学校与社会并进、技术与人文并进;在人才目标的改革中,要从重点训练“成功的就业者”转向重点培养践行美好生活的“平民英雄”,让每个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行善去恶”的生命意义,让每个人的劳动价值都得到尊重和满足。就像哲学家杜威所指出的:“职业是唯一能使一个人的特异才能和他的社会服务取得平衡的事情。找出一个人适宜做的事业并且获得实行的机会,这是幸福的关键。”[19]
[1] 人民网评:疫情之下,生命重于泰山.人民网[EB/OL].(2020-01-26)[2020-01-26].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82798192&ver.
[2] [美]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M].李荣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1.
[3] 江恒源.十六年来之中华职业教育社[J].教育与职业,1933(2):397-477.
[4] Paulo Freire. The people, the poor, and the oppressed: the concept of popular education through time[J]. Paedagogica Historica Vol.47, Nos.1-2, February– April 2011,1-14.
[5] Christopher Winch. Georg Kerschensteiner—founding the dual system in Germany[J].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32, No.3,July 2006,381-396.
[6] Heinrich Rubi. Pestalozzi’s Biography[EB/OL].http://www.bruehlmeier.info/biography.htm.
[7] [瑞士]裴斯泰洛齐.林哈德和葛笃德[M].北京编译社,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75.
[8] 梁漱溟.怀念卢作孚先生[J].名人传记,1988(5).
[9] 蔡昉.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发布时间[N].人民日报,2020-02-12.
[10] 胡敏.更大力度多措并举稳就业[N].光明日报,2020-02-14.
[11] 汪勇,吴雪.快递小哥搞定金银潭医护难题:我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人啊[N].人民日报,2020-02-16.
[12] [美]詹姆斯.真理的意义[M].刘宏信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
[1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
[14] 习近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央视新闻[EB/OL].(2019-03-18)[2020-02-20].https://mp. weixin.qq.com/s?src2019-03-18.
[15] 庄子.庄子[M].石磊评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211.
[16]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等译.华东师范学大学出版社,2014:130.
[17] 徐平利.职业幸福感: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J].职教通讯,2012(7):31-36.
[18] 习近平.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EB/OL](2014-06-23)[2020-2-24].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23/.
[19]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27.
Original Intention, Mission and Ultimate Concer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lected during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XU Pingli
()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is a war. Let us re-examine “vo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reflect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love and dedi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When our country has a disaster, the mission,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al goals and ultimate concer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manifes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ims to cultivate heroes out of ordinary people with noble spirit and technical skills. The ultimate concern is to form a sense of happiness and vocational fulfillment. In this sen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deepen its reform.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vocational education; original intention; mission; ultimate concern
2020-03-11
:“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20-2022)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成果,主持人:徐平利
G710
A
1672-0318(2020)02-0003-06
10.13899/j.cnki.szptxb.2020.02.001
徐平利,男,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教育学,职业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