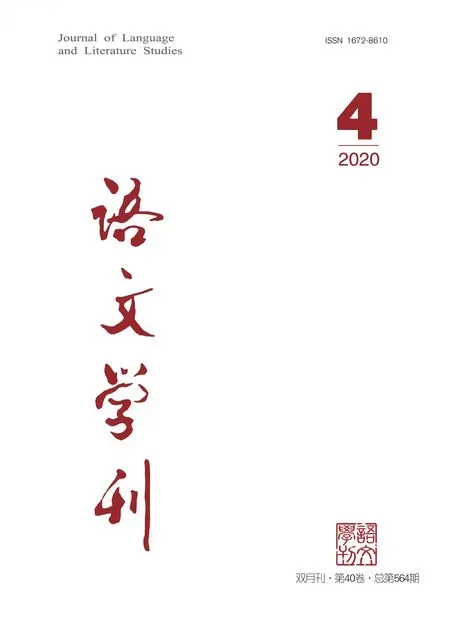多重图式化观相重构与形而上质再现赏析
——基于《登鹳雀楼》的汉英对比与翻译
○ 赵明
(中国矿业大学离退休工作处,江苏 徐州 221008)
当代波兰现象学美学家和哲学家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在其著名的姊妹篇《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和《论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1937)中,阐释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存在模式、多层结构以及读者体验作品的方式等问题[1]39。他认为:保持内在统一性与基本性质的文学作品都由4个异质层次组成,它们是语音层、语义层、图式化观相层和再现客体层。在这4个基本层次之上还有一个形而上质层,“所谓形而上质,是指如崇高、悲壮、恐惧、神圣、凝重、飘逸”[2]、“怪诞、娇媚、轻快”[1]39等性质。形而上质通过作品的再现对象得以显现,是作品的韵味、氛围与精魂,是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体现[3]52,也是文学作品思想的最高境界。英伽登对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体现了他的文学作品存在论或本体论的美学思想,是他关于艺术作品层次的独特性理论体系,也是他对文学理论的主要贡献[1]39。
如果没有读者,作品只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与认知赋予作品以审美价值。基于作品的4个本体结构层次以及它们相互作用关联所构成的整体,读者带着“先验”和“预设”对作品这一审美对象进行“具体化”的阅读,填补其中的“不定点”,创造性地对作者所“描绘的世界”进行“复现”或重构。本文将以英伽登4个层次中的图式化观相层为基点,探讨汉英文学翻译的图式化观相重构与形而上质的再现问题。
一、图式化观相层概念及其在汉英翻译中的读者认知
“文学作品是由包含许多不定点的再现的客体系列构成的图式化观相。”[1]38“文学作品本身只是一个图式化的、潜在的存在形式”[4]173,需要读者对它进行重构或者具体化。“图式化”指的是对再现客体的某些方面的骨架化或图式化的表达或呈现,即轮廓性的勾勒。观相是客体对象的呈现方式或外观。文学作品“都只能用有限的字句表达呈现在无限的时空中的事物的某些方面”[5]28,图式化说明了“作品中意向性关联物的有限性问题”[5]28。因此,图式化观相层是作品本身和读者对作品的阅读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框架结构[1]38,它具有规定性,是读者理解作品的基本依据,在一定范围或程度上约束读者对作品进行无度的任意解读。
“观相既不是客体本来就具有的,也不是仅仅存在主体心理上的,而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产物”[4]173,文学作品的图式化观相是自身同一恒定不变的[4]173,读者阅读时会“把作品中图式化性质的再现客体重新建构成多少类似于作者创作时所‘描绘的世界’”[4]174。在此,“类似于”是客观的表述,读者阅读的时空过程的动态性使重构不能达到与原作的绝对等同,读者不可避免会带着自己的主观因素阅读作品,读者的先期背景不同,阅读也会千差万别,特别是涉及两种语言文化的读者,更是如此。就翻译而论,虽然原作的图式化观相层具有一定的规定性,但不同背景读者的主体差异性也会使观相达不到理想的同一性。汉英翻译就是要协调两种语言读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性,避免任意的多元性,达到相近或类似于原作的读者效应。译者作为沟通原作与译语读者的中介,要在准确把握原作图式化观相、深谙原作者意图的前提下,在目的语中进行适宜译语读者的图式化重构,使译语读者取得同原语读者同样或类似的再现客体观相,最终达到原作中4个层次所烘托的形而上质在译语中成功再现的翻译目的。
二、对《登鹳雀楼》的汉语图式化观相解读、英译重构与形而上质再现译例分析
汉语具有概括力强、表述含蓄的语言特性,汉语言简意赅,颇具解读张力;英语属于分析描述型的语言,表达细腻具体,显化性强。汉语诗歌多以白描为主,所以,要使英语读者正确解读汉语诗歌,获取与汉语读者等同或相近的各种阅读观相,在汉英翻译时,译者要经过由简约型的图式化解读向复合描述型图式化重构的转换过程。
汉语古诗中采用白描手法表达的意象极为丰富,汉语读者习惯于这种关于景、物、人、事的以景托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能够正确解读出其中的意蕴。例如,盛唐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诗句可谓字字珠玑,短短的十个字,浓缩了对祖国山河的赞叹与热爱,道出了诗人的情感、胸怀、气势、抱负与豪迈。汉语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落日的余晖与流连,可以听到奔腾不息的黄河流水声,可以感受到山的胸襟与落日的情感,可以读出诗人不凡的志向与理想,可以领会诗人所处的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这些都是对诗中客体系列和所描写事态的审美充实与填补,都是客体系列在读者脑海中产生的种种联想和想象观相。
在《登鹳雀楼》第一句中,“白日”与“依”和“尽”相伴,相互照应加强,共同烘托出了“依偎”这一温暖的触觉观相和落日“归家”温暖愉悦的隐喻观相;橙红暖色的夕阳、落日之霞彩同样会给读者以暖的体悟、暖的隐喻和暖的想象观相。读者仿佛能够触摸到那一片片沐浴于大地之上的余晖彩霞,能够感受到那徐徐晚风拂面吹来,这种触觉观相是多么的美好!可谓“落日余晖映晚霞,一抹夕阳美如画”。太阳依傍山峦渐渐沉落,这不仅展示了一副美丽祥和的动态视觉观相,还伴有一种悄然无声顺滑下落的静谧“听觉”观相。而此后的“黄河入海流”诗句则另有一番风情,黄河滚滚向东奔向大海,展现给读者的是动态磅礴之壮美的视觉观相和滔滔黄河咆哮东流入海的听觉观相。望着脚下的金色黄河,诗中人物是否还能嗅到黄河水汽中的泥土味?这种由视觉观相转移而来的嗅觉观相同时也存在于人物的想象观相中。读者阅读这两句诗时,可以感受和想象诗人登楼所望见的远处残阳与脚下黄河之动人景色,这一远一近的视觉观相和与之相符的一静一动的听觉观相,与读者的想象观相融为一体,给读者带来的别样感受是难以尽书的。在诗人笔下,落日之瑰丽与柔美、黄河之壮观与气势都给人以声色俱佳的美感观相享受,无论是词语指称、事态描写,还是作品客体世界的整体再现,都颇具阐释张力。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浅显的语言,将进入其视野的祖国万里河山,生动形象高度浓缩于十个汉字中,彰显了其驾驭语言的功力,诗风的清丽秀美与豪放壮美并举。透过诗人所创设的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各种感性观相和想象观相,读者与作者共鸣,深切感受到了对祖国的浓浓情愫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登鹳雀楼》描写自然景色的开笔两句,寓神奇于简约平易的字句里,缩万里于咫尺间,寥寥数词,尽显风流,简约的图式化,给人如此丰富多彩的观相,这成就于汉语的含蓄与多义。简洁朴素的文风,远近景描写,借此抒怀,极具阐释张力,真正体现了汉语表意抒怀的含蓄与简洁。但在英译时,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直译无法达到等同原文的观相效果,西方读者未必能够真正解读其中的丰富蕴涵,因此,为适应西方读者的审美取向,使得译作具有等同原作的审美价值,译者需要采用“景物具象法”[6]48进行翻译,即采用适当的文内词语增减、下义词或修辞格等方法,对所涉之“象”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锁定话语范畴,再现原作意境与精神。
在英译《登鹳雀楼》开笔两句的过程中,译者根据英语特点,采用恰当的增词或下义词的变通手法,在功能效果方面使译文尽量贴近原文。译者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译为“Ling’ring is the setting sun about the mountain height. Surging is the Yellow River eastward to the sea”[6]48。在此,词语“ling’ring”是“lingering”的缩写形式,其中字母“e”的省却使第一诗句减少了一个音节,这样,两诗句译文的音节数分别都为13个音节,等同的音节数能够更好地满足诗歌节奏鲜明、韵律和谐的语音层面的要求。另外,两诗句的英译文同原作一样,字数相同,工整对仗。因此,无论是从诗句音乐性的听觉观相,还是从诗句结构齐整的视觉观相而言,英译诗句都取得了等同于原文的效果。
从语义层面而言,汉语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表层意思是:太阳依山沉落,黄河流入大海。西方读者不习惯于汉语古诗的白描手法,对诗句颇具张力的含蓄意指不能像汉语读者那样做出创造性的解读,因此,直译就会流于肤浅,不能很好地再现诗人的情怀。就诗作的再现客体层而言,对汉语诗句所描绘的客体世界,中、英读者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与反应,中、英读者对其中的意象、意境及不定点会做出不同的解读、把握和具体化的填补。针对这种差异,译者应该突破原作诗句白描的表层意义,帮助英语读者产生与再现客体相关的丰富联想或观相。因此,以上两句英译文采用了增词和下义词的变通手法,注重细节描写,将原作白描手法表现的景色显化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在第一句译文中,译者运用了增益手法,将原诗句中笼统概括的“山”字英译为“mountain height(山顶)”, 增加了“height”一词,确切具体地描述了太阳落山的位置,符合英语善于具象表达和逻辑关联显化的特点,提高了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第一句英译中的下义词“ling’ring”[6]48(lingering的缩写)表达了“徘徊”“逗留不去”的意思,译者用此描述夕阳的“尽”,深层次上比用“set down”或者“down”更具情感色彩,更契合诗意。它点缀了夕阳冉冉下沉的徘徊与绵长,描绘了夕阳以柔和的光芒和最美的景致结束了一天的旅程,具有诗学表达的丝绒般绵柔美的审美价值,给读者以美感的视觉观相、触觉观相和想象观相。第一句英译文描绘了恬淡、纯净、清新的夕阳景色,英语词语“lingering”将原作白描手法隐含的鲜明生动的形象显化再现,这种烘托使相对静默的描写状态多了一份灵动,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词语“lingering”描绘了夕阳在观者的不知不觉中冉冉沉落,但在这种相对的动中主要还是体现了“静”的内涵。译文契合原作的氛围与韵味,诗句所构建的各种感性观相融为一体,透露着平和与从容,宁静与淡然,从实质上再现了原作所表现的形而上质。
在第二句的英译中,原文字面的“流”如直译为“flowing”,表达不了汉语诗句白描隐含的饱满语义,会扭曲原作的想象观相。因此,译者用下义词“surging”[6]48(汹涌澎湃)画龙点睛,在译文的方寸之间对简笔创意的汉语诗句进行了活灵活现的显性描述,绘声绘色地突出了原作中物象与事态的主要特点与内涵,译出了原作的形而上之“神韵”。黄河在中国人脑海中具有汹涌澎湃、九曲回荡、一泻千里等语外含义。“黄河”这一汉语的图式化表达,对中国读者而言,产生的各种观相极为丰富,难以尽书,但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而言,传递的也仅是河这一指称意义,不能产生中国读者对黄河的浓厚情感与丰富联想。所以,为了很好地表达原作客体的内涵,译者必须进行提炼性的显化具象翻译,对黄河的声貌进行具体描述,以尽量贴近原文的表达效果。译者以“surging”一词对原作进行艺术重构与再现,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与听觉观相,滚滚流过的黄河具有排山倒海之势,汹涌澎湃,黄河流水似千军万马之咆哮,震耳欲聋。译文创造性的生动描述具有力透纸背的表达力度与深度,同时,也具有理想的温度,透过“surging”一词表现的激越与奔放,译者力图引导西方读者体会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赞叹和激昂情怀,准确理解中华民族对母亲河的那份浓厚情感。
译者采用倒装图式化结构,分别将“ling’ring”(即lingering)和“surging”放在两句译文主位的位置上,主位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信息焦点,译者之良苦用心就是要强调诗句所描述画面的主要特点和内涵,形成鲜明的观相对比。如果说第一句译文由于下义词“ling’ring”的使用而使夕阳沉落具有柔和美的宁静及特有的舒缓与从容,那么,第二句则因下义词“surging”的运用而使黄河入海具有烟波浩渺、汹涌湍急的雄浑美的跃动。这两个画龙点睛下义词的运用创设了风平浪静与汹涌澎湃的鲜明对比,在此,细致与粗犷相宜,柔美沉静与奔腾澎湃并存,祖国山河壮丽秀美,宽广辽远。这种生动的具象描写手法,将原作表层看似相对静默的状态调活了,提高了译文的美感与接受度。译者深谙原作诗人借景抒情、体物缘情的意图,译文开笔两诗行间流露出的激情涌动为后面的收官诗句所表达的哲理与昂扬向上的精神做好了铺垫。
在《登鹳雀楼》中,从夕阳着笔到对大海的描述,最终到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收官两句的抒怀,诗人先抑后扬,开笔两句看似不经意的平铺直叙却流露出了作者的自信与洒脱,为潜含着深刻思维与哲理的后面两诗句奠定了基础。诗人情感从平静逐渐到激昂,在篇末酝酿到了情感的最高潮,以昂扬的笔触和向上精神收笔。夕阳并不代表哀伤,它在平淡中充满希望;黄河流水也不是那么平静,它浩浩荡荡,奔腾不息,孕育着中华儿女无穷的力量。译者深谙原作意图,在描述前两句中的客体对象时,用了两个生动的下义词“ling’ring”(即lingering)和“surging”进行了适合西方读者的艺术提炼与重构,意境优美的译文诗句,抑扬张弛运筹有度,速度节奏起落得当,能够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真正体验作者情感,感受诗作神韵。在此基础上,卓振英将后面两句译为:“Aim higher and up the tower take another flight. To acquire a vision broader than one thousand li.”译文可谓水到渠成,像原作一样借景抒情立志,突出表现在“aim higher”和“acquire a vision broader”两词组的运用上,译者画龙点睛、篇末点题地译出了“志存高远”(aim higher)的哲理与教益,译出了“宽广的视野”(broader vision)与“博大的胸怀”(broader vision)及对未来的“宏伟愿景”(broader vision)和“丰富的想象”(broader vision)。译者没有流于“登楼观景”的肤浅直译,而是根据原文表层与深层的双关语义,精心选词,对原作再现客体的“留白”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填补与显化,不仅帮助译文读者获取了登高望远的感性观相,更重要的是使读者获取了高瞻远瞩、意境深远的联想和想象观相,还原了原作的主旨内蕴和读者效应。译文读者情绪会随着所读诗句的进一步展开被调动起来,情到深处,志气也高昂了,读到句末自然会心潮澎湃,胸怀激荡,充满着奋进的力量。前两句通过写景抒发了爱国情感,后两句通过再上一层楼表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前后两部分译文丝丝相扣,服务于诗作的整体氛围——形而上质的再现,使读者对译文文本中潜在无形的形而上质有了深切的感受。
三、《登鹳雀楼》汉、英图式化结构对比、英译观相重构及形而上质再现特点分析
就《登鹳雀楼》的图式化表达而言,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可谓不分轩轾,二者表现手法不同,殊途同归。汉语简笔画型的图式化表述,简洁含蓄,饱含阐释张力。开笔两句,寥寥数语,看似轻松拟就、平易简约,却精彩地描绘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与诗情画意般的夕阳图,呈现给读者以丰富的观相。英译文也毫不逊色,短短26个字,尽显多少事。英译文具象描述型的图式化手法,体现了英语惯于细节分析的特点,针对概括力强的汉语原文,译者依靠写实的方法尽量填补了原文所特有的阐释空间,解决了汉英在表达习惯和逻辑思维方面的差异问题。
就观相再生而言,译者很好地处理了读者主体与再现客体之间的关系,着力于译文中再现客体的生动着彩,译者对译文的艺术加工不仅使作品更具审美价值,更是满足了英语读者的审美期待。译者预测到英语读者解读原作图式可能会产生的误解,翻译时通过恰当的变通方法,使译语读者能够与原作诗人产生共鸣,取得了契合原作意图的观相。这些观相包括感性观相和非感性观相。感性观相包括诗句再现世界中的多彩秀丽的夕阳图、雄浑壮丽的黄河图、登高远望的辽阔视野图等给读者带来的视觉观相,包括悄然无声白日落山之“静”与汹涌黄河之咆哮给读者带来的听觉观相,包括夕阳沉落时的流连与夕阳柔和光线产生的柔绵美给读者带来的触觉观相,同时还会在读者中产生像诗人那样伫立鹳雀楼上所感受到的和风拂面的触觉观相。非感性观相包括感情观相和想象或联想观相。诗歌字里行间透出诗人面对流光溢彩、金碧交辉的奇景所表现出的激动心情和爱国激情,这种浓厚的感情色彩体现的是感情观相[7]153,译文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体会诗人的感情观相。橙红夕阳依偎青山、金色黄河奔腾归海会带给读者以温暖感受的联想观相,而“更上一层楼”的宽广境界带给读者的是丰富的想象观相。较之视觉、听觉、触觉等狭义的感性观相,想象观相是广义的,当人们在想象某些客体时,就会产生想象观相[7]153。在《登鹳雀楼》的4句译文诗行中,无论是白日落山、诗中人物登楼远眺的短暂过程,还是黄河入海滚滚不息的永恒运动,一个个生动画面连续出现,读者阅读时,“就可以‘想象’那些在情节中直接参与的人和事以及事件发生的经过是怎么样的”[7]156,这些感觉和想象出来的观相饱含着十分感人的感情质[7]156,特别是最后两句给人以希望、憧憬、无止境探求、雄心勃勃、宏伟蓝图等想象观相,充满着生机与力量。以上译文在读者中产生的各种观相融为一体,对再现原作古诗中所渗透的“崇高”这一形而上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形而上质的传递而言,以上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可谓旗鼓相当,汉、英诗句中的再现客体在读者中产生的诸多感性观相和想象观相以及与之不可分割的语音层、意义层和再现客体层的复调和声共同烘托出了作品中渗透的形而上质,这种形而上质是读者在吟诵或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思想感情悟出来的,它是非理性的最高“思想”境界。只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才能显示出形而上质[1]39,作为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体现的是“崇高”这种形而上质。译者作为原作读者和译作作者,对原作与译作进行了有效关联,使二者具有共同的形而上质内核,这种形而上质是静观沉思性的,是意向性的,作者通过作品中的再现客体体物缘情,感物抒怀,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与崇高思想。作者意向被译者领会把握,并再现于译文中,将这种具有哲学品位与高度的形而上质传递给了读者,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总之,中国读者能够准确把握汉诗白描图式化背后丰富多彩的观相,对西方读者而言,由于文化和语言习惯的差异,这种潜在的丰富观相不易生成,因此,在英译时,译者需要采用各种变通手法,将原作的白描转换为译作的细节描写。汉英诗歌翻译的这种由简约型图式化向复合描述型图式化的转换,能够使英译文读者取得等同或相近于原文读者的各种观相,并达到深刻领会原作形而上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