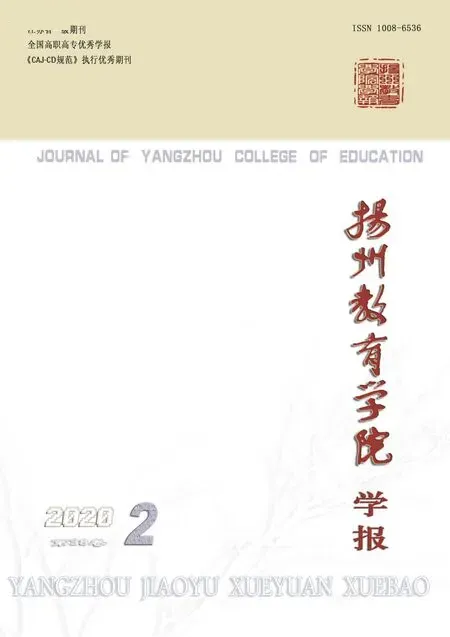《流浪地球》与现代性语境下的本土经验表达
马愫婷, 贾冀川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7)
2019年春节期间,在众多春节档的优秀影片中,电影《流浪地球》一枝独秀,掀起了全民性的观影热潮。一直不温不火的中国科幻电影,由于《流浪地球》而让人刮目相看。作为一部现象级的科幻电影,作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流浪地球》现象及其对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意义值得人们进行认真冷静的探究。
不容否认,《流浪地球》是一部令观众耳目一新的“中国制造”的科幻电影。它以绝佳的视觉特效、合家欢式的戏剧性情节设置,以及娴熟流畅的电影语言,讲述了“带着地球流浪”这样一个浪漫而孤勇的故事。作为一部成功契合了观众审美接受心理的电影,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合理表达的前提下,《流浪地球》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对现代性文化的传递与反思,进行了一次本土性的经验整合与表达。
一、全球化视阈中的本土化叙事
《流浪地球》展现了中国电影产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的科幻特效,生动地演绎了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故事。电影结合全球化下的时代背景,通过构建符合新时代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电影文本,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本土性叙事。同时,影片将“个体”与“集体”交织展现,通过个体经历的展现凸显个体的成长历程。最后,影片基于家庭伦理本位的民族理念,以“家”为叙事内核,讲述全球化视阈中的民族故事。
首先,《流浪地球》通过展现共时性的生命体验,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精神旨归,开启了将不同国家、多元文化纳入视野的全球化叙事。
《流浪地球》在影片伊始就将镜头对准世界,各个国家的新闻报道画面依次出现,旁白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深情说出“再见,太阳系”,刘培强对刘启说:“爸爸要去执行任务,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影片将叙事本体放置在全球视阈中,面对生死存亡的共同难题,人类有了共时性的疼痛体验,韩朵朵通过全球广播召集支援是这种共同体验的集中表现。当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们赶来救援时,一段快节奏的剪辑展现了众人奋力“推针”的场景,同时配以悲壮激昂的音乐,令观众感同身受的观影体验达到高峰。
《流浪地球》借助灾难的故事背景,试图弥合现代生活中日益加剧的文化、民族、国家等矛盾,在跨地域、跨文化的层面上将全人类聚集在一起。影片不再明显地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而是以一种世界性的姿态望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流浪地球》不仅是在科幻电影的特效上表现得更为纯熟,在文化心态上更学会了进行相对成熟的思考。“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突破了八十年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叙述,也改变了21世纪加入WTO之后中国作为世界秩序学习者和模仿者的状态。中国一方面有资格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问题,另一方面也尝试用自己的方案和经验来回应普遍性的问题,这是《流浪地球》所带来的文化启示。”[1]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所展现的异国情景中,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总控制中心、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控制中心等,后者还是影片最后一个高潮节点所在地。可以看出,《流浪地球》开始尝试使用发达国家的视角,对东方国家展开不同于“西方他者”以我为主的全球化叙述。
其次,《流浪地球》没有重蹈好莱坞式超级英雄的个体英雄之路,而是在个体展现与集体展现间做出了微妙的平衡与折衷,从而弥合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沟壑,强调了个体在集体中的适度位置。
影片中,刘启作为个体展现的主要部分,有着相对完整的人物角色弧线,也就是相对完整的成长曲线。在众多非议之中,喧嚣声最突出的一部分指向刘启这一人物的丰满度,有人认为刘启没有足够饱满的羽翼担当起拯救地球的任务。然而仔细审视全片,创作者似乎无意将刘启作为一个传统叙事学角度中的“英雄人物”来表现,也并没有将拯救地球的重任完全放置在他的身上。“父亲的缺失/离家出走——偷开姥爷的车落入监狱——地木危机发生/前往庇护所/遇到救援队——路途中姥爷去世/与王队发生争执/带着妹妹离开——再次加入救援队/众人协力点燃木星/父亲去世——成为英雄回到地下城,自由进出地面”,刘启所对应的叙事段落,基本上耦合普罗普叙事学范畴中的英雄人物成长单元(“准备——纠纷——转移——对抗——归来——接受”)[2]。但是,影片自然而又巧妙地将刘启放置在众多次要人物之中,尤其是在与其父刘培强的对照中,隐去了传统好莱坞式个体英雄的光环。在刘启提出点燃木星为地球提供转向动力之后,解释行动原理以及分配实际任务落在了李一一的身上;而在实际行动的叙事段落里,韩朵朵向全球喊话、王队长推针、李一一和老何解决电路程序、刘培强牺牲撞向木星等叙事链与刘启推门这一叙事链交织并行;虽然刘启这一叙事链在情节中有至关重要的功能,却没有占有过多的叙事份量。实际上,个体一直不是国产主旋律电影所着力表现的对象,以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为主流的价值观构成了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话语。《流浪地球》既相对突出了个体的表现,又强调个体与集体、民族乃至世界的融合,期间的分寸拿捏恰到好处。
再次,《流浪地球》在“拯救地球”的宏大叙事中巧妙建构“回家”“团圆”这样的中国经典叙事内核,从而建构家庭伦理本位的民族理念,完成对当下民族主义情感的有效链接。
中华民族对“家”的依恋与坚守是根深蒂固的。回溯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的民族性与“家国同构”思想一直“难舍难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电影往往在潜层家国意识的表达下,以类型化的电影范式讲述不同时代的个体或集体经验。与原著小说的悲剧内核以及缺乏显性中国指向的中性描述相比较,“电影则仅以‘带着地球流浪’为叙述背景,将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作为‘鲜明的价值导向’”[3]。影片的叙事起点“带着地球流浪”便具有恋家意识,无论遭遇何种灾难痛苦,家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弃、丢下的;即便面临的是漫长的征途,也要将原本的家连根带起,走向未知的宇宙深处。在刘启的家庭设置中,妹妹韩朵朵作为被姥爷捡来的孩子,与刘启的母亲“共享”一个名字。名字这个能指符号指向家庭中“女性/母亲”的角色,韩朵朵的存在为这个破碎的家庭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弥补。而父亲刘培强远在空间站,给主角家庭造成了一种“缺失”,因此影片在带着地球流浪的叙事前提下,隐藏着“回家”“团圆”的叙事线。刘培强一直在等待着回到地球,与家人重逢的那个时刻,刘启虽然桀骜叛逆,也时时关注父亲回归的信息。最后刘培强带着三十万吨燃料驶向木星时,既是表层意义上牺牲自我拯救了儿子,更是深层意义上拯救了整个地球,乃至全人类。刘启家庭的设置与父子关系的冲突等个体情感性的呈现,均是在为刘培强最后的牺牲拯救这一升华行为铺平道路。而刘培强对家庭的渴望,也最终为拯救家庭、拯救全人类的信念所替代。至此,“小家庭”组成“大国家”、有“家”才有“国”(全人类)的精神已跃然银幕之上。
此外,作为一档春节期间上映的贺岁电影,《流浪地球》在影片中设置了大年初一的时间节点。春节本是充满民族性的象征,而影片选择让拯救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此时,可以说是一种充满民族与国家文化自信的表现。在本该是阖家团圆的大年初一,地球上的人类几近家破人亡,又终究被中国人所拯救,得到了相对圆满的结局。中国年悄然成为普世同庆的日子,一个国家的盛典成为全人类的盛典,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传递与印证。
二、现代性的投射:中国式科幻审美
不少影评人将《流浪地球》视为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也许就此开始。《流浪地球》的制作从剧本改编到成片历时四年,摄制准备中,三百人历时十五个月,画了两千张概念图和五千多张分镜头,前后总共动用了七千多人的团队参与制作。影片的特效完成度基于中国目前的电影制作水准来说是相对较高的,导演郭帆坦言:“影片有75%的特效是由国内团队来完成的,另外25%是韩国和德国的团队完成。我们从海外团队中学习了很多的经验,也利用他们的成果来激励我们国内的团队。”[4]显然,在全球化语境下,电影工业也早已是全球化的作业流程。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独立制作,《流浪地球》仍然是一部“血统”比较纯正的中国式科幻片,投射出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对科技的理解与思考。
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潮流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是在民族存亡与国家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语境下被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回望五四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中国一直处于对科学、工业的热烈渴望中。“这种近代以来中国渴求现代化的经验带来双重后果:一是对现代的焦虑症和文化自卑感,体现为中国始终觉得自己不够现代以及缺少文化自信;二是对现代、科学、工业的强烈崇拜,以至于形成‘现代=科学=科技=工业=科幻’的价值链,相信科学、技术会带来更大的进步。”[5]实际上,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反现代、反科学主义的观念。中国形成的科幻文化对科技理性的思考是复杂的,既交织着迫切的渴望,又夹杂着一丝自我怀疑,同时在国富民强的时代影响下包含着几分昂扬。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流浪地球》较为契合地展现了中国在现代性语境下产生的科幻审美。
首先,在中国,“从总体上说,科技已经无须为自己进行合法性论证。反过来,它已经成为证明其他对象、目标或规划合法性的最重要的依据”[6]。《流浪地球》对未来科技的呈现表露出了这种社会倾向,科技的发达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象征。回看影片的叙事起点——太阳老化,太阳系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于是人类被迫带着地球离开太阳系。基于这个起点展开的故事结构,对现代科技生活所带来的灾难恐惧从人类本身的行为反思,转移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也就没有让人类社会与地球环境成为矛盾对立的双方,而是让人类成为地球的“救世主”。在领航员空间站的叙事段落中,空间站的主色调为深蓝、洁白,布光十分均匀饱满,窗外是浩瀚无垠的宇宙星空,全世界的精英集结在此操作飞船,为观众勾勒了一幅具有魅力的未来科技图景。同时,作为一部以末日灾难为叙事前提的科幻电影,影片在叙事上将情节阻力设置为地木危机;在叙事过程中,地木危机仅作为必要的情节推动点出现,影片讲述的是以刘启等人为首的人类如何度过危机。在传统的西方学者眼中,现代性给文化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本雅明写道:“现代性给人的自然创造冲动造成的阻力,远非个人所能抗拒。”[7]而《流浪地球》用恢弘的场景展示结合昂扬的背景音乐,似乎更多意在营构一场如奥德赛史诗般浪漫的中国现代宇宙神话,而非启示录般反思现代性冲击。山洪、地崩、海啸等特效场景串联起来形成的并不是对人类科技发展造成的生态后果的反思与谴责,而是一种站在生态文明恶化的废墟上,依然生生不息的文明力量。
影片中人工智能莫斯也并不是反感性的、纯智性的设定,这与其原型《2001:太空漫游》中的HAL有着本质上的区别。HAL是人类科技智性发展阶段的终极成果,它冷漠、聪慧,能置人类于死地;而莫斯则仅是一个高阶人工智能,是工具式的存在。在《2001:太空漫游》中,宇航员大卫与高智能电脑HAL的对抗代表着人类与终极智性的对弈;而在《流浪地球》中,莫斯给予了地球(人类)高科技帮助,它无意直接毁灭地球。作为叙事链中潜在的一大阻力,最终莫斯所起到的叙事作用便是推动刘培强牺牲自我点燃木星,而非展现人类与科技的对撞,或是现代性与文化精神的分裂。与此同时,影片几乎一笔带过关于科技迫害下人性道德的问题,即抽签决定谁有权力进入地下城。与《2012》等灾难片不同的是,《流浪地球》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燃情点展开叙事,由此也就削弱了影片对现代化、现代性危机的批判。
其次,影片对科技的展现也别有中国式的意味。电影文本的叙事起点——带着地球流浪,这不是逃离旧家园,而是直接以造物主的姿态“携带”着地球离开太阳系,寻找另一个栖息地,这是一种颇具悲壮意味的方式。故土难离的家园意识是《流浪地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表达。因此,作为人类逃生的避难所,地下城这一充满现代科技意味的空间被表现得非常具有“故土气息”。尤其是在北京地下城场景里,“王府井”作为一个地标性的符号出现在背景中,昭示着这是一个重建之后的“新北京”:人们在这里吃饺子喝酒,在这里上学、购物——这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地下城市,而不是逼仄的了无生气的避难所;这不是疏离冰冷的高科技工业产品,而是人类居住并赋予感情的地方。同时,这样的安排承载着现实意义与历史文化,是故乡情怀的投射,赋予中国观众可以移情的银幕图景。这些具有“乡土气息”的空间,让观众沉浸在与现实形成呼应的各类视觉奇观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故事背景中的灾难恐惧。
在科技景观的构建中,影片也做出了“中国化的”处理。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K所生活的城市布满虚拟屏,极具设计感的场景布置无不暗示着这是一个精致的虚假的世界,人类情感的交流与表达被压迫至边缘。两相对比之下,《流浪地球》中的科技景观则是现代元素与本土元素恰如其分相结合的产物:与现实空间相差无几的店铺、学校,结合重工业型的地下城基本设置,以及“忠义”牌匾、关老爷神位、博古架、龙形根雕等物件摆设与各类现代科技服饰、器械等。导演曾在采访中说道,在学生校服的选择上,团队特意选用了最具现实感的北京高中校服,而非科技感十足的未来校服。这种元素设置在鳞次栉比的重工型布景中,能够广泛引起了观众的“怀旧”情绪。可以说,《流浪地球》用充满中国本土化色彩的元素,将带有西式特色的现代科技或者说传统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景观,改造成为符合中国本土观众审美经验的科幻景观。
导演郭帆在谈及对中国科幻电影的认识时说:“首先,对于中国科幻电影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观念和精神指向层面,如何定义中国科幻片的问题。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包含中国文化内核的科幻片才能被称为中国科幻片。因此,我们在前期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能够与我们中国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文化内核。”[8]基于此,主创团队将影片的主体基调定位为对“植根于中国民族精神信仰的土地情结”这一核心观念的表达,最终呈现出具有本土经验特色的科幻特效。
三、结语
虽然并没有超越好莱坞式的科幻电影,但作为一部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科幻叙事。通过对现代性、对科技、对工业的独特思考,通过对超越国别和民族的科幻故事的“中国式”演绎,《流浪地球》对中华民族的当代生存与当代精神予以了展示,从而建构了一部全球化视域下的民族寓言。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流浪地球》取得的成绩对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启示是:以我为本,拿来主义。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9]期待《流浪地球》之后,有更多优秀的中国科幻电影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