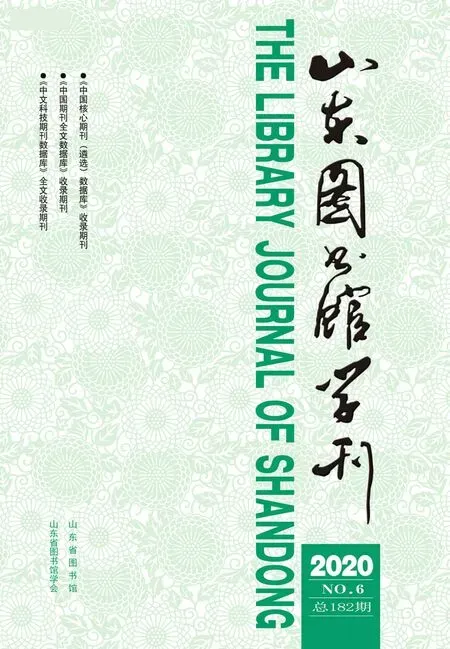匠心独运
——纪念《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问世40周年*
周余姣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天津 300387)
1 “亟命工补缀”——古籍修复的重要性
书籍之存世,不可避免有损毁之虞。为了延长古籍的寿命,历代藏书家们对古籍的修复予以了高度重视。下仅以藏书家周叔弢(1891—1984)为例,以见藏书家们对古籍修复的态度和要求。
1.1 “悉存旧观,不轻改易”——对古籍修复的态度
古籍修复与书画装裱界常言“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周叔弢对古籍修复的态度也非常审慎,如其曾在《李文公集》述古堂抄本题识中谈到:“余初见此书时,尚是旧装一册,与《结一庐书目》合,旋为书估改装四册,古意遂漓矣。余尝谓书之精神在纸光墨采中,非极渝敝,不可轻付装潢,况世之能手如钱半岩者又不可多得耶。庚午(1930)除夕展阅因记。”[1]48此处强调“不可轻付装潢”,并表彰“世之能手如钱半岩者”。钱半岩,清嘉庆间之良工也,本名钱瑞正,常为清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装订修复书籍,且父子相传。据黄丕烈称:“余家古书装潢,皆出工人钱瑞正手,性甚迂缓,如取归装成,动辄半年,故戏以钱半岩呼之。余延至家装书,由老屋以至迁居再迁居,几二十余年矣。今日声价甚高,余亦力绌,未能如向日邀之之勤,且有子可继其业,故鲜动手焉。”[2]清代装书匠有名者,除钱半岩外,还有许沛苍[3]等。
以修复工匠与能手钱半岩者相比拟,可见周叔弢极力主张须请名家改装,如不慎付之拙工,造成不可挽回的修复结果,良可痛也。周叔弢在《纬略》题识(1935年)中也曾谈及:“此本惜经俗子改装,已非士礼居之旧,殊不耐观,乃命工易书衣及前后副叶,书中衬纸则未换,恐拆订伤书也。余所见古书能多存旧装者,当推海源阁,若今人知重此者益鲜矣。”[1]96此处,拙工又被称为“俗子”,周叔弢为“俗子改装”而痛惜,只得请良工重新装订修补。1946年周叔弢请人为《赵清献公集》补缀后,也题写了数语,表明其修复观点:“书中缺叶计十一番,北平馆本可补者九番。其余二番则不遇朱本无从抄补。兹命工将影抄之叶,依次补入,护以乾隆库青纸书衣。余悉存旧观,不轻改易,此固余之素志也。”[1]165“悉存旧观,不轻改易”是其历来之观点,亦可见其对古籍修复之审慎态度。
1.2 “勿损原书为要”——对古籍修复的原则要求
虽愿“悉存旧观,不轻改易”,然对古籍修复的需求终是不免。为加强对古籍的保护,周叔弢每当收得好书,即请琉璃厂的良工予以重加装褫。如其1936年致信给王晋卿:“送上《拾遗录》,请照张十二爷《林和靖集》改装,用库瓷青纸面,并请格外小心,勿损原书为要。”[1]108可见装褫时,周叔弢对改装的模板、材料(库瓷青纸)都有要求,并指明其原则是“勿损原书为要”。对于装褫不善,则要求返工。同是《拾遗录》的装褫,周叔弢致文禄堂书中不免质问“原来四周所接旧纸何以换去,另用新纸?所用新纸是用何色染?颇有臭味也,望示之为盼。”又要求王晋卿“《拾遗录》臭味仍未能解除,已经数月矣,望将衬纸拆去重换为荷。”[1]108如此改装,致使周叔弢常不免为拙工之作苦恼。如其弟周进所拓的《秦瓦量影》,本是很珍稀之本,赠给周叔弢,“惜付劣工装池,致多损毁,见之令人心恶,遂搁置不复省览。”[1]115
对请人装订修补之事,周叔弢采用题跋的形式,多记录甚详。如1938年周叔弢先后请人对清嘉庆刻本《吴郡图经续记》、明抄本《吹剑录》进行装褫[1]117,1939年又重装明徐兴刻本《毅斋诗集别录》[1]123,1940年正月装《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并为之题跋数语,说明“合浦珠还,为之大喜过望,亟命工补缀,装之首册,虽索值奇昂,亦不遑谐价矣。”[1]1311944年5月9日,又命工装李典臣赠元本《注心赋》。其在《注心赋》题识记录其过程“此书则因辗转流传,遂横遭割裂,而装池更污损,非复旧观。既命工略加补缀,爰记数语以寄慨云。”[1]156诸如此类,可见,周叔弢对古籍修复的需求较多,也不计成本,但其对古籍修复确实有严格要求,“勿损原书”为最低的标准。
1.3 “天衣无缝,良工之作”——对古籍修复的高品质追求
古籍修复之事,可谓是周叔弢藏书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对刻本、写本等重装修复外,1961年起周叔弢开始收藏不为人所注意的清代活字本,并请人为清代活字本进行装褫。例如,1962年周叔弢请天津图书馆古籍部的邢俊斗先后装过真一堂活字本书两种、活字印本《河朔访古记》《金石例四种》等。由于对古籍的装褫修复需求很大,见多识广,周叔弢依据长期接触古籍的经验,对前人修复的古籍也颇能鉴别出修复质量的好坏。如其经手后捐赠给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的宋本《棠湖诗稿》,周叔弢曾评价该书的修复质量为:“宋刻纸有补缀处,亦宋时旧样,平贴如天衣无缝,良工之作也。”[1]191该书符合周叔弢的“五好标准”——版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收藏印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1]232。如此,方是古籍之“善本”也。
除装订外,为进一步加强对古籍的保护,周叔弢也尽量要求配置新的装具。1937年,周叔弢屡次致信王晋卿,问询韩左泉《昔昔盐》的改装事,并提出“拆去衬纸,并成二本,如太厚,即改四本,绸面。做一杨木匣,因为要送人也。”[1]115要求新做一杨木匣。同年还请王晋卿为《古文苑》改装。周叔弢对于函套书匣也都要求严格,曾致信王晋卿说明“请告复盛斋,前次携来书匣六个,皆不合适,望便中来津取回收拾为荷。”[1]117无论是对古籍本身的修复,还是加强对古籍的外在保护,周叔弢均精益求精。
由上可见,仅从周叔弢一例可以看出,藏书家们对古籍装订修补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也非常依赖古籍修复技术,请人装订修补成为他们藏书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好古籍修复工作,实是延续古籍寿命的重要保障。然而古籍修复良工成才不易,精湛的装订修补技术也难以承传下去。以手工为业的修书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多以父子或师徒相承的方式进行口耳相授的承传,难以用文字的形式传承,这也是古籍修复这一行业传承上的一大困境。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录》中跋《近事会元》五卷后云:“是册装池尚出良工钱半岩手,近日已作古人,惜哉!其子虽亦世其业,而其装池却未之见,不知能传父之手段否?甲戌闰春,复翁偶记。”[4]钱半岩之子在古书装订修补史上无甚名气,似未获其父真传。长期给周叔弢装订修复的王晋卿,又名王文进(1893—1960),文禄堂主人,有书目题跋《文禄堂访书记》五卷,记其三十多年间所见闻的七百五十余种善本。1956年文禄堂并入中国书店,王文进被聘为顾问,其技艺由其侄锡华继其业,也未知其侄是否得其妙技。可以看到,传统古籍装订与修补技艺的承传,多赖父子、叔侄、翁婿等传承,传承面狭窄,实难持续,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
2 明前修之大业——《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问世
2.1 《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作者
自明周嘉胄《装潢志》、清周二学之《赏延素心录》以来,对古籍装订修补的记载可零星见于各种书籍中,但未见系统之著作。良工如“钱半岩”者,也未能留下关于修复的文字著作,殊为遗憾。正如《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后记”中所论,“过去以单篇文章介绍书籍装订的作品虽多,但不是因为资历缺乏而论述不详,就是由于出自文人学者之手而难于具体,因而很难掌握操作方法;至于经过实践系统成书的著作,至今还未曾出版刊印过。”[5]99可见关于古籍装订与修补技术的著作,实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
本书的作者,肖振棠为著名的“三肖”(肖顺华、肖振邦、肖振棠)之一,为原北京图书馆的古籍装修组组长,有着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不仅会修书,还懂书。“三肖”入馆修书,源于1950年《赵城金藏》入藏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53年,该馆正式成立科级建制“图书修整组”,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对《赵城金藏》等古籍的修复。从1950年到1965年修复工作结束,《赵城金藏》的修复共用了近16年的时间。其工作流程是:“一批古籍书领来后,肖振棠先生召集各位师傅,研究每部书的修复方法和修复时间,没有登记册,只是写在纸条上,夹在书里。修书人按纸条上所写的内容进行修复,并按时完成任务。每个人修复完成后,都要交给肖振棠先生检查验收。”[6]1961年7月至1963年7月,文化部群众文化局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第一期装修古籍线装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肖振棠即为当时的主要师资人员之一。该班以“师带徒”的形式进行,6位师父共带7位徒弟,肖振棠所带的徒弟是北京图书馆的宋康民。在此次训练班中,肖振棠承担了较多的工作,据当时学员回忆:“主要是由肖振棠等老师带领学员修复《赵城金藏》,在实践中学习修复技术,积累经验。”[7]1964年初又办了第二期。如本书《后记》中所说:“这本小册子是一九六四年初,在工余之暇进行编写的,时写时停,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可见该书确有《赵城金藏》修复实践以及修复训练班之教学工作总结的背景。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长时间未能进一步修订。
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通过吴庆彤做出指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作为周总理的遗愿之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得以启动。在编制古籍善本书目的过程中,一些古籍善本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图书馆和古籍书店等单位,对搜集整理古籍已掀起了一个高潮。相应地对古籍的装订修补工作和培训这一工艺技术的人员,更加有着迫切的要求。”[5]1-2随着古籍重装修复的需求的日渐增多,“一九七八年通过一些从事整理古籍工作的同志建议将此书出版,以供使用或保管古籍单位参考。因此又将尘封十数年的底稿找出来,进行了全面地改写修订……”[5]100《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问世,可谓是恰得其时。
本书的另一作者丁瑜,从事古籍保护研究多年,主要从事版本鉴定与古籍编目工作,有较高的理论研究素养。从二位作者的合作来说,肖振棠为从事古籍装订修补50余年的良工,丁瑜为古籍编目界的专家。一个有丰富的实践,一个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因此才有该书的合作问世。书中还由张耀华绘制插图,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古籍装订修补技术。
2.2 《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内容
该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为书籍装订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第二章为装修古旧书籍常用的名词,第三章为装修古旧书籍应有的设备及常用材料,第四章为古旧书籍的修补与装订,第五章为古旧书籍的各种不同装修法。在笔者看来,第一章为“史”,第二章为“学”,第三章、四章、五章为“术”。尤其是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书的重点,所占篇幅也较大。现以“史”“学”“术”为线索,探讨该书的相关内容。
2.2.1 从纵向角度,构建古籍修复简“史”
探讨中国书史的相关著作,较为著名的就有刘国钧的《中国书的故事》,初版于1955年,再版于1963年,其中对中国书的形制和起源也做了部分探讨。《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用了7页的篇幅简要回顾了中国的书籍装订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包括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书籍的形式变迁,从龟甲、金石、简牍、简帛到纸张,并探讨各种装订技术的优缺点。得出“总之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创造书籍所用的材料不同,书籍的装订形式也随着有所变化。龟甲、兽骨、竹简、木牍是一片一片的,装订它的方法,是用捆扎的形式;缣帛质地柔软,则采用卷轴的形式外,更逐渐改进到采用折装,到十世纪初,又由旋风装过渡到蝴蝶装,以后又改进为包背装以至到今天还流行的线装”[5]8的结论。这一看法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一个研究领域的形成,离不开对学术史的追溯,这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本书对书史和古籍装帧形制的纵向总结,尽管简略,但不可或缺,且有着重要的意义。1982年丁瑜在《漫谈书籍修复与书画装裱》[8]一文同样也追溯了古籍装帧形式的发展,笔者据此判断,此一章的内容应是丁瑜所作,为古籍装订与修补技术的相关研究赋予了理论色彩。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章应还可以写得更深入、详细一些为好,但作者或以为书之重点在装订修补技术,所以亦不便分外苛求。
2.2.2 从学理角度,规范古籍修复“学”
(1)对装修古旧书籍常用的名词进行界定
行业专有名词的掌握和熟练运用一般是判定是否“入行”的标准。该书也意识到这一点,提到“在传授或学习装修古书的操作过程中,对一部书的各个部位及其附属或有关的配件,必须准确地掌握其名称,才能保证古书装修的质量。”[5]10因此该书对装修古旧书籍常用的名词一一作了界定,共有:书品、边栏、书耳、版心、鱼尾、天头、地脚、书脑、书根、书背、副叶、封面、书皮、书签、帙、褾、带、签、囊、书套、纸匣、木匣、夹板、函24个专用名词。其中书中将书品从广、狭义两个角度进行了界定。认为:“广义的包括刻本书籍的初印、后印;抄本书的新旧;刻本或抄本的纸张,墨色、字体、插图的优劣;行格、款式的疏密工致;有无序跋、封面、牌记;藏书印鉴及批校题跋的真伪、装订形式的工拙等。狭义的指书籍边栏外面四周余纸的大小和书籍的破旧程度。”[5]10笔者日常学习研究中,常听人提及“书品宽大”“书品好”之类的评价,觉只是泛泛而论,不能具化,难以从细判之。此书对“书品”的广、狭义二种解释,尤其是广义的定义,当能让读者产生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另外笔者也曾看到有些古籍用薄纸蒙住封面,未得其故,该书给出了解释:“古书的封面位于副叶的后边,封面上印有书名,撰书人姓名和刊板地点等。其作用原为保护书叶,但因我国古书的封面多注重题写书名的书法,尤其重视题字的人名。因此常以极薄细纸罩在上面,使封面上的字迹隐约可见,以保护封面,而逐渐失掉装配封面的本意了。”[5]11-12此一段,适可解笔者心中之惑。
另外我们还可通过最新的国家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GB/T21712—2008)来看,其中界定的古籍修复相关的术语有31个:古籍、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书叶、版框、版心、字迹、跑墨、烘色、褪色、天头、地脚、封面、护叶、书芯、书头、书脚、书口、书脑、书背、书眼、书角、书衣、书签、标序签、补纸。相同者有:版心、天头、地脚、书脑、书背、副叶(护叶)、封面、书皮(书衣)、书签9个,由于各自着眼点不同,所以不尽相同,但仍可以看出承传的路径。为此,徐家泉认为该书在一些术语的确定上为此后奠定了基础,如:“书中对破损古籍的补救工作主要使用了‘古籍修补’这一称谓,部分地方则使用了‘古籍装修’‘古籍修整’的概念。”并认为“这些名称大概就是古籍修复行业在现当代时期最早的称谓了。”[9]该书所用的术语中,题名是“古籍装订修补”,书中也曾用“古籍修补”“古籍装修”“古籍修整”“古书装订”等概念。《后记》中用“装订修整技术”。但究其实,仍可以以题名中的“古籍装订修补”概括之。今人口中的“古籍修复”,说到底无外乎“装订”与“修补”两大内容。现在称“古籍修复”,应是为名称更合雅驯之故。
(2)对一些重点问题的探讨
书中对“旋风装”的探讨尤为引人重视。对于“旋风装”的形制,因现存实物稀见,有多种说法。在该书中,作者将旋风装的定义为:“即把卷子折叠成册,然后用一张比折子宽一倍的厚纸,从当中对折起来,上半折粘于卷首,后半折粘于卷尾,折叠时像一册平装书,全部拉开如同一个大的纸套。翻阅时既不会有散开扯断的缺点,还可以从第一叶翻起,直翻到最后一叶,并仍可继续由最后一叶翻到前面;周而复始,不会间断。这种回环往复翻阅的书,宛转如旋风,就叫它作‘旋风装’”[5]6。1982年丁瑜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旋风装’亦称‘龙鳞装’或‘鱼鳞装’,其装制是首叶单面书写文字,其他各叶均两面书写,以一长条卷作底,除首叶因单面书写,把无字的一面全幅裱于卷端外,将其余双面书写的叶子,把每叶右边栏外空白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在首叶末尾的卷底上,看去好似鱼鳞错叠相积,收藏时,从首至尾卷起,外表完全是卷轴的形式,但开卷之后,除首叶因裱于卷底不能翻阅外,其余均能逐叶翻阅。”[8]关于“旋风装”的形制,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书中的观点,李致忠认为是附议了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等著作中关于“旋风装”的看法[10]。丁瑜的后一种观点,现已被收入曹之的《古籍版本学》[11]等著作中。故宫博物院保存有国内唯一一部旋风装图书《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被多人用来证明是属于后一种观点的旋风装形制。对于“旋风装”具体为何种形制,是否有更多的形制,将来或还有待更多的实物证明。不过,仍可看出本书作者持续探讨相关问题的不懈努力。
2.2.3 从技术角度,认真传授古籍修复之“术”
此一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也是凝聚本书作者经验心得最为集中的地方。
(1)利器美材,种类齐全的装订修补工具
《髹饰录》中谈及“凡工人之作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此以有圣者,有神者,皆示以功以法。故良工利其器。然而,利器如四时,美材如五行。四时行、五行全而百物生焉,四善合、五采备而工巧成焉。”[12]若要得“良工”,须有“利器美材”,方能“工巧成”。为此,本书在第三章重点介绍了装修古旧书籍应有的设备及常用材料,包括:装订室应具备的条件和设备、装修工作所必备的35种工具、17种常用材料,可谓是构建现代修复实验室的指南。如今,各图书馆纷纷建起了古籍修复实验室,似仍可从本书中找出最初的雏形。
(2)浆糊制作与使用,繁复如“冷香丸”
读者在读《红楼梦》时,当对薛宝钗所吃的“冷香丸”印象深刻,用料精妙,工艺复杂,让人瞠目结舌。如果说那是小说家言,不尽真实,那么本书所介绍的浆糊制作似也有同工之妙,并且真实可信。该书介绍浆糊制作,一共须经提炼淀粉、澄清、制浆糊、熬浆糊、捣浆糊5个阶段。其中“澄清”部分,看似简单,然过程亦十分繁杂,试看:“淀粉洗出沉淀后,须放在清水盆中过三至五天,等清水变成较稠的黄汤,用净勺将黄汤撇出,更换清水与淀粉搅合均匀。经过三天左右,水又变成淡黄色。按上法再更换一、二次清水,以清水不变色,能保持清汤为度,即可用之熬制浆糊。”[5]22从时间上说,先是3—5天,又3天,又3或6天,加起来少则9天,多则14天;此外还须观察黄汤的颜色浓淡,再撇出黄汤,再观察,直至清水不变色再进行下一步。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而已,可见整个过程工艺较为繁杂,蕴含了良工的心血巧智。当然,这是繁杂的一面,为照顾多方面的需求,书中也为“对于需要浆糊不多而又不经常使用的单位”,介绍了制作浆糊的简单方法。
对于浆糊的用量,书中也做了详细介绍。“书叶纸厚用糊不可过稀,书叶纸薄不可用稠浆糊。因为用稠浆糊容易起皱,而且难于捶平,用过稀的浆糊容易开裂。所以浆糊调的是否适当,对于修补残破书籍的质量有着很大的关系。”[5]39浆糊的使用,可谓是古籍修复的“灵魂”,无怪乎作者如此认真了。
(3)金针度人,装订修补方法全总结
书中第四章全面介绍了书叶去脏法等8种修补古旧书籍的基本技法,罗列了虫蛀鼠咬书叶修补法等6种破损书叶修补法,并对15种古旧书籍装订的程序和操作法进行了逐一分解。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对线装书籍、毛茬书籍、卷轴书籍、折装(梵夹装)书籍、蝴蝶装书籍、包背装书籍6大类装帧形式的不同装修法,其中又分列出线装书籍金镶玉装修法4种,蝴蝶装装修法4种,包背装书籍装修法4种,可谓是对古籍装订修补方法的全面展示和总结。
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写书根字。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胡贸 虞山孙二 钱半岩(装订一首)》诗云:“蚕丝牛毛善离合,得钱即买酒盈缸。书根双腕能齐下,嘉话真堪继湧幢。”此三人,胡贸“善离合”、虞山孙二善写书根,钱半岩善装池。善写书根的孙二,《藏书纪要》载其“写书根最精,一手持书,一手写小楷极工,今罕有能者”[13]。可见,“写书根字”确实是古籍装订修补工作中的一项流程。如书内所说,“书的下脚写书根字,使人检查某一册书,顺手可取,起到索引的作用,特别是册数多的丛书,写书根字对取阅书籍更较为方便。”[5]66但现在出于古籍保护的考虑,已不宜再在书根上题写,这更像是一门“绝技”。但对于当代的新印古籍,或仍可采用这种方式,或写或印,使这门“绝技”得以承传。书中对如何写书根字,介绍入微,有兴趣者或可一一尝试。对于原书带有书根字的,修复时须原样保留。
另外,金镶玉装修法也让人大开眼界。“金镶玉”又称“穿袍套”“惜古衬”,该书在脚注中说明“后来人们把这一名词借用在镶书的方法上。也有的解释为旧书多为黄色,镶上白色的新纸,故称为金镶玉。”[5]75并说明“穿袍套”“惜古衬”均是南方的名称。作者介绍了线装书的四种金镶玉装修法,分别是:一般法、衬镶法、连粘带镶法、裱镶法,另还有一种蝴蝶装金镶玉装修法,这些主要针对善本书而定。金镶玉是一种极具传统美感的装帧形式[14],这些详尽的操作指南,成为后人古籍重装“金镶玉”时的重要参考。
2.2.4 概括总结,提炼修复的原则
(1)修旧如旧原则
1950年5月14日,在《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上,赵万里提出“过去本馆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自(民国)廿三年后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15]可见,在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就已意识到“要保持原样”的原则,也是周叔弢所提的“勿损原书为要”的原则。在该书前言中,作者也提出“残破的古旧书籍,经过精心装订修补,不但能翻旧成新,还要整旧如旧,以延长书籍的寿命,恢复其特有的风格,并且加以美化。”[5]1“装修旧有古籍,既要有所创新,更要保留古书原有的时代风格。”[5]67其中就提到现在古籍修复的原则——翻旧成新和修旧如旧。尤其是“修旧如旧”,是该书屡次强调的重点。如谈及缺栏补字时,“如果是明朝以前的古旧书,可以不补字划栏,因为对古本书最好保持它的原来面貌。所以在修补古旧书籍时,应该注意这一点,掌握整旧如旧的原则。”[5]36“珍贵的善本书要加工细修,还要注意保持原书的时代风格。”[5]37“如有损坏,只能在保持原来形式风格的基础上进行装订修补,不能任意改变破坏它旧有的风格。”[5]46一而再,再而三,对“修旧如旧”这一原则再三强调。现在此一原则像一枚烙印,已深深烙在每一个古籍修复工作者的头脑中。
(2)区别对待的原则
对于珍贵的善本书,与一般的古籍修复均有不同,前者的修复会要求更高,“修旧如旧”的理念贯穿始终。“对时代较早,有版本价值的善本书籍,须采用整旧如旧的装修法,以保持文物特点。装修时,要求不补字、不描栏、不划栏、不要有求全的思想。对珍贵的古书来说,一字的模糊,或一段界栏的断线,都是考定板本的有力证据。所以在装修时,不能随意补字、描栏以冒充初印。清代内府‘天禄琳琅’藏书多为宋、元、明善本,但在装订时多有补字描栏。这样既失去了古书的真相,也影响了考定板本的证据。这是一种损坏古书的做法,必须注意。”[5]70对于一般古籍,该书中提及“如有缺字的地方,可按照同一种书,用墨笔临摹补写齐全,以便阅读。”[5]68其后,丁瑜在其论文中也重申了同样的观点[8]。目前古籍修复界出于保护和畏难的情绪,基本不再主张划栏补字,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思[16],也是遗忘了本书中所提倡的“区别对待”原则。同样,对书皮进行修复时,也可见出区别对待的原则,“原有书皮,如果是清乾、嘉以前时代较早者,必须一律修裱整齐,依然在原书上使用。年代不足百年的书皮,又无收藏家题字者,可以更换新皮。”[5]95当然后人在此基础上,也曾提出“修复普通书必须像修复善本书一样”[17],是强调不能在修复普通书时偷工,与本书这一原则并不冲突。此外,后人还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更多的原则,如可逆性原则等,在古籍修复理念方面更为进步。
在该书中,处处可见作者多年心得的总结。如难于溜口的书叶时,“例如明代末年闵齐伋刻印的书籍,就用这种伸缩性很快的纸,溜口时十分困难。”“根据工作中的经验遇到这类书叶,要采取速抹浆糊,速溜口,才能避免发生干后书口弯曲的现象。”[5]31此非亲历者不能道。其中介绍的“热气蒸揭法”,也是从修复“赵城金藏”时总结而来的。1989年,夏国军跟随肖振棠学古籍修复时,还得其口授此种“蒸揭法”[18]。其中也有较为难解的,如“书叶两面有字修补法”“书叶随布分成两个单叶,粘在布上了。”笔者经询问相关修复专家,得知该修补法确实是可实现的,足见我国古籍修复技术的高超。
3 结语
该书继承了明周嘉胄《装潢志》、清孙庆增《藏书纪要》等前人关于古籍保护和修复的知识,既为中小型图书馆介绍了简易修书法,也介绍了高深精湛的修复技艺。自出版后,即被誉为“使濒于灭绝的古籍装修传统工艺得以保存,对当前的古籍装修工作和使祖国千百年来优良的装订技术有所发展和改进,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19]近年来也获有定评:“比较全面展示了经验性技术时期的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尤其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修复技术,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古籍修复技术体系。”[20]两位作者的合作也可谓是“珠联璧合,厥功至伟”[21]。自1980年出版后,下启近40余年来古籍修复之事业,对后来的古籍修复专家,如潘美娣《古籍修复与装帧》、朱赛虹《古籍修复技艺》、杜伟生《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曾被列为博物馆学研究的参考论著[22]之一。1987年又被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翻译成了英文[23],2016年该书被收入丁瑜的《延年集》[24]中,以广流传。同年,经姑丽尼格尔·艾斯卡尔、米娜娃尔·阿不都翻译,该书有了维文版[25]。该书也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26]。如今,古籍修复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得到了较为完善的保护,还设定了传承人制度。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除了用文字来记录古籍修复的技术,我们还可以用视频的方式完整记录修复的操作过程和方法,相信古籍修复事业将来会发展得更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