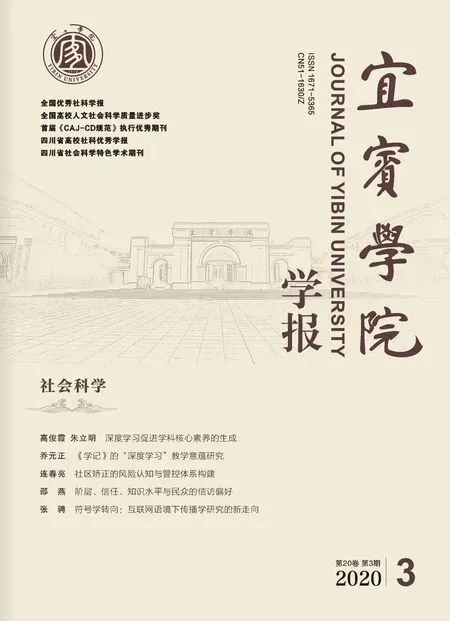《学记》的“深度学习”教学意蕴研究
乔元正
(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重庆408100)
深度学习是学习者在理解学习的基础上,改组改造原有认知结构,建立新旧知识经验的联结,最终实现知识迁移的有意义学习过程。国外深度学习的理论与实践源起于计算机科学、人工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加拿大学者辛顿(Hinton, G.)在《利用神经网络刻画数据维度》(Reducingthedimensionalityofdatawithneuralnetworks)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计算机深度学习模型和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概念,掀起了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的高潮。源于人工智能、脑科学和学习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深度学习逐渐引发了教育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和重视。国内关于深度学习的系统研究是最近十余年才开始起步的,黎加厚教授的《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一文首先介绍了国外深度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对深度学习的本质进行了最早的概括。郭元祥教授较早而且系统地对深度学习进行了研究,并在前期基础上推动了能力导向的深度学习理论和实验研究。时至今日,“深度学习”依然是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并非唯一的学习主体,教师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和教师统称为学习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学记》①),就“教学相长”的原初意义而言,教师通过知识学习而“知不足”,通过教学实践而“知困”,《兑命》曰:“学学半”,教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深度学习概念虽经国外引入并广为研用,然而深度学习蕴含的教育智慧在我国最早的教育学著作《学记》中就已有之,我们在重温教育经典的同时关照当下课堂教学,返本开新地理解传统文化中深度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有利于摆脱西方话语主导的困境,推进深度学习的本土化研究,凝练中国教育经验、贡献中国教育智慧。
一、 “少教多学”的理念与深度学习的提出
当前中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存在“教的多,学的少”现象,教师以教材为中心、以讲授为主的传统注入式教学法依然根深蒂固。“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学记》),教师教学习惯于照本宣科、汲汲于教学进度,热衷于“满堂灌”而不自思,以致学生学习流于呆读死记、机械被动,仅仅停留于记诵复述的低层次思维,分析解决问题的高阶思维和批判能力无从培养。“学习不是对知识的简单加工,不是单一的知识训练活动,而是复杂的、深层次的、多向度的意义建构活动”[1],有意义学习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师生双向互动建构生成的。高效课堂应该是“教师少教、学生多学”,学生在课外学习课程相关知识,通过课堂合作讨论的方式完成知识内化,教师从“课堂主导者”变身“学习促进者”,帮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建立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实现认知结构的改组和改造、培养高阶思维并形成问题解决的能力,以期最终实现有意义学习,这个过程正是“知识建构”和“知识迁移”的深度学习过程。
(一)国外深度学习概念的提出
国外教育学领域首先明确提出深度学习概念的是美国学者马顿(Marton, F.)和萨尔约(Saljo, R.),1976年出版的《论学习的本质区别:结果和过程》一书中表述了表层学习和深层学习的概念。[2]他们通过一项阅读能力(reading ability)的实验深入研究了阅读学习的层次问题,发现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实际使用了两类知识学习的策略,即表层学习(surface learning)和深层学习(deep learning),前者属于简单识记事实的符号表征学习,后者属于理解思想内涵的概念或命题学习。该阅读实验中的表层学习是简单陈述性知识学习,主要为符号表征学习(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和事实学习(facts learning),难点不在理解而在保持,其知识获取和保持依靠复述(rehearsal)策略,对知识的处理是机械化的,教师教和学生学均为被动的反应。深层学习则为浅层学习的深化,属于基于理解的复杂陈述性知识学习,学习者依靠组织策略清晰地知觉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基于知识的内在结构,通过对知识完整处理,引导学生从符号学习走向学科思想和意义系统的理解和掌握的学习”[3]。深层学习以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发展能力并实现有意义学习为最终目标。
加拿大学者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在深度学习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引导方面贡献卓著。2013年,富兰与英特尔、微软等国际教育集团以及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科技公司联合启动了“为了深度学习的新教育学”(new pedagogies for deep learning)的研究项目。他认为深度学习是一种质性判断,而不是单纯的量化概念,“这一学习从关注书本知识转换到聚焦学习过程,发展和引导自己学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一教学的目标不仅是掌握现有的知识内容,且是在现实世界中创造和运用知识”[4]7。质而言之,富兰的深度学习旨在培养学习者问题解决、合作和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并提升其批判性思维。与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J.S.Bruner)和奥苏伯尔(D.Ausubel)一样,富兰重视“知识迁移”(knowledge transfer)的作用,他认为深度学习有助于将原有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陌生情境的问题解决过程之中。就教学目标而言,“为迁移而教”,学习的迁移量越大,说明学习者适应新情境或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越强,教学的效果也越好。
(二)深度学习本土化研究概述
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深度学习思想,其宗旨皆在于培养性理明达、道德昭彰的人,人的“发展”是其理论旨趣。我国最早的教育学著作《学记》开篇指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开宗明义地强调了教育的作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通过类比形象地指出了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成人”,人不经教育便不懂得政治和伦常的大道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开篇便讲学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则进一步阐明了学习与思考的关系。“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教学无定法,其精神要旨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认为学习是人不断丰富、不断成长的过程。“学莫便乎近其人”“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学恶乎始?恶乎终?”《劝学》对师生交往、学习方法和学习过程等基本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论述。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深度学习思想,应当充分发掘其教育和心理意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了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并实施深度学习的要求,即“教育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独立性、体验性和问题性”[5]。国内学者对深度学习的定义是学习者在理解学习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整合已有知识并将新知识融入原有认知结构,在知识迁移过程中完成有意义学习并做出决策、解决问题的学习,其特征表现为注重深层次理解知识、重视整合知识内容、培养学生主动积极的学习态度和发展学生高阶思维四个方面。例如,郭元祥教授认为深度教学是对表层知识符号教学的超越,教学要注重知识的内在逻辑和意义领域,深入挖掘知识的内涵价值,促进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发展。[6]罗祖兵教授认为深度教学是让学生深刻理解学习内容且深度参与教学过程的教学。[7]李松林教授认为“深度教学是立足学习过程,抓住学科本质,触及学生心灵深处,促进学生持续的发现和理解,并建构知识、经验、能力、意义的教与学活动”[8]。郭华教授认为深度学习是促进学生知识、技能、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全面参与、全身心投入的活动。[9]张浩等认为“深度学习要求学习者掌握非结构化的深层知识、主动的知识建构、有效的迁移应用及真实问题的解决,实现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高阶能力的发展”[10]。黄志芳等认为深度学习是学习者在知识掌握基础上自主学习、沟通协作及解决问题等能力的培养过程,学习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学习情绪体验。[11]
二、 《学记》中深度学习的关键特征发凡
深度学习具有深层理解知识、主动建构知识和发展高阶思维等三大特征。首先,教师不为“记问之学”,博学而约取;“使人由诚”,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教人尽材”,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则有利于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其次,学生“知类通达”,举一反三;“教有正业”,课堂上内化吸收知识;“退有居学”,课前自主探求知识,则有利于知识的主动建构。最后,教师“善喻”,擅长启发引导学生;师生均“善问”,教学相长、在交往中建构生成;教师“善待问”,深谙教学艺术并启迪学生的深层思考,则有利于高阶思维的发展。
(一)深层理解知识:“记问之学”“使人由诚”与“教人尽材”
表层学习的策略为复述和精加工,适用于符号表征和事实学习,学习往往流于表面的机械识记,学习者无法了解学习内容的意义,教师或学生“念滑句”式的教或学无法使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旧知识与新知识建立联结,知识迁移难以达成更无法实现有意义学习。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者不是空着脑袋进入课堂的,教师需要将学生原有经验视作课堂教学设计的生发点和课程内容的来源,并将其作为学生知识、技能、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培育的首要素材。例如,课堂设计可以将“运用你的经验”环节作为“先行组织者”,迅速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然后通过合作讨论等环节让教学成为唤醒、重组、运用和反思经验的动态生成过程。因此,教师应精心挑选明了的、系统的、易于与学生已有经验契合的知识,促进教学与学生生活经验的融合,以利于实现深度学习。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全无实学,只凭记诵以待问”的教学方法是为《学记》所批判的。只教授“记问之学”说明教师教学方法单调乏味、知识和教学经验贫瘠浅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做到因材施教,不足以称之为“人师”。“夫人之才性有明暗之殊,而其学有浅深之异。或学博矣,而约有不能”[12]167,教师的才性或聪颖或驽钝、知识广度或宽泛或狭窄。然而,深度教学需要教师具备博学约取知识的能力,紧密连接学生的已有经验和情感体验,以“博学”的充分广度促成知识的意义建构,以“约取”的充分深度引导学生从符号表征学习到有意义学习的逐渐转化。“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学生提出问题而又不明究竟的情况下,教师开始做解释的功夫,如果解释后仍旧不理解,则暂时搁置问题,留待以后再解释。教师解答学生的疑问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知无不言、可以“留白”亦可以“搁置”,正如佐藤正夫所言,“与其发问频繁,不如让学生沉着彻底地思考”,“留白”或“搁置”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让学生保持继续探究的欲望,促进学习向深层次发展。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学记》批判了教师“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这种照本宣科、机械诵读,汲汲于进度的拙劣教法。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吟诵课文是必要的,然而教师如果一头扎进“故纸堆”,无视知识内容的难易程度、视学生为无物,便无法唤醒学生的经验、激发学习的兴趣。“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教师如果不考虑教学的巩固性原则,不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设问与传授知识远离学生的经验,那么学生就无法从“表层符号和事实学习”跃入知识的“逻辑与意义领域”,难以实现意义建构和深度学习。“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学记》认为这种不深层理解知识、没有知识迁移的教学和学习方式,只会导致学生厌学厌师,即便勉强结业了,知识也会短时间内迅速遗忘。
(二)主动建构知识:“知类通达”“教有正业”与“退有居学”
深度学习是学习者积极主动的自觉行为,学习者倾向于主动接受知识信息。课堂教学中的深度学习是师生双向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明确学习的目的和意义,教师善于将学生的已有经验作为教的出发点,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相关知识并善于将已有知识作为学的出发点。然后,通过课堂内合作讨论的方式将新知识与旧知识连接起来,在改组改造原有认知结构、采用同化或顺应策略以主动建构新的知识意义,“教师要引领学生深入知识的逻辑形式和意义世界,使知识的符号表征、价值意义和逻辑形式完美融合起来”[13]。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学记》在此处提出了深度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问题。“中年考校”,首先考的是“志”,“志”是学习者自觉学习的心理基础,指向学习者的深层学习动机、学习情感、学习态度和学习价值观。“志不立,学必无成”,学习者只有坚定正确的学习观、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激发自主学习潜能,深度学习才能达成。学生主动建构深度学习的过程离不开教师的引导作用,无论“离经辨志”“敬业乐群”,还是“博习亲师”“论学取友”都是教师“视学”与“考校”的对象,都离不开教师周密的要求和明确的约束。“知类通达”说明学生在长期学习以后,其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已经臻于纯熟,可以放手让学生独立进行知识的“再生产”,“再生产”的过程是有意义学习的过程,也是知识建构的过程,更是深度学习的过程。“强立而不反”,矢志不渝坚持学习的志向则更离不开学生的自觉主动性。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教的少,学的多”教学理念的基础是深度学习理论,其达成依靠教学方法的转化,即变革“课堂传递知识、课后内化知识”的传统教学方法,转变成为“课前传递知识、课堂内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按时进行正课教学、课后从事课外作业,既有课内任务、又有课外任务,既有教与学的配合、又有教师与学生的配合。“时教”要求教师作为“学习促进者”提供合作讨论的场域以帮助学生实现深度学习,“居学”则要求在课外闲暇时刻自觉主动学习。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离不开教师课内外的启发引导,教师的启发诱导又离不开学生的课外自觉学习。“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学生在课外学习操缦、博依、杂服等行为的实践操作以后,才可以在课堂上更好地学习《乐》《诗》《礼》等理论知识,学生在课外主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扩展知识学习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参与实践活动实现新旧知识经验的联结,最终完成有意义的深度学习。
(三)发展高阶思维:“善喻”“善问”与“善待问”
所谓高阶思维是一种高层次认知水平为主的综合性能力,主要表现为批判和超越已有经验,提出问题并运用策略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提高课堂效率、实现深度学习,师生需要具备“好问”和“善问”的积极态度。教师准确把握问难契机,才能激发学生的深度思考,而学生的善问则能促成深度体验、深度探究和深度思考。《学记》注重启发式教学和问答式教学,二者在教学过程中互为运用、相辅相成。问答式教学适用于符号表征学习和事实学习,用以培养学生的记忆、表达能力,对应浅层学习;启发式教学适用于逻辑系统和意义关系学习,用以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创造能力,对应深层学习。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引导学生而不牵着走,严格要求而不过分施加压力,启发诱导而不把道理和盘托出,如此可以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道”“强”“开”表明教师处于主导的主体地位,学生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弗牵”“弗抑”“弗达”是教师教学机智的显现,不是不能“牵”“抑”“达”,而是教师意识到了学生具有学习主体性。“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教与学的矛盾迎刃而解,学生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尊重,不仅不将学习视作畏途,还培养了自觉主动的意志品质和独立思考的创造能力。
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这里将“善问”的过程类比为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部分,然后砍那关节的部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问题自然得以解决,这个“善问”的过程可视作从浅层学习到深度学习的过渡和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善问”既可以指教师问而学生答,也可以指学生问而教师答,师生在问答的过程中互为主客体,体现了教师和学生的双向建构交往关系,即学生“善学”必然“善问”,学生“善问”必然倒逼教师“善待问”;教师“善问”必然导致学生“善学”,学生“善学”必然倒逼教师“善问”的良性教学循环。其中,“善待问”又比“善问”更需要教学的艺术,“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面对学生的发问,教师的解答要从易到难、螺旋上升,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向深层次的问题逻辑和意义层面思考,待学生有所领悟以后教师进而“转向”在点子上追问,让学生在疑难处思疑解疑,方可使学生对所问所学深刻理解,掌握知识本质、发展高阶思维,达成深度学习。
三、 《学记》教育思想对实现深度学习的启示
《学记》中的深度学习教学意蕴及其生动案例为实现知识建构和知识迁移的有意义学习,达成深度学习的教学目标提供了可能路径。首先,深度学习的达成有赖于教育哲学观的转向,教师应成为学生深度学习的“促进者”“善歌者”和“善教者”,帮助学生自主建构生成知识。其次,深度学习的达成有赖于教育心理观的转向,教师应具备“为迁移而教”的心理意识,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学以致用的能力。最后,深度学习的达成有赖于教学方法的变革,借助“翻转课堂”对教学要素的全方位重置,促进学生自主化、个性化和深层化学习的展开。
(一)教育哲学观的转向:“善歌”“善教”与知识建构
建构主义认为在一定教学情境下,学习者借助教师的引导和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习得知识,而非通过教师教授获得知识。“借助教师的支持,学习者能够自主建构知识”[14],教师需要改变课堂角色定位,做学生深度学习的“促进者”“善歌者”和“善教者”,而不是“主导者”“强牵者”和“强抑者”。意义建构是深度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是教师与学生主体交往互动的结果,意义建构体现了学习者根据已有经验建构知识意义的能力以及对知识逻辑和意义系统理解掌握的能力,而非符号表征和事实知识的记诵能力。可以说,意义建构的过程是学习者自主发现、探究,建构知识经验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学习者深度学习的过程。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尔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善歌”“善教”的教师支持和引导学生,学生由衷地跟随教师的指引自主学习。“善教”的教师使学生“继其志”,儒家“志”的落脚点是“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的“道”,深度学习领域的“志”即知识学习的意义系统和内在逻辑。“志”的学习深奥且抽象,教师为了引导学生深入发掘知识的内涵价值、实现知识建构的有意义学习,需要摒弃生拉硬拽、“满堂灌”的注入式教学方法。“约尔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教师需学会运用透彻凝练的语言、微妙精道的论理和恰到好处的讽喻等教学技巧,引导学生从自身经验中生产、创造出新知识,通过同化或顺应策略等改变原有认知图式,建立已有经验与新知识之间的联系,赋予新知识以理性意义,最终达成深度学习的目标。
(二)教育心理观的转向:“为裘”“为箕”与知识迁移
知识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知识、技能、情感和态度均可以实现迁移。学习者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并进行比较,通过引入“先行组织者”,以原有经验为出发点领会新知识,最终学会深度学习。奥苏贝尔(D.Ausubel)认为“为迁移而教”的实质是塑造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培养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和学以致用的能力。知识迁移意味着“深层地理解知识内容的同时能够识别何时(when)、如何(how)和为什么(why)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15]。知识迁移作为深度学习的策略,并不是符号表征和事实学习的简单机械记忆,而是要以“知类通达”的深层思维摆脱点状发散的浅层学习,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网络,以便在问题解决时迅速提取有用的知识。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查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经验丰富的铁匠传授儿子冶铁手艺,总是先教他学会用皮革制作鼓风裘;经验丰富的弓匠传授儿子造弓手艺,总是先教他学会用柳条编制箭袋子。“冶与裘异工,弓与箕异器,但其理可通”,“冶与裘,弓与箕,绝不相谋也,而相悟。”[12]173“为裘”与“冶铁”,“为箕”与“制弓”虽属于不同的具体的技能活动,然其“理可通而相悟”,学习“为裘”与“为箕”有助于学习“冶铁”与“制弓”。在相同类型知识和技能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形成了知识迁移的能力,即将某类具体知识和技能学习凝练为一般规律,再去指导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将“为裘”与“为箕”的知识技能学习迁移到“冶铁”与“制弓”的新情境中,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的联系实现了问题解决。在知识迁移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并鼓励学生突破对已有知识的理解、深入思考和分析新问题,最终进入深度学习的状态。
(三)教学方法的转向:“时教”“退息”与翻转课堂
就源起而言,翻转课堂源于对“课堂传递知识、课后内化知识”传统教学模式和浅层学习方式的不满,翻转的时空重置操作旨在通过革新教学理念实现学生的深度学习。就字面意义而言,是指课堂内外形式上和时空上的颠倒或转换。就本质而言,“所谓的翻转课堂,归根结底是教学观念的改造”[16],它以主动学习理论(active learning)和基于问题的学习理论(problem—based learning)为理论基础,旨在实现教学关系、教学过程、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反转”。就目标而言,翻转课堂通过对教学时空、师生角色等要素的重新配置,旨在通过良性的师生和生生交往,促进学习者自主化、个性化和深层化学习的开展。就操作方式而言,翻转课堂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搜集、识记和整理过程置于课外,课堂内以师生、生生合作讨论的形式分析、评价、运用和创造知识。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学生在课外练习缦乐、声律和洒扫沃盥等实践技能,目的就是为了在课堂上更好地学习《乐》《诗》《礼》等理论知识,实现“兴其艺、乐其学”的教育目的。事实上,操缦、博依、杂服在课外学,也在课堂内教;《乐》《诗》《礼》在课堂内教,也在课外学,教与学在课堂内外互换位置、交互作用,教师引导学生参与知识分享、深入思考、模拟真实情景并学会运用,促成有意义学习和深度学习的达成。《学记》这种“教有正业,退有居学”的师生互动教学方法可视为翻转课堂的原始范本。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时空的重置、师生的互动、学习流程的颠倒至少能够促成学习者发生两次知识内化。首先,学习者课外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新旧知识碰撞并开始联结,发生了第一次知识内化;其次,学习者课堂上将自主学习习得的“旧知识”通过师生、生生合作讨论再次获得新的理解,发生了第二次知识内化。通过认知结构的改组和改造,学习者原有知识经验与新知识经验建立必然的实质性关联,这种知识深加工的过程正是深度学习达成的过程。
结语
综上所述,深度学习是学习者在理解学习的基础上,改组改造原有的认知结构,建立新旧知识经验的联结,最终实现知识迁移的有意义学习过程。为了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更加直观地面对当下课堂教学的种种弊病和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更加真切地激活对当下教育问题的思考,我们在积极引进、研究和运用“舶来”的深度学习概念的同时,更应当将教育研究的触须根植于民族和国家的传统文化经典的肥沃土壤之中,不断回望并返本开新地阐释《学记》中有关深度学习的教学意蕴。以审慎的姿态将教育研究置于民族文化的理想视域之中,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本土化语境中深度学习的命脉并探寻达成的可能路径,彰显深度学习的重要价值,从而引发更多人对深度学习的研讨和实践。
注 释:
① 本文所引用的《学记》参考版本:《礼记》宋岳珂刻本(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翻刻),《礼记》宋抚州刻本(清同治九年楚北崇文书局翻刻),《纂图互注礼记》(《四部丛刊》影印皕宋楼本),《礼记注疏》(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