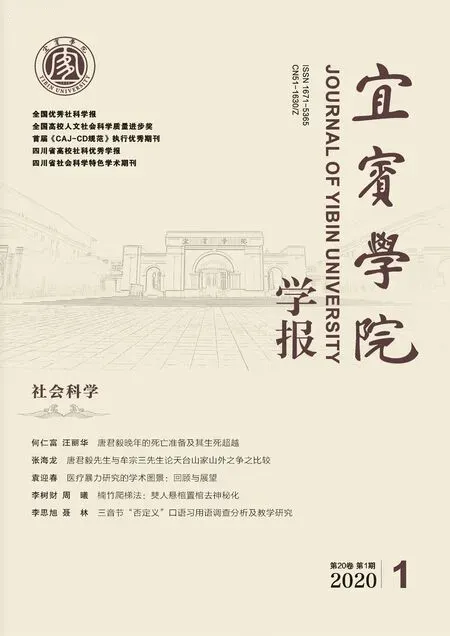“轻逸”与“沉重”──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迷宫叙事之比较
李明芮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博尔赫斯的热爱与赞美,且多次引用博尔赫斯的作品来阐述自己的文艺理论。因此,国内外批评界常常将两人一同提及。学术界对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各自的迷宫叙事有分别地探讨,但并没有对两人进行深入、系统地比较分析。中国学术界对两者迷宫叙事的比较研究鲜有研究资料,只有焦圣芝曾在《比较视域下的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创作研究》中,立足于二人的创作,对卡尔维诺是怎样将博尔赫斯虚构的小说变为真实以及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应对迷宫的策略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该文章缺乏对迷宫叙事本身的具体讲述,也没有对两者对迷宫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进行考察。因此,对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迷宫叙事的比较研究在国内尚属于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领域。卡尔维诺曾在创作上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但由于二人生活体验的不同,前者又对后者进行变异,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一、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
博尔赫斯身处20世纪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战争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思想文化同样发生了激烈的变化。面对时代的重大变革,作为作家的他选择以迷宫叙事应对。迷宫本是一种充满复杂通道的、错综复杂的建筑物,人们在迷宫中迷失、彷徨,无法到达中心,也难以找到出口。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迷宫具有非线性、循环、矛盾、交叉等特征,它指涉了现代人的焦虑与困苦。博尔赫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建造了一座又一座迷宫,他把迷宫看作是自己思想状态的正确象征,并直言:“它们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感受和生活的方式,并不是我选择了它们”[1]50-51。
(一)迷宫主题
博尔赫斯在青年时期受到了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在《自传随笔》中,博尔赫斯说:“在瑞士的某段时期,我开始读叔本华”[2]109。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本质,然而人的意志是始终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人生便是痛苦的。现实的混乱与复杂让博尔赫斯走向迷茫,眼疾更是让他饱受折磨。在重重打击之下,博尔赫斯选择以沉重严肃的语调探讨了自己对生存的看法。因此,对生存困境的探索便成为博尔赫斯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迷宫主题。
《永生》讲述了土耳其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在一份手稿中发现曾经的经历。他原本是驻扎在红海之滨的执政官,在一名垂死的骑手的激励下,他走向了寻找永生的道路。经历重重困难之后,他进入了永生之城,却迷失在其中,成为永生者的他选择了逃离。他走遍新的王国和帝国,找到消除永生的河流,迎接他的将是梦寐以求的死亡。执政官认为,人永远无法摆脱死亡带来的恐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去寻求永生并获得了永生,但却发现,永生并没有使人类摆脱生存困境,永生者迷失了自我,丧失了活力,彻底地走向了虚无,这时,他才意识到“死亡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3]15。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在死面前无路可走,并不是当出现了丧命这回事才无路可走,而乃经常从根本上是无路可走的,只要人在,人就处于死亡之无路可走中”[4]159。博尔赫斯正是用他那沉重的文字告诉世人:人们注定无法超越生存的困境,只能选择直面它、接受它。
(二)迷宫意象
除了将“迷宫”作为主题外,“迷宫”也被博尔赫斯作为意象来使用,这一意象在其作品中主要以抽象与具象两种形式展现。
《小径分岔的花园》为读者展现了抽象的时间迷宫。“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5]52除此之外,“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5]4。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各个时间的交叉与分岔形成了无数的可能。俞琛比马登上尉先一步到达月台,使俞琛在时间上领先了马登上尉,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时间在此开始分岔。阿尔贝说:“我们并不存在于这种时间的大多数里:在某一些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里,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一些里,您我都存在。”[5]52在小说中,俞琛处于现在,曾祖父存在于过去,俞琛站在现在的时间去回顾曾祖父的故事,现在与过去以这样的方式交叉;阿尔贝立足于现在的时刻对将来进行了大胆的预言,“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5]53。这句话的应验造就了现在与未来的交叉。博尔赫斯的这种多维时间观是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下产生的。相对论认为时间是相对的,它颠覆了传统的绝对时空观,博尔赫斯认为“这种观念认为不是只有一个时间。我相信这一观念受到了当代物理界的庇护”[6]54。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博尔赫斯在《对时间的新驳斥》中直接大胆地表示:“我否定一个唯一的时间的存在”[7]3。并通过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以时间的交叉与分岔构成了抽象的迷宫意象,表达了多种时间并存的观点。除了时间外,博尔赫斯也曾运用过空间、梦境、生存环境等抽象的迷宫意象。而在《永生》中,出现了具象的迷宫意象,具体表现为永生之城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有九扇门,八扇通向一个骗人的迷宫,最终仍回到原来的房间;第九扇(经过另一个迷宫)通向第二个圆形房间,和第一个一模一样,我不清楚房间总数有多少;越是着急越是摸不到正路,房间也越来越多”[3]7。博尔赫斯痴迷于自己的迷宫,无论是俞琛还是永生者都在迷宫的混乱繁杂中迷失、流亡。
(三)迷宫人物
在传统的西方叙事文学中,人物的塑造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些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在西方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人物是模糊与不确定的。
博尔赫斯十分推崇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里讨论了“一”与“多”的关系,他认为“一”即是“多”。这种观点落实到博尔赫斯身上便是他那种“一个人可以变成许多人”的构思。博尔赫斯在《恶棍列传》中塑造了一系列“恶棍”形象,这些形象让人眼花缭乱。出现在美国杂志上的莫雷尔的照片不是他本人,他从不摄影留念,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容颜。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有5个名字,如同“累人的假面游戏”。除此之外,他的身份也扑朔迷离,他起初是鸟店老板,1894年在舞厅任保安一职,1899年起,又成为重要选区的把头,后因解决地区争端被捕入狱,出狱后的蒙克最终成为步兵。博尔赫斯对于人的身份问题的困惑同样来源于他对自我的追问,他曾说道:“为了知道我是谁,我没有必要回忆我,比如说,曾在巴勒莫、阿德罗格、日内瓦、西班牙住过,同时,我必须感到现在的我不是住在那些地方的我,我是另一个我,这是我们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不断变化的身份的问题”[8]189。博尔赫斯通过模糊的形象、人物的多重身份来完成对迷宫人物的塑造,这些迷宫人物在各自的文本世界里迷失了自我,最终走向了死亡。
(四)迷宫结构
博尔赫斯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消解了传统西方文学中线性的、封闭的叙事结构,而以极具创新性与反叛性的意识,构建了具有不确定性与多样性的迷宫结构。这种迷宫结构在他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嵌套与对立。
1.嵌套结构
博尔赫斯的《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中的赫伯特是一名作家,他的作品《四月三月》是一部“逆行枝蔓”的小说,运用倒退的叙事方式构成“无限的故事,无限的枝蔓”。其中,第一章讲述了一个故事,第二章讲的是第一章前夕的事,第三章和第四章都是讲述第一章可能的前夕,三个前夕中的每一个分为另外三个前夕。全书包含九部小说,每一部小说包含三章,这些小说题材不同,有共产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侦探小说等。博尔赫斯通过赫伯特的叙述展现了对于嵌套结构的初步想法,并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完成了对于嵌套结构的实践。《小径分岔的花园》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以俞琛为主要人物的间谍故事,而其中却嵌套了汉学家阿尔贝的故事以及云南总督的故事。
2.对立结构
前文提到博尔赫斯深受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是原本和摹本的关系,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博尔赫斯的创作。《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以特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展现了现实与幻想的真假难辨。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中,自我具有双重性,博尔赫斯深谙这一观念,《博尔赫斯和我》《作家博尔赫斯谈博尔赫斯》《另一个人》以对立的“我”与“博尔赫斯”表现了自我的分裂与迷茫。可以说,博尔赫斯的对立迷宫既让人丢失了自我,也让人分不清真实与虚构。
二、卡尔维诺的变异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强调:“我们可以说,从我这一代人开始,过去二十年来从事创作的人都深受他(博尔赫斯)的润泽。”[9]277并表明“我在博尔赫斯那里认识到文学理念是一个由智力建构的世界”[9]277。如果说博尔赫斯笔下的迷宫世界展现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混乱,那么卡尔维诺则在博尔赫斯的影响下保持客观理性的状态,用心灵的秩序对抗世界的复杂性。他凭借自身的文学悟性对博尔赫斯的迷宫加以发展,构建了自己的迷宫,也以轻逸的姿态飞出了迷宫。
(一)迷宫主题
卡尔维诺从小家境优越,生活无忧无虑。他曾在《青年政治家回忆录》中将自己的父母称作“自由思想家”[10]21,自由更是他一生的追求。青年时期的卡尔维诺加入了共产党,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让他对自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苏共的强硬与意共的软弱让他更加珍惜文学的美好与包容。因此,他远离政治,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他在《美国讲稿》中以古希腊神话为例:珀耳修斯拒绝直视美杜莎的面孔,而是通过铜盾的反射割下了美杜莎的头颅。在卡尔维诺看来,人的一生虽然不得不面临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但却可以以一种“轻逸”的方式去面对。
经历了二战后的卡尔维诺发表了颇具童话色彩的《树上的男爵》,他运用另一种方式去展现生存困境。男爵柯西莫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的双重压力,在一次午餐中,因拒绝吃姐姐巴蒂斯塔做的蜗牛,他一气之下选择在树上生活。尽管生活在树上,柯西莫并没有脱离与家人、社会的联系,反而找到了另一种适合彼此的相处之道。面对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柯西莫始终坚守自己的内心,凭借自身的智慧与才能,以“诗意地栖居”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卡尔维诺不仅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反映了人们面临的生存困境,同时,他还为人们提供了化解这一困境的办法,即回到最原始的心境,不被外界的纷扰蒙住双眼,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二)迷宫意象
与博尔赫斯不同,卡尔维诺不再使用抽象的迷宫意象,而是为文本“减重”,将迷宫意象以具象形式展现,例如城市、棋盘、塔罗牌等。其中,城市这一意象最具代表性。城市是人类世界的缩影,见证了社会的发展。从卡尔维诺自身的经历看,他与城市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1923年出生于古巴,两岁时迁回到故乡圣莱莫,1945年全家迁往都灵,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卡尔维诺常常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辗转,并对城市意象情有独钟。他在《美国讲稿》中提道:“城市这个形象比晶体与火焰的形象更为复杂,我可以用它来表现几何图形的合理性与人类生活的混乱状态之间的矛盾。”[11]70
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他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城市意象,人们在城市中迷失了自我,城市就是一座让人无法逃离的迷宫,然而他却为每一座城市取了女人的名字,女性向来是以温柔、善良著称,给人以亲切感。在“轻盈的城市”中,卡尔维诺为我们描绘了建在地下湖上的千井之城伊萨乌拉,她依靠地下湖泊提供养料;建在高教桩柱上的珍诺比亚具有悬空的走廊与纵横交错的阳台;阿尔米拉是一座由管道构成的城市,受水泽仙女和水神庇佑;索夫洛尼亚由两个半边城市构成;蛛网之城奥塔维亚悬在半空,行走在木板上,脚底是飘逸的云朵。多个城市的交织呈现构建了复杂的迷宫,通过这些城市意象,卡尔维诺揭示了现代城市空间中残酷的生存境遇,然而温柔的女人的名字与飘逸的城市姿态却消解了城市带给人的沉重、压迫。卡尔维诺曾表示自己是一个塔罗牌迷,因此塔罗牌意象在卡尔维诺的作品中同样具有超凡的魅力。在法国符号学的影响下,卡尔维诺创作了《命运交叉的城堡》,小说中的人们在穿越森林后离奇失语,只能依靠78张塔罗牌讲述自己的故事。每张塔罗牌具有多重含义,对每一种意义的取舍只能根据故事的环境加以裁定,因此,每张塔罗牌的意义并不是取决于它自己,而是依赖于其他的塔罗牌。塔罗牌在文本世界中组建成了一个庞大的迷宫,然而,塔罗牌的出现消解了传统的、只能依赖于文字叙述的文本所带来的压力,可以说,塔罗牌与文字的综合叙述反而给文本营造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轻逸的叙事空间。
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了极为精妙的迷宫意象,这些迷宫意象筑造了庞大的迷宫系统,成为小说发展的线索。如果说,博尔赫斯的迷宫意象迫使主人公陷入其中,也带给读者沉重的压迫感;那么卡尔维诺的迷宫意象看似繁复沉重,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它的重量,带给读者轻逸感。
(三)迷宫人物
约翰·巴思曾说:“这位伟大的作家(博尔赫斯)从没有真正创造过任何人物,就连他那难忘的‘博闻强记富内斯’也如我在别处评述的那样,更接近于一种病理学上的典型,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物。而卡尔维诺有趣的Qwfwq、马可·波罗、马可瓦多和帕洛玛先生,都是一些叙述功能执行者的范例,跟叙事/戏剧性文学中特色至为鲜明的人物毫无可比性。”①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对人物的塑造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与《命运交叉的城堡》中塑造了一系列的迷宫人物。这两部作品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在此期间,卡尔维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语境的影响,因此这两部作品也被称为“卡尔维诺后现代派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的“我”有着迷宫人物的鲜明特征,他始终处于焦虑与困惑的状态,又同时拥有主人公、作者、读者的三重身份。而在《最后结局如何》中,“我”取消了一切,回归到了最初的“我”,并和女主人公步入婚姻的殿堂,获得了幸福。《命运交叉的城堡》有受惩罚的负心人、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被罚入地狱的新娘、盗墓贼等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依靠塔罗牌决定自己的故事走向,他们的形象具有不确定性,正如文中所说“我的故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肯定包含在这些纸牌的交错摆放之中”[12]61,而最终“我”丢失了自我的故事,“我”在失去自我的同时又发现了新的“我”。卡尔维诺让笔下的人物以“轻”的形象走出了迷宫,获得了人生的幸福与自我的解脱。正如他在《美国讲稿》中所说:“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是想我是否应该像珀耳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11]7
(四)迷宫结构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说:“在小说创作中,如果要我指出谁是最完,美地体现了瓦莱里关于幻想与语言的精确性这一美学理想并写出符合结晶体的几何结构与演绎推理的抽象性这类作品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疑地说出博尔赫斯的名字。”[11]113卡尔维诺在博尔赫斯的影响下同样运用了嵌套与对立的晶体结构模式。
1.嵌套结构
卡尔维诺受到了《四月三月》与《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影响,他在《美国讲稿》中表明“这些考虑是我所谓的‘超级小说’的基础;我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便是我努力创作的这种小说之一。”[11]115《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全书一共十二章,前十章包含两个故事层面:一是男女主人公根据书籍的装帧错误寻找故事结局,二是十部戛然而止没有下文的小说,而这十部小说中同样有超现实主义、侦探小说等题材。如果说博尔赫斯提出了嵌套结构的理论,并将嵌套结构运用到自己的短篇小说中,那么卡尔维诺则将嵌套结构完美地运用到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嵌套结构成功地拓宽了小说叙事的空间,改变了以往文学作品单线的叙事结构,为读者建立起了阅读壁垒,给读者带来了迷宫般的阅读体验。
2.对立结构
除却博尔赫斯的对立结构对卡尔维诺的创作具有一定影响外,卡尔维诺的研究专家凯瑟琳·休姆还表明,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对卡尔维诺的创作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面对对立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卡尔维诺却找到了一种解决的方式。《我们的祖先》三部曲采用了人性与生存的对立结构。其中,《分成两半的子爵》通过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体现了人性的分裂与异化,而其结局却以善与恶的统一完成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树上的男爵》以地面世界与树上世界的尖锐对立给人们提供了另一种面对现实的方法;《不存在的骑士》通过肉体与没有肉体的盔甲,即对灵与肉的思考告知人们:人是灵与肉的结合体,只有灵与肉的完美聚合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卡尔维诺深谙对立与统一的密不可分,并告诉人们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在于让矛盾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状态。
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都热衷于迷宫叙事,但二者对“迷宫”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坚持“沉重”的博尔赫斯通过迷宫叙事给人以压抑之感,让人们不得不去面对沉重的现实;而坚持“轻逸”的卡尔维诺却决定对博尔赫斯进行创新,在作品中实现了对迷宫的飞跃,并于1960年在《梅那坡》杂志上发表的《向迷宫挑战》中说:“不能向现存的条件投降,也不能蜗居斗室,而是要寻找一条出路,向物质世界的汪洋大海,即‘迷宫’挑战。”②
三、接受与变异的因由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都热衷于迷宫叙事,前者对后者既有接受与继承,也有发展与创新。如果说博尔赫斯是以重写重,那么卡尔维诺则是以轻写重。前文出于对文本分析的需要,粗略地提到了接受与变异的部分原因,本部分将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接受与变异的原因。
博尔赫斯出生于文科家庭,受家庭中浓厚文学氛围的影响,从小便阅读了诸多作品,这给他的文学生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祖母送给博尔赫斯的第一本书便是《圣经》,这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神秘主义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尔赫斯自小便热爱父亲的藏书室,他在那间藏书室中阅读了狄更斯、马克·吐温、爱伦·坡、雪莱、济慈、吉卜林、菲茨杰拉德等英美作家的作品。在日内瓦学习期间,博尔赫斯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使得博尔赫斯的文本中时常出现对形而上问题的探讨。除文学、哲学、宗教作品外,博尔赫斯还热衷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钱伯斯百科全书》,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作为读者的博尔赫斯即便在晚年双目失明的状态下,依然委托阿尔维托·曼古埃尔为自己朗读某些著作。可以说,正是这般丰富的阅读经历造就了博尔赫斯思想的复杂性与写作的多样性。
文学阅读同样对卡尔维诺的创作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为什么读经典》 中,他介绍了对自己带来深刻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在前言部分,卡尔维诺直接大胆地对爱伦·坡、马克·吐温、吉卜林、菲茨杰拉德等作家表示出强烈的偏爱,这与博尔赫斯的阅读经历不谋而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卡尔维诺大力推崇博尔赫斯的契机。出生于理科家庭的卡尔维诺对自然科学也有所涉猎:伽利略的“数学语言”让卡尔维诺始终保持一颗冷静清醒的头脑去面对混沌的世界;西拉诺对于引力、悬浮的思考给卡尔维诺带来对于“轻”的初步设想。宽广的阅读面使得卡尔维诺同样追求“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理念,他直言“20世纪伟大小说表达思想是开放型的百科全书”[11]111,并直接以博尔赫斯的作品举例,足以体现博尔赫斯对卡尔维诺的深远影响。
从两人的阅读经历看,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热衷于阅读,阅读面极为广泛,两人对英美作家表现出强烈的偏爱以及对“百科全书式的”文学观念的追求注定了卡尔维诺会接受博尔赫斯的文学思想。
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两人均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环境优越并受到父母熏陶。然而,文科家庭与理科家庭的差异导致了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变异。
博尔赫斯1899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律师家庭,博尔赫斯家族在阿根廷有着悠久历史。从血缘谱系看,博尔赫斯的家族既有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血统,也有阿根廷、乌拉圭血统,这让博尔赫斯时常陷入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为他今后对迷宫的探索埋下了一颗种子。博尔赫斯的曾外祖父是一名上校,他曾参与胡宁战役,为南美的独立做出了伟大贡献。他的外祖父曾参与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的战斗。博尔赫斯的祖父也曾担任边境司令。除此之外,博尔赫斯在《自传随笔》中谈到:“我父亲的家族有文学传统。他的舅祖父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是阿根廷最早的一位诗人……我父亲的外祖父爱德华·扬·哈斯拉姆创办了阿根廷最早的英文报纸之一《南方十字架报》,而且还是海德堡大学哲学或者文学(我不能肯定是哪门学科)博士。”[2]102童年的博尔赫斯通过长辈了解家族史,并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人类一直面临的苦难,再加上家族中文学传统的熏陶,博尔赫斯决定用文学反映人类的苦难。
卡尔维诺1923年出生于古巴,两岁时迁回到故乡圣莱莫。卡尔维诺在《巴黎隐士》中对自己的家庭作了如下描述:“我是科学家之子……我是家中败类,唯一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10]12他的父亲是出色的农学家,经营着自己的农场,早已将身心交付于自然,母亲是著名的植物学家。因此,年幼的卡尔维诺便与大自然有着亲密接触,与此同时,他的文学观深受父亲影响。他在《圣约翰之路》中表示父亲与大自然是统治、斗争的关系,而他对此进行反思,他认为人与大自然的理想关系在于生活在大自然中又置身于它之外,卡尔维诺进一步说明:“正是文学帮我找到了这种关系,把意义归还给一切的事物,然后突然间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清晰真实、触手可及、可以拥有。”[13]2可以说,家庭背景对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道路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充满理性又富有诗意,从而妙趣横生。
通过对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家庭背景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博尔赫斯的家庭崇武尚文,似乎天生具有一种“沉重感”;而卡尔维诺的家庭自由理性,这一点给他的文学观带来了直接影响。
博尔赫斯在家庭的影响下,理所当然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914年,博尔赫斯全家奔赴欧洲,受一战影响,博尔赫斯一家被迫滞留在日内瓦,1919年到1920年,博尔赫斯全家迁往西班牙,直到1921年博尔赫斯才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开始从事图书馆工作,并正式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却深陷单恋的泥潭,苦苦追求堂妹诺拉·朗厄无果令他备受打击。1946年到1955年间,博尔赫斯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因此被免去市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被侮辱性地下放到市场做家禽检查的工作。政治上的摇摆与天真令博尔赫斯再次陷入迷茫,一直到庇隆下台,博尔赫斯才被重新起用,担任了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饱受眼疾的折磨,晚年又陷入双目失明的窘境。
卡尔维诺却有着和博尔赫斯截然不同的经历。尽管卡尔维诺的童年正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大肆推行独裁政治的时期,但是家庭的庇护却在很大程度上使卡尔维诺免遭动乱的侵扰,在此期间,他迷上了电影,沉迷于想象。二战期间,卡尔维诺认识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不幸与沉重,二战后,意大利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让卡尔维诺有足够的精力去思考人类的前途问题。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让人们再一次陷入不安与恐惧之中,意大利共产党的软弱让卡尔维诺失望透顶,他远离政治,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他把作家的使命与人类的社会责任紧密结合,正如他在《美国讲稿》中所说:“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只能靠文学及其特殊的手段提供给我们”[11]1。他意识到一味地以重写重只会加剧人们的精神危机,只有通过轻逸的步伐去迎接沉重的现实,才能把握人生的真谛从两人的社会生活看,博尔赫斯的人生更加的崎岖坎坷,他也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他筑造了沉重的迷宫,自己也陷入了其中。卡尔维诺一边勇于面对社会现实,一边在心里暗自反思,寻找解决精神困境的道路,并自觉承担起缓解人们精神压力的重任。
结语
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这两位身处同一时代的“作家中的作家”以敏锐的洞察力与高超的叙事技巧构建了一座座文学的迷宫。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继承体现了优秀作家之间的惺惺相惜,然而,不同的家庭背景与人生经历也造就了他们的不同,沉重的博尔赫斯深陷迷宫之中无法自拔,而轻逸的卡尔维诺勇于向迷宫挑战,找到了迷宫的出口。
注 释:
①参见约翰·巴思于1997年4月4日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Davis]伊塔洛·卡尔维诺讨论会上的发言。
②转引自崔道怡《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4年,第8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