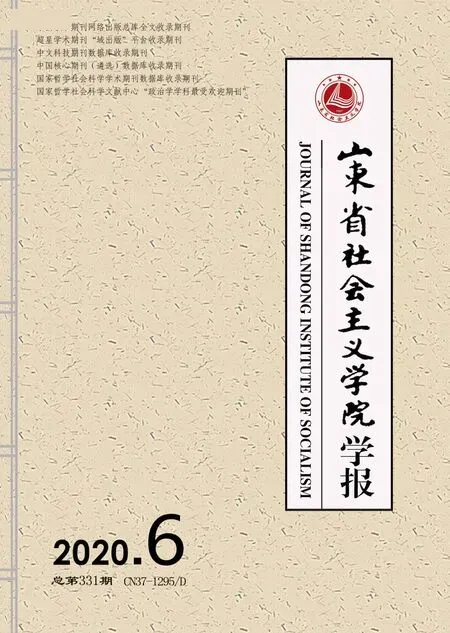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为四大文明中唯一未曾断流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既具有整体性、内聚性,又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还具有“大一统”历史的连续性。在当代,中华文明的这些特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根柢
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文明整体性、内聚性特点得以形成的地域条件。同时,中华文明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更新自身。各民族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根柢。
(一)整体性、内聚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性较强的地理单元。北有西伯利亚荒原,西北横亘着大沙漠和沙漠化的干旱地区,西面耸立着青藏高原,西南有横断山脉,东部地区临海。这种封闭性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文明形成内聚性特点。外来文化传入较晚,原生型的华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圈的核心文化,并具有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华夏族同周围其他民族在长期竞争中又互相吸收融合。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集中探讨政治统一、“华夷一体”等问题。一部先秦史可以说就是夷夏融合、由“夷”变“夏”的历史。秦的统一是这个历史水到渠成的结果。汉承秦制,延续和发展了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汉民族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及凝聚的核心。[1]以汉族为主体的秦汉帝国实行的制度和政策,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方面的进一步统一,加强了边疆与内地、“中原”与“四夷”一统的观念。这之后,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主持中央政权,都以统一作为最高目标。尤其是元朝和清朝,把全国所有民族地区纳入版图,并置于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之下,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这种“天下统一”的局面,成为中华文明整体性、内聚性特点形成的标志,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一庞大的民族集合体,也延续和发展了中华文明,使之成为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
(二)开放性、包容性
在数千年文明史中,产生于先进的农业文明之上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先进的民族文化,作为该文化起源和核心的华夏文化,及后来形成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兼容并蓄和开放开明的气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2]
根据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所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56个兄弟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共同体。所谓“一体”,是指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中国各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形成,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在秦汉时代,当中原地区以汉族为核心实现了农业区的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区形成了以匈奴为核心的统一体);第三步,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形成后,对中华民族强烈的认同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长期的历史发展,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强烈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不仅存在于56个民族内部,同样也存在于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之中。各民族内部人民相互信赖,相互依靠,通过民族共同利益的实现来实现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各民族之间也是通过共存共生、共同发展来实现本民族的利益。在古代,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往往自称华夏“先王”之后,在族源上与汉族认同,以谋求自己的发展。如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历史上与汉朝的甥舅关系,上接汉统,标榜自己政权的正统性;鲜卑拓跋氏以汉魏正统自居;契丹耶律氏以轩辕之后自居;党项人以夏人之后自居。这些都说明在古代统一的中华民族概念已深入到少数民族之中。
在此基础上,各民族文化也相互交融,结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中,各民族分别以其文化的个性,使中华文化异彩纷呈,又以其文化的共性,表现了中华文化的趋同性和整体性。如果说中华民族存在多元一体的格局,那么中华民族文化也存在多元一体的特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
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表现在:一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二是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地域辽阔,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区均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即使是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也有较大的差异。较为典型的是汉民族文化,东西南北文化习俗的差异很大,八大方言的差异比许多民族语言间的差异还要大。
中华民族文化一体性则表现在文化同一性、同质性。一是中华民族文化不是56个民族文化加在一起的总称,它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交融、整合而形成的文化整体。二是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交流中形成同质化、一体化现象。价值观念的一体化或同质化进程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争霸,人们认识到天下要安宁必须统一。孔子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韩非子力主建立中央集权制,以实现统一。这种追求国家统一、多元文化整合的价值观念和趋势,反映了各地各族人民实现大一统的要求。秦朝实施的“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等举措,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固的基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了政治和文化的大一统。唐朝时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归附、内迁并互相融合为一体。
总之,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的特点,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保障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二、民族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前提
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特点是“大一统”历史的连续性,体现在疆域统一、“夷夏一体”、制度有效、文治教化。中华文明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中交替演进,但以统一和兴盛为常态,以分裂和衰落为变态。即使在分裂时代,分裂政权大都不甘于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3]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实现大一统,必须解决“夷夏之防”的矛盾。大一统既指“诸夏”一统,也蕴含着“夷夏”一统,它不是将“夷狄”摒弃于中华之外。一是认为王者无外。“《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内外之辞言之?”(《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王者一统天下,也包括夷狄,正如何休所说“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二是强调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皆是“中国人”。清人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在注释“夏,中国之人也”时说:“以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这是依据古义和传统观念做的解释。王绍兰在《说义段注订补》中对这条段注加以订补,谓:“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之人也。” 三是强调肯定各个民族的不同特征和差异性。“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并提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四是确立了“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民族政策:羁縻制。推行“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唐高祖)的羁縻制度。
在此基础上,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秦汉的统一与边疆开发,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创造了“夷夏一体”的现实,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强烈追求统一的时期。这种大迁徙、大融合,进一步加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隋唐是“大一统”实现的时代,统一而稳固的疆域使“大一统”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人们无不以“一统”为常,而以分裂为变。“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的交流交融进一步加强。唐朝出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的历史壮观。宋代的现实是辽、金、夏压境,一统无存,宋人于是强调“正统”,以表明宋室天下一统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辽、西夏、金积极推行汉化与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和发展。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它所实现的空前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以后的分裂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中华整体观念的加强。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诏告天下说:“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忽必烈据汉文化经典而改建国号,进一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再单是蒙古民族的国家,而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明朝建立者以“华夷之辨”作为号召反元的思想工具,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当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之后,明帝开始强调正统,一变而称“华夷一家”,强调“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这充分说明,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交融与文化认同,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民族大熔炉的锻炼,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清入关后,即以宗主视天下。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清王朝接受并发展了“大一统”思想。清朝抽去了“大一统”理论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以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之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清朝以天下之主自居,不能容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分裂割据出现,同时密切关注边疆事务,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帝国。[4]
分裂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说来版图会扩大一次,到清朝版图是非常大的,这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所自然形成的。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需要政治统一来加以巩固。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句话并不是泛泛而谈的。[5]正是因为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沧海桑田而生生不息。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中华“大一统”的发展史。[6]
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国多制”的治理体系。以清朝为例,清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民族整合,解决了中原和异族的矛盾。在民族政策方面,实施蒙古八旗制度、西藏噶厦制度、西南土司制度等,保持对蒙古、回部、西藏和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皇帝兼任满族族长,保持着满人的认同,形成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一国多制”的治理体系。在宗教政策方面,以“崇儒重道、黜邪崇正”为纲,通过度牒发放来管理佛道正教,严厉打击白莲教等邪教,对藏传佛教颁布金瓶掣签制度,把达赖、班禅继任人选的决定大权由西藏地方集中到朝廷中央。
三、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7]当前,要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更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
(一)以文化认同激发各民族同胞对中华文化根源的怀想
“认同”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迄今为止并无一个统一的定义。英国学者麦克盖根认为,“认同是一种集体现象,而绝不仅是个别现象。它最频繁地被从民族主义的方面考量,指那些身处民族国家疆域之中的人们被认为共同拥有的特征。”[8]一些社会学还分析了认同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比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等。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关系极为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基石,后者则是前者的胶合剂。
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由此形成了一个族群的“自我意识”、传统文化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他们所特有的语言、习惯,是保持其独特性的基础。具有整体性、内聚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大一统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化,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多民族的主权国家都在不断增强各民族的价值观念的同质性或共同性,不断推动一体化或同质化进程。我们在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方面,一方面要保留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培育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事实上,中国几千年以来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华民族这种始终不变的大一统格局,原因有三:第一,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基于文化的统一,政治的统一随之。第二,中华大地曾同时并存许多部落种族,之所以能融合为一个大民族,就是由于中华文化具有特别强大的同化力。第三,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所以绵长不绝,关键在于其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不因一时武力上的失败而衰亡。几千年来,不管什么朝代,不管是不是征服民族,也不管中间有多长多短的分裂,一个民族只要到了这块土地上,往往被中华文化同化,认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信奉“大一统”“大中华”的理念。所谓“征服者被征服”,指军事征服后,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被毁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被中华文化同化。
在当代,增强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二)以民族认同激发全体中华儿女骨肉同胞之情
民族由许多因素构成,包括名称和共享的记忆,在血缘纽带、文化传统和习俗、体质方面与其他群体的不同,还有集体认同等。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和参与行为,个体对族群的认同主要依赖于体质体貌特征、记忆、血缘纽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要素。民族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基石,文化认同则是民族认同的胶合剂。一个人若无民族认同感,固然无法产生民族文化认同感;而文化认同感不存在或不强烈,也无法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由于民族是由血统、遗传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由选择,但文化则是可以选择与改变的,所以文化认同比民族认同更为复杂。因此,民族认同感必须同时含有血统与文化两种成分,单凭血统而产生的民族认同是不完善、不牢固的,对于强化民族或国家的凝聚力,也不能产生持久可靠的作用。
应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代中国的“大一统”,集中体现为作为现代“超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超多民族国家”的存续是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关切,甚至是根本关切。在民族问题上,民族主义并不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现代民族观依然带有传统中国的印记,强调共性而非差异,追求交融而非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坚决反对操弄族群意识,进一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