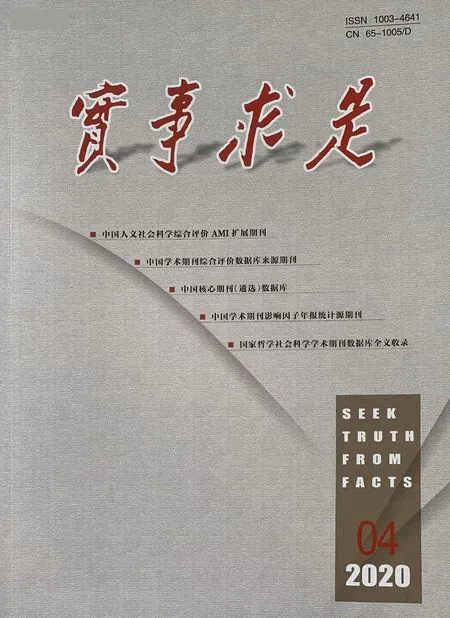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中国场景与时代价值
彭绍帅 郭 玥
(1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研究生部 四川 成都 610072;2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 四川 成都 61007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舆论的论述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和实践的理论渊源。据学者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先后提到“舆论”一词达300余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舆论的重视,反映了在他们那个历史时期,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潜在力量已经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实践中,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使其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注重从人的社会属性和舆论的社会本质分析舆论的内涵特点,深刻指出舆论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和社会情绪的映射,通过报纸发挥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一)舆论是“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
最早对公共舆论思想作出阐述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1](P331)他强调无论在哪个时代,公共舆论都具有巨大力量。16世纪的欧洲出现了第一批定期出版的报纸,市民可以购买到专门的新闻报纸。报纸业在此后迅速发展,到了18世纪,一群关注舆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舆论的观点和主张,开始将报纸作为无产阶级进行舆论宣传的主要工具。圣西门在《论万有引力》一文中认为:“人们把舆论称为‘世界的女王’,这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当代最巨大的道德力量,只要它明确表态,人间的其他一切力量都得让步。”[2](P98)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身在报刊工作方面的实践成果,用批判继承的方式,详细阐述了公共舆论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把舆论称为“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3](P384)他们认为,“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3](P544)反映了“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4](P658)并将舆论上升为公众普遍的一般的交往状态。黑格尔以及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对公共舆论作了原始性的阐述,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吸收前人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了科学的、发展的舆论思想。
(二)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年代是报纸业蓬勃发展的年代,报纸作为当时大众传媒的主要工具,承载着信息传递、社会沟通、舆论引导等多项功能。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新莱茵报》时将政治讨论居于其次,以向公众介绍时事、讨论问题、提出改良方法以及形成舆论和共同意志作为主要方向。1850年11月,马克思作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主编,在第5~6期合刊上刊登了一篇国际时评,对半年来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政治时事作出评论,在谈及法国时提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德国有一则谚语“打麻袋,吓驴子”,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则谚语,形象生动地阐述了报刊和舆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报刊比作驴子,将舆论比作驴子身上的麻袋,即报刊是驮“袋子”(社会舆论)的“驴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纸币是作为金银的代表而在市场上流通的,与此类似,报纸是作为舆论的代表流通的,其价值是根据报纸所报道的舆论是否可信的程度所体现的。“‘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3](P384)
但是,报刊并不等于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报刊也分“好”与“坏”,只有积极引导舆论的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马克思就指责其不是“指导舆论”,而是根据国内形势“屈从于舆论”的报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报刊和舆论之间应是这样的辩证关系,即报刊只有源源不断地通过正确反映和表达舆论,才能更广泛、更深刻地引导社会舆论;舆论使得报刊必须在“好报刊”(反映舆论)和“坏报刊”(歪曲舆论)之间作出选择,以此来界定报刊的性质。
(三)舆论是社会情绪的“晴雨表”
舆论作为社会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与表达主体的国别、阶级行业以及所涉及的利益集团息息相关。舆论具有普遍性、自发性和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他们所处的阶级社会中,舆论“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们对一件事情的一致态度”,[5](P76)也代表了一定阶级和群体的诉求。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执政期间,忽视了社会一定阶层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温和的政治诉求,同时对巴黎工人通过舆论表达诉求的做法视而不见,加速了其在议会选举中的失败。马克思在《〈勒·勒瓦瑟尔回忆录〉摘要》中指出,这种失败源于吉伦特派“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6](P374)而秉承着自由和平等的宪政之友社——雅各宾俱乐部则发挥自身的优势,凝聚了一大批品格坚毅并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仁人志士,从而获得了公众舆论的支持,建立了雅各宾派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舆论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英国舆论的左右摇摆就反映了这一特点,从最开始表示对普鲁士的同情,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转向对法国的同情。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曼格的信中说道:“除了人民群众对共和国的坚决同情、上流社会对明如白昼的俄普同盟的愤怒,以及普鲁士外交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以来所发出的无耻腔调以外,进行战争的方式——征集制度、焚毁村庄、枪杀自由射手、扣留人质,以及令人想起三十年战争的种种暴行,在这里已经激起了公愤。”[7](P167)
(四)舆论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
在旧欧洲的专制统治下,政治经济以及宗教等组织掌握着对舆论的监控,例如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更有甚者还借助宗教裁判所的力量,禁止出现与权力组织不一致的意见发表和流通。[8](P135)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新兴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新阶级运用新思维带来的舆论力量冲击着封建主义神学。马克思、恩格斯将国家权力分为政府的行政权力、议会的立法权力以及报纸的监督权力,这三种权力或相互制衡或相辅相成,他们认为“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9](P503)舆论的力量不容忽视,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3](P237)舆论成为社会可资利用的工具,也是监督社会的公共资源。舆论为公众提供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的评价尺度和衡量手段,同时舆论也成为了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普遍又自然的社会监督权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主动寻求舆论监督,即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将事实和问题诉诸舆论,借助舆论的力量达到监督的目的。同时,舆论在经济立法中也具有推动作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十小时工作法案的通过视作工厂主们“怯懦地向舆论让步”。[10](P342)
二、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主要来自于内在延续和外来融合,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舆论理念的综合和提取;另一方面是汲取国外成功经验,特别是受到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舆论认知的基础上,高度结合了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从而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加强了党在舆论工作方面的领导。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舆论思想的提出
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指出:“本志宗旨,重在反抗舆论。”[11](P127)他提出:“共和国里当然要尊重舆论,……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共和国舆论不是如此?”在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处境下,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南陈北李认为在这一时期更需要鼓动民众舆论,唤其觉醒。因此,要“刺激言论,运广长舌”,拨动“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12](P16)要“广舆论之涂”。[12](P117)李大钊则表示“对付资本主义的种种祸害,有两个方法:一是舆论的鼓吹,二是劳动者的团结”。[13](P363)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也充分肯定了报纸所带来的舆论作用,1927年3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要到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14](P1311)中国共产党逐步将新闻舆论阵地的建设作为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强大的舆论引导力,将舆论工作与当时的时代主题“抗日、民主、和平”相结合,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政府以及汪伪政权进行了大量的舆论斗争。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国民党召开专门会议研讨“共产国际解散问题”,国民党顽固派紧握这一机会,对中国共产党发起舆论攻势。面对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中国共产党不卑不亢,运用掌握在手中的舆论工具,宣告了对共产国际解散的立场和态度。中国共产党主动发声、积极发声、敢于发声,对不实的舆论予以反驳,引导舆论向更加有利的方向挺进,确保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导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舆论阵地的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与实践不断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在改革实践中加强舆论阵地建设。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提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党的舆论机关。”[15](P688)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首次在党的文件中将舆论机关和舆论部门定性为新闻媒体和新闻单位。1982年5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广播电视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广播电视部的成立,使党的舆论阵地建设朝专业化和体制化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报纸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其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地方以及各行各业开始出版相关的报纸、期刊。为加强对报业的指导和管理,1987年国务院成立新闻出版署,其主要功能是加强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统筹管理。随后的一段时间,国外对于中国的报道掺杂着大量的歪曲丑化,为了辨是非、正视听,使世人更好地了解中国,1991 年1 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新闻办公室,负责中央对外宣传工作。2001年4月,新闻出版署正式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其行政级别也上升为正部级。2005年9月至2008年2月期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期刊、报纸、图书的出版管理规定,填补了新闻出版制度上的一些空白,对党的舆论阵地建设制度化起到了推动作用。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舆论阵地建设格局,同时也带来了互联网监管的复杂问题。201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成立,解决了互联网阵地“多头管理”的缺陷,在制度层面实现了互联网管理部门权限的统一。为解决新闻出版系统和广播电视系统的“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的问题,国务院在2013年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这次机构合并打破了新闻舆论阵地长期分管的格局,推动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进入新阶段。2018年4月,为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舆论阵地的发展变化和时代建构,是中国共产党舆论阵地建设长期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我国新闻舆论工作进步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演进
将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与中国舆论实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舆论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舆论工作,从舆论宣传到舆论监督再到舆论引导,呈现出循序渐进、深化拓展的趋势。据考察,舆论监督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甘惜分教授在1980年撰写的《新闻理论基础》一文中,就指出了舆论监督作用,并明确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舆论监督开始代替过去通常使用的“批评报道”“负面报道”等词。自党的十三大以来,舆论监督被正式写入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舆论观的另一个侧面就是“舆论引导”,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共识,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良好舆论环境。邓小平曾明确提出:“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6](P255)江泽民在1996年9月视察人民日报时提出,舆论引导既区别于“组织舆论”,又不同于“指导舆论”,而是根据时代要求,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作出的改变。2008年6月,胡锦涛在人民日报考察时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17]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18]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前进道路上,始终把凝心聚力、增信释疑作为发挥党的舆论阵地的着力点。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出党夯实舆论宣传工作的决心。
三、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昭示,掌握舆论阵地和话语权对于一个社会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维护和发展主流舆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思想领域凝魂聚力的作用,是舆论工作的主要目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了更好地发挥舆论的积极作用,体现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时代价值,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为核心理念和理论精髓,广泛吸收借鉴人类舆论思想中的精华,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保证党在舆论工作上的与时俱进。
(一)掌握舆论纸币“发行权”,夯实舆论阵地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来看,报纸的存在就是舆论的纸币。现如今,这种“纸币”的形态从报纸、广播、电视扩展到互联网等新媒体、自媒体,使得舆论“纸币”的概念不断丰富,舆论工作的主阵地也在不断拓展。掌握舆论纸币“发行权”,也就是要加强舆论载体、舆论阵地建设,将“喉舌论”“党媒姓党”“媒体融合”等舆论观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主流媒体是党掌握舆论阵地的重要基石,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19]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加强主流媒体建设,“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17]在夯实舆论阵地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要按照社会舆论传播符合新闻传播规律,满足舆论工作具有正能量、建设性的特点以及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等现实需要,使主流舆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改革创新精神,自觉抵制庸俗信息。
(二)对照社会“晴雨表”,增强舆论引导力
在现代社会中,舆论引导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新闻媒体根据时代需求来设置议程和议题,通过一定的传播载体引导受众朝着预设的方向去认识和理解新闻,从而实现对受众的引导。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时代的舆论环境及其思想内涵发生了深刻改变,对照社会“晴雨表”,加强舆论引导力建设迫在眉睫,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工作的崭新命题,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思想基础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20]在增强舆论引导力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为指导,始终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始终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握守正创新的根本要求,坚守党管媒体的原则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舆论宣传方式,使党的声音占据舆论高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完善舆论宣传工具融合质变,坚定以互联网为工具的思维发展,充分结合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优势,同向发力,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三)妥善运用“批判法庭”,强化舆论的监督作用
舆论的“批判法庭”包含两种含义,即社会监督之意和保持公平正义审判之意。在商品经济社会,舆论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的社会监督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18]这是舆论宣传工作的基本理论遵循。发挥好“批判法庭”的社会作用,不仅能够让正义和公正之光照进社会阴暗的角落,揭露丑恶的现象,还能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利用各种舆论载体进行积极关注报道,疏解群众的疑问、安抚群众的情绪。首先,新闻媒体应当发挥舆论的积极影响和监督作用。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媒体监督政府的工作,反映自身诉求,既有利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又可以疏导社会情绪,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其次,新闻媒体与其他监督手段共同发力,能够有效完善党的监督机制,真正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后,互联网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平台,因此还要以互联网的监督为抓手,做好相关舆论监督工作,形成舆论监督机制闭环。
(四)坚持与时俱进,开创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中国化的新篇章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20](PP331~33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行了宏观思考和战略部署,为做好新时代党的舆论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和行动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传统基因,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必须以习近平新闻舆论观为指导,深刻把握舆论斗争新态势,将舆论宣传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之中,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人民至上”的主体意识、治国理政的时代要求和“四个自信”的精神气质[22](P4)充分体现在舆论宣传工作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