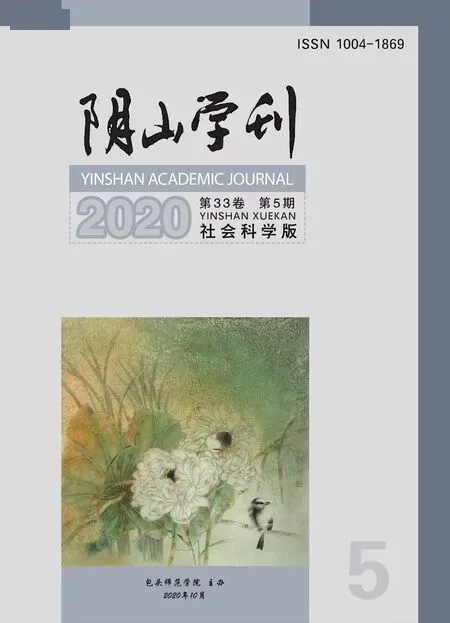性别视角下的一篇悖论式文本
——《为奴隶的母亲》新解
马 龙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为奴隶的母亲》是左翼作家柔石创作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小说,不仅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而且也曾数次搬上银幕进行演出,可以说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的一篇“经典文本”。回顾学术界对此篇作品的接受史,大致可以归化为三类:第一类是阶级视野下的解析,其中的代表性观点是认为这部作品“描写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一个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形象地展示了一幅阶级对立的图画,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1]。第二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下的解析,不少论者开始超越阶级分析的局限,进而从人性的角度对该作品进行分析阐释。比如,学者李乐平从分析春宝娘这一人物形象入手,最终认定小说的主题是“从母性的角度深刻控诉了那个罪恶的社会不仅无情摧残劳动妇女的肉体,同样也还蹂躏着她们作为母亲的心灵”[2]。第三类是西方各种文艺理论的引入,大大扩展和深化了此篇作品的接受视野。学者蓝棣之曾经借助西方解构主义理论,对小说存在的双层结构进行分析,他认为“表现阶级性的显在结构与叙述人性的潜在结构,似乎并非相互补充的关系,而是相互颠覆和解构”[3]。另一位学者刘俐俐则采用西方结构主义诗学理论和语义分析方法,对《为奴隶的母亲》艺术价值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索。[4]
除去以上三种各具视野的基本阐释之外,以性别视角引入本文的分析也值得我们注意。有些学者敏锐地指出作家柔石的男性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本的内在面貌,小说仍然无法避免男性中心意识的投射。[5]这种论点洞察了男性创作主体潜隐于内心深处的男权无意识,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文本在“典要”这一显性层面所着重表达的男权批判主题。其实,除去叙事细节层面所凸显的男性中心意识以外(1)乔以钢、宋声泉在《〈为奴隶的母亲〉小说叙事的性别分析——兼及与〈生人妻〉的比较》一文中从叙事者对女主人公的称谓、叙事者对女主人公的出场安排以及叙事者的话语设置等叙事细节层面,详细分析了其中隐含的男性创作者的男性中心意识。男性中心意识是一种具普遍意义的客观存在,它的出现,正与中国几千年来与父系社会制相伴随的男权文化历史观念密切相关。,小说中的“母性”叙事也隐含作家以男性为本位的叙事立场。对于春宝娘“母性”的过度挖掘与表现,不仅透露出一种“母性就是女性”的标准男性主义思维,而且也于无形中重构传统的母性神话。母性神话仍是男权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表达的是男性视域下对女性的期待性想象。由此可知,在女性主义视域的观照下,《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充满了矛盾与紧张,呈现出一种既有意识批判男权又无意识认同男权的悖论式状态。
一、批判男权的性别主题
从性别视角进入小说文本的语义系统,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对封建男权文化的批判。仅就小说标题而言,《为奴隶的母亲》已经显示出女性人物(在文本中主要以母亲的角色出现)“奴隶”的身份,它表明女性已经失却自身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完全沦为男性的囚徒。通过描写普通农妇“春宝娘”在“典妻”陋习下的悲剧性命运,作者柔石相当深刻地向广大读者揭示了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的生存真相——女性作为物品、作为男性附属物与所有物的生命真相。虽然小说仅仅关注“典妻”制下的女性悲剧,但其中所揭示的女性被“物化”命题,无疑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它适应于有着几千年物化女性历史的中国社会。
女性被“物化”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里,“物化”并不仅指文学作品中形容女性的修辞方式(2)中国文学中历来存在着强大的物化女性的修辞传统,这种传统习惯于将女性的人体外观转喻为外在的客观物品,这时候的女性往往被抽象为爱欲的承载体,变成纯粹为男人所观赏的“他者”。,它的意指显然更加残酷——“女性”作为消费品、商品,在男性社会进行流通交易的实际现实。以致有学者尖锐地提出:“‘夫妇’二字,正是父系社会完成对女性的历史性压抑的第一个高捷式的宣布”[6]。总而言之,无论是作为“父之女”,还是“夫之妻”,女性的生存境遇都是“第二性”的,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和所有物而存在,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的“物化”真相。
在《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中,作者柔石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被物化的典型形象——春宝娘。正是借由对春宝娘“物化”境况的揭示,柔石向封建男权文化提出了批判。春宝娘的“物化”集中体现在她仅仅充当一个生育的工具,在两个男性人物之间流通。女主人公春宝娘是皮贩商黄胖的妻子,但由于生活日渐贫苦,便被自己的丈夫出典给秀才家。典妻的实质是将妻子作为物权客体,议价典(雇)给他人,典约期满,以价赎回。[7]在一定程度上,“典妻制”正是封建男权文化的高度象征,它表明女性是属于男性的物质性资产,可以由男性随意买卖或交易。当作为一家之主的黄胖承担不起家庭重担的时候,作为妻子的春宝娘就变成了丈夫用来换取钱财的抵押品,抵押的条件则是为别的男人生一个孩子。小说中的丈夫黄胖完全是一副封建暴君的面孔,不仅对妻子没有丝毫怜惜和疼爱,而且还残忍殴打自己年仅五岁的儿子,这位凶残之父还曾经亲手将自己的女儿扔进沸水烫死。面对这位冷酷的丈夫,春宝娘更是经常陷入失语的境地。在得知自己被出典给秀才家时,春宝娘“简直痴似的,一句话没有”;被出典的当天早上,春宝娘想对自己的丈夫说几句话,却是“一句也说不出”;老妇人催促她快些出行,春宝娘也是讷讷的,“声音是在她底喉下”。诸如此类的叙述细节构成极具深意的性别意味象征:在男权文化主宰的社会里,女性是没有声音的。
春宝娘被典当之后,其在三年的典当期内,就变成了典当主——地主秀才的拥有物。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春宝娘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生下一个男孩。虽然秀才家的生活要比原先好一些,但是春宝娘的悲惨境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她不仅要忍受秀才大妻无休止地侮辱谩骂,而且还要独自承担繁重的家务。唯一值得温暖的是,秀才对她非常体贴,在她刚来时会主动向她求媚,当她遭受大妻谩骂的时候,这位临时丈夫又会对其施以安慰。尤其在春宝娘怀孕之后,临时丈夫秀才更是异常欣喜,对她加倍的好,甚至还瞒着大妻送她青玉戒指。小说曾经提到秀才想要将春宝娘永远买下,或是延长春宝娘的典期,但在故事的最后,这位临时丈夫因气愤春宝娘将戒指典当,再加之惧怕大妻的威势,还是如期将春宝娘归还原家。如此一来,秀才前述颇具温情的行为便带有一种反讽性:所有这些“好男人”的表现,并非出于男女两性之间平等真实的爱恋,秀才的“好”也只不过是为了利用春宝娘的生育价值,以达到延续香火的目的。在得知戒指被典当的那晚,秀才的一句“那只戒指是宝贝,我给你是要你传给秋宝的,谁知你一下就拿去当了!”无疑会让春宝娘痛彻心扉。
总而言之,春宝娘仍然是封建男权文化的牺牲品,她其实远未得到两个男人、两任丈夫的真正尊重与爱护。作为一个被物化的女性,春宝娘没有话语言说,没有生命意识,只能像一个生育工具那样,机械地在两个男人之间流通。作家柔石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封建男权文化的批判。
二、传统母性神话的重构
男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表达的首先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可能还以性别面具的方式曲折地传达着男性对自我性别的确认、反思、期待。[8]在《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中,男作家柔石塑造的“春宝娘”这一角色,不仅是一个饱受封建男权文化压迫的悲惨女性形象,而且更是一个无私奉献、含辛茹苦的受难母亲形象。前一形象的塑造,使得作品具备批判男权文化的性别主题内涵,而后一形象的显现,不仅隐含男性创作者自身的性别立场、是作家受男权文化观念影响后的产物,而且这一受难而伟大的母亲形象塑造正于无形中重构传统的母性神话。
小说的标题“为奴隶的母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人物的奴隶身份,但作家的着眼点似乎并不在于女性本身,而是女性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母亲。柔石在文本中所着力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女性的悲剧,而且更加突出的是这个女性作为母亲的悲剧。在小说的基本情节中,典当期中的“春宝娘”已经被迫与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春宝分离,而典当期过后,她又不得不遭受与自己第二个孩子秋宝残忍分离的相似命运。在春宝娘的生命行旅中,她要么得到春宝而失去秋宝,要么得到秋宝而失去春宝,这是一位母亲面临的两难困境。故事的最终,春宝娘返回原夫家,可她面临的现状却是:不仅丈夫黄胖会对其进行言语上的嘲讽,而且孩子春宝也已经对自己这位母亲变得陌生而隔阂。更加意味深长的在于,当春宝娘躺在原夫家冰冷的床上,身边虽然已经有了春宝,可她的心里仍然在默默想念秋宝。
按照这一情节线索来看,女性的母性问题成为小说叙述的一大重心。母亲权利的被剥夺以及母爱的无法两全让春宝娘这一女性人物的苦难更见沉凝。然而母性毕竟不是春宝娘的生命第一性,作家柔石在挖掘放大其母性的同时,却也压抑了春宝娘作为女性生命个体的其他丰富性。换句话说,春宝娘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个母亲,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柔石在小说中却是将母性视为春宝娘的生命第一性、视作其生命经验的全部来表现的。这样的叙事立场实际上映射出作家本人的男性性别姿态,是柔石受男权文化观念影响的一大表征。因为在传统的男权文化观念中,女人与母亲就是自然而且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母性是女人的天性与本能”构成女性内在的生命逻辑,也只有与自己的孩子紧紧相连,女性本体的生命价值才得以凸显。遵循这样的男性主义思路,柔石在小说里并未将春宝娘视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加以表现,而是将其紧紧绑定在母性之柱上。事实上,对于这种“天然母性”的男权集体无意识,早有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异议。波伏娃就曾在《第二性》中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母亲的态度,取决于她的整体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9]另外一些更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则直接将“母亲与孩子的连带关系”视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表现,它实际上服务于男人对女人的压迫。[10]这些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对于我们考察母性叙事中所隐藏的男性作家心理,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虽然小说的母性叙事总体上立足于春宝娘作为“母亲”的悲剧,但是文本中还是多次表露出这位母亲的母性爱特质。比如,当皮货商丈夫告诉春宝娘要出典她时,这位母亲既不关心自己以后的生活将如何度过,也不在意自己与丈夫的感情是否受到亵渎,这位母亲心心念念的只有自己的孩子春宝。“担心春宝以后没有母亲照顾,将无法生存”是这位母亲得知自己被典当后的首要想法。甚至在她临行之前,这位母亲都不曾对自己有过些许考虑,只是痛苦地回忆起曾经被丈夫活活烫死的小女儿。被典当之后,虽然春宝娘在秀才家生下了秋宝,但她还是无时无刻不在挂念春宝。在得到秀才感情上的安抚,并且生活也日渐稳定之后,这位母亲甚至幻想有一天等到丈夫黄胖病死以后,自己能够请求秀才把自己第一个孩子春宝也接来,这样两个孩子便可以一起抚养。“母亲”的角色身份,让春宝娘这位女性人物显得高尚而伟大,作者柔石显然也是对其保有的“母性爱”持赞扬态度,因此孜孜不倦地在小说中加以表现。殊不知,对于“母性爱”的过度强调与表现,正于无形中重构传统的母性神话。
母性神话无疑是父权制社会的得意产物。自父权社会形成以来,男性便大声讴歌女性作为贤妻良母的意义,不停高唱其作为贤妻良母的崇高喜悦;与此同时,女性则被贴上繁衍养育后代、贞节温顺、慈爱包容、无私奉献、甘于牺牲等标签,这些标签最后被抽象和定性为女性的“天性”——母性,这便是父权制所设置的“母性神话”。[11]在一定程度上,柔石塑造的“春宝娘”这一伟大的受难母亲形象,恰自显示出父权制下母性神话的复归。父系社会所贴在女性身上的各类美德标签,无一例外地都在春宝娘的身上有所体现。换句话说,作家柔石在强调春宝娘母性爱的同时,恰恰忽略了母性之爱对于春宝娘生命主体性的束缚。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母性爱”虽然让春宝娘的形象得以高大,使其堪称博大宽厚、慷慨无私的“大地之母”,但也正因为“母性爱”,春宝娘丧失了作为女性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和丰富性,从此完全沦为孩子的附庸与奴隶。
三、结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左翼文学的经典文本《为奴隶的母亲》进行重新解读,最终发现文本内部潜隐的悖论性质,这种性质来源于男权文化这一强势文化的鬼魅式影响。一方面,男性作家柔石想要对此进行驱魅,因此写下一个“典妻”的故事,真诚地为女性立言,并借此表达对封建男权文化的批判。但另一方面,作者的立足点又并非在于女性本体,而是母性本体。对于春宝娘“母性”的过度挖掘与表现,不仅隐含“母性就是女性”的男权主义逻辑,而且更于无形中重构传统的母性神话。如此一来,小说文本就具有一种分裂性:显文本的“典妻”叙事明显地表现为对男权文化的有意识批判,而隐文本的“母性”叙事又隐约流露作家对男权文化观念的无意识认同。显文本与隐文本之间存在相互解构的紧张关系。本文适时指出这一悖论式关系,并非对柔石及其本人创作的苛责,只是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一独特角度。另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研究一直十分匮乏,本文对于“男性中心意识影响左翼男作家的女性形象书写”这一文学现象的指出,也恰恰证明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性别意识反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