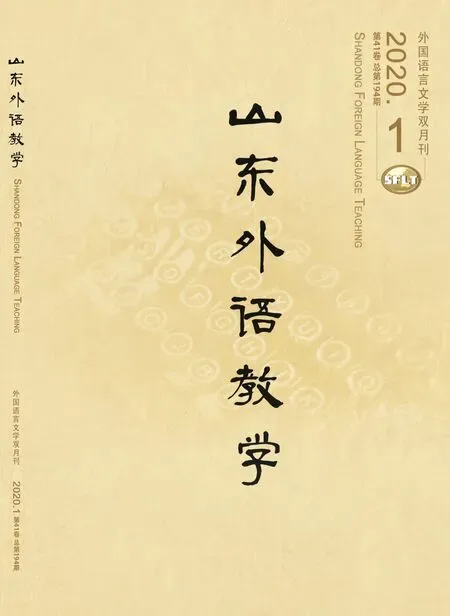跨文化语境中的西方文学与卡夫卡研究
——曾艳兵教授访谈录
尚景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38)
尚景建(以下简称尚):曾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山东外语教学》的采访。您是卡夫卡和外国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卡夫卡是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宗师“鼻祖”,对文学创作和研究有巨大的影响。您是如何与卡夫卡结缘,是怎样看待他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的?
曾艳兵(以下简称曾):谢谢你和《山东外语教学》的采访。我关注研究卡夫卡已近三十年,首先这里有一个学术发展逻辑:在研究卡夫卡之前,我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对现代主义影响巨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后现代主义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现代主义的鼻祖,他的作品直接体现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流派的精神特质,是西方传统文学的“弑父者”,又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之父”。而后现代又是对现代性的深入推进,对历史和传统的消解颠覆,我在《东方后现代》一书中评价过后现代:“过去不是废墟,而是虚幻;现在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将来不存在,有的只是重复和复制。”而卡夫卡承前启后,正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后现代的中枢地位,通过他可以更清楚地绘制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其次,研究卡夫卡也是个人精神情感的投射,借用荷尔德林的一句话就是“我通过卡夫卡栖居在大地上”。我把卡夫卡融入到自己的生活、思考和学术中,卡夫卡遭遇的荒诞世界,我们可以在工作生活中随时体验。卡夫卡是一种表达的可能,是一种思维方式,更多的是一种内心感受。
大家知道西方小说传统主要从文艺复兴后期开始的,无论是塞万提斯还是笛福,都围绕冒险探索主题,并逐渐形成个人主义传统,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个人,缺少家庭和社会等外在因素,体现为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十七、十八世纪的小说虽然也有冒险,但其中的人物更多把眼光放到了社会,换句话说,社会的完善发展,对“反家庭”的个人主义做出矫正,人必须受制于时代,这在雨果、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很全面的表现。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每个人都受制于社会,变成人与等级、科层和意识形态的缩影,体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卡夫卡则重新回到个体传统,当然这是更高层面的回归,他不太关注历史和社会,没有19世纪文学家的雄心壮志,也不在文学中注入传统的关怀形式,只是将文学完全视为自我的世界,他的作品主要关心内在和个人感受,主动与时代保持距离,所以当时的人并不太能理解他。从西方小说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卡夫卡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一环,他同时又突破传统,是构成西方文学大厦的标志性大师。
尚:按您的说法,卡夫卡虽然反抗传统,仍然是西方文学主流和正典。中外学界对卡夫卡的评论汗牛充栋,对他也有各式各样的解读,您是怎样理解卡夫卡的?
曾:卡夫卡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不同时代、社会和思潮运动的人们对他会有不同的解读,布鲁姆看到的是犹太教中的卡夫卡,阿伦特看到的是极权下的卡夫卡,阿甘本看到的是法哲学中的卡夫卡,反之亦然,可以借助卡夫卡来解读布鲁姆、阿伦特和阿甘本。我认为应该至少在三个层面上理解卡夫卡。
在艺术层面上,卡夫卡作品是最纯粹的艺术,他不像古典时代的作家那样有着明确的道德、宗教、社会目的,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他也不是后来为生计创作的职业作家,不主动迎合读者,他临死前要布洛德烧掉所有作品。他的写作不向大众敞开,而是封闭的、自我的。所以,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他把艺术周边的功能都剔除掉,把历史、社会、宗教、道德、国别和情感等诸多外在的因素全部虚化处理,将最纯粹的艺术展示出来。卡夫卡作品中只有“人”——人的感受、境遇,他以近乎残酷的冷静态度观察人,叙述人,拯救人,像上帝一样将人类赶出伊甸园,让我们在这个无聊的世界中流浪徘徊。正是这种纯粹的特性,使得卡夫卡作品有一种哲学意味,展现为形而上的诉求。
在精神层面上,卡夫卡的作品的确难以理解,他同时代的艾略特、乔伊斯、贝克特等作家也有这种倾向,伟大的作品要超越时代,体现出对传统的颠覆性和对未来的预见性。卡夫卡重新开启了一种书写的可能,这是对传统的否定;卡夫卡作品可以学习但不可模仿,这是对未来的否定,卡夫卡有很多未完成的作品,这是对自我的否定,也是对“文学整体观念”的否定,“完整”无论对个体生命还是对作品而言或许都是个神话,卡夫卡刺破了这个泡影。因此,在卡夫卡身上体现了否定和自我否定,这是一种精神的不满足,是浮士德精神的代表,这就是《西方正典》将卡夫卡与歌德比较的一个重要原因。卡夫卡作品有强烈的反讽精神,这或许是对世界和人生悲观的嘲弄,但更是一种传播真理的方式。他像苏格拉底一样,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大甲虫、狗和乡村医生的马身上,也隐藏在饥饿艺术家、K和《法的门前》中的乡下人身上,真理或许并不存在,正如从《在法的门前》中看到的那样:“门,作为没有真理的真理,它守卫着自己,但它并不是自己守卫自己,而是由一个门卫守卫着,但门卫什么也不守卫,因为门一直开着,其实门里面什么也没有。”这种悖论式特质是卡夫卡作品的特征,也是他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
在自我存在层面上,大家通常把卡夫卡理解为荒诞、异化、表现主义的代言人,因为这些简单明了的标签把卡夫卡作品变成了“可读的”“及物的”“大众的”文学,而这可能恰恰是卡夫卡所不愿看到的。比如异化问题,这是一种人类脱离自我的状态,正是因为有异化,我们会看到自我的本真状态,才会有回归的思想。奥德修斯的回归是异化后的回归,《神曲》中的但丁是升华式的异化,哈姆雷特和浮士德都是异化式的升华,可见异化是对自我和世界的深层次思考。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和格里高尔一样变成大甲虫,格里高尔或许不想重新变成人,即便他再次变成人,也绝非之前的那个格里高尔。如果没有对自我生存有过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理解的。再比如爱情问题,卡夫卡在小说中几乎从不谈及,但《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书信之一”。爱情之于他人是激情,是梦想,但对卡夫卡来说是深渊,是绝望,这有可能就是爱情的本质。布拉格是卡夫卡存在的物理空间,卡夫卡几乎无处不在,但又很难找到一处真正属于卡夫卡的地方。这一切就是卡夫卡式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像卡夫卡一样悲观。事实上,卡夫卡有助于我们超然乐观的看待世界。人生是一场体验世界、认识世界的过程,必须深入体会、认真思考才能认识它的全部面貌。因此加缪认为卡夫卡的作品越是充满悲惨的境遇,那么我们怀抱的希望就越强烈,而不能陷入“一切障碍在摧毁我”的境地中,这是存在主义者的解释。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对悲观思想的克服,我们越是深入理解卡夫卡就越有助于理解这个时代、这个世界。
尚:曾老师,您对卡夫卡的重新定义深刻而富于意义,您能谈一下中国卡夫卡研究的历程吗?他对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有怎样的意义?
曾:有关卡夫卡早期的中国研究可以用他名字的捷克语义“寒鸦”来形容——孤寂无闻。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很少,除了自己买走的以外,几年才卖一本,甚至一度被自己的国家和城市遗忘。伟大的作家都是时代的先觉者,他们开启一个时代,同时也会终结一个时代,但丁之后再无但丁,莎士比亚之后再无莎士比亚,卡夫卡之后再无卡夫卡,所以卡夫卡的孤独是大师的孤独,这是凌驾于时代的超越性。卡夫卡经过几十年的学院化、经典化和大众化,对他的评价已经趋于固定,但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看待。
中国对卡夫卡的引进大约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只限于简单的介绍。文革期间也有少量介绍,但带有浓重的阶级对立色彩,认为他是必须彻底批判的“颓废作家”。八十年代前后,伴随着对卡夫卡作品的大量翻译介绍,对他的研究也变得日渐兴盛。截止到现在,中国知网收录的以卡夫卡为主题的文章已有三千余篇,硕博士论文也有二百余篇,可见其非一般的热度。其主题涉及归属、身份、形象特征、文化分析等多个方面,既有西方视角下的卡夫卡,也有中国文化视角下的卡夫卡,特别是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主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中国的卡夫卡研究仍有不足之处,比如研究团队和主题较为分散,视野不开阔,重复度也很高。我以前的著述和眼下正在做的项目均力图弥补上述的缺憾,争取做好中国的“卡夫卡学”,全面推进卡夫卡的中国研究。
在文学创作方面,卡夫卡也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作家都有影响的焦虑,都不肯承认自己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好凸显自己的独创性和天才,但当代文学家却很乐于寻找创作学习上的先辈,卡夫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学习对象。卡夫卡对荒诞世界的描述、对抽象异化的表达方式、“写作即存在”的思想等都深深震撼着中国当代文坛,一改当时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也冲击了传统文学的写实风格。莫言、余华、格非、马原、残雪等作家都谈到卡夫卡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就会是另一种面貌。
尚:曾老师,您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和很多著作文章都聚焦于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否说明卡夫卡的某些思维或写作方式和中国有内在的暗合性?
曾: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恐怕很难几句话讲清楚。但如果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对理解卡夫卡和中国文学有一定的意义。我们经常讲文学通约的基础是文化通约,相同相近的文化基础,相似的文学价值观、审美特性和书写方式,容易相互接受,否则会有长时间的磨合过程,甚至水火不容。比如东亚文学、中亚文学、欧洲文学、南美洲文学有明显的区域性,这种区域性就是能够暗合的基础。卡夫卡阅读过老庄思想,在作品中有很多中国意象,在中国又有这么多喜欢卡夫卡的读者和研究者,卡夫卡和中国有天然的内在关联性。
西方文学有注重再现的摹仿论传统,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巴尔扎克要做“历史的书记员”,还是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都可以看到西方文学关注现实,力图再现社会。中国文学的传统也对历史和社会有深入的剖析,但和西方文学相比,我们的文学更注重内心感受,有“表现论”的特征,比如“诗言志”“文以意为主”“风骨”“气韵”等都表明文学注重体悟和化境,而诗词曲赋传统更表明我们的文学遵从内心感受,注重表现自我。而这些特征在卡夫卡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被称为表现主义大师,提倡主观感受,强调内心真实,不关注外在现实,是一种“我笔写我心”的方式。这是卡夫卡理解中国的可能,也是中国理解卡夫卡的可能。
我把卡夫卡的写作总结为想象中国、阅读中国、描绘中国和创作中国四个过程。刚才已经说过,卡夫卡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他自称“一个中国人”,被视为欧洲18世纪以来最能表现“中国主题”的作家。他的《中国长城建造时》《一次战斗纪事》《往事一页》等作品中有很多中国意象,他对《聊斋志异》和一些中国诗歌也表现出喜好。研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两重考量,一是通过研究“卡夫卡眼中的中国”可以凸显中国的学术研究分量,这个命题植根于中国当代的文化土壤,不同于歌德眼中的中国、托尔斯泰眼中的中国,其中的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亟待深入研究。二是“中国眼中的卡夫卡”可以凸显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这个命题展示西方经典作家的本土化过程,是当代作家学习借鉴,自我的修正和更新的过程。如何在当代作家作品的美学主张、写作方法和思想内容上寻找这些事实影响证据实属不易。简单的平行研究很容易导致空泛,而纯粹的实证研究又极易忽略原始材料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深化这个问题。三是“卡夫卡与中国”可以在更高的视角下对两个要素进行比较,对比中外文化文学之间审美机制、大众化、经典化等问题,可以对卡夫卡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尚:这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您的作品涉及中外历史、法律、音乐、京剧等多个方面,您能谈谈卡夫卡和中国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吗?
曾:卡夫卡在中国是个受欢迎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流行符号,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界都很喜欢他。这个问题我留意过,在流行音乐、绘画、旅游、房产、家具、餐饮等领域都有卡夫卡出现,高考题中也出现过卡夫卡主题。有《飞啊!卡夫卡》和《奔跑的卡夫卡》等电影,有名为《卡夫卡》《卡夫卡不插电》等流行歌曲,还有《卡夫卡的七个箱子》《蜕变》等戏剧作品。2017年,我和台湾艺术家吴兴国对谈,讨论过他的作品《蜕变》,《蜕变》是卡夫卡《变形记》的台湾译名。吴兴国的这部作品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受到好评,剧中他将科技与京剧、昆曲等艺术元素融合起来,也将卡夫卡的作品做了中国古典式的解读,体现了卡夫卡与中国、中国大众文化的融合。我们可以用“无处不在的卡夫卡现象”说明这种现状。卡夫卡的中国化包括学者学院化和作者创作化,也包括读者大众化。一般来说,经典作家和流行作家有着明显的界限,他们之间会有认知和审美上的差异,但卡夫卡作为学院派研究的作家能被大众推崇,的确让人感到惊讶。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一样,近年来,文学研究有一种泛文化倾向,将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经济等问题引入文学研究中,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文学研究的外延,当然国外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倾向更突出,这样可以消解学科壁垒,形成更具有当代意识的共同体观念,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研究,但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仍然有巨大的距离。如果混淆二者的关系,对文学学科的发展和未来都会有不良影响,甚至让文学研究消融在文化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应当坚守,但又不可固守,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尚:的确如此,在研究中要确立文化和文学的界限,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要有足够的认识。您的著作《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也是2018年唯一入选的外国文学方向著作,您如何看待中国学者发出的国际声音?
曾:中国学术近几十年有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理论和著作。中华外译项目从设立以来向世界推出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提升国际研究的分量,发出中国声音。如果一直跟在其他国家的后面,就会永远运行在他人的逻辑中,导向他人的目的。我们还要制定规则,占领学术高地,这样才能彰显自身的力量。随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外译项目数量增加,与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经济学等学科形成鼎足之势,但外国文学类立项不多。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大部分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没有深入体现“中国”特征,我们不但要有中国视角、中国研究的语言和体例,还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能确保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提升中国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国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也是广泛吸收了佛教和周边民族文明变得更强大,特别是从近代开始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更多。科学技术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文化文学是深层次的表现,鲁迅身上有果戈里、尼采、象征主义等身影,郭沫若受泰戈尔、惠特曼等人的影响,当代文学中,莫言受到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福克纳的影响,而受到卡夫卡影响的作家更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扩大自己的影响,西方也曾经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比如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盛唐时期日韩对中国的学习,启蒙时代伏尔泰等人对中国伦理道德的推崇,今天的孔子学院也受到一些国家的欢迎。通过中华外译项目,可以让其他国家认识中国的学术现状和学术力量。
尚:您应邀参加国际卡夫卡学术会议并发表讲演,引起学界关注,国外对卡夫卡与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是怎样的?国外与国内研究有哪些区别?
曾:在纽伦堡-埃尔兰根大学召开的“卡夫卡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就是这个主题,在这个会议上我和国内其他学者为中国学术发声。国外学者对卡夫卡与当代中国文化、文学关注的学者并不太多,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域外学者如孟伟严、周建民、戈贝尔、夏瑞春、诺伊迈尔等人都从卡夫卡的作品中寻找中国因素,朗宓榭从易经、道教等汉学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对卡夫卡作品的影响,哈塞尔贝克和迈耶尔研究长城的隐喻和皇权等问题。这类研究有一定的受众群体,但还未形成规模。究其原因,大概是国外的卡夫卡学者对中国文学没有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兴趣。要想在这个领域有较大的推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外卡夫卡研究和国内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成果丰富,方法多样,涉及的领域宽广,包括文学、哲学、宗教、政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法学等学科。目前,国外研究卡夫卡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转向,其主题有翻译、宗教、现代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捷克文化现代性、电影叙事、圣经美学、文学草图(绘画)等角度,这些研究可以在牛津大学卡夫卡中心的文章和讲座中看到,他们多是把卡夫卡放到一个具体的语境或学科领域中进行切面研究。举个例子,很多人知道卡夫卡非常喜欢看电影,在他的信件和日记中有很多记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忽视了他对电影的理解和表现,也忽视了他作品中的电影表现手法。国外的一些研究探索卡夫卡小说中的电影叙事形式,包括图像链接技术、图案、视觉视角、人物肢体语言等方面。大家也会发现,卡夫卡的很多小说就是一部电影的蒙太奇表现过程,这类研究就很好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比如,国外学者对卡夫卡绘画的研究,卡夫卡有大约五十幅绘画作品,这些绘制的草图是文学写作的一部分,词语、图像相互映射,构成互文性,生成丰富的文学场景,需要我们去挖掘它们之间的关联。很显然这和我们中国卡夫卡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既要深挖卡夫卡与中国关系,也要多学习西方研究者的方法和理论。
尚:您最近致力于文学源头问题研究,在学界讨论广泛而又热烈,在近期的一次学术活动中,有学者将您的这种“福尔摩斯式”研究当作一个巨大的隐喻。您能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吗?
曾:这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西方文学、东方文学和中国文学在表现形式、人物塑造、表达理念等方面有着很多相异相通之处,在其背后一定有更深的源头。我们做好比较文学,需要在本体上进行对比和相互参照,可以借鉴词源学或知识考古学方法,找到源头才能回归到本真,才能做到胡塞尔所说的“回到事物本身”。
我将这个寻找过程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隐喻中,就像寻找河流的源头一样,对起源的终极性考察会发现这个过程是一个闭环,源头潜隐在支流中,支流又蕴含源头的要素,最后消融在各种形态中,虽然找不到所谓的“第一滴水”,但寻找的过程就是无限接近真相的过程。这种福尔摩斯探案式的探究,一要有严密的逻辑和充足的事实材料,争取在蛛丝马迹中寻找始源性的大问题。现在有关西方文学源头的主流观点是“两希”,古希腊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克里特文化,但克里特文化的源头则起源于东方,再向前追溯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可能要依赖历史学、古文字学、人种志等学科的新材料、新发现。有人提到《荷马史诗》可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但在荷马所代表的世俗文学之前还有鲜为人知的宗教文学,古希腊神话也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顺着这几条线索会发现源头晦暗不明,就像河流的源头一样,越靠近发源地就会越模糊,只能人为地赋予它们一个所谓的源头。但在寻找源头的过程中,会发现源头问题远比武断的结论复杂。从结论角度寻找证据是惯用的方式,也是简便的方式,但如果从源头向后寻找,则更加复杂。
尚:您的思考对重写文学史、外国文学研究意义重大,您最近一直都在编撰文学史,您是如何看待这次重构过程的?
曾:文学和文学史不是简单的酒与酒瓶的关系。文学是人类思想和审美的结晶,是个人对时代的反思,伟大的作家都会在作品中体现出自己的天才特征,他们修改传统,制定自己的标准,这在莎士比亚、歌德、卡夫卡、艾略特等作家身上都有明确的体现。反观文学史的写作截然不同,文学史要隐去自我,凸显文学本身,重在史料和叙述,而少有情感价值判断,这样可以更好地显示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大部分文学史都是合作完成的,为了平衡只能有所取舍,所以就其中心和主旨而言有的不甚明晰。更严重的是,一些教材为了经济利益考虑,会扩大阵容,很多学者专家把体例、格式、字数等问题提前分配好,这样做一来可以整合各位专家的特长,二来可以提高发行量。特别是在后者的刺激下,出现多种文学史,造成大量的重复性工作,从而把个性的观点给消解了。
在我看来,一部文学史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个人观念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一场文学远征,是整个欧洲的社会史、思想史和灵魂史,这种宏观的文学史写作直至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欧洲文学史,文约意丰,披沙拣金,完全印证了他“人的文学”的思想。还有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和木心的《文学回忆录》都可视为个人文学史,他们都是用“六经注我”方式来写作,甚至借用文学史论证自己的观点。我正在整理多年来的外国文学讲稿,西方文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我反复思考、写作过的材料,也是我多年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结晶。希望撰写一部外国文学史,通过大量的材料和考据式研究,对原典性问题进行界定和考辩,更加深入地推动相关的研究。
尚:曾老师,您从教三十余年,可谓桃李满天下,您在人民大学深受学生的喜爱,获得了“教学年度优秀奖”,您是如何思考教育教学问题的?
曾:教育观体现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该培养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大学精神,低层次方式是灌输知识,这是可习得的,而高层次的是授之以渔,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前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他们是社会上的精英,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今天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只是人生中的一段经历,学生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读好大学、找好工作、挣大把的钱,曾经的远大理想让位给世俗的追逐。这本身没问题,但如果所有的大学生都没有担当和责任意识,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这就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教学问题。在我看来要培养大学精神,首先,要有自由的思想,自由意味着独立选择,不跟风不媚俗,有自己的志向和理想,追求自我的价值,从而形成独立的人格。其次,要学会创新,注重创造性,今天的科技突飞猛进,依靠死记硬背、知识累积的传统方式会被人工智能代替,学生在学习中要以创新意识、问题意识为导向,这样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有就是注重人格熏陶,一个好的老师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用好的生活方式感染学生,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寻找自己的幸福。当然这是一种内在的影响,而非干预他人。
尚:曾老师,您对学术和人生等问题的真知灼见让我受益匪浅,相信大家也可以从中找到真谛。再次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