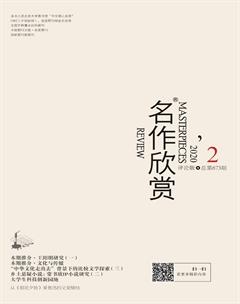海明威笔下“强势”女性探寻:以弗朗西丝和玛格丽特为例
摘 要: 本文从《太阳照常升起》入手,以分析弗朗西丝的人物形象为引子,结合另一部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另一人物玛格丽特的形象分析,探究在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经历下作者对于强势型女性的思考,并分析对比二者,从而探寻此类女性人物形象出现的必然性,最终落脚于海明威对于女性的思考,寻找《太阳照常升起》的新价值和当下启示。
关键词: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 玛格丽特 弗朗西丝 女性
一、暗流涌动的美利坚
1926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是惊涛骇浪的一年,如果说一战二战算是两场海啸,那么1926年大概也就是处于涨潮期的大海的日常,“从1922—1929年美国进入了它的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有人称作‘自由放任的十年”a。在这十年的经济膨胀中,在表面繁华的背后,正潜藏着一系列的危机,这种泡沫般的经济在自由放任的发展导向之下,股票投机和贷款行业膨胀,实体经济和第一产业表现萎靡,消费主义盛行一时,美国建国初形成的清教主义精神正在慢慢倾塌,老一辈清简的生活观念正在被挤压,渐渐被搁置在过去,被搁置在少数仍具有计划和节俭精神的人中,多数人已经淹没在消费主义的洪流之中。然而正如福克纳在《美国经济史》中所说的一样,“把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事件描述成是‘复兴,便是对这个名词的曲解”b。盛名之下,实际难副。
《海明威评传》 中说:“这部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写作起念于1925年夏天。当年他与哈德莱(海明威当时的妻子)同一批侨居巴黎的英美籍朋友们去西班牙看斗牛。在这期间友人之间因争风吃醋发生了争吵甚至斗殴。海明威深有感触,他把这些无谓的争吵升华为战后一代青年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冲突与碰撞,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c同时,海明威的感情生活也并不顺利,他和妻子哈德莱的矛盾深化,发展到分居甚至离婚的地步,同时海明威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位情人——保琳,海明威本想保持着丈夫、妻子、情人这种平衡之中,“哈德莱了解他的弱点:有人向他表示爱意,他是会接受的,即使他不爱此人。保琳崇拜他,作用则更大”d。最终,这样三角关系以海明威和保琳在一起,哈德莱远走而告终。美国经济的浮华、朋友之间的分歧、个人婚姻生活的波折,在海明威面前仿佛就像一片混乱的垃圾场,混乱而热烘烘的表面让人不得不去思考自身所在位置。而正如《太阳照常升起》 的两个序言一样,对于生活在其中的青年男女来说,他们是迷惘的一代;对于这个浮华的时代,言语的空虚和生活的空虚并存,让人无法脱身其中。也正像是第二段序言说的一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e。时代社会的浮华和混乱总会过去,紧接着是下一代的出场,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太阳依旧升起,海明威虽然处于迷茫的时代中,却有着一种先觉的意识,一眼望尽浮华,看到太阳依旧升起。
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 便有了其相对应的时代意义和精神指向,笔者在此并不打算从揭示主题的角度去考量这部书的价值,而是通过在主客体的背景和影響状况下,选取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弗朗西丝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中的玛格丽特两位女性形象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在时代背景和个体成长背景下,根据作者的描写和情感倾向,一探海明威对于这一类女性的思考。
二、弗朗西丝的变动与离开
自女权运动以来,女性这个词的含义渐渐沉重起来。“现实中的女性可以从人格的角度,以本能指向为根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女性型的,即具有自恋、被动和受虐特点的女性,这一类女性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她们按本能的指向在发展。另一类是男性型的,她们表现为主动、竞争和攻击”f。抛去分类者的个人色彩不说,女性型人格的女性占大多数,并具有更多传统女性的色彩,而男性型人格的女性在古代社会并不常见,更多出现在自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妇女经济趋于独立的时期,这种人格在主动的倾向下侧重于控制、强势,以及占有等方面。譬如在《太阳照常升起》 中出现次数远低于女主人公(勃莱特) 的弗朗西丝。
弗朗西丝这个名字在《太阳照常升起》 中一共出现了三十一次,主要是在故事的前半部分,在第十八章又出现了一次。根据作者的初始描述,弗朗西丝被这样书写道:“指望跟这家杂志一起飞黄腾达的女士。”g很明显,作者对于弗朗西丝的认识是贬义的,然而他又能以特有的冰山风格不着边际地在文本中多个地方,悄无声息地塑造了一个不同于勃莱特的女性形象。这位女士不同于勃莱特在各色男人中游移的状态,而是在年老色衰后紧紧抓住了科恩。文中开篇就有这样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地方,当杰克提到斯特拉斯堡有一个可爱的姑娘时,弗朗西丝板着脸,而科恩紧接着表明了自己不可能去的态度。在后文中,舞会之后,科恩也是跟着弗朗西丝回家,科恩之所以去不了南美也是因为弗朗西丝,先前慷慨相助后来索要路费的也是弗朗西丝。
科恩,默默忍受着刻薄话语的发出者——弗朗西丝。弗朗西丝,这一人物对于科恩的性格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科恩在女性面前的懦弱。杰克也一语道破了科恩在弗朗西丝的控制下很不好过的事实。随后,当科恩从纽约回到巴黎,意识到自己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时,情况大大地转变了。说话“滔滔不绝”,“个子很高并且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弗朗西丝再也无法掌握他。她跟杰克倾诉,告诉杰克自己为了和科恩结婚而离婚,并且想为他生孩子,做一个好妻子。然而当科恩出现的时候,她的数落又一次开始了,那种命令式的词汇如“是不是,罗伯特”,“听着,罗伯特”的话语像子弹一样一颗颗发射出来,终于使得杰克听不下去而选择离开,而科恩只是脸色惨白。随着二者主导位置的变动,弗朗西丝去了美国,在接下来的描写中,弗朗西丝仅仅出现了一次,在第十八章中,当比尔问起杰克“他过去的情人是谁?”回答仅仅是“一个叫弗朗西丝的”h。至此,弗朗西丝在整部小说中的出镜到此为止,严格地说,在第八章就结束了。
从这些断断续续的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立体而复杂的女性形象。我们看见了弗朗西丝的强势、控制欲、占有欲、富有攻击性的话语指向,以及年老色衰之后的不自信所产生的对于科恩救命稻草一样的依赖感等个性上的瑕疵。海明威以其一贯的冰山风格,把弗朗西斯外在行为的八分之一写了出来,剩下八分之七的情感与价值取向隐匿在文本之中。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海明威对于女性的性格与行为在内心已经有了自己的衡量倾向。带有“妖妇”魔鬼色彩的弗朗西丝,对于自己外貌的不自信(她曾提过自己年轻时可以获得很多有结婚冲动男子的欢心,这恰恰是对自己当下容颜不再的不满和不甘心)和性格上的强势已经构成了其主要的特征。
对于弗朗西丝的分析,因为作者着墨不多,且较之勃莱特来说实在是逊色很多,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而广泛的注意。但从弗朗西丝、勃莱特等女性形象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女性形象的丰富思考,弗朗西丝的存在一定有其存在的意义,文风极简的海明威不会随便牵扯上这么一个人物,随后便不了了之。弗朗西丝和科恩这条线索,在文中并不起主导地位。但是却有着深广的意义追寻。“在阿德勒看来,妇女之所以具有自卑感,并不是因为她们没有阳具的缘故,而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男性优越地位。他曾一度将自卑感和缺乏男子气概与女人气等同起来(霍尔和林赛,1970年)。有些妇女如痴似狂般地追求权利与名譽,以此来对自卑感做出反应,阿德勒称之为‘反男性”i。弗朗西丝的强势更带有一种虚张声势的效果,她并没有强大到科恩离开她也无所畏惧的内心,相反,在发觉到自己的弱势地位时,她选择了妥协,又带着一种强势,一种对于科恩控制冲动的情感惯性。强势的弗朗西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而是带着一种外向型的依赖心理——并非处于爱情,而更多处于两人的利益关系,弗朗西丝的行为与话语被杰克所不屑和反感。弗朗西丝和科恩的两性关系也是不正常的,一直处于一种不平衡之中,要么是初期科恩对于弗朗西丝的被动,要么是后期弗朗西丝对科恩主动权加强之后的被动。
三、玛格丽特的枪声与决断
在海明威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类似于控制与被控制的场景,不过在这个场景中,男女之间的角色被置换过来了。然而两部小说中的女性仍旧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九年后出版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也是海明威较满意的短篇小说之一。此时,危机已经过去,战争已经结束,然而在美国的和平时期,海明威选择远赴非洲狩猎。“玛丽·威尔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不景气的日子里谈起她的丈夫时说:‘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他有时变得很平凡。你看,他在和平时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然而就在那一段暂时平静的时期,他们到非洲去猎狮子了。”j这部小说即写于猎狮之后。
海明威对于这一类倾向于强势的女性的思考从来都没有结束。它一直占据着海明威思想的某一部分,直到后来塑造出这位集美丽的外表和强势的性格于一体的世俗女性——玛格丽特,即麦康伯太太,巧的是,她的丈夫叫弗朗西斯。而这位太太,是“极好的美人儿,凭着她的美貌和社会地位,五年以前,她用几张相片为一种她从没用过的美容品做广告,得到了五千元酬金”,可见她的外表的美丽。不过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玛格丽特作为女性被观赏的广告价值,而这就有着一些被物化感的体现。然而作者在对其容貌大加赞赏之后却很微妙地引入了一个相似于《太阳照常升起》 中的一个情节,当玛格丽特紧随威尔逊去打野牛的时候,而她的丈夫弗朗西斯·麦康伯表示了否定,结果却是玛格丽特的坚决压倒了丈夫的命令。而作为旁观者的威尔逊,却认为她在离开的二十分钟里,“涂上了美国女人那种狠心的油彩。她们是最最该死的女人,确实是最最该死的”k。而那种“狠心的油彩”,是因为“当她们变得冷酷时,她们的男人就得软下来,要不然,就会精神崩溃”。这种倾向性的描写无疑是十分明显的,在威尔逊看来,玛格丽特身上带有一种强势女性的色彩。在威尔逊“游猎队里的女人真麻烦”的心理活动中再次体现出对于女性参与男性活动的不适应的。和在《太阳照常升起》 中相对模糊的写法不同,海明威在这里通过威尔逊之口相当直白地道出了对女性的强势与控制欲的反感和厌烦。玛格丽特的淡玫瑰红的卡其衫引起了他对英国的美妙联想,这又体现了作者既对女性的色彩的着迷,又厌倦女性的过分强势之矛盾心态。
当其丈夫打倒公牛,变成了一个无所畏惧受到威尔逊喜爱的男子汉时,玛格丽特又感到十分惊吓,甚至打冷战,嘴里不停地说着讨厌,这似乎印证了,当她的男人一旦脱离了她的控制,她便会精神崩溃。而在文中“她非常害怕一件事”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似乎是为后文她向丈夫开枪做了铺垫。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麦康伯的心理,他一整晚都受到狮子吼叫的困扰,当狮子出现,他一系列的行为显示了他无可辩驳的慌乱,连打两枪都没有打中要害,当狮子因为负伤而倒下,他反而“胃里感到难受,握着斯普林菲尔德手枪的双手仍然做好设射击准备,还在发抖。”l这种性格软弱的表现与玛格丽特在狮吼之夜的安然熟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时候,海明威描写人物的风格便体现了出来,也正如他所说的:“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角色,他们必须出自作者自己经过消化了的经验,出自他的知识,出自他的头脑,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m直到后来,当麦康伯和威尔逊再次开始狩猎的时候,玛格丽特忽然举起了手枪,她射中了麦康伯。至于玛格丽特到底是不是故意呢?笔者在玛格丽特后期的表现中,感受到了她对丈夫反客为主的家庭地位的恐惧,自从麦康伯射中了水牛,玛格丽特便陷入了持久的恐惧和挣扎之中。直到后来她“失手”射中丈夫,面对威尔逊的话语,她只是不停地重复着“别说啦”。开枪的那一刻,玛格丽特是什么心态,在作者不着痕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至少,在她的潜意识中,她是有着开枪的冲动的。
故事就此收束,麦康伯的幸福生活似乎只持续了半天,二人的依存关系仅仅是彼此的美貌和金钱。麦康伯的软弱和玛格丽特的强势形成了对比,玛格丽特对丈夫的要求也常常无所触动,甚至反向为之,夫妻二人的关系处于控制和被控制之间,而几乎与爱情无关,与小说的题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仅仅针对麦康伯,那么幸福生活的指向在外人看来也就是他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日益上升的社会地位,而就其本人来说,结婚以来的压抑、妻子的控制并没有构成所谓真正的幸福,所接受的也仅仅是外人指向的那种生活;就夫妻二人来说,所谓二人的幸福生活也只是外人眼里的幸福生活而已。
玛格丽特这一人物形象一反海明威众多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的柔和色彩,再也没有了像凯瑟琳一样的温柔和对情人的支持,而是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抗。近代社会以来,女权运动声势浩荡,极端化的女性主义呈现出强大的力量,“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初,天真地在菲勒斯中心的话语囚笼中为自己设计了一个陷于悖论的奋斗目标,那就是颠覆男权,反客为主,争取女权。这就使得女人追求的这场反征服运动仍未跳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战争状态,只不过是由男权中心变为女权中心而已,而这种价值追求不过是对男权话语的沿用”n。在这种情形下,女性所追求的这种解放、和平便变得很奇怪。当代学者也曾讨论过关于男女平等的话题,而那种取消了男女性别差异的平等无疑是对女性解放的误读。当我们回到玛格丽特行为的现场,玛格丽特追求女性的独立,做出自己行为的选择,利用自己的外表进行商业活动和利益获得是她合理权益的体现,这无可辩驳,然而玛格丽特对于两性关系的理解却和麦康伯一样有着个人色彩的误区。面对丈夫内心强大的变化,她变得恐慌,而不是像正常两性关系那样选择彼此鼓励,为对方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欢心。这种倾向于权力型人格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海明威看来,便是一种危险。
四、从警示到枪声,两位女性的对比探寻
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女主人公勃莱特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她留短发,戴男式帽子,辗转于男人之间的一系列行为却没有引起读者的过分反感。虽然当海明威写完《太阳照常升起》并拿给母亲看时,母亲对其的评价并不高,“她‘不能再保持沉默,说她的儿子‘写了本年度最下流的一部书,她认为她的儿子‘除了他妈的和婊子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词语——你写的每一页都叫我恶心”o。但是勃莱特作为一個敢于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人物毕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与玛格丽特相比,算是温和得多。
盛年时期的海明威,给我们的印象常常是“硬汉形象”,“大男子主义”“,没有女人的男人”,然而,海明威一生中都没有和女性分离过,从母亲、妹妹到几任妻子和情人,可以说这些女性时时刻刻影响着他的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海明威的创作。他在追求强大的同时也在探寻着自己作为男人的最大极限,即使有时会有心理负担,有时会产生敏感的情绪,然而我们却总是能看到一个立体的海明威。在他的小说中,展示了男性力量的强大,体现了父权传统下雄性的力量,然而海明威无论如何高大,他毕竟也是凡世一人,在女性地位上升的过程中他能敏感地抓住不同女性的表现并塑造出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在父权分崩离析的初始阶段依旧寻找着一个作为男性的尊严和选择,这使得他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男性与女性时有着复杂的想法,这便引起后世读者和评论家的各种判断和猜想。笔者在阅读海明威的有关资料时发现了这样的一段话:“他最后一次谈受伤的情形,是在1951年1月1日写给评论家哈维·布雷特的信中。当时他已因多次事故又多次负伤。此信的笔调颇像他写的短篇《死者的自然史》 (1933),超然物外,欣然而谈:将手放在膝盖上,觉得膝盖已经没了,手不由自主地去摸伤口,惊恐不已;发现阴囊受伤,惊恐不已;手榴弹爆炸担心会把眼睛炸瞎,惊恐不已。”p在伤痛之外,他最为恐怖的是灵魂上的残缺(包括自身意志或者由于生理缺陷带来的男性气质的转变等),海明威最终选择了开枪自杀。
海明威对于女性的态度很难从单向度去思考,至少包含着两种以上的矛盾认知。他既欣赏女性的美貌又忌惮女性美貌下过于简单的大脑,譬如凯瑟琳与玛格丽特;他既依赖着女性的崇拜和支持,又畏惧着女性的强势,譬如弗朗西斯与勃莱特;他既肯定女性对于自我价值的和追寻,又对女性带有控制倾向的行为表现出厌恶与反感,譬如勃莱特与弗朗西丝。
玛格丽特性格的强韧度是高于弗朗西丝的,而弗朗西丝向现实的妥协也是玛格丽特所做不到的;玛格丽特没有弗朗西丝的啰唆和自卑,她对与自己的容颜呈现出一种绝对的自信,而弗朗西丝则开始对于自己的外貌产生不自信的倾向。然而她们对于男性的依赖并不体现在传统的爱情和安全感上,她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外在的、物质上的安全感,而在个性独立上的选择已经呈现出自足的现象。弗朗西丝最后的悻悻离去和玛格丽特的枪声似乎震醒了我们脑海中某些模糊不明的区域。单向度地去评判分析海明威的人物选择似乎总是显得很苍白,强势的女性形象给我们以黑色的美的感受,带着几分美狄亚的反叛和绝情,同时又折射出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性格的个性化使得每个人都带有各种各样的锋芒和触角,在女性强势主导的两性关系中,男性的个性化发展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而反过来也是如此,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出海明威对于两性关系的重视,爱情、婚姻、女人在海明威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不停的思考展现出海明威一系列的矛盾心理,而对于性格的尺度的探寻,永远都在路上,趋于而无止境,能从其中得到一些启示,亦是一种收获。
a 黄安年:《二十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9页。
b 〔美〕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4月第1版,第314页。
co董衡巽:《海明威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54页,第64页。
dp 张禹九:《总有女人的男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80页,第9页。
egh〔美〕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赵静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页,第6页,第242页。
fi张海钟主编:《现代女性心理学导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57页,第38页。
j 〔美〕库·辛格:《海明威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第5页。
kl〔美〕海明威:《海明威短篇小说集》,陈延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6页,第20页。
m 董衡巽编选:《文化生活译丛海明威谈创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5月第1版,第3页。
n 于冬云:《谁杀死了弗朗西斯·麦康伯———从男人、女人与菲勒斯文明转向说起》,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作 者: 刘烁,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本科生。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