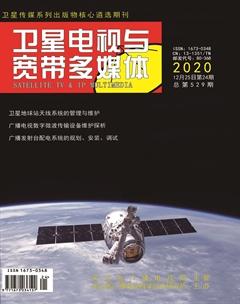从媒介研究的视角看影视改编创作

【摘要】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分别在1987年和2014年被改编为电影《红高粱》和电视剧《红高粱》,三部作品都讲述了高粱酒坊女当家人与当地土匪头子的传奇爱情和他们联合当地村民英勇抗日的故事。本文分析了两部影视作品情节不同的改编手法,比较了三部作品在叙述主体的视角、情节和人物关系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媒介研究;影视作品改编; 红高粱 ;符号学;叙事学
中图分类号:J91 文獻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0.24.050
电影《红高粱》创作于1987年,由张艺谋执导,改编自莫言同名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主要是对其中第一章中篇小说《红高粱》的改编。进入21世纪,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又被改编为60集电视连续剧《红高粱》,由郑晓龙执导。从类型上看,两部作品皆为历史题材改编,都讲述了高粱酒坊女当家人与当地土匪头子的传奇爱情故事和他们联合当地村民英勇抗日的故事。但由于媒介类型不同,两部影视作品对故事情节的改编手法不同,三部作品所呈现的叙述者身份、视角、情节和人物关系也存在差异。
1. 叙述者、叙事视角差异
创作者不等同于叙述者,创作者会根据不同的叙事要求为叙述者寻找合适的角色并确立合适的视角,使叙述者更好地承担起叙事任务。叙事视角是创作者观察事件的立足点,也是叙述者在叙事中的角色定位。结构主义学者法国的兹韦坦·托多洛夫把叙述视角分为三种形态:全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后两种也称限知视角。全知视角是指叙述者无所不知,可以全方位地描述人物与事件;内视角是叙述着与故事人物知道的一样多,不能像“全知全觉”那样,提供人物自己尚未知的东西,也不能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说;外视角是指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一切不仅不全知,反而比所有人物知道的还要少,他像是一个对内情毫无所知的人,仅仅在人物的后面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行为和语言。
原著《红高粱》以叙述者“我”的讲述串起整个故事,“我”是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大段的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体现了叙述者的全知全能。小说中除了“我”的视角外,还有“我父亲”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比如从“我父亲”的角度去讲述最后抗战的画面和罗汉大爷被剥皮示众的场景。“我父亲”作为目击者是充当了历史代述者,而“我”的叙述属于子孙后辈的想象,带有当代社会语境,同样的事情切换不同的叙述视角,打破了时空阻碍,将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和文化意蕴,同时将作者的观点通过“我”这个隐含作者之口表达出来。
电影《红高粱》部分保留了叙述者“我”的全知视角,又增加了故事主人公的内视角。故事开头是由镜头外的“我”向观众讲述的,“我”用画外音形式以第一人称解说“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接着就是“我奶奶”的出嫁场景。大多时候,叙述者“我”隐藏起来,以故事内人物——九儿、余占鳌和豆官的视角讲述故事。
电视剧《红高粱》的叙事视角灵活多变。该片没有出现异故事叙事者的解说,也没有让故事中的某个人物直接向观众讲述故事,总的来看,叙述者是导演的话语和精神的化身。从电视剧的叙事特色来看,摄像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视点,使故事好像并没有讲叙者,呈现超话语的叙述模式。电视剧具有即时的直观性和时效性的美学特征,比电影改编更具通俗性、大众化,更强调时代感和生活气息,具有更多的悬念设置。电视剧《红高粱》共有60集,每晚三集连播,播出周期比电影更长,剧情比电影更加碎片化,需要观众以比对电影更加热情的态度连续“追剧”,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结合的叙事方法更能造成悬念,引发观众的兴趣。
从媒介特点上看,文学给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时空错位的表述方式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十分契合;电影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异故事叙述者“我”偶尔出现的第一人称讲述能够更深地带领观众沉浸到电影的氛围中,此外电影还发挥了视听功能,将文学中“我”的感受用充满隐喻色彩的画面加以表达;而电视是一种陪伴式的媒介,导演利用视角的转换尽可能“还原”了故事的发展,虽然剥夺了观众解读的权力,但是符合影视剧消遣、娱乐的功能定位。
2. 情节、人物关系差异
电视剧与电影改编相比,在长度和容量上比电影更具优势,因此电视剧更适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改编,而电影更适合中篇小说《红高粱》的改编,这也造成了电视剧比电影的情节更丰富,人物关系更复杂。总的来说,电影改编——提炼中心、化繁为简;电视剧改编——分散人物功能、增加支线剧情。
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采用插叙的方法进行叙事,展现了土匪、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侵略者几方势力交杂中的乡土社会,借助高密东北乡原始而野性的风土人情,抒发了作者心中呼唤民族自尊、反对奴役并渴望自由的主题。
就文学与电影来说,前者以语言文字为其媒介,后者则以画面与声音组合而成的镜头为媒介,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来替换已有的文本样式,改动似乎不可避免。电影《红高粱》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是按照《红高粱家族》的第一章《红高粱》改编的,支线情节和人物参考了其他章节。电影主要讲了爱情和抗日两件事,还对这两个故事做了简化。对爱情故事的简化体现在,删去了封建家长“单廷秀”,简化了九儿的父母和单扁郎(片中叫李大头),删去了爱情破坏者恋儿、黑眼,将九儿与罗汉的情愫用隐晦的方式表现出来;也简化了抗日故事,删去了具体政治人物冷麻子、胶高大队长、江小脚、曹梦九等,删去了余占鳌落草的故事,精简了余占鳌等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战争。导演只保留了李大头、九儿、余占鳌、罗汉、伙计们、儿子豆官、蒙面劫匪、土匪秃三、屠夫、九儿她爹、侵华日军还有叙述者“我”等主要角色,第一阶段歌颂原始的爱情,第二阶段歌颂民族热血,二者的共同之处便是本片的主题——歌颂像高粱一样野性热烈民族生命力。根据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理论,我们可以将电影情节分为两个阶段,四类人物。
从以上两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一旦剧情发展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非主题和非反主题人物大都聚拢到主题上,借助电影中不断出现的高粱符号的隐喻,传达出一个概念——野性热烈的民族生命力。可见,导演通过对原著情节和人物的梳理和精简,结合电影艺术的特点,结合电影叙事的特点展现了原著的精神内核。
电视的传播性质决定其叙事语言与小说、电影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种大众艺术,电视剧面对是千家万户的普通观众,而不是走进影院的消费的有一定审美层次的受众,这决定了电视剧艺术在叙事上注重情节、有生活气息,符合普罗大众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电视剧《红高粱》的叙事主要围绕女主角九儿展开,全剧有13个主要人物,在原著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人物还添加了几个人物,增加的人物有:九儿的青梅竹马、进步青年——张俊杰,土匪花脖子的妹妹——灵儿,九儿与余占鳌的女儿——琪官,心怀不轨的黑眼的义子——玉郎,守着贞节牌坊过日子的单家大儿媳——高淑贤以及单家一系列眼馋家产的叔嫂长辈。这些人物的出现凸显了时代背景,丰富了故事情节,分散了原著中人物的功能。
单家一系列眼馋家产的叔嫂长辈的出现丰富了九儿的家庭环境,讲酒坊塑造成一个与各方势力沾染的封建大家族。此外,张俊杰、灵儿代表进步青年,高淑贤代表受封建迫害的妇女,这两种类型的人物设定凸显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复杂的社会背景。电视剧还把原著中支线人物的经历安放到了九儿身上。原著中九儿与余占鳌育有一子,恋儿与余占鳌育有一女,而电视剧改编为九儿与余占鳌有一双儿女,恋儿跟余占鳌没有子女——原配儿女双全,“小三”不孕不育——符合当今大众的期待。电视剧改编还按照世俗标准美化丰富了九儿的形象。九儿未嫁时爱上的青梅竹马张俊杰是一个文质彬彬、知书识礼的进步青年,可以看出九儿身上带有反叛的特质,两人约定私奔不果,引发了国民党剿匪军队、封建观念影响下的普通百姓、余占鳌等几种人的势力纠葛;在原著中,九儿与罗汉有一段感情,但是电视剧将罗汉的感情嫁接到了寡妇大嫂高淑贤身上;九儿为报复余占鳌出轨,与黑眼同居,而在电视剧中改为九儿去说服黑眼救余占鳌一命。导演通过对人物的删改,完整地刻画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主角九儿不仅要跟常人一样面对婚姻与爱情的困扰,还要应对封建家庭内部的斗争、日本官兵对大家族的威逼利诱,还要处理干爹(国民党)、余占鳌(土匪)、张俊杰(共产党)之间的矛盾。电视剧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把《红高粱家族》的故事与当今社会的价值观相结合,把文学的想象变成了具体的影像视听语言,把抗战时期的社会矛盾都加之于女主人公九儿身上,将九儿树立成了一个忠贞、智慧性格刚烈的母亲形象。
3. 总结
文学、电影、电视剧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媒介形式,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依据媒介提供信息的清晰度或明确度及信息接受者想象力的发挥程度及信息接收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将媒介划分为冷媒介与热媒介。文学是热媒介,电视剧是冷媒介,而电影居于二者之间。从视角上看,三部作品都采用了多視角叙事,电影保留了文学作品的第一人称叙事,电视剧则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因电视剧的大众性和娱乐性,这样安排更符合人们认识规律。从情节和人物关系上来看,因为时长和电影美学的符号化特征,电影的情节和人物关系是最简单的,同时电影将人物的情感用气势恢宏的声画语言表现出来,在表达情感上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文学作品和电视剧在情节和人物关系上都比电影丰富得多,但是电视剧艺术在叙事上注重情节、有生活气息,符合普罗大众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译林出版社,2011.
[2]张琼.关于电影改编忠实性原则的思考[J].电影文学,2011(13):13-15.
[3]刘晶.叙事学视野下《红高粱》的改编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6.
作者简介:董方红,女,(1995.12-)汉,山东烟台人,硕士学位,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