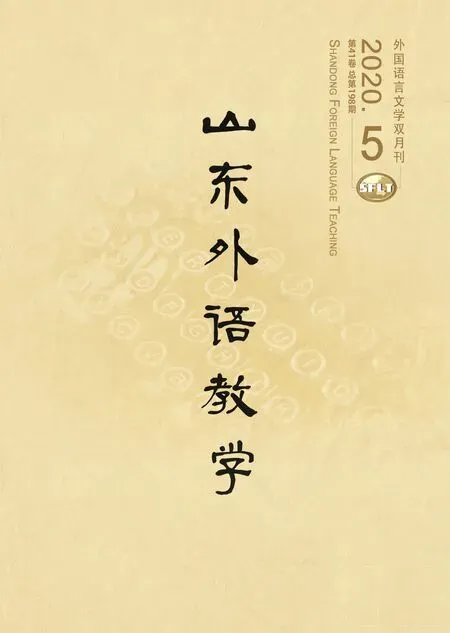《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的文明互鉴与去中心化营构
朱振武 薛丹岩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1911年,加纳(Ghana)①作家约瑟夫·艾夫拉姆·凯斯利·海福德(Joseph Ephraim Casely Hayford,1866-1930)出版了小说《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Unbound:StudiesinRaceEmancipation)。这部作品不仅是海福德本人的处女作,也被认为是“西非英语小说鼻祖”(Dathorne,1974:144),甚至被认为是“非洲的第一部英语小说”(张毅,2011:11),乃至“黑非洲英语文学诞生的标志”(朱振武、韩文婷,2017:98)。但这部非洲英语小说的开山之作却被草率地定义为一部缺乏故事性的、探索非洲民族主义哲学的说教式作品(Ward,1970:82),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仔细考察会发现,《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以主人公夸曼克拉(Kwamankra)的见闻与思想为主线,是一部杂糅了纪实、议论、演讲等多种文体风格的“非典型”小说。这种信马由缰式的写作风格看似不合文学想象的规范,实则是对小说创作成规的挑战,是海福德反叛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这部“非典型”小说对种族、文化和教育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对同时代以及后来的文学创作与政治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非洲英语小说乃至整个非洲英语文学的先锋之作。
1.0 多元文明的平等与互鉴
由于大沙漠的阻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地缘上曾一度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发展落后乃至停滞。相反,19世纪下半叶,经历了工业革命洗礼的欧洲诸国在全世界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市场。“优生学”与“进化论”为逐渐膨胀的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所谓的理论依据。殖民者开始以自身为标准,将科学、技术等物质因素作为衡量一个民族有无文明的标准,从而明目张胆地给非洲贴上了野蛮的标签,进行妖魔化宣传,以贬低和抹杀非洲文明。但从一开始,非洲各国各地区的有识之士就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对殖民者口诛笔伐,针砭时弊,为自己正名。以图图奥拉、索因卡、阿契贝以及本·奥克瑞为代表的尼日利亚作家“借助殖民语言,向全世界呈现崭新而真实的非洲形象”(朱振武、韩文婷,2017:102)。诺奖得主、著名南非作家库切运用独特的叙事空间表达了“反抗殖民体制,追索身体自由和心灵自由的强烈渴望”(蔡圣勤、芦婷,2018:86)。海福德则是加纳作家的先驱与代表。
海福德出身显赫,父亲是著名牧师并在政界颇有名望,母亲亦出身名门。在优渥家庭条件的支持下,他在本土接受到了当时最为优质的教育,对《圣经》以及基督教义也十分熟稔。而后,他游学海外,在英国学了三年法律,这使得他有机会深入欧洲文明,并对之进行深入考察。得天独厚的国内外学习经历使得海福德能够以多重视角审视非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使他能够对面临的问题做出理性的判断,形成了既不狭隘也不媚外的“交互”(reciprocity)思想。他的大量作品中表达的共同主题,即“整个人类的自由”和“人类的普遍尊严以及法律之下的平等问题”(Ugonna,1977:160),都与他的这种思想密切相关。
海福德对非洲文明有着清晰的定位和深刻的认识。非洲文明孕育于非洲大陆,流淌在黑人民族的血液中,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非洲文明与欧洲文明样态确有差异,但各有所长,不能以优劣高下区分之。李安山(2018:44-45)提出:“文明互鉴是指不同民族在交往中能吸收其他文明成果并运用到实践之中,使之成为自身价值体系或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文明互鉴的情况有两种。一是不同文化的相通性,二是不同文化的互补性”。这种多元文明“相通”与“互补”的思想在海福德纵横捭阖、引经据典的叙述与议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但也存在着内在肌理上的相似性和精神实质上的相通性。在《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中,海福德追本溯源到西方文明的滥觞——古希腊文明,认为“当人们翻阅《奥德赛》这个精彩的故事时,他们就会碰巧发现希腊人和芳蒂人在思想和行为上有着惊人的相似”②(海福德,2019:164)。无独有偶,作者还将芳蒂族的本土神灵与希腊神话中的神灵进行对比,将埃及奥西里斯神崇拜、拜火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斯多葛学派与基督教进行对比,认为不同信仰之间同样具有相通性。比如斯多葛学派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沉思录》(TheMeditations)中的思想与拿撒勒教义在某些说法上具有惊人的相似,而非洲人的思想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欧洲的基督徒更好地贯彻了基督精神。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提出“‘异教徒’是一个相对的术语。也许你们普通的英国人没有权力把一般的埃塞俄比亚人称为异教徒”(23)。
多元文化之间不仅具有相似性,更具有互补性,这一点文化界基本形成共识。黑人民族同样可以为其他民族提供有益的启发。英国女王神学院学生怀特利(Whitely)向夸曼克拉提出了自己关于“神”(God)的困惑,夸曼克拉则运用芳蒂语从词源上对“神”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夸曼克拉认为怀特利之所以产生困惑,是因为“神”一词并不来源于欧洲。在盎格鲁—撒克逊以及日耳曼文化中,“神”这一单词与“好的”、“无所不在”等意思毫无关联。而在芳蒂语中,万物之神名为“NYIAKROPON”,可拆解为“Nyia nuku ara oye pon”,意为“独自一人的他是伟大的”。由于含义明确,芳蒂族人并不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困惑。在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而罗马文明又曾经受到非洲文明的启发,非洲对于“神”的理解亦可以为欧洲提供借鉴。因此,文明之间理应相互包容和借鉴,没有哪个民族或文明应该受到歧视和否定。
与文明互鉴的思想相对应的一点是,作品以杂糅、含混的文体特点表现出了作者去中心和反权威的思想。“在非洲,小说是唯一一种完全脱离本土模式被引进和强制推行的文学艺术形式”(Dathorne,1974:143)。换句话说,与源于口头、具有表演性质的戏剧和诗歌不同,小说对于非洲来说是绝对的舶来品。彼时欧洲已有大量经典小说作品出现,且已形成稳定的创作标准和权威的批评话语。对于非洲作家来说,英语文学创作本就难以脱离欧洲规范的桎梏,英语小说创作则更是容易落入窠臼,不是东施效颦遭遇嘲讽,就是亦步亦趋难以出新。《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则另辟蹊径,表现出明显不合小说规范的杂糅式特征。伯明翰大学教授斯蒂芬妮·纽维尔(Stephanie Newell)形象地提出,“在海福德的手中,小说犹如一个可以无限扩展的布袋,有关政治和精神的各种思考都可以放入其中”(Newell,2002:136)。这一比喻恰如其分。《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没有完整的故事线索,也不以塑造人物为意,而是将幻想、纪实和议论融为一炉。作者无视小说创作规范,更无意讨好西方文学批评家,只专注于灵活运用各种文体来表达关于种族、政治、宗教、教育等主题的思考。“文学普遍性通过将某种特定文化(在现代语境下,是指欧洲)的价值奉为真理,奉为文学或文本的永恒内涵,助长了强势话语的中心性,黑非洲国家对普遍性的批判无疑就是反文化霸权的努力”(高文惠,2007:110)。含混、杂糅的文体风格是对传统小说规范的反抗,是海福德反欧洲中心论思想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实践。
由于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遭际,黑人与白人的体貌特征不同,非洲与欧洲的文明形态也明显有别。在文明互鉴理念的观照下,人类社会是多元文明的统一体,且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相通性与互补性。欧洲文明不应是中心和权威,非洲文明亦不必自惭形秽或妄自菲薄,这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经殖民主义变异后的“文明”予以批判与讽刺,对黑人民族个性与精神的重建予以深刻思考。
2.0 对文化一元论的批评与反叛
在诠释多元文明相通互补的基础上,海福德颇具隐喻意味地讽刺殖民者“一手拿着杜松子酒瓶,一手拿着《圣经》,极力主张着道德的完美”(57)。实质上,他们所鼓吹的“现代文明”不过是文化一元论衍生出的骗局和谎言,其本质是为了掩盖殖民野心而发起的一场文化攻势。
19世纪末,西方强国相继步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为开辟更多的商品市场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扩张。英国加快侵占黄金海岸的步伐,不仅赶走了荷兰殖民者,还多次发动打击土著阿散蒂王国(Ashanti Empire)的侵略战争。“还在1897年,当英国以黄金海岸殖民政府的名义通过《公有土地法案》,宣布当地‘一切无主之土地’都是‘英王财产’时,很快引起加纳有识之士的警觉与反对”(任泉、顾章义,2010:65)。以海福德为首的有识之士成立“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协会”(the Gold Coast Aborigines’ Rights Protection Society),并于1898年派代表团到伦敦交涉土地问题。③海福德对殖民之前的历史和文化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在他的非虚构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Wehrs,2008:40)。与海福德此前所写的政论文和历史调查相比,小说给予了他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聚焦牧师、官员等不同群体,展现他们在面对种族问题时表现出的言行矛盾,揭穿殖民者营构的宗教骗局与政治谎言。
首先,小说通过两个“宗教之问”讽刺了欧洲殖民者的宗教伪善。夸曼克拉在英国留学期间,向怀特利提出一个大胆颠覆传统的问题:耶稣之母是否有可能是埃塞俄比亚妇女?深谙基督教教义的怀特利立即否定,却含糊其辞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圣经》中“他从一本造出了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使徒行传》17:26)以及“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2:50)④所宣扬的正是种族无差的平等观点。但事实上,白人基督教徒绝对无法接受耶稣之母是黑人妇女。夸曼克拉提出质疑:“说一套、做一套的宗教信仰还值得追随吗?”(18)多年之后,成为殖民地牧师的怀特利再一次面对类似的抉择:黑人和白人能否合葬?他坚决反对黑白合葬的态度直接地表现出了种族主义者的真面目。牧师助理夸乌·拜多(Kwaw Baidu)秉持基督教精神据理力争,却遭到解雇。黑人信徒南希在听说这一事件后对自己所信仰的基督教产生了怀疑,来到怀特利处寻求答案,在信念完全幻灭后猝然死去。
怀特利的两面性充分展现了欧洲人所宣扬的基督教义的虚伪性,而南希之死则象征着芳蒂族的信仰危机。要认识一个民族,先要了解他们信仰的神;同样,要统治一个民族,先要同化他们的信仰。西方殖民者深谙此理,他们向非洲本土传教时制造了一种看似平等博爱的虚假基督精神,实质上暗自将黑人信徒拒之门外。被传教的黑人们放弃了本土信仰,但他们在这样虚伪的基督教中不被承认、得不到真正的救赎,最终陷入了信仰崩溃的危机之中。
除却讽刺殖民者的宗教伪善,作品还展现了黄金海岸民生凋敝的真实状况,揭露了殖民政府当局的腐败与堕落。赛康第(Sekondi)是黄金海岸一个缺水状况异常严重的地区。然而“在塞康第这个备受英属黄金海岸政府宠爱的保护区,还没有像自来水这样的供给……政府当局根本没有想到人是会渴的动物”(54)。火车站是“文明的第一迹象”,但铁路运营秩序十分混乱,这类基础设施实质上是为了方便攫取更多的资源。殖民政府根本不关心人们的生活状况,它的职责是加强对黄金海岸的控制。对此,稍有正义感的政府官员时刻面临着工作职责与内心良知之间的矛盾。官员大卫·麦坎(David Macan)为人正直诚实,他尽力团结当地酋长,在各地区建立学校,希望帮助黄金海岸人民过上更为健康持续的生活。然而,在黑人中备受好评的他却遭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与责骂。麦坎的反思颇具讽刺意味,“他从未想过原来有一个理论上的政策和实际上的政策,后者的目标就是要在埃塞俄比亚国内使埃塞俄比亚人永远为他们的白人保护者和所谓的朋友伐木和取水。这就是他的上级希望他做的事。这样对吗?他能凭着良心来这样做吗?”(83)
与反叛文化一元论的思想相对应的是,海福德的创作语言同样体现了反叛标准英语的自觉意识。“毫无疑问,非洲英语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英国的殖民扩张及殖民统治密切相关”(朱振武、袁俊卿,2019:136)。“由于没有本土书面文学传统可资借鉴,早期的黑非洲文学主要处在对欧洲文学的模仿阶段”(黎跃进,2012:115)。但海福德并不止步于此,他在创作中努力运用民族语言元素,体现了其反叛殖民话语、创立新叙述语言的自觉意识。作者首先是运用英语对本地的芳蒂语进行翻译,将其书面化,如作品中神的名称、诗歌以及方言俗语等就都保留了芳蒂语元素,以此来展现自己民族的个性与特性。另外,海福德有意对不同人物的语体做出区分与保留,如列车上的售票员作为黄金海岸本土人使用的是混杂方言和英语的“皮钦语”(Pidgin),文本中这样的特征随处可见。“他们的作品尽管是用欧洲语言创作的,但从其词汇、句法及特定的语言因素的运用中,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作品中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欧洲国家”(张荣建,1995:80)。后来的非洲著名本土作家如恩古吉、阿契贝等都意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性,并开始用带有本土元素的英语或纯粹的本土语言进行创作。从这一点来说,海福德作为20世纪初期的作家,真正走到了非洲作家的前列,并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努力和尝试。
3.0 黑人民族精神和民族个性的重构
海福德并不是一位只知批判、不知建设的空想主义者。他怀抱对非洲文明与黑人民族的信心,在借鉴多种理论、多种道路的基础上勾勒出民族解放的理想蓝图,指明了现实的道路。
海福德受到当时较为活跃的思想家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1868-1963)、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1856-1915)特别是爱德华·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1832-1912)的影响,在思想的交锋中阐述其自身的政治理念。“布克·华盛顿认为,南部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着贫困、无知和犯罪等问题,这是黑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黑人遭受歧视和被剥夺权利的根本原因”(张聚国,2000:69)。换句话说,布克·华盛顿认为黑人应当远离政治,潜心投入最普通的工作中。海福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布克·T. 华盛顿追求的是促进美国黑人的物质文明”(133)。杜波依斯认为布克·华盛顿的思想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于1903年发表《黑人的灵魂》(TheSoulsofBlackFolk)一书向华盛顿宣战,认为黑人不应当放弃自己的公民权利。他犀利地评论杜波依斯的局限性并指出,“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追求的是在一个不适合民族发展的环境中取得社会选举权”(133)。海福德认为,华盛顿和杜波依斯远离非洲大陆太久以至于丢掉了自己的根基。在对比的基础上,他极力推崇爱德华·布莱登提出的“非洲个性学说”。黑人民族解放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物质的发展,也不在于争取法律地位的平等,而在于非洲个性和民族精神的重建。
在《爱与死亡》一章中,夸曼克拉的灵魂离开了肉体,到芳蒂众神居住的“纳纳穆—克罗姆”(Nanamu-Krome)进行了一次游历。此处,作品借鉴了《天路历程》和《神曲》的叙述框架,并将芳蒂族的文化内核置入其中,表达了作者对善恶的评判、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和对得救道路的思考。
守城的丑陋怪物象征着骄傲自大的欧洲白人。这个半人半兽的怪物曾经是野心勃勃的人类,以为凭借自身的知识和想象就可以进入神的居所。但在这里,自认为掌握了知识就可以为所欲为被视为一种严重的罪孽。他被众神惩罚在城外为凡人指路,一千年不得进入纳纳穆城。这实质上蕴含着作者对于欧洲殖民者的批判。殖民者们自以为掌握了物质和技术就可以肆意操控其他民族,但这种心理显然是霸道和畸形的。
纳纳穆城内景象则展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夸曼克拉突然意识到这群聚集在一起的人代表了天下的每一个族群、民族、种族和国家。这是一群精选的灵魂的集合,这些灵魂在另一种生活中都是谦逊且很好地履行了自己职责的男男女女,仅此而已”(46)。在理想世界中,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得到平等的对待,不同民族的人也可以和谐相处。人们只要拥有谦逊的灵魂和虔诚的信仰就可以得到救赎,不再有人因为肤色被拒之门外。在尘世中的人们如果坚持抑恶扬善,拥有了完美的灵魂和品格,就会在纳纳穆城为自己建起一座神殿。凭借勇气和纯粹的信任,人们可以打破死亡之门,渡过难以逾越之湖进入纳纳穆城,成为真正的神。实质上,海福德的憧憬可以在中国文化中找到共鸣。儒家秉持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宏观理念,正是期望实现协和万邦的理想,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和谐世界。可以说,他的理想与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遥相呼应,具有颇多相似之处。
在理想蓝图的指引下,海福德借鉴不同民族的解放道路,阐明了重构民族精神的现实路径。首先,一个民族必须守护和捍卫自己的文化。他认为,丹麦、爱尔兰和日本在历史上都曾遭到外来民族的侵扰,但却从没有丢弃自己的语言、风俗和制度,都在坚守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来发展自己。相比之下,许多芳蒂族人崇洋媚外、盲目跟风,完全否定本民族文化。埃西·梅努原本是一位淳朴善良的芳蒂族女子,她曾与夸曼克拉一起在月光下唱着传统的歌谣“桑科”(Sanko),如今却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认为夸曼克拉是异教徒和魔鬼;为了庆祝“帝国日”(Empire Day),芳蒂民众穿上隆重的节日服饰、举行盛大的仪式,却全然不知“帝国”二字的背后正是殖民者对他们的控制和剥削;更有“过于精致的非洲绅士们每隔两三年就提起为了防止神经衰弱而要逃到欧洲去的打算”(155-156)。作者痛心疾首地控诉“文明”正在侵蚀黑人民族的本质。
其次,本土化教育是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关键。教育的核心目标在于避免西方文明的荼毒,培养真正的“热带之子”。海福德热情描绘了教育的理想蓝图:应当在远离黄金海岸影响的地方设立一所大学,聘请历史系教授讲述历史知识,尤其着重讲述非洲自身的历史及其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应当聘请教授芳蒂语、豪萨语、约鲁巴语的教授,以复兴本民族的语言传统。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海福德认为,只有真正的本土精英知识分子才能引领非洲走向独立与富强。
海福德的思想具有先锋性和超前性,但同时要看到的是,他依旧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守性和妥协性。“或许是他所接受的法律教育使得他更倾向于制度化和和平的方式……因此他的和平主义只是实用主义”(Ugonna,1977:163)。小说大部分依旧使用标准英语进行创作,其本土价值观和民族主义思想均是借用欧洲文学的框架进行表达。正如很多非洲知识精英一样,海福德这样做当然是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但也表明他依旧寄希望于作品打动欧洲读者,使他们承认非洲文明的平等地位,以此来争取非洲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同时,他对民族独立道路的探索还停留在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培育上,所做出的反思还停留在思想层面上,还没有深入到民众中去。多数普通民众还处在被忽略或忽视的状态,还不知道团结民众的重要意义。这也注定他终究是一位改革家而非革命家。
4.0 结语
作为海福德的唯一一部小说,《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继承作者以往的严谨风格,真实反映了20世纪初黄金海岸的社会面貌以及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思想状态,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历史佐证。但小说的虚构特性使作者得以摆脱严肃文风的桎梏,蕴嬉笑怒骂、憧憬幻想于笔端,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讽刺和反抗。
《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的写作风格与主题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作品的写作风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其他作家。加纳作家弗朗西斯·塞罗米伊(Francis Selormey,1927-1988),塞拉利昂作家罗伯特·威尔斯利·科尔(R. W. Cole,1907-1995)和威廉·法夸尔·佐顿(W. F. Conton,1925-2003)的创作都明显受到海福德自传性写作风格的影响。另一方面,《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后世非洲作家创作的思想宝库”(Gikandi,2003:89),其中所论及的文化冲突、泛非主义、黑人个性等被后来的文学作品反复探讨。科比纳·塞吉(Kobina Sekyi,1892-1956)和海福德都属于接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非洲人,他们的作品都表达了对殖民文化的批评和反抗(Osei-Nyame,1999:137)。阿玛·阿塔·艾杜(Ama Ata Aidoo,1942-)的戏剧《鬼魂的困境》(TheDilemmaofGhost,1965)以及科菲·阿翁纳(Kofi Awoonor,1935-2013)的小说《航海者归来》(ComestheVoyageratLast,1992)皆对泛非主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与思考。
《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于历史纵深处高擎一盏思想的明灯,为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区域文化建设指引了方向。作品所宣扬的政治理念成为西非国民大会建立的思想基石;非洲个性以及相关教育思想成为非洲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作品为处理不同文明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紧密维系在一起,思考不同文明间的关系问题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与此相关的启示意义不应忽视。作品中的文明交互思想揭示出,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中心文明或者权威文明,不同文明必须通过彼此之间的相通性与互补性实现平等交流和对话。这是一部仍然具有较强当下意义的作品,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注释
① 曾为英属黄金海岸(The Gold Coast)殖民地,1957年取得独立,更名为“加纳”,1960年成立“加纳共和国”。
② 引文出自J. E. 凯斯利·海福德:《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陈小芳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③ 海福德围绕土地问题创作了《西非土地问题真相》(TheTruthAbouttheWestAfricanLandQuestion,1898)和《黄金海岸的本土制度》(GoldCoastNativeInstitutions:WithThoughtsuponaHealthyImperialPolicyfortheGoldCoastandAshanti,1903)等,均产生较大影响。
④ 引文出自《圣经·中英对照》(中文:和合本 英文:新国际版),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7年,第242页,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