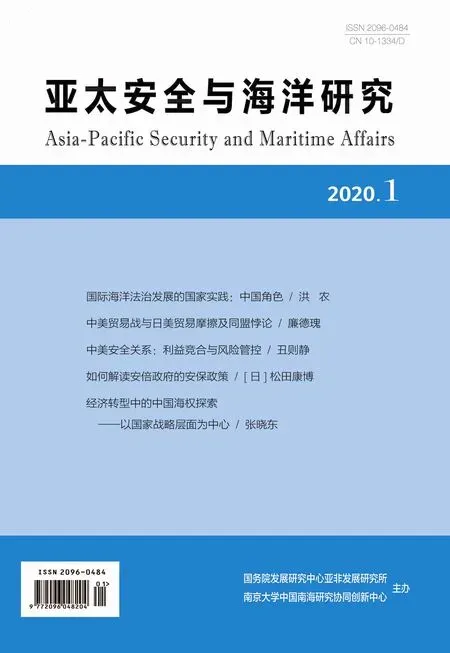如何解读安倍政府的安保政策
[日]松田康博 著 张瑞婷 译
[内容提要]分析安倍政府强化安保政策的背景和方向,可以得出中国国内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并无说服力的结论。日本战后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得以集中力量实现经济发展。将一战后的德国同二战后已发展了70年的日本比较没有意义。日本首相和内阁受法律和政治的多重制约,即使怀揣极端政治理念的政客上台,其诉求也必定不会实现。受财政和经济状况所掣肘,日本大规模扩充军备或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既不合理也无可能。安倍强化安保政策的背景,非源于观念上的军国主义思想,而是为应对周边安全环境变化借势而行,从而在原已成型的安保构想基础上,成功改变日本的安保政策。
2018年10月,日本安倍晋三首相正式访华。2019年6月,在日本大阪召开G20峰会之际,习近平主席表示将于2020年春天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由此可见日中关系将要“完全回归正轨”。而这一点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对“安倍政府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的担忧已经消弭。原因在于,习近平主席应该不会去访问一个正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国家。那么,这是否代表着安倍政府本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呢?
笔者认为,其实更多还是因为中国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的对日认知发生了变化。若单从日本方面观察,很难说安倍政府的性质在短期内有何重大转变。且安倍上台之初,中国国内出于种种因素,对安倍政府抱有极大不信任感。像后文将提到的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日本国内对安倍的批评声音十分强烈,甚至在2019年的今天依旧争议不断。而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在看过日本国内对于安倍的批判、听过访华的日本学者对安倍的批驳后,自然是不会提出“中国应当放心与安倍政府来往”的政策建议的。
但中国若对日本等重要国家的政权性质产生误判,对对方怀有过度警惕,就很可能错失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机会。在西方国家中,对自己国家的政府进行公开批评是在野党、媒体以及知识界的责任,这一现象也是日本的常态。但这一点却会使得我们所见到的西方国家的政治言论内容大多都是在指责政府。如果中国不能跳出这一思维,完全采信这些批评言论,可能导致在重要判断上出现失误。在对外政策的判断上,比起关注该国政府在国内遭到何种褒贬,更重要的是准确判断这届政府能多大程度上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贡献。
笔者很早之前就曾指出,安倍政府具有稳定日中关系的意向,日中关系或将在安倍时期出现稳定趋势。(1)Yasuhiro Matsuda,“Ameliora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t the APEC Summit?: Driving Forces,Opportunities,and Risks of an Abe-Xi Meeting,” An Asia Pacific Seminar,East-West Center,Washington,D.C.,September 17,2014,http://www.eastwestcenter.org/events/amelioration-the-sino-japanese-relations-the-apec-summit-driving-forces-opportunities-and-ris. Yasuhiro Matsuda,“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More Stable than They Seem,”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February 28,2018,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events/sino-japanese-relations-are-more-stable-they-seem[2019-08-18].如何正确理解日本的政权性质,不仅是中国也是东亚各国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对中国学者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观点进行归纳梳理,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对日本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变化和政府的相应对策进行阐释;最后,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中国国内常见的日本“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中的合理以及不合理之处进行解读。
安倍首相在本文写作之时尚在任内,且任期很可能持续到2021年乃至更长。但是算上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2006—2007年),安倍政府已经有历时七年以上的政策成果,因而已可以从中总结出一定特征。希望本文能够对中国如何处理安倍时代及“后安倍时代”的日中关系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一、“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的三种类型
笔者观察,中国国内所指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中,既有同一学者的主张同时包含这三种类型,也有不同学者各自强调其中的一个重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右倾化”的最终落脚点是“军国主义复活”,尽管两者在概念上大相径庭,但还是应放在同一延长线上结合分析。
第一类是(A)“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这种情况下的“左”,代表的是经济繁荣稳定、主张和平主义,对华态度友好的日本社会;反之,“右”则是因经济萧条引发社会动荡,并伴有对外扩张的好战倾向,对华采取敌视态度的日本社会。
例如,吕满文提出,日本政府2012年“购岛”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活军国主义。他认为,军国主义之所以能在日本存在,主要源于由于日本战后未废除天皇制,以及美国出于冷战考虑,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残留。他还指出,自近代丰臣秀吉之后,日本“好战成性”,其“侵略的基因”已经渗透到军国主义的骨髓之中。(2)参见吕满文:《解析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原因》,《殷都学刊》2016年第4期,第41—46页。应霄燕认为,有三点因素导致2012年“购岛”问题逐步恶化:一是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的民主改革不够彻底,二是日本政府和社会在历史认识上缺乏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和认识,三是因长期经济低迷使得日本执政者希望以领土问题转移民众视线。(3)参见应霄燕:《警惕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发展与危害》,《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11期,第58—59页。谢卫军则将2012年的日本与德国纳粹作比较,认为“一战后的德国命运与二战后的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战败国,战后经济政治都面临着严重困境”,并认为日本经济增长乏力是军国主义得以复活的原因。(4)参见谢卫军:《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德国纳粹崛起分析当今日本军国主义的危险性》,《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23—24页。孙桦、王侠认为,对外扩张的战略选择是日本作为岛国的“地缘文化之天然本性”。(5)参见孙桦、王侠:《剖析日本国家战略右倾化的文化根源》,《海军工程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31—32页史式在文章中断言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堡垒”。(6)参见史式:《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与靖国神社》,《文史杂志》2014年第2期,第27页。由此可见,社会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形势的变化造成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而文化决定论者则倾向于,日本未来只能日益走向“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方向。
第二类为(B)“政治层面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持这种观点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日本政治中,自民党右派的政治理念已占据主流。在这一情况下的“左”,指的是坚持现行日本宪法,即使修宪也要维持住基本的原则,并认为坚持对过去的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殖民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谢罪的这一立场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右”则是主张当前的日本宪法为美军占领下的“强迫宪法”,要通过修宪让自卫队成为“军队”,在宪法中写明天皇为国家元首,并认为应当削弱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同时,认为日本在过去战争和殖民中并非全然恶行,尤其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应当由国家出面举行对战死者的追悼仪式。
例如,解学诗强调,1955年成立的自民党在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上随着时间推移而日趋右倾化,就连普遍认为是自由派的民主党(2009—2012)也与日本右翼同流合污,并指出安倍政府正顺着这股潮流推行右倾化。(7)参见解学诗:《评战后日本政府右倾化政策和发展道路》,《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第102—105页。柯劲松则关注安倍个人的历史观和战争观,主要列举了安倍就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在国会上宣称“理应向为国牺牲的英灵表达敬意,我们的阁僚不会屈服与任何威胁”,以及针对1955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就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和歉意的“村山谈话”(8)「村山富市内閣総理大臣談話」、日本国駐華大使館、1995年8月15日、https://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2019-08-18]。,安倍声称“安倍内阁不会全盘继承村山谈话”,而对于1993年日本承认慰安妇与日军有关并对此表示反省与道歉的“河野谈话”(9)「慰安婦関係調査結果発表に関する河野内閣官房長官談話」、外務省、1993年8月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kono.html[2019-08-18]。,安倍同样持否定态度。(10)参见柯劲松:《安倍晋三历史观与战争观探源:基于家族影响和从政经历的视角》,《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16—117页。此外,廉德瑰指出,新兴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对安倍具有较大影响,认为“日本会议操纵安倍晋三从事右倾政治活动”。(11)参见廉徳瑰:《日本会议与日本右倾政治分析》,《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第46—48页。彭光谦甚至断言:“安倍决意最后一搏,力图挣脱宪法约束,使日本再次成为可以用战争手段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国家。”(12)参见彭光谦:《安倍复活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为哪般?》,《军事文摘》2017年第13期,第29页。上述这些观点,均认为日本政治正面临整体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而安倍就是其中最大的右翼分子。
日本国内同样也有类似声音,中北浩尔就认为,从自民党修宪草案的变化可以看出自民党的观念逐步右倾化。在过去的自民党内部,自由派对宪法修正案的影响力较强,在2005年自民党执政时期所制定的宪法修正案中,除提出将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之外,其他方面较原宪法没有较大变更。但2012年,作为在野党的自民党的修宪提案则变得极为激进,如提出应在宪法中写明天皇为国家元首,并削弱基本人权,以及自卫队改建为“国防军”等。(13)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央公論社、2017年、282—286頁。中北将之视为自民党特别是在野时期政治立场右倾化的明证。
第三类是(C)“安保政策层面的右倾化论”。这种情况下的“左”,所指的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和武器共同研发,并维持对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右”则是增强进攻力量,放开武器出口和共同研发,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强化日美同盟。而更为极端的“右”,则指的是日本应废除日美同盟,进行核武装,谋求国防自主化。
例如,袁扬针对安倍在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并解禁集体自卫权一事,认为“至少未来在与我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朝鲜半岛、台海以及南海局势发生变化时,日本武力介入的现实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并指出“解禁为日本‘军事正常化’提供了新支点,大规模扩军备战将成为可能”。(14)参见袁扬:《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国军事科学》2016年第6期,第120页。军事研究专家的一大特点,是对日本如何强化日美同盟以及新防卫计划大纲所显示的方向性等具体政策方面的担忧和警惕更为明显。(15)参见李大光:《安倍内阁给亚太安全带来阴影》,《国防科技工业》2013年第2期,第66—67页。张晓刚和张昌明就对日本政府《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防卫计划大纲》中的“对敌基地实施攻击的能力”的相关内容和明显针对防范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而强化的警戒监视能力以及“强化弹道导弹防卫能力”等与提升防卫能力相关的具体政策十分警惕。(16)参见张晓刚、张昌明:《安倍晋三新政权在外交与安保领域上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大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70—71页。
“正常国家论”(17)参见周永生:《日本政治、社会右倾化问题探讨》,《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3期,第28页;袁扬:《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国军事科学》2016年第6期,第119—120页。则是从(C)类型中所延伸出的一个分支。战后日本在安全问题相关的政策手段上进行了自我限制。“正常国家论”这一论调,最初是由原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其著作《日本改造计划》(18)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中所提出,具体指的是要去除这种仅加诸日本的政策限制,使日本变为“正常国家”。小泽后来一直担任在野党的领导人,他的这一说法在日本已几乎无人提起,但在中国学界尚有关于此观点的诸多讨论。
综上所述,不同的学者对于“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的分析重点虽有不同,但无论是(A)类型的“社会和文化”、还是(B)类型的“政治”或(C)类型的“安保政策”,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同一种模式,即这些分析多从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会成为中国“现实的军事威胁”的这一模式来展开讨论。
二、如何合理解释“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
中国国内也存在反对用“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解读日本的声音。王占阳就认为,日本不可能再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并指出原因有四:一是“日本的和平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军国主义重新成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二是“和平主义与民主制度相结合,使军国主义更加成为不可能”;三是“现代日本经济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侵略战争”;四是“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财政基础”。(19)参见王占阳:《日本已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环球网,2014年10月9日,http://opinion. huanqiu. com/opinion_world/2014-10/5160295.html?agt=15422[2019-08-18]。笔者赞同他的这一分析,并持有相似观点。下文就尝试从三方面来对中国国内常见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进行辩驳。
(一)根植于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和维持现状的意向
首先来看(A)类型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是否接近日本社会的现实?自1945年后,享受了近80载和平年代的日本国民,甚至有“和平呆子”之称,对外交和安保问题缺乏兴趣。日本广播协会(NHK)广播文化研究所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最希望政府重视的政策课题”以及“内阁应当致力应对的政策课题”等问题的回答中,排名靠前的几乎都与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有关,选择外交和安保以及修宪的人数通常只占不到10% ,几乎未出现超过20% 的情况。(20)「政治意識月例調査」、NHK放送文化研究所、https://www.nhk.or.jp/bunken/research/yoron/political/2019.html[2019-08-18]。
以NHK广播文化研究所2013年8月的舆论调查结果,可以解读当前日本社会的现状。在2013年这一年,日本除面临朝核危机外,还与中国、俄罗斯以及韩国因领土争端关系急剧恶化。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68.8% 的受访者都抱有“日本有被卷入战争和冲突的危险”的忧虑。但是,如果日本偶然卷入冲突,选择“立即反击”的人数只占13% ;在“如果现在日本遭到他国侵略发生战争,你会如何做”这一问题上,仅有6% 的受访者选择“亲自上阵杀敌”;赞成强化自卫队能力的人数占29.6%,而54.8%的受访者赞成维持自卫队现状;49.5% 的受访者赞成维持日美同盟现状,赞成强化日美同盟的人数比例则仅有26.3% 。(21)「2013年8月平和観についての世論調査 単純集計結果」、NHK放送文化研究所、2013年8月24日、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30815.pdf [2019-08-18]。
从上述舆论调查数据可以清晰看出,(A)类型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几乎完全没有说服力。不同于老一辈们对战争记忆犹新,如今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口占据了较大比例。因此,基于自身经历的反战主义与和平主义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弱化,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尽管如此,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教育,仍决定了大多数日本国民并不热衷战争,对扩充军备也同样持反对态度。
此外,针对安倍首相于2013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虽然调查显示有44% 的民众予以认可,但持反对态度的民众则占比更高,达到52% 。而认为首相今后应当继续进行参拜的比例仅占27%,认为不应继续参拜的民众则占38% ,另有30% 的民众的态度比较模棱两可。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日本国民虽然认为应当对战争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但考虑到中韩两国的反对态度,超过半数的民众还是认为应当停止每年的参拜行为。(22)「安倍内閣『支持する』54%『支持しない』31%NHK世論調査」、NHKニュース、2014年1月14日。
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与内阁支持率关系不大。在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曾是一种惯例仪式。即使鸠山由纪夫在选举中提前表示本人及阁僚都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其就任首相后的支持率依旧高达72%。(23)「政治意識月例調査2009年」、NHK放送文化研究所、https://www.nhk.or.jp/bunken/yoron/political/2009.html [2019-08-18]。小泉纯一郎首相连年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在选举时已有公约承诺在先。而安倍则并未在选举时作出将在首相任期内进行参拜的承诺,且安倍虽在2013年12月进行了参拜,但其支持率几乎没有任何变化。(24)「靖国参拝でも内閣支持率1ポイント増 世論調査で55%」、『日本経済新聞(電子版)』、2013年12月29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2901K_Z21C13A2000000/ [2019-08-18]。
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我们很难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军国主义复活这二者间找出因果关系。如果首相参拜与军国主义复活之间真的有所关联,那么可以说中国过去还曾与军国主义化的日本联系密切。因为无论是推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首相,还是对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福田赳夫首相,都曾在其任期内数次参拜靖国神社。人们通常说的靖国神社内供奉有甲级战犯一事,其实始于1978年(被报道出的时间是1979年4月),此后日本首相仍然继续参拜。而曾十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曾根康弘,在其任内依旧保持了大体良好的日中关系。1985年中曾根将参拜一事官方化后,才真正让首相参拜成了日中间政治争议焦点。在此之后,日本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次数才开始大幅减少。(25)一谷和郎「第二章 靖国神社参拝問題」、家近亮子·松田康博·段瑞聡編著『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晃陽書房、2007年、40頁。
(二)自民党政权难以“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的原因
(B)类型的“政治层面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的共同特点,是几乎都未将日本内阁及首相所面临的制度性限制因素考虑在内。换言之,即前文列举的大多数讨论的前提,都是认为领导人和政党性质能极大左右政府行为,在言行举动上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
例如,虽然不少研究都在讨论自民党的“右倾化”,但自民党在野时期或选举时期提出的主张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看其在赢得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首先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都必须暂缓搁置自身此前主张,并在继承以往政府政策和基本立场的基础上着手运营政权。其原因如下:
第一,日本修宪的门槛很高。要进行修宪,必须由众参两院2/3以上的国会议员发起动议,在国民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以上的投票支持才能够成立。因此,尽管自民党从成立以来一直主张自主制定宪法(现在称为“宪法修正”),但目前为止的日本宪法仍然只字未改。
在自民党修宪的理由中,还包含了一种政治手腕和技巧的考量。自民党抛出修宪的话题,可以有效离间混合了护宪派与修宪派的在野党势力,破坏在野党的团结。这一情况在今天也是如此。暂且不论修宪能否真正实现,只要自民党继续主张修宪,就能争取到保守派的支持,而保守派正是自民党的支持基础。自民党即使无法真正达成修宪,只要继续提出这一主张,就能够获得对自身有利的政治成效。
就算万一自民党达成修宪,其内容也必须能够在国民投票中赢得多数国民赞成,这就使得激进的修正案很难在该条件下获得通过。事实上,安倍目前所提交的宪法第九条修正案内容,不过是将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自卫队添加进宪法。(26)「『第9条』について意見交換」、自民党憲法改正推進本部、2017年6月21日、 http://constitution.jimin.jp/news/2017/000026.html[2019-08-18]。由于目前日本学界仍有一类观点认为日本拥有自卫队是违宪,因此安倍才欲通过将自卫队明文“入宪”来打消这类疑义。尽管如此,如今的日本民众对修宪的支持率依旧不高,特别是对于规定了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战力的宪法第九条,还是更倾向于维持原状。(27)根据2018年4月的调查数据,认为有必要进行宪法修正的民众数量占29%,赞同宪法第九条的人数比例达到70%。对于安倍所主张的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的相关修正案,有31%的人表示赞成,23%表示反对,两者都不是的人数占40%。参见:「世論調査 憲法に関する意識調査2018」、NHK NEWS WEB、 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kenpou70/yoron2018.html[2019-08-18]。
安倍的宪法修正案,与当初自民党在野时期(2012年)所提出的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的修宪草案已大相径庭。纵观美国也是如此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所呈现出的对华严厉态度,与其当选后中美关系大幅改善的现实情况截然相反。政党在野时,往往提出极端主张,一旦上台执政便将这些主张收回,这一情况在西方国家中屡见不鲜。自民党的宪法修正案,同样是自民党在野时为夺回政权炒作话题的手段,是为确保获得保守选民支持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第二,日本政府受法律的制约。日本是立宪制国家,即宪法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国民权利,限制政府行为。内阁既要维护宪法,也要维护现有法律制度。若想对宪法或法律解释做出变更,必须就此进行公开讨论,并在国会答辩中接受质询。由于国会答辩包含法律解释的性质,因此必须应对得当。而日本国会的所有讨论内容都被记录在案,并予以公开,以便在将来作为参考。(28)日本往年所有国会审议内容,参见:「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http://kokkai.ndl.go.jp/。正因为如此,政府在推行决策时必须时刻考虑与以往见解的一致性。如果社会怀疑政府有违反法律、损害国民权益的行为,政府也会面临遭国民起诉的风险。
第三,首相难以改变历届内阁继承的立场。前文提到安倍虽曾否认“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但在夺得政权不久之后,却表示会“全部继承”这些内容。安倍质疑东京审判结果亦如此。安倍在2015年的“战后70周年纪念谈话”中,通过最后将关键词落在“发动侵略”、“殖民统治”、 “反省”和“致歉”这四点上,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来自中国和韩国的批评和反对。(29)「内閣総理大臣談話」、首相官邸、2015年8月14日、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814danwa.html[2019-08-18]。所以说,想改变历届内阁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并非易事。
第四,政府内外存在牵制者和挑战者。自民党总裁任期为三年,总裁会定期受到来自党内人员的挑战。无论是在国会质询中应对不力,还是遭到媒体舆论强烈批判,或是爆发丑闻,都会拉低内阁支持率。一旦内阁支持率下降,政权的向心力就会弱化。因为低支持率会引发对下次选举中自民党的议席大幅减少的担忧。参议院每六年进行一次超过半数的改选,而众议院任期虽为四年,但在任期结束前经常会被解散,这就代表着自民党政权每一到两年就要面临一次大规模的选举。
如此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势力格局:一旦首相和内阁出现失策行为,现任国会议员出于解散议院和丢掉政权的担忧,就会要求首相下台。首相则必须时刻在这种紧迫感下运作政权。而执政党即便当下维持住了过半数席位,但接下来的选举中如果并无胜算的话,政权也会急速出现“跛鸭效应”。这样一来,日本的首相受党内、国会和媒体的三方牵制,加之选举的多重压力,难以轻易出台不受欢迎的政策。
此外,当前的自民党政权是自民党与公明党成立的联合政权。由于联合政权要靠对方的合作来赢得选举,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对自公两党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公明党的支持基础主要是佛教徒,相比自民党而言,公明党的安保政策更倾向于温和的“鸽派”,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自民党采取更为激进的“鹰派”政策,而自民党对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变更内容也须在公明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否则将会难以施行。
(三)日本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决定了“军国主义政策”难以推行
除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制约之外,财政和经济因素决定了无论哪一方势力掌握政权,日本政府都难以实施“军国主义政策”。
第一,日本财政方面限制极大。即便修宪获得通过,日本对外行使武力的法律门槛下降,但日本自卫队目前仍然是以防卫为主的装备体系。日本自卫队没有装备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航母和核武器等进攻性武器,明确表示“不做军事大国”。如果日本政府欲强化军国主义政策,就必然要提升自卫队的进攻能力,推行全方位的军备扩张。但日本并不具备这项财政实力。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236%(2018年),在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中情况最为恶劣。(30)「債務残高の国際比較(対GDP比)」、財務省、http://www.zaisei.mof.go.jp/pdf/04-k02.pdf [2019-08-18]。
因此,日本政府要强化自卫队装备,就不得不在有限的预算中增加防卫支出。然而,增加防卫预算很难在选举中扩大得票。2019年3月,日本政府预算尽管达到了101.4571万亿日元,但防卫预算在这一年才终于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预算高达34.593万亿日元。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用于社会保障相关的费用预算是防卫预算的五倍以上,受国内少子老龄化影响,这项开支每年都会增加数千亿。日本执政党若在选举中败北就会丢失政权;若为增加防卫预算而压缩社保开支,不顾持续增加的老年选民人数,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安倍防卫预算“六连增”,主要得益于“安倍经济学”的成效。政府税收增加,使得总体预算上升,防卫费用得以水涨船高。尽管如此,日本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少子老龄化社会,要在财政支出上实现大幅军扩的难度可谓一目了然。
第二,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日本若想发展经济,必须绝对避免发生对外战争。假设日本政府在财政上甘冒大险、实现军扩,是否就意味着日本就会发动对外战争呢?要知道,战后支撑日本经济的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即美国霸权保护下的和平环境以及以欧美市场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自由贸易体制。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实现繁荣增长,有赖于这些战争远离日本本土,日本得以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为美军提供后方补给的机会扩大生产力。然而,由于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特别是1970年之后,全球任何地方爆发战争都会导致石油市场和外汇市场动荡不安,对日本经济也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自身深刻参与世界经济之中,更加清楚战争损害经济发展的道理。二战后的日本则更早融入了世界经贸体系,战争会破坏经济发展已是日本国民的共识。其中最需要规避的,就是同周边地区爆发冲突。举例来说,当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的日中贸易额达到3537.7293亿美元。(31)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海外調査部中国北アジア課「2018年の日中貿易」、2019年3月、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_Reports/01/275fdcb1f46d0f9f/20180049.pdf[2019-08-18]。日本如果要对中国发动战争,所遭受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更兼之中国本身为核大国之一,与中国进行军事对峙更伴随巨大风险。若非要说日本欲与一个拥有核武、对日存在巨额贸易关系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生战争,对日本到底有何利益可言呢?(32)王占阳:《日本已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环球网,2014年10月9日,http://opinion. 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4-10/5160295.html?agt=15422 [2019-08-18]。只有对华维持稳定与和平友好的近邻关系,才真正有利于日本今后的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见,日本无论是谁上台执政,受政府财政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在安保政策上都会呈现较强的连贯性。即便有哪位政治理念特殊的政客当上了首相,日本在政策层面也难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一直主张“自卫队违宪论”的日本社会党党首村山首相,在上台执政后也表示认可“自卫队符合宪法”,并称“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可见,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日本首相的首要任务都是维护政权稳定性和政策连贯性。即使想要作出改变,也要从长期执政的考虑出发,在取得民众支持、履行必要手续的基础上加以实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三、日本安保政策变化的原因:安全环境的日益变化
前文虽列举了数项日本安保政策较难出现改变的原因,但事实上,日本的安保政策仍在持续变化发展。笔者认为,造成日本安保政策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日益变化。
(一)朝鲜的核开发与导弹技术的增强
自朝鲜1993年1月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并被曝出擅自进行核技术研发以来,日本就一直处于严峻的安全威胁之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就是联合国军相对安全的后方基地。而如今朝鲜的核武器与弹道导弹所带来的威胁日益增加。朝鲜已于2006年10月、2009年5月、2013年2月、2016年1月和9月、2017年9月分别进行六次核试验。据称,朝鲜在核弹头小型化方面已经取得进展。这些核试验的开始时间正与安倍第一次上台后的时期完全重合。安倍政府不得不全力应对来自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
另外,在核弹头运载手段上,1993年5月朝鲜成功进行了射程涵盖日本的准中程导弹(MRBM)发射试验,即通常所说的“大浦洞”导弹。在此之后“大浦洞”导弹被装备于部队,截至2018年,朝鲜人民军总共配备有数百枚该导弹。(33)「日本射程ミサイル、数百基 首相が北朝鮮の脅威強調」、『日本経済新聞(電子版)』2018年2月14日、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26892660U8A210C1PP8000/[2019-08-18]。一旦朝鲜具备了核武器小型化能力,那么日本将直接暴露于朝鲜的核威胁之中。而且,据称,朝鲜目前正在进行生物和化学武器的研发(34)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平成30年版〉』、日経印刷、2018年。,今后很有可能利用导弹来搭载生化武器。
不同于朝鲜战争时期,今天的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战争,日本将直接暴露在朝鲜导弹射程范围内,成为直接面对威胁的前线。日本除了面临朝鲜“强军”的威胁外,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日朝之间仍存在“绑架问题”,更遑论建立政治互信。朝鲜还一直对日本参加基于联合国决议的对朝制裁予以强烈反对。这种局面下的日朝两国,想就解决问题开展双边对话沟通可谓难上加难。
2018年6月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委员长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谈以来,截至2019年8月,美朝之间已进行了三次首脑会晤。在此期间,朝鲜暂停了中长距离导弹发射试验和核试验等高烈度的军事挑衅。但另一方面,朝鲜也仅爆破了一处核试验场,完全没有弃核的打算,核开发仍在继续进行。简而言之,朝鲜核开发及导弹研发的这一情况完全没有改变,很难说朝鲜未来某天是否会再次针对日本发出军事挑衅。(35)「北朝鮮の核開発、民間施設を利用―国連報告書『無傷で継続中』―」、共同通信、2019年2月17日、 https://this.kiji.is/469742782459708513[2019-08-18]。
(二)中国的崛起与对外行为的强硬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伴随对外贸易额的加速扩大,中国开始走向崛起。中国的崛起体现在方方面面,而在安全领域的存在感和实际行动同样不容忽视。
将日中两国的国防预算统一换算为日元后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若从日本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日本的心态已不言自明。中国政府公布的国防开支自1989年起几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2007年起中国的国防预算开始超过日本,在十年的时间里增至日本的近四倍。(36)「平成31年度防衛関係予算について」、『防衛白書』、防衛省、2019年3月、https://www.mod.go.jp/j/yosan/2019/kanren.pdf[2019-08-30]。目前,中国的国防开支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而如果在此期间,日中关系能够保持良好,那么日本对于这种变化大概不会感受到威胁。但事实恰恰相反,近十年间中国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日中关系同样处于低谷状态。
即使一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只要该国在行为上没有变化,那么其对地区影响的改变仍十分有限。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的行为没有实质性变化,中国的崛起对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举例来说,即使中国解放军和海上执法机构等部门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频率在“量”上有所增加,也可以视为国家成长与发展过程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的海军舰艇经过日本西南诸岛进入西太平洋的活动增多,以2008年为契机迅速增加,2013年到达顶峰,之后则维持在每年12次到15次之间。(37)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平成30年版〉』、日経印刷、2018年、106頁。
从日本航空自卫队针对东海上空出现的中国军机而采取的紧急升空次数变化,可以看出,2010年以后中国军机紧急升空的次数呈现显著增长。(38)防衛省「中国情勢(東シナ海·太平洋·日本海)」、防衛省、2019年4月、https://www.mod.go.jp/j/approach/surround/pdf/ch_d-act_201904a.pdf[2019-08-18]。从这一数据能够确认,自2010年起中国空军飞机在东海上空的活动频率有所增加。但“紧急升空”其实是为防范侵犯领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大部分情况都到不上侵犯领空的程度。因此,比如像2012年12月中国军机飞临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上空时,虽然过去针对这种状况无需做出反应,但日本航空自卫队出于对上述情况的“忧虑”,仍有可能决定派军机紧急出动。此外,日本划定的防空识别区对于中国来说范围过大,并与中国在2013年11月划设的防空识别区范围多有重合,同样会导致日本自卫队紧急升空的可能性增加,虽然自卫队对紧急升空与否的判断含有一定主观因素。
上述两种情况是中国的对外行动在“量”上呈现扩大化的案例。然而,中国的行为不仅在“量”上有所增加,更发生了“质”的变化。2010年9月“撞船”事件以来,特别是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购岛”后,日中关系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此后,根据日本政府的报告,出现了中国海监飞机飞临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上空(2012年12月)、海军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2013年1月,中方予以否认)等种种“危险行为”。此外,2013年5月有不明身份(媒体推测为中国所属)的潜艇曾四次进入西南诸岛周边毗连水域潜航。在紧张形势尚未平息的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在东海划设包含钓鱼岛周边空域在内的防空识别区。之后,又出现了中国军机“异常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2014年5月和6月,中方予以否认)的事件。
但在2014年11月,APEC峰会在北京召开之际,习近平主席同安倍晋三首相进行首脑会谈后,上述的“危险行为”几乎再未出现。因此,可以推断,日中关系的恶化与改善,与中国对外行动的强硬化和平静化确实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
与上述“危险行为”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是中国公务船进入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海域及毗连水域的次数变化。(39)「尖閣諸島周辺海域における中国公船の動向と我が国の対処」、海上保安庁、http://www.kaiho.mlit.go.jp/mission/senkaku/senkaku.html[2019-09-08]。除去以往种种例外情况,中国的类似行动最初始于2008年12月。2008年日中关系尚且良好,日本不可能先行挑衅。在此之后,以2010年9月“撞船”事件为标志,日中两国进入对峙状态后,中国方面的政府公务船几乎变为定期进入周边毗连水域,并且数次中就会有一次进入12海里海域范围内。可以推断,中国的公务船是借此来试探日本的反应。以2012年的“购岛”事件为标志,中国公务船经常数艘同时进入毗连水域,并反复进出12海里海域范围内。这种危险接触行为在2013年夏天之后逐步减少,此后维持在每月三次的大致频率。
对于日中关系的恶化,毫无疑问日中双方都有责任。在中国看来,日本是同美国一道在战略上抗衡中国的国家。并且,在领土问题上,中国似乎也将日本视为主动“挑衅”的过错方。但在日本看来,中国才应该是正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国家。
(三)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
随着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日益恶化,日本政府开始在外交上努力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承诺。虽然美国目前仍是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大国,但其相对实力正在逐步下降。
日本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的担忧早已有之。奥巴马政府力推“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举动,正是针对这一趋向所采取的补救措施。(40)森聡「オバマ政権のリバランスと対中政策」、『国際安全保障研究』第41巻第3号、2013年12月。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这种倾向开始加速。一位难以理解同盟国重要性的美国总统的出现,对日本无疑是一种巨大打击。有报道称,特朗普曾向其亲信透漏出日美同盟不利于美国,并可能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想法。(41)Jennifer Jacobs,“Trump Muses Privately about Ending Postwar Japan Defense Pact,”Bloomberg,June 25,2019,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6-25/trump-muses-privately-about-ending-postwar-japan-defense-pact[2019-08-18],accessed on August 18,2019.从特朗普所采取的弱化美欧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的政策来看,他的这一想法并非信口开河。
因此,在日本看来,当前日本面临安全环境不断恶化、最为仰仗的日美同盟的信赖度不断下降的局面。当然,这些还要看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是否能够继续获胜,以及美国对日美同盟的轻视到底是一种长期趋势,还是仅为暂时性现象。
四、安倍政府的现实主义安保政策
即使日本政府已认识到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逐步恶化,为此必须强化日本的安保政策,但正如前文所述,想要实现这一点非常之难。与大多数保守派政治家一样,安倍晋三本人也极力反对现行日本国宪法中的“放弃战力”以及作为该项解释的“不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内容。(42)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社、2006年、123—134頁。安倍政府正是在面临上述课题,或者说以此为契机的情况下,在原有安保构想的基础上,以小步慢行的方式,逐渐改变日本的安保政策。
(一)经济政策与安保政策的相互作用
安倍政府的目标,是以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为抓手,强化日本自身实力。具体内容为:振兴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放宽应对东亚地区严峻安全环境的法理限制以及强化自卫队和日美同盟。
日本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与之配套的日元汇率贬值与积极的财政支出是安倍经济学的最大特色。这一政策使得日本股市大涨,日经指数从民主党时期的平均7000余点,攀升至2万余点。这意味着日本股市在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上涨了3倍,日本2019财年的预算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大关,创历史最高纪录。通过给民众带来耳目一新、改善经济的印象,安倍政府收获了巨大成功。而安倍的超高支持率也正是来源于此。目前为止,包括2019年7月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在内,二次上台后的安倍政府已经在众参两院选举中取得了五连胜。
安倍政府的安保政策制定过程的一大特点,就是先通过推行有效的经济政策来维持较高支持率,在此基础上再行推进不受民众欢迎的安保政策。
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内阁决议案”和“新安保法”以及“修正刑法”,都是不受民众欢迎的。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国民在安保方面维持现状的意愿较为强烈。另一方面,这些法案和政策更遭到了自由派媒体的强烈反对。如果政府要强化保密规则,媒体的情报来源就会受限。而集体自卫权一旦被解禁,自卫队的行动范围就会扩大,仅这一点就提高了日本卷入国际纷争的可能性。2017年的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即所谓的“共谋罪”法案,指的是即使没有实际犯罪行为,在合谋犯罪阶段也可能会遭到逮捕和处罚。这些内容虽有助于强化日美同盟和打击恐怖主义,但却是对刑法内容的大幅改变。出于这些担忧,自由派媒体对安倍政府以上政策和法案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那么,安倍政府究竟是如何达成这些变革的呢?
日本政府的预算主要基于上年1—12月的税收,在当年的1—3月的例行国会上进行制定。而上述这些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法案,基本没有任何一项是在预算制定期提出的。因为政府必须极力避免在野党反对,导致耽误财政预算通过。安倍通过这些安保相关决议的时间,都避开了1—3月的预算制定期。
并且,日本还会举行定期和不定期选举。参议院每六年进行一次超过半数的定期改选。众议院尽管为四年任期,但在期满前可能会由首相择机宣布解散,提前进行选举。除避开众参两院选举时期之外,还要避开地方自治体选举集中的时期。在这类选举之前,敏感而不受欢迎的法案很难获得通过。此外,政治丑闻同样也会导致支持率下跌。安倍会事先看准时机,避开会因提交敏感法案和政策引发支持率下跌的时间段,选择年末年初的假期以及暑期等时间,趁选民的关注点转移之际,适时推行这些不受民众欢迎的政策决议。
可见,安倍政府是一个具备灵活政治手腕的政府:先通过经济政策拉高支持率,再择机调整国会与选举日程,以保证不被民众和媒体认可的安保政策得以通过。如果能够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安倍政府,就不难理解当前日本所发生的改变。
(二)安倍政府安保政策的特征
由于一国国防层面的安保政策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迅速转变,因而我们必须从长期视角出发对此进行观察。事实上,安倍政府的安保政策大多还是基于往届内阁政策基础上的延伸。
首先,安倍政府的安保政策会根据周边环境变化,采取随机应变的调整。例如,小泉时期为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政府决定于2003年12月引进导弹防御系统,在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上部署了“标准-3”型拦截导弹,并为航空自卫队引进了具备地对空拦截能力的“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系统。通常来说,日本会先在《防卫计划大纲》中制定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总体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小泉则逆程序而行,于一年后的2004年12月才出台《防卫计划大纲》。也就是说,为应对朝鲜导弹的威胁,在制定总体军备计划之前,小泉选择了提前部署个别装备,即先行引进了导弹防御系统。
2017年,美朝关系急剧动荡,朝鲜数次向日本周边发射导弹,令日本负责海上导弹防御的“宙斯盾”驱逐舰及其护卫舰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此,日本政府在同年12月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配备陆上部署型导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的决定。无独有偶,安倍政府也是直到2018年12月才修改了《防卫计划大纲》。安倍政府仿效了小泉政府的做法,为应对安全环境的变化采取了适时的调整。
其次,安倍政府确实在安保政策上有所强化,但事实上这一点不过是延续之前政府的做法。日本战后长期将“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作为防卫政策的根本,将之修改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的,正是民主党时期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43)「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2013年12月17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2019-08-18]。通过这一改变,日本的防卫政策不再是应对所有威胁,而是大幅转型为防备特定威胁(主要指海上和空中威胁)。虽然安倍上台一年后再次修改了《防卫计划大纲》,(44)「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2013年12月17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2019-08-18]。但其中的“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概念与民主党时期的“机动防卫力量”几无差别。也就是说,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大幅转型,基本上都是为应对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趋势所作出的调适,并非只是安倍时期所独有的变化。
最后,安倍政府虽然作出许多大胆调整,但大部分都是基于以往讨论成型的内容。其中包括:(1)通过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局,构建安保方面的首相辅助体制;(2)通过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45)「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年12月17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2019-08-18]。,完成比《防卫计划大纲》更高级别的战略筹划;(3)通过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武器出口及装备合作研发;(4)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武力行使三条件”:遭受武力攻击,无其他适当手段时,允许日本行使必要且最小限度的武力);(5)放宽日本自卫队在参与联合国维和等活动的行动标准;(6)在2018年《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构筑“多维联合防卫力量”,将防卫范围扩展到宇宙、网络和电磁波等新领域;(46)「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2018年12月18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2019-08-18]。(7)将“出云”号大型护卫舰“事实航母化”,等等。
在上述七项中,(1)与(2)为制度改革,基本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主;(3)是经过了包括民主党时期在内的长期讨论,才逐步实现的阶段性改革;(5)都是在联合国等国际合作的框架范围内,日本的武器使用标准在国际上并不出格;(6)目的虽是为了强化自卫队能力,但重点也是为应对多元化威胁;(7)虽说是“事实航母化”,但由于自卫队并未计划在舰艇上搭载攻击型航母必备的战略轰炸机,因此日本的“准航母”仅是作为防范入侵领空的措施之一,用以弥补舰队防空和西南地区航空基地不足的问题。
这样看来,安倍政府最明显的特征和最大的变化只有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点。但集体自卫权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明确记载的内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都可享有自卫权,集体自卫权更属于自卫权的一部分。因此,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作为安倍政府独有的政策特征,也不过是放宽日本特有的法律限制,使日本更加接近国际社会常识而已。
五、结 论
本文在重新审视了中国国内的日本“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深入分析了日本政府强化安保政策的背景和趋向,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A)类型的“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并无说服力。日本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地区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日本通过在安全上依赖美国,降低了国防开支,得以集中力量实现经济发展。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较小,社会福祉居于亚洲领先水平,失业率也较低。将一战后的德国同二战后已经发展了70年的日本作比较毫无意义。日本是一个发动战争遭遇巨大失败、在和平年代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孕育而生。因此,大多数日本国民在安保方面希望维持现状的倾向,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第二,(B)类型的“政治层面的右倾化论及军国主义复活论”同样不具备说服力。一方面,日本的首相和内阁受到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多重制约,即使怀揣极端政治理念的政客上台执政,其诉求也必定不会实现。日本作为法治国家的这一事实,是阻碍政府出现右倾化、复活军国主义的最大防波堤。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被财政和经济状况所掣肘,进行大规模扩充军备或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既不合理也无可能。在当今时代,贸然发动会招致财政崩盘、经济崩溃的大规模军扩和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对于时刻面临选举压力的西方国家政府来说,几无胜算。同样,民主也是阻碍政府出现右倾化、复活军国主义的另一道防波堤。
第三,(C)类型的“安保政策层面的右倾化论”虽具备一定说服力,但在阐释“军国主义复活论”上却难以令人信服。安倍强化安保政策的背景,主要是为了应对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种种变化,而非源于政治观念上的军国主义思想。安倍是借势而行,趁安全环境变化之际,在原已成型的安保构想基础上,成功修改了安保政策。针对这种情况,日中间可通过开展防卫交流和安全对话等有效措施,不断增进双方互信,以改善这一局面。双边关系的整体改善,双方信赖关系的打造和沟通对话的制度化,都会有助于避免两国出现擦枪走火。一旦这种威胁感下降,日本民众很可能将不再支持政府改变安保政策现状的做法。
日中两国是“永远的邻居”,且双方在经济增速放缓和少子老龄化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的课题。因此,日中两国可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到目前为止,日中都是在相互不信任的前提下各自推行本国安保政策,而扩军备战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增进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2018年到2020年,日中两国终于开启了中断已久的首脑互访,期待日中两国能够以此为契机,携手朝着构筑相互信赖关系的方向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