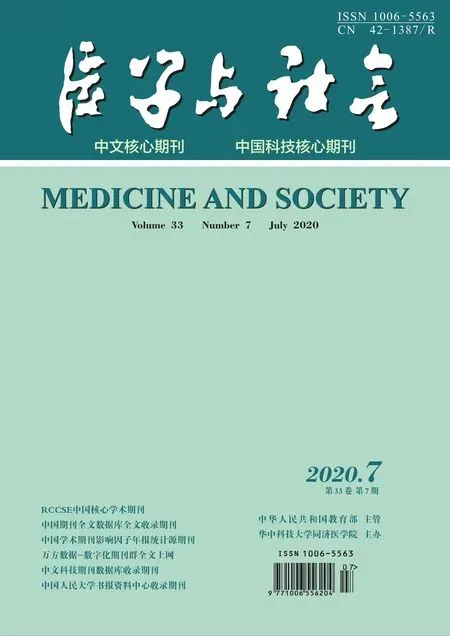《大医精诚》新释
——一个中国哲学史的视角
陈 焱
上海健康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318
传统上,我们对《大医精诚》篇的研究偏重于技术与实用层面,经常将其比附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道德他律。而从中国哲学上说,以儒家与道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哲学更倾向于确立一种道德自律原则,这一点也体现在《大医精诚》篇中。
因此,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去审视这一中医史上的经典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医学伦理学中的道德自律维度。
1 大医之大:简论《大医精诚》篇中所体现的医者之理想人格
《大医精诚》整个篇目之中始终没有解释题眼——“大医”二字的意义,当然在孙思邈的年代,知识阶层对于这一概念可能是不需要额外注解的,但这却是当代《大医精诚》研究必须要先厘清的问题。尽管已经有学者通过文献数据库比对认为“大医”概念来自于佛教的“大医王”概念的本土化[1],但笔者认为,从“大医”范畴的概念内核来看,《大医精诚》之成篇可能受到中国本土儒道之学的影响更大。对孙思邈的佛学造诣,史无明载。但他在儒道哲学方面的背景却是明确的。如《新唐书》云:“孙思邈,京兆华原人。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2]从“善言老子、庄周”可见其道家的知识背景,而“国子博士召”这一记载表明,他显然深谙儒家之学——自汉代至隋唐,各王朝官方的博士头衔一般都授予通晓儒家五经的学者。而关于孙思邈的儒学背景,在《新唐书》中还有一个旁证[2]——照邻曰:“人事奈何?”(思邈)曰:“心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之谓也。胆为之将,以果决为务,故欲大。《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谓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方之谓也。智者动,天之象,故欲圆。《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圆之谓也。” 上文的“照邻”指孙思邈的弟子卢照邻,从其与孙思邈的问答来看,后者显然是深谙儒家五经的。孙思邈在答问中,先后引用了《诗经》、《易传》与《周易》三部儒家经典。此外,他还另外提及了《孟子》中的“心君”概念与《论语》中的“仁智”概念。
从上述引文来看,尽管在《大医精诚》篇中孙思邈并未解释何谓“大医”(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在唐代这次相对十分通用普及,摩尼教、佛教等思想派别皆有使用[1])。同时,在上述对话中,他却反复提到了他对于“大”的理解,并且其诠释根据来自于先秦儒家的相关经典,并认为其正对应于传统中医学概念上的“胆”。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胆”主决断,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得意志判断。之后,他又引用了一句诗——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来说明这这一点。这句诗出自《诗经·周南·免罝》,意思也十分清楚,就是描写捍卫国家的武士之忠诚。但为什么孙思邈用武士之忠诚来诠释其心目中的“大”概念呢?在儒学传统之中,“大”概念非常重要,与之搭配的都是儒家思想中非常核心与关键的概念。如“大学”,或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如“大体”、“大人”,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3]又如《周易》的《乾》卦之彖辞中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4]概而言之,所谓大学之“大”,根据南宋大儒朱熹的诠释就是大人之学。同时此“大”通“泰”(太),所谓“大学之道”就是指人心中最本然而未被欲望蒙蔽的虚灵不昧之心[3]。在《孟子》中,同样根据最为流行的朱熹的诠释:“大体”指的是天赋的道德反思之心,若能摆脱物质私欲(小体)的蒙蔽,通彻天赋的道德之心,则能“立乎其大”成其为大人[3]。最后,《周易》中的这句彖辞,歌颂的是《乾》卦之“元亨利贞”中的元,“大”是赞词,根据当代一般的理解,是赞美万物初始本然生机勃勃的自然之貌[4]。因此,先秦儒家典籍中的“大”概念,其首要指向的是某对象之自然、本然、原初的状态,而落实到人,就是指个人所天赋的道德本然状态。若一个人能摆脱物质欲望的影响,彰显这种自然天赋的道德本然状态,这便可称为“大”。
所以,孙思邈所引的“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一诗,其中体现的正是儒家之“大”概念所蕴含的这种简单朴素而又自然刚健的精神气质。从思想逻辑上来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篇中的所倡导的医学伦理学原则,本质上就是儒家“大体之大人”与“大人之学”这些道德理想人格概念在中医哲学范畴中的具体化。
2 唯诚方精:《大医精诚》篇中医家人格塑造与专业素养之间的内在逻辑
由上文可知,从传统儒学的角度来看,“大人”或“大人之学”(大学)或“大哉之天”,指向的皆是道德人格的终极理想境界,在伦理学上说也就是道德理想人格。因此,孟子有“大体小体”与“大人小人”之比,而孔子也有“君子小人”的划分。而进一步言之,“小人”相对于“大人”,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不仅是缺乏对于自身道德本然之性具有清晰认识的“人”,甚至其有时候根本不能被以作为具有人格的“人”概念来加以指代,对此儒家有个更等而下之的称呼:“禽兽”。而儒家这一将理想人格作为概念定义之价值判断标准的思想范式也同样体现在孙思邈的观点中,在《大医精诚》篇中,与“苍生大医”概念相对的并不是“乡野小医”而直接就是“含灵钜贼”——拥有思想灵魂的邪恶之辈。就此言,“大医”的反面不是“小医”(从概念上说“小医”仍旧是医)而是“非医”。因此,孙思邈对于“医者”概念的定义顺序是伦理意义上理想人格先在而专业技能次之的。
考诸文本,孙思邈对于“医生”这一概念的此种人格先在的定位不仅见于《大医精诚》篇,在其另一篇专论医者职业素养的《大医习业》篇中也同样有非常经典的论述。孙思邈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5]依孙思邈的角度来看,除上述第一句话所针对的是传统医家的专业知识系统之外,其余所涉及的《周易》、《五经》、《老庄》等都是中国古典的哲学著作。如《周易》的象数六壬,这实际上是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方法论系统。而在《周易》之后,其复次强调的就是儒家《五经》、《三史》以及《内经》和其余的子书,认为这是体认仁义、慈悲喜舍、任真体运的基础。而这里,如果我们去掉《黄帝内经》的话,那这个书单基本上就涵盖了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几乎所有的传统中国主流的思想文化经典。
若去掉当时医学的专业知识部分,光从孙思邈的这个书单来看,其与唐代培养一个儒家君子士大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储备要求别无二致(唐代的科举考试有明经科,主要考试内容就是先秦儒家典籍)。显然比起医家专业知识来,孙思邈认为,了解、认知与修养这些经典上的内容,对于一个医者更为重要。因此,若以此原则来设计医学教育体系,则医家的专业素养可以被看作是大树枝干,而其自身作为医者的人格塑造则为巨木之根系,它们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孙思邈眼中的医道之圆满。而《大医精诚》篇中也同样蕴含着这一理想人格与专业技能之间的本末关系。如在卷首,孙思邈提到,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已。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5]此间孙思邈所着重使用的概念是“精”。他认为医方与疾病皆“至精至微之事”,因之在“若非神授”的前提下,除了精勤不倦之外,别无成事之法。就此言之,《大医精诚》篇中的“精”意味着:必须勤奋不缀地去探求研究复杂繁难的经方与临床病症。而“精”的这一方法论诠释,以上述引文中孙思邈的话来说就是:“用心精微”。从中国传统上说,“精”不论是作为动词还是名词,也确实都与心灵紧密相连,并且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说,此间的“用心精微”之精不仅有知识性的认识意义,同时还有道德性的反思内涵。如先秦典籍《尚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3]上述引文本是是儒家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从思想内容上说,“允执厥中”是儒家中庸之德的核心要义,而“惟精惟一”作为方法,其根本作用对象也是人的道德之心。儒家传统认为,人心流于物质欲望之危险常在,而天赋的道德自然之心又微茫难测,同时人心道心从人的知觉上又混同为一,因此人心极其容易失守而道心则极其容易失察。
自宋明儒学的传统上说,这段话一般可以理解为:心从其本然状态上说并没有道心人心的划分,但从后天认识论的角度上,因为个人生来的禀赋与知觉之不同,则造成人心危殆不安与道心微妙难见的情况。因此“精”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非常清晰地认识与区分这两者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精”恰好兼具知识认识与道德反思之义,在“十六字心传”的框架里,以“精”的这一清晰的认识、分辨、反思的方法论基础出发,人们才能坚守住道德本心,此即所谓“一”。同时,“允执厥中”并非一种瞬时的状态转换,而是一种长久的坚持过程。这一点也恰与孙思邈所理解的“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医道追求永远“在路上”的过程性定义相同。
这里的“不倦”概念显然并不仅指对于医学知识的探究之无穷尽,显然也有儒家对于自身道德之心的反思与修持不放松的意思,若非如此,则在孙思邈看来,就会陷入“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需要注意,儒学意义上的“愚”不仅是智力层面上的判断,也是道德层面上的判断。如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以及“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的境地。而这种他所批评的自我膨胀、自高自大的思想态度境地也恰好印证了儒家十六字心传中“人心惟危”论断。
所以,若以上述儒学原典与孙思邈思想的对照分析言之,“大医精诚”之“精”就不仅仅指向一种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对于医学专业知识不断精益求精的把握,其同样指向一种对于自身心灵状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精神境界的反思与修持。而这种反思与修持显然是传统中国哲学式的并且深具伦理学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精”就是孙思邈所确立的向着本文第一小节所言之作为理想人格的“大医”前进的,在认识方法上的不二法门。而上文所谓之“精勤不倦”背后的内在动机是什么呢?对此,孙思邈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5]他认为,推动医者提高专业素养(治病)的根本动机只有大慈恻隐之心这一内在动力,而不可将从医的动机求之于外(所以他强调要“无欲无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医精诚》中,道德理想人格的塑造必须在逻辑上先于专业素养的训练,换言之,“精诚”是“大医”的前提,而“精诚”又是医者勤奋研习专业技术提高专业技能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应该是科学的前提,并且区别于科学。正如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伦理学是出自想要谈论生命的终级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这种伦理学不可能是科学。”[6]
3 精诚动人:《大医精诚》篇对处理医患关系的理论预设与思想旨归
孙思邈对于医疗行为之内在道德动机的强调,充分表明了其在伦理学立场上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传统儒家士大夫,因为其所定义的专业以及道德行为动机全都发自内在,而其这一内在化的理论逻辑在中国哲学史上乃是由孟子确立起来的。甚至孙思邈讲的“恻隐之心”就出自《孟子》一书,孟子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3]
所以,恻隐之心在儒家的语境来说,一定是个人内在最真实而不带任何功利计算(如内交父母、要誉乡党)本然真实的道德生发,而指代这种本然真实的道德生发,在唐代普遍使用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诚”——大医精诚之“诚”。在与孙思邈同时代成书的孔颖达之《礼记正义》中有云:“诚者,天性也。”[7]孔颖达是孙思邈的同代人,而《礼记正义》也是唐代官方的儒学教科书,因此,将“诚”理解为人的自然天性显然是唐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立场。就此言之,孙思邈在前述引文中所讲的“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其从本质上讲的就是儒家所认为的区分“人”与“非人”的“善性良心”。于孙思邈,一个大医之所以能做到常人不及的“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工夫,从根本动机上说,是因为其首先确立了天生内在而未被后天欲望所遮蔽的真诚无妄之大慈恻隐之心。就此而论,《大医精诚》所倡导的伦理学体系中的道德动机是先天内在的,其根植于儒家孟子心性一脉的内在超越传统之中,是一种道德自律。
对照而言,与西方医学经典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同,以《大医精诚》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与哲学思想对于医者的伦理价值并不寻求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力图将其转化为一种归属于人类天良善性的道德理性之要求。这一结论,在孙思邈这里,就可以从“必当安神定志”之“必”字见出。这一“必”字意味着:一种由内在恻隐之心生发的道德动机的确立,是作为成为一名理想人格层面上的“大医”的必要之伦理前提,同时对于医学在技术层面上的探究,也必须仅以此种道德动机作为推动,这是孙思邈对于中国传统医学伦理学的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如果说已经有学者在试图证明“大医”的词源有其佛学的来源的话[1],那么“精诚”的词源则确然来自于先秦道家。在《庄子•渔父》中,有一段孔子与隐士渔父的一段对话。或曰:“孔子愀然,曰:“请问其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8]对此与孙思邈同是唐人的成玄英疏云:“夫真者不伪,精者不杂,诚者不矫也,故矫情伪性者,不能动于人也。”[8]前文中提到,孙思邈认为:“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所以上述成玄英对《庄子》的这一疏解当可部分地代表其在《大医精诚》篇中对于医者的道德伦理要求的道家思想来源,也可以同本文上述两小节中的儒学思想诠释比论。进而,从“精诚”的词源概念内涵出处上说,《大医精诚》篇也可以看作是在唐代之前整个传统中国哲学思想框架内对医生应该与患者建立怎样的伦理关系这一问题的最终思考总结。对照《庄子·渔父》中的说法,“精诚”本身并不仅仅是医者钻研专业技艺、勤习不缀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指向孙思邈对于医患关系的定位。
他认为医者是医患关系的主体或者主动方。“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5]显然孙思邈对于体会病人苦楚的强调,从医者的本心上说就是其恻隐之心生发的结果。而从前文所引用的孟子对于恻隐之心的定义来看(非邀誉乡党、内交父母),恻隐之心之生发的根本特质就是“真”,而“真者,精诚之至也”。所以孙思邈说病人苦楚而医者欢娱乃“至人所不为”。孙思邈在这里讲的“至人”,同样出自《庄子》。《逍遥游》篇中有所谓“至人无己”之说,“无己”就是“无私”(陈鼓应先生对此注曰:“无己就是扬弃为功名束缚的小我……根据束景南先生的说法即去知去欲”[9]),“无私”则“无伪”,而正如前文中成玄英所言:“真者不伪”。因此,从孙思邈所用的“至人”一词中我们也能很好地体会到其“精诚之说”背后所蕴含的对于“真”概念的强调。
4 结论:《大医精诚》篇所承继的中国哲学精神
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3]笔者认为,这句话正体现了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篇中所要表达的“大医”之精神气质。回到本文开头《新唐书》所述及的孙思邈对于“人事”的划分,他将心(理智认知)认作小,而将胆(精神意志)看作大。因此,根据上文的分析,若这一区分落于医者层面,则医学专业技术或可谓之“小”、而精诚动人、忠诚不二的理想人格或可谓之“大”。所以,孙思邈所理解的“大医”应该是一个坚定地与疾病与苦痛作斗争的战士。除了佛教意义上的慈悲普救之胸怀,这一理想人格及其所代表的精神气质背后还蕴含着儒家对于道德理想人格的要求与道家对于生命至真的追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医精诚》就是一部探讨医者之为医者应该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气质与生命境界的中国哲学著作,这也体现了传统中医学与传统中国哲学在精神价值上的承继性。
- 医学与社会的其它文章
- 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反思人体试验中的知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