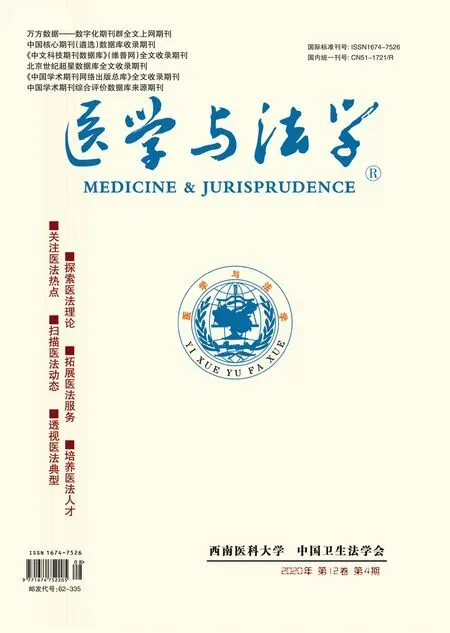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伤残鉴定2例
洪玲 连婴婴
一、案例资料
(一)案例一
高某,女,66岁,2017年12月1日因交通事故受伤至某医院就诊。查体:昏迷,双瞳孔不等大,左∶右=2.5∶2.0,对光反射迟钝,双侧外耳道血迹,右耳活动性出血,双侧鼻腔出血,右侧颜面部擦伤,右眼眶周及右侧颧弓处肿胀明显,颈软无抵抗,病理反射未引出。急诊头部CT示:右侧颞顶部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枕骨(累及额骨)骨折;左侧上颌窦及双侧筛窦、蝶窦炎。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给予对症治疗,2017年12月28日出院诊断: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颞骨骨折(双),蝶窦骨折(左)。出院时患者一般情况可,未诉明显不适。
2018年1月26日磁共振血管造影(以下简称“MRA”)示:左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显示不清,局部团片状血管影。2018年3月30日高某因“外伤后左眼胀痛伴颅内杂音4月”至某医院就诊。专科情况:神清语利,眼眶部听诊可闻及颅内连续性吹风样杂音,与动脉搏动一致,压迫左侧颈内动脉可使杂音减轻或消失,左眼视力粗测下降,视物重影,左眼外展不能,瞳孔直径2.0mm,对光反射消失,右侧瞳孔直径2.0mm,对光反射迟钝,四肢活动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征未引出。2018年4月3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以下简称“DSA”)提示:左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carotid cavernous fistula,以下简称“CCF”)。2018年4月9日全麻下行左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栓塞术,术后予以对症治疗。2018年4月17日出院诊断: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外展神经麻痹等。出院时患者诉双眼胀痛较术前好转,视物仍较模糊,左眼外展不能,有不适感,精神状况可。
(二)案例二
胡某,女,54岁,2015年6月18日因交通事故受伤至某医院就诊。查体:神志浅昏迷,刺痛无睁眼、发音,右侧肢体刺痛定位,双侧瞳孔不等大,右侧约6.0mm,左侧约3.0mm,对光反射消失,双侧病理征未引出;急诊头颅CT示:双侧硬膜外血肿,右侧颞枕硬膜下血肿,气颅,枕骨骨折,颅底骨折;急诊行“双侧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术后予以对症治疗。治疗期间患者出现右侧眼球肿胀,头颅CT血管造影术检查提示:右侧CCF。2015年8月7日全麻下行DSA示: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内血流量大,经海绵间窦向对侧海绵窦引流及经双侧眼静脉及面静脉回流,海绵窦以上断流,左侧颈内动脉造影可见向右侧大脑前动脉及中动脉代偿供血,未见血管畸形及动脉瘤改变;遂行海绵窦瘘栓塞术,手术顺利,术后予以对症治疗,患者并发脑积水,给予腰大池释放脑脊液。2015年9月5日全麻下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继续予以对症支持治疗。2015年11月3日出院诊断:脑疝,弥漫性脑肿胀,双颞硬膜外血肿,右颞枕硬膜下血肿,颅骨多发骨折,气颅,右侧脑脊液耳漏,右侧CCF,脑积水,吸入性肺炎及肺部感染。出院时查体欠合作,右侧眼睑无法完全闭合,右侧肢体活动自如,左侧上肢肌力0级,左侧下肢肌力2级,右侧额颞、左侧颞顶颅骨缺损,骨窗脑组织塌陷明显。
2016年1月6日胡某因“脑外伤术后6月余,反复口角及肢体抽搐4小时”入院。查体:神志模糊,查体不合作,右侧额颞、左侧颞顶颅骨缺损,双侧瞳孔不等大,右侧约4.0mm,对光反射消失,左侧约3.0mm,对光反射迟钝,右眼无法闭合,给予对症支持治疗。2016年1月9日出院诊断:癫痫,脑外伤后遗症。出院时查体:神志欠清,言语少,光反射迟钝,右眼无法闭合,肌力检查无法配合。
二、伤残鉴定要点
CCF是由于颈内动脉海绵窦段破裂引起海绵窦内压力增高,其内外展神经、动眼神经、三叉神经等受压,眼上、眼下静脉回流受阻,从而引起的神经眼科综合征。其临床表现主要为血管杂音、搏动性突眼、视力障碍等进行性加重。CCF可由自身因素导致,也可在颅脑外伤后即可或迟发出现[1]。
(一)因果关系分析
正是由于自发性CCF的存在以及外伤性CCF迟发出现的可能,故明确CCF与外伤性事件的因果关系,在伤残鉴定中显得尤为重要,可从以下方面加以分析。
就发病机制而言,外伤性CCF必须有明确的头面部外伤史。颅底骨折碎片、外来异物等直接刺伤该段颈内动脉或其分支,或者因为颅脑运动状态急速变化导致动脉壁撕脱、牵拉、破裂,从而引起动静脉相互交通。其症状的迟发性出现可能是由于血管破裂后形成血肿,被结缔组织包裹形成假性动脉瘤,在血流不断冲击下,最终破溃引发症状[2]。而自发性CCF常见原因包括个体雌激素变化,以及先天性及后天性血管因素,如血管壁的先天缺陷、动脉炎、动脉瘤及血管畸形等。就临床特点而言,第一,常见发病人群不同,外伤性CCF常见于30岁以上,男性多见;自发性CCF多见于妊娠期及绝经期女性。第二,临床分型不同,A型多为外伤性CCF,B型多为自发性CCF。第三,动脉血管造影表现不同,外伤性CCF瘘口单一,盗血量大,多位于海绵窦的水平及后升段;自发性CCF瘘口小,分支多,多位于颈内动脉脑膜分支[3]。第四,临床表现不同,外伤性CCF的眼部症状在伤后即可出现,也可在数日、数周、数月内发生,症状较明显;而自发性CCF起病隐匿,症状较轻[4]。
故而,实际鉴定时可从上述不同点出发,对鉴定材料综合分析,明确外伤性事件在CCF中的实际作用。案例一中高某发生交通事故后首次住院期间未诉眼部不适,伤后4月余因眼部症状再次住院治疗。CCF诊断的首次客观证据也出现在伤后1月左右(2018年1月26日MRA),故其CCF与交通事故的关系成为本次鉴定要点,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被鉴定人为老年女性,住院期间未发现动脉粥样硬化及血管畸形征象,无引发CCF的其他自身因素;第二,此次交通事故致其双侧颞骨骨折、左侧蝶窦骨折,具有引发CCF的损伤基础;第三,其眼科表现为CCF典型症状,在交通事故后经过临床无症状间歇期后出现,症状明显,与交通事故之间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病情呈进行性发展,符合迟发型CCF发展演变规律。综上,现有材料表明本案例中2017年12月1日交通事故与其后发生的CCF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案例二胡某发生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及颅底骨折,住院治疗期间发生右侧CCF,易判断交通事故与CCF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二)伤残等级评定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指出,因果关系明确后,可行伤残等级评定,且伤残等级评定需以损伤治疗后果或结局为依据进行客观评价。案例一中高某可以其眼部症状评定十级伤残。但案例二胡某因头部损伤严重,认知功能部分受损,其无法准确表述其眼部不适,无法配合眼部检查。部分鉴定人认为可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附则6.1,比照最相似等级5.8.3.2颈总动脉或者颈内动脉严重狭窄支架置入或者血管移植术后,评定其八级伤残[5]。但笔者认为此比照方法依据不足,第一,二者颈内动脉损伤节段不同,按Fischer分类法,5.8.3.2条款中颈内动脉损伤位于C1、C2段,头颈部外伤可引起;而颈内动脉海绵窦漏其损伤部位位于C4段,由头部外伤所致;第二,二者临床表现不同,颈内动脉狭窄或严重狭窄引起脑供血不足,出现失语、偏瘫等症状,而颈内动脉海绵窦瘘以眼部症状为主;第三,二者预后情况不同,外伤性颈内动脉严重狭窄致死致残率较高,即使及时治疗,其已出现的临床症状较难恢复,而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中,部分患者可临床自愈,手术治疗预后较好。故笔者认为外伤性CCF的伤残评定不可比照5.8.3.2条款,其伤残等级评定,必须根据其损害后果,借助临床辅助检查,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具体条款,进行客观评定,不可随意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