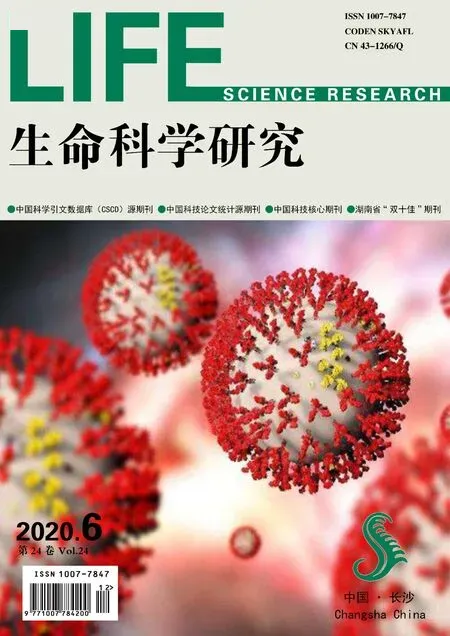C-反应蛋白的构象变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的研究进展
沈志远,张 林
(1.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2.西安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061)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而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CVD的主要病因。AS是一种炎症性疾病,由低密度脂蛋白(low-density lipoprotein,LDL)在动脉壁的沉积和随后的修饰引起[1]。白细胞(主要是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被内皮组织所表达的黏附因子招募聚集,渗透浸润到动脉内膜并产生大量的炎症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2~3]。之后,浸润的单核细胞分化成巨噬细胞,摄取修饰后的LDL并逐渐变成体积较大的泡沫细胞,进而促进AS的发展[4]。现有研究显示,多种不同类型的炎症反应参与AS的发生和发展[5],因此,各种炎症生物标志物被广泛的研究,用以提高CVD的风险预测[6]。
在迄今报道的炎症生物标志物中,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是最重要的炎症指标之一。CRP是一种由相同亚基组成的五聚体分子,主要以五聚体CRP(pentameric CRP,pCRP)的形式存在于血液循环中,在急性炎症或感染发作时由肝脏分泌产生[7]。在临床上,CRP被用作炎症、感染和组织损伤的非特异性标识物[8]。在机体发生炎症或者组织损伤时,CRP血清浓度6 h内可增加1万倍,而且其分解代谢率与它的血浆浓度并无关联[9]。CRP不仅是炎症的重要指标,还是炎症的调控因子。其被认为是先天免疫的模式识别受体,可以识别并结合多种内源与外源配体,如破损的细胞膜、细菌胞壁和核酸等,结合配体的CRP可以通过其效应面进一步与补体分子C1q和C4bp等结合,激活补体途径,促进有害物质的清除[10]。此外,CRP还可以通过其效应面结合不同的细胞表面受体,如 FcγR(Fcγ receptor)[11]、FcαR(Fcα receptor)[12]和 LOX-1(lectin-like oxidized LDL receptor-1)[13]等,从而激活多种免疫细胞的应答。以上这些特征都表明,CRP是宿主防御、免疫调节和炎症的重要组成部分。当pCRP经循环系统进入炎症微环境或暴露在病理条件下时,可从五聚体解离为单体CRP(monomeric CRP,mCRP)。与pCRP相比,mCRP可以与不同的受体结合,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特性[14]。mCRP也是一个很强的炎症调节因子,可以通过激活补体[15~16]、活化内皮细胞[17]和内皮祖细胞等多种途径来发挥其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CRP的功能取决于其构象和定位的不同[14,18~23],而mCRP则是其参与局部炎症调节的主要构象。在此基础上,我们旨在探究CRP构象的变化对AS的影响。
1 CRP与动脉粥样硬化
炎症被认为在AS的各个阶段都起着关键作用,大量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升高已被证明可以预测CVD的发生。而这些因子中,与CVD最密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之一就是CRP。血清中的低浓度CRP(小于5 mg/L),以前被认为没有临床意义。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的、更敏感的CRP检测技术的发展,这些低浓度的CRP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被称为高敏感性CRP(high-sensitivity CRP,hs-CRP),之后这种测试方法迅速产生了临床影响。1997年,Ridker等[24]首次描述了hs-CRP的升高与动脉疾病风险增加的相关性。之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于hs-CRP测量的CRP可以独立于传统危险因素,用于CVD的风险预测,并且与传统的风险因素(如高脂血症和高血压等[25])一样密切[26~27]。基于以上证据,hs-CRP已经成为在CVD风险预测中领先的生物标志物,并被归类为Ⅲ类B级证据[28]。在雷诺兹风险评分中,除了传统的风险因素外,人们还加入了hs-CRP的风险评估,以提高总体风险预测的准确性[29]。研究人员甚至可以基于 hs-CRP 浓度(小于 1.0 mg/L、1.0~3.0 mg/L、大于3.0 mg/L),对低、中、高CVD风险进行分类[26]。而且,根据hs-CRP的水平可以独立预测正常人群CVD死亡的风险[27]。
此外,CRP在人AS的早期病变组织中可以被检测到[30],而且其在炎症部位的水平与疾病的发展密切相关[31]。有证据表明,AS斑块大小的变化和治疗后复发事件的风险也与患者CRP水平的变化紧密关联[32]。除此之外,CRP 还与修饰的 LDL[33~35]、激活的补体[36]和泡沫细胞[30]等致AS介质共定位。这些都意味着CRP不仅仅是一个风险预测因子,还是CVD的直接参与者。事实上,大量的在体和离体实验证明,CRP可以通过调控CVD相关的炎症过程影响病情的发展[37~40]。
尽管有上述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CRP与CVD并无因果关系。一些流行病学研究发现CRP与疾病之间并无相关性[41~44]。例如,CRP基因的非编码核苷酸多态性影响CRP的基础血浆水平,但与未来发生CVD事件的风险并无关联[44]。除此之外,许多动物模型实验也都表明CRP与AS毫无关联[45~52]。这些争议使我们无法明确CRP在AS中的确切作用。除了这些离体和在体实验出现的大量矛盾外,CRP的急性期血浆浓度过高也是一个问题,浓度变化如此巨大的CRP是如何精确调节炎症反应的?hs-CRP又是如何能成为CVD的风险预测因子的?这些关于CRP在AS/CVD中的功能作用的种种疑问,都亟待去解决。
2 CRP的活性依赖其构象转变
上述这些矛盾以及谜题,或许可以通过CRP在局部炎症发生的构象以及活性的变化来解答。pCRP的五聚体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53~56]被破坏,从而形成单体的亚基,即为mCRP。pCRP解离为mCRP的过程伴随着二级结构元件的丢失和三级结构的显著改变,这导致了mCRP独有表位的表达,也赋予了mCRP新的生物活性与功能[16,54,57~60]。
事实上,CRP变构为mCRP会显著增强其与各种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激活补体的能力。实验表明,mCRP与天然的和经过修饰的LDL有强烈的结合,而pCRP与LDL只有低至中度的结合[60]。此外,mCRP在游离状态和结合状态下均可与C1q有相互作用,而pCRP仅在与多价配体结合后才能结合C1q[16]。mCRP通过结合C1q激活或者抑制经典补体途径,这取决于mCRP是处于游离状态还是表面结合状态[16]。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mCRP通过结合细胞表面的C1q、因子H和C4b等补体成分,发挥其促进细胞凋亡以及坏死细胞的非炎症清除作用[15,61]。另外,mCRP还可以在短时间内(4 h)通过顶端刺激人冠状动脉内皮细胞,上调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8,IL-8)、IL-6、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和E-选择素(CD62E)等因子的表达,进而激活内皮细胞[17],而pCRP则需要较长时间(24 h)[17,62]。这些研究说明,之前发现的CRP的相关功能很可能是pCRP发生构象变化解聚为mCRP所致。
3 炎症局部发生CRP变构并增强其生物学活性
mCRP的生物活性明显增强,说明mCRP可能是一种被激活的CRP变体,而pCRP则只是mCRP的前体,是一种基础状态的结构。然而,自从mCRP的概念提出以来,关于mCRP的生物学活性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主要的问题是,pCRP的分子结构非常稳定,而mCRP的制备则需要对pCRP进行高度变性处理。因此,识别具有病理生理相关性的pCRP解离途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通过电镜成像、免疫荧光等途径,Ji等[54]发现pCRP与受损的生物膜(包括脂质体和细胞膜)结合可导致其部分构象快速的变化,进而解聚为mCRP,期间还伴随着补体系统的活化。另外,有研究发现pCRP在坏死细胞和活化的血小板膜表面也可以以溶血蛋白依赖的方式结合和解离[56]。受损细胞膜诱导的pCRP解聚进一步揭示了mCRP的显著积累和有效作用最有可能发生在炎症位点,即损伤坏死细胞和受损细胞膜富集的地方。使用高特异性抗体的免疫组化分析显示,在AS斑块[56,63]、糖尿病[64]以及脑卒中[65]等疾病中,局部病变部位存在的CRP主要亚型都是mCRP,而不是pCRP。病灶处pCRP的解聚不仅用于增强其生物学活性的表达,还是一个缓冲机制,避免了急性炎症期pCRP浓度急剧升高而导致的全身性效应,这也为我们解释了CRP极有可能是通过构象的改变从而实现其对炎症反应的精细调控。
迄今发现的所有pCRP解聚生成mCRP的途径都与局部炎症条件有关,如细胞膜受损[54,56,61]、病理蛋白质聚集[66]和活化细胞释放的微粒[55]等。另外,活化的巨噬细胞/单核细胞的直接合成也是mCRP的一个来源[67],但是这条途径也与炎症相关。因此,pCRP可能只是作为全身炎症的标志物,而mCRP则是局部炎症的活跃分子。尽管如此,如果局部形成的mCRP能够释放到循环中,它极有可能成为比pCRP更好的潜在炎症标志物。研究发现,循环系统中的细胞微泡上就携带有mCRP[55]。另有研究报道,mCRP自身抗体与自身免疫病[68~70]等全身性炎症疾病密切相关。因此,相较于pCRP,mCRP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炎症标志物。最近,Zhang等[71]优化了血浆中检测mCRP的ELISA方法,该检测方法可重复,而且灵敏度非常高(达到1 ng/mL)。这为研究mCRP与AS以及其他炎症疾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简捷有效的工具。
4 mCRP活性调节的机制研究
mCRP在炎症各方面的作用正在逐步被人们发现,但是mCRP的具体作用机制仍不太清楚。研究发现,从不同的制备方法中获得的mCRP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生物学活性。通过尿素变性pCRP和基因重组两种方法制备的mCRP,虽然它们都表达相同的表位,但后者却具有更强的促炎活性,例如:与LDL的结合力更强[60];具有较强的结合补体C1q并进一步激活补体的能力[16];可激活HAECs细胞,促进单核细胞与HAECs细胞的黏附[62]。然而,随着亚基间二硫键的还原,来自pCRP脲变性的mCRP会表现出与重组mCRP类似的活性,说明亚基间二硫键是mCRP功能的一个重要开关[58]。每个CRP亚基都包含两个进化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Cys36和Cys97),它们形成二硫键以稳定亚基的疏水核心。当pCRP解离为单体亚基时,二硫键才会被还原,说明pCRP的解离是亚基间二硫键还原的先决条件[72]。硫氧还蛋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对二硫键氧化还原稳态至关重要的还原酶,研究发现它可以高效还原mCRP,而且mCRP还与硫氧还蛋白在AS斑块中共存[58],说明mCRP的还原可能发生在局部炎症中。在半胱氨酸突变的mCRP中,人们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58]。这些结果表明,亚基间二硫键是调节mCRP活性的重要开关。
FcγRⅢ(CD16)是mCRP的受体。mCRP通过与CD16的相互作用,可以延缓中性粒细胞凋亡,并诱导其活化、黏附和迁移;也可以激活HAECs细胞,刺激单核细胞产生活性氧。然而,研究发现添加CD16的阻断剂仅能少部分抑制mCRP的活性[62,73],这说明细胞上还存在有其他更重要的mCRP受体。脂筏是细胞膜上特有的信号传递平台,细胞信号网络的许多重要组成部分,如G蛋白偶联受体、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和T细胞受体等,要么是组成性地驻留在脂筏中,要么是在特定的刺激下迅速被募集到脂筏中。研究报道,mCRP可以直接插入内皮细胞细胞膜富含胆固醇的脂筏微区[57]并与之结合,继而激活内皮细胞;通过MβCD(methylβ-cyclodextrin)和制霉菌素破坏脂筏的结构,能有效地抑制mCRP对内皮细胞的活化[57]。因此,脂筏可能是mCRP在细胞膜上的主要受体,与脂筏的相互作用,可以给予mCRP特有的优势去激活各种信号元件。上述结论在一些实验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mCRP可以通过脂筏介导其与单核细胞以及血小板的结合[56];脂筏的破坏可以逆转mCRP在内皮细胞纤维蛋白凝块形成中的促进作用[74]。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发现,mCRP上存在一段在进化中非常保守的序列——胆固醇结合基序35~47(cholesterol binding sequence,CBS;aa 35~47),而且该序列是负责介导mCRP与多种配体结合的关键序列[57,75]。例如:mCRP与脂蛋白ApoB、补体成分C1q以及膜脂成分胆固醇等多种配体的结合,都可以被合成的CBS多肽抑制,而其他CRP的多肽序列则没有此功能[75]。除此之外,mCRP的C-端八肽(aa 199~206)被认为是mCRP插入脂筏的主要决定因素[57]。结构分析显示,在pCRP中,CBS位于亚基的疏水核心,而C-端八肽位于亚基之间相互作用的界面。随着pCRP在细胞膜上的解离,CBS序列暴露出来。然后,mCRP通过CBS与胆固醇结合,并通过其C-端八肽插入脂筏,激活对应的下游信号分子,进而发挥其相应的生物学功能[57]。
5 总结
CRP在AS中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在炎症微环境中,pCRP通过各种途径解聚为mCRP[54~56,66]。在AS的早期,CRP 水平只有少量升高,mCRP的含量也相对较少,这时,mCRP通过调节补体途径[15~16,61]和LDL的代谢[13,22,35,60],促进损伤物质的清除,起到保护以及缓解AS的作用;随着AS的进展,血液中的pCRP浓度急剧升高,病灶处大量的坏死细胞也为CRP提供了足量的变构配体,同时CRP亚基间的二硫键进一步还原,使其暴露出更多的CBS位点,导致单核细胞、血小板以及补体等的过度活化,从而发挥其促炎作用,最终促进AS的发展以及血栓的形成(图1)。这种多层次的级联机制使CRP可以通过其构象变化,完成其对炎症的精细调控。但是,对于mCRP在AS整个进程中的作用及具体分子机制,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以及系统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CRP不同构型的研究可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也可为我们构建新的AS动物模型提供帮助与指导,这对于理解CRP不同亚型在AS发展过程中的确切功效也有很大帮助。除此之外,通过干预CRP的构象转换以及mCRP发挥作用的途径,也许能够帮助人们找到治疗CVD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