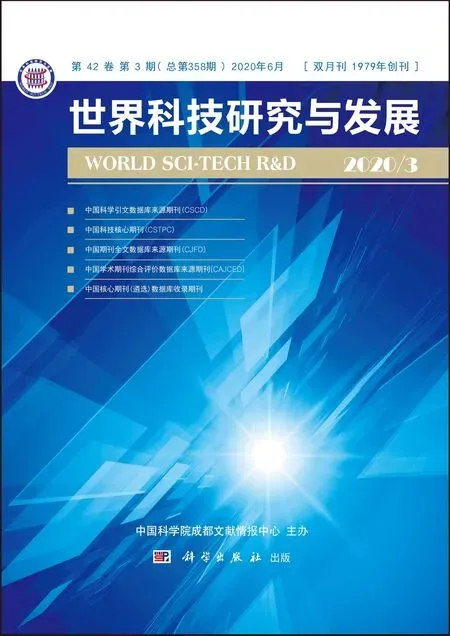主要国家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体制简析*
梁慧刚 黄 翠 张 吉 朱小丽马海霞 宋冬林 袁志明**,
(1.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武汉430071;2.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北京100190;3.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430071)
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从描述生命发展到解释生命、再发展到改造生命,最终实现创造生命,并在人类健康、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生物技术作为两用技术(Dual-use Technologies),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因为误用和滥用,给人口健康、生态环境、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可能[1]。以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正处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中,在医疗、农业等诸多领域为人类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物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近年来,由生物技术的发展导致的生物安全事件频繁出现,暴露了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的漏洞,给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2001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在鼠痘病毒中加入白介素4(Interleukin IL-4)基因后意外产生强致死性病毒;200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人工合成了脊髓灰质炎病毒;2005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重新构建了1918流感病毒;2012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修饰了H5N1流感病毒,使其具有在哺乳动物间传播能力等。
生物安全的概念起初是用于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防止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的产生。随着生物技术的逐步发展,生物安全的概念也在不断深化,加入了传染病防控、生物恐怖防范、禁止生物武器、防范外来生物入侵、应对细菌耐药性、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的保护和开发、防止生物技术的误用和滥用等内容。可以说生物安全的发展历程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生物安全是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保障和要求,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是生物安全的目标。特别是近年以来,生物技术快速发展,出现了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编辑等具有颠覆性作用的技术[2],生物技术误用和滥用的风险加大,如2018年1月19日,加拿大科学家大卫·埃文斯等人在PLOSOne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他们成功通过化学合成手段合成马痘病毒,这也是人类首次合成正痘病毒家族,批评者指出这种方法可能导致人工构建出天花病毒[3]。2020年2月21日,瑞士等国研究人员团队在已知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基础上,首次在试验中通过反向遗传学手段在酵母菌中快速构建出了活的新冠病毒,使得生物安全防范的难度加大,特别是未来的病毒溯源工作会更加困难[4]。
鉴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风险问题日益加剧,世界各国已达成了加强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的国际共识。很多国家采取的管理方式是在政策规则引导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审慎的法律监管。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这意味着中国对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也对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和生物安全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国既要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以造福人类,也要加强生物技术的安全管理,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手段。文章在分析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生物安全立法和管理体制的基础上,针对建立健全我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提出建议。
1 美英俄等国的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体系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生物安全体系治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完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保障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美国采取的是分头管理机制,通过立法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针对生物技术还颁布了专门的规章,建立了专门的咨询机构;俄罗斯和英国则采取了集中管理的机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1.1 美国
1)立法体系
1996年,美国发布《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The 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6)后,美国卫生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制定了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生物制剂清单;然后在《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确定对生物制剂的访问权)、《管制病原的拥有,使用和转移》(根据上述生物制剂清单制订)和2002年的《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防范措施法》(Public health security and biological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of 2002,该法禁止“受限人员”进行分类、使用和转移管制病原)的指导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通过联邦管制病原计划(Federal Select A-gent Program,FSAP)来监督管制病原的拥有、使用和转移[5]。对于受到广泛关注的生物安全和双重用途研究(Dual-Use Research Concern,DURC)问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成立了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dvisory Board for Biosecurity,NSABB),以就出现的问题向美国政府提供建议[6]。
2)管理体制
美国生物安全管理实行的是分头管理的机制,尚没有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全权负责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而是由涉及多部门的多个机构负责监管,不同的部门分别负有独立的责任,往往也会出现重复管理的现象。负责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的管理部门分别是HHS系统的CDC、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OSHA)、NIH、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环境保护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运输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商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DOC)等。
各部门分工如下:DOT负责对特殊病原运输进行管理,DOC对特定传染病因子的进出口进行管理,OSHA通过《针刺安全和预防法案》(The Neediestiek Safety and Prevention Act)对工作场所的普遍预防措施作出了要求,CDC和NIH共同编写了《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Biosafety in Micro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Laboratories,BMBL)作为研究实验室的指南,NIH通过重组DNA和核酸分子指南对实验室活动进行管理,HHS和USDA通过特殊病原监管对病原体的活动资格进行管理[7],NSABB主要负责研究、评估和监管生物技术。2012年3月,美国率先发布了国家层面的两用生物技术研究监管政策,对从事和资助两用生物技术研究的部门和机构的职责进行明确规定[8];随后在2013年2月,美国颁布了研究机构层面的两用生物技术项目监管政策,细分了个人、研究机构、基金资助方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监督责任和角色[9]。2013年5月,NIH在操作规范层面将以往的《重组DNA指南》修订为《涉及重组 DNA或合成核酸分子研究的指南》[10]。通过上述举措,美国已经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活动等层面对两用生物技术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监管。
1.2 俄罗斯
1)立法体系
1993年俄罗斯发布了《国家卫生条例》(The national Sanitary Regulations,SR),这是俄罗斯关于生物安全实践发布的第一个政策。该文件自其最初发布以来已进行了更新,更新的内容涉及设施生物安全分类、对生物安全政策的责任制和生物安全培训标准。2008年发布的《风险等级3和4的微生物处理条例》(The Russian's Regulations on Handling Microorganisms in Pathogenicity Groups 3,4)确定了专门针对高风险病原体的指导原则,该条例于2009年进行了广泛修订,旨在为联邦和私人机构提供生物安全指导原则。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生物安全文件是2010年发布的《英语-俄语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统一词典》(English-Russian Harmonized Dictionary in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2010),该词典提供了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术语以及有关生物安全组织的信息。
2)管理体制
俄罗斯的生物技术安全管理机制如下: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福利监督局(Rospotrebnadzor)是执行机构,负责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和立法,以及制定和批准国家卫生和流行病学准则以及卫生规范。此外,Rospotrebnadzor负责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进行联邦州卫生和流行病学监测以及联邦州监测[11]。《风险等级3和4的微生物处理条例》是重要的生物安全指南文件,其中详细介绍了标准操作程序和实验室最佳做法。根据这些规定,设施运营实验室的经理负责日常运营中的安全监督,而Rospotrebnadzor和公共卫生办公室则负责国家层面的监督[12]。
1.3 英国
1)立法体系
1995年英国发布了《伤害、疾病和危险事件报告条例》(Reporting of Injuries,Disease and Dangerous Occurrences Regulations 1995,RIDDOR),成为报告生物安全意外事件的指南,该条例在2008和2013年分别作了修订。1998年英国颁布了《特定动物病原体命令》(Specified Animal Pathogens Order 1998,SAPO)规定了动物病原体处理原则。SAPO是一种许可制度;颁发的许可证规定了在检查实验室和文件后,如何处理病原体的条件,许可证通常有效期为五年。2000年,英国颁布了《生物制剂批准清单》(The Approved List of Biological Agents),对生物制剂进行了分类。2000年,英国颁布了《转基因生物(封闭使用)条例》(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Contained Use)Regulations 2000,GMO(CU)),对保护人和环境免受转基因生物的危害作了规定。2002年,英国颁布了《危害健康的物质控制条例》(Control of Substances Hazardous to Health Regulations2002,COSHH)涉及风险评估,预防或控制生物制剂的暴露。这也符合《欧洲指令2000/54/EC》,该指令要求工人在工作中免受暴露于生物制剂的风险,同时要求成员国对生物制剂进行分类。2014年,英国颁布了新版《转基因生物(封闭使用)条例》(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Contained Use)Regulations2014,GMO(CU))涉及保护人员不受转基因生物封闭使用带来的风险。与COSHH和SAPO不同,新版GMO(CU)根据场所对环境和实验室人员的风险将场所进行(1~4级)分类。
2001年发布的《2001年反恐怖主义犯罪和安全法》(The Anti-Terrorism Crime and Security Act 2001,ATCSA)允许对处理特别关注的病原体的实验室实施安全措施。由国家反恐安全办公室(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Security Office,NaCTSO)实施。2001年发布的《微生物防护实验室的管理,设计和运营》(Management,Design,and Operation of Microbiological Containment Laboratories)为生物安全二级和三级设施的一般管理提供指南。COSHH和《批准的操作守则》(Approved Codes of Practice,ACOP)一起,要求雇主评估接触生物制剂的风险,并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防止接触或适当控制。同时至少需要在开始前20天完成通知工作。2005年颁布的《生物制剂:管理实验室和医疗场所的风险》(Biological Agents:Managing the Risks in Laboratories and Healthcare Premises2005),用于确定使用不同制剂进行实验室研究的必要控制措施的指南。2012年发布的《生物制剂和转基因生物(封闭使用)条例》(The Biological Agents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Contained Use)Regulations2012),是一份涵盖人类和动物病原体以及基因改造研究的单一指南文件,该文件取代了2000年颁布的GMO(CU)以及部分SAPO和COSHH,至此英国将人类和动物病原体以及基因改造研究实行了统一的管理。
2)管理体制
2007年以后,英国对其生物技术安全的政策与监管程序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生物安全监管政府机构,称为健康与安全执行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HSE)。HSE是病原体监督、研究,实验室检查和研究监测的主要监管者;同时还可以作为生物安全政策的顾问、监管者和执行者[13]。在HSE内部,下设有具有生物安全职能的委员会,如危险病原体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Dangerous Pathogens,ACDP)[14]。HSE下设的基因改造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on Genetic Modification,SACGM),为关于良好实践的非强制性法规提供建议[15]。
2 关于建立健全我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思考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生物技术安全管理,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生物技术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在管理方式上各国存在一定的差异,尚无统一的国际标准,一般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各机构间分工明确等。美国采取分头管理机制,通过立法明确各部门的职责,针对生物技术还颁布了专门的规章,建立了专门的咨询机构;俄罗斯和英国则采取集中管理的机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当前,我国在生物安全立法方面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例如,我国2000年就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致力于建立科学完备的生物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但因生物安全涉及众多领域,这一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够完善。我国现阶段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存在重利用、轻监管,各部门管理职责分散,缺乏统一有效领导等问题。
1)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的风险评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和应用中的不确定性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危害行为发生或者推迟对风险行为的控制,将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一项新兴技术出现时,需要对其可能的风险进行仔细评估。2020年2月,科技部出台了《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实验室发挥平台作用,服务科技攻关需求,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实验室,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确保生物安全。为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的规范管理和服务,首先需要评估其潜在的风险,为响应政策和法规的制定提供依据。
鉴于生物技术的两用性,需要对其研究及潜在应用中存在的生物安全风险进行评估,这就需要研究能够监控生物技术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预测每个环节所面临风险的评估方法。研究人员需要全面评估生物技术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危害,建立相应的评估程序、方法和工具,制定与其风险水平相适应的管理措施和策略,评估技术、人员和应用等的安全性[16]。
2)完善政策和管理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现有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系统性、针对性不强,造成管理无法可依、缺乏操作性的局面。另外,管理体制有待健全,各部门间协作机制不完善,资源交流共享不畅,容易造成行政资源浪费且不利于工作开展。
2019年10月21日,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2020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草案明确提出要防范和禁止利用生物及生物技术侵害国家安全,还规定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安全管理,为完善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建议强化国家层面的科学设计和统筹布局,聚焦于近期和中长期要求,结合此次新冠疫情的经验和教训,合理谋划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并基于桌面推演和情景假设等方法,预测未来的风险,做好战略和政策储备。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吸引多方参与和同行评议等措施建立合成生物学从宏观政策到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全面管理体[17]。病原体管理、研究机构管理、研究人员管理、研究活动管理、DNA筛查等方面对合成生物学实行监督和管理。同时充分利用还应设立生物技术安全和伦理审查,规范相关制造商和研究人员生产和操作生物的行为。我国立法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生物技术滥用、恶意利用等行为和事件的监管,明确监管部门和监管职责,确定相应的责任和处罚。
3)加强国际合作
生物技术的监管离不开国际合作,但是我国参与国际科技治理的水平与我国的科技实力不相适应,在整个国际科技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差距更大。
建议扩大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科技合作与交流,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高国际科技话语权,加强国内外科技智库交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生物安全科技问题,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的治理,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制定能力[18],鼓励科研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提高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支持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发言、接受外媒采访、承担国际组织专家咨询工作、担任国际学术组织官员。加强与国际同行在生物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相关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安全和伦理隐患,可以取长补短,发现问题并探索建立相关标准,在技术和政策两个层面共同应对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