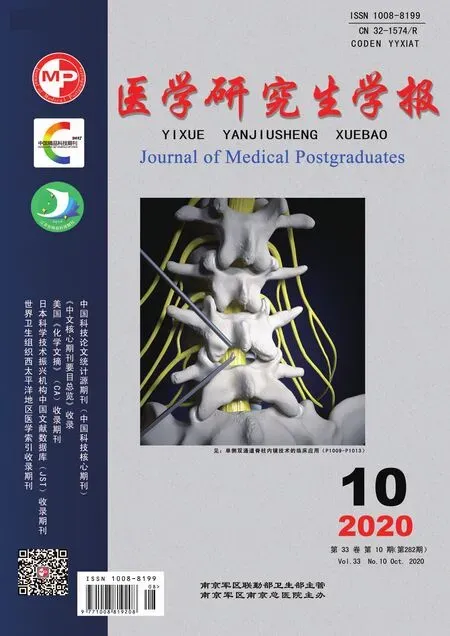冠状病毒感染与糖尿病的研究进展
李 静综述,乐 岭审校
0 引 言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报道了多例病因不详的肺炎病例,该病被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所致[1]。基因学研究发现2019-nCoV、SARS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的基因序列具有明显相似性[2]。SARS-CoV、MERS-CoV也曾先后引起全球性暴发流行,截至2003年8月,共有8422人患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截至2019年12月,共有2496人患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2]。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受遗传和环境因素影响,病毒感染是诱发及加剧糖尿病的环境因素之一。近期发布的关于COVID-19的多篇临床研究均发现,糖尿病患者为其易感人群,合并COVID-19的糖尿病患者出现更严重的炎症风暴,重症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3-7],既往SARS和MERS也有相似报道[8-9],本文主要就冠状病毒感染与糖尿病的关系作一综述。
1 冠状病毒
1.1 冠状病毒的结构特点冠状病毒是一类单股正链RNA病毒,主要由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 S蛋白)、核衣壳蛋白(nucleocapsid, N蛋白)、膜蛋白以及包膜蛋白4种结构蛋白组成[10]。对不同冠状病毒的基因学研究发现,SARS-CoV和2019-nCoV的功能性受体均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均可利用ACE2进入细胞从而感染人类[11-12]。
1.2冠状病毒的致病特点冠状病毒可感染鸟类和哺乳动物,导致呼吸和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13]。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hCoV)可分为低致病性和高致病性hCoV,低致病性hCoV通常引起轻微上呼吸道感染症状,高致病性 hCoV通常引起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甚至肾损伤、淋巴细胞减少等肺外临床症状[14],目前已知的高致病性hCoV包括2019-nCoV、SARS-CoV和MERS-CoV。冠状病毒感染可累及多处器官,如肺、免疫器官和全身小血管等。Ding等[15]对3例SARS进行尸检,发现病理改变主要涉及4个方面:以肺泡炎和支气管炎为主要改变的肺部病变;以脾脏和淋巴结坏死为主要表现的免疫器官损伤;系统性血管炎可看到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肿胀和凋亡,许多免疫细胞沉积在小静脉血管的周围以及器官血管壁,其中一些小静脉可见局部坏死以及血栓;全身毒性反应可看到肺、肝、肾、心脏和肾上腺的实质细胞变性和坏死以及大脑的神经细胞变性。Ng等[16]对1例45岁男性 MERS进行尸检,发现主要病变为弥漫性肺泡损伤,其他器官有慢性病变征象,如斑片状心肌纤维化、外周血管病变、肝脂肪变性。Xu等[17]对1例COVID-19进行尸检(样本取自肝、心及肺组织),发现病理改变与SARS、MERS情况相似。
2 冠状病毒与糖尿病
2.1 冠状病毒可诱导高血糖冠状病毒感染诱导糖耐量正常者出现血糖升高主要在SARS的研究中。一项对220例 SARS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51例高血糖患者中有糖尿病史者仅10例(19.6%),无糖尿病史者达41例(80.4%)[18]。郑宝忠等[19]对61例 SARS患者研究发现,26例血糖升高的患者中有24例被诊断为继发性糖尿病,存活下来的20例继发性糖尿病患者愈后血糖恢复正常。Yang等[20]对39例无糖尿病史且未使用类固醇治疗的 SARS患者进行了为期3年的随访,14例在住院3天内出现糖尿病,20例在住院2周后出现糖尿病,所有患者出院时仅6例仍诊断糖尿病,3年后仍罹患糖尿病的只有2例。以上研究提示冠状病毒感染可引起机体出现糖代谢紊乱,但这种紊乱可能大多数为短期存在。
2.2冠状病毒直接损伤胰岛细胞SARS-CoV S蛋白是SARS-CoV和2019-nCoV的结构蛋白之一,可介导病毒识别宿主细胞的受体,促进膜融合[21-22]。血管紧张素Ⅱ(Ang-Ⅱ)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system, RAS)的活性肽之一,Ang-Ⅱ可从多方面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转导从而促进胰岛素对靶细胞的抵抗。ACE2是RAS系统的负调节因子,可将Ang-Ⅱ裂解为血管紧张素1-7,通过靶向Ang-Ⅱ,ACE2对许多器官有保护作用;研究发现ACE2与血糖调节密切相关,ACE2可拮抗Ang-Ⅱ对β细胞及胰岛素信号通路的不利作用从而保护β细胞; ACE2与跨膜蛋白27共享相似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可刺激胰腺β细胞的增殖和胰岛素的胞吐过程; ACE2可使胰岛的血流增多,从而保护胰岛β细胞,提高其存活能力;因此认为ACE2具有保护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的作用[23-24]。研究发现,SARS-CoV可通过ACE2直接侵入胰腺内分泌腺损伤胰岛细胞,影响胰岛素分泌,也可通过侵入胰腺外分泌腺导致胰腺炎症间接损伤胰岛细胞。郭丽敏等[25]选取Wistar大鼠内脏组织制成切片检测各组织ACE2的表达情况,发现胰腺、肺、心、肾、脾、肝、回肠、膀胱8种组织均有ACE2表达,还将C57 BL/6 J小鼠及ACE2基因敲除小鼠的胰尾包埋固定并制成切片,发现胰腺内、外分泌腺均表达ACE2,电镜下在胰腺内分泌腺、外分泌腺均可见点状、颗粒状标记物,ACE2在内分泌腺集中于某一种特定的细胞,定位于细胞质内的分泌颗粒。季秀娟等[26]检测ACE2在人、大鼠和小鼠胰腺的表达情况,发现胰岛及胰腺外分泌腺均呈阳性表达,内分泌腺主要表达于胰岛中央部,显微镜下可见阳性表达集中在细胞膜与细胞质上。
2.3冠状病毒降低胰岛素敏感性SARS-CoV N蛋白也是SARS-CoV的结构蛋白之一,参与了核衣壳的组成[27]。胎球蛋白A(A2-heremans-schmid glycoprotein,AHSG)是一种血浆蛋白,通过抑制胰岛素受体的活性从而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的传导[28]。研究表明,AHSG可通过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来影响体内的糖代谢和脂代谢,SARS-CoV N蛋白可作用于AHSG间接影响体内的糖代谢和脂代谢。陈婷[29]通过酵母双杂交系统发现AHSG可能与SARS-CoV N蛋白相互作用;在人及小鼠的血清中,AHSG与SARS-CoV N蛋白形成多聚体,该多聚体沉淀量与 SARS-CoV N蛋白浓度相关,两者呈浓度梯度依赖关系,提示AHSG与 SARS- CoV N蛋白密切相关;使用胰岛素、AHSG及SARS-CoV N蛋白处理小鼠脂肪细胞3T3- L1,发现胰岛素可刺激小鼠脂肪细胞3T3-L1的IRS-1和 Akt蛋白磷酸化,SARS-CoV N蛋白呈浓度依赖性增加AHSG对上述胰岛素刺激作用的抑制;动物实验发现,加入SARS-CoV N蛋白共同处理时,胰岛素对Balb/c小鼠肝组织中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 FAS)、胆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sterol-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SREBP)-1、硬脂酰辅酶A去饱和酶和HMG-CoA还原酶的基因mRNA的刺激作用被抑制,且这种抑制作用同样与SARS-CoV N蛋白的浓度呈梯度依赖关系。张春梅等[30]在人肝细胞系HL-7702细胞的研究中得出同样的结果,SARS-CoV N蛋白可抑制胰岛素刺激的FAS、SREBP-1基因的表达,这种抑制作用与 AHSG有关;动物实验发现,注射SARS- CoV N蛋白的野生型 C57小鼠的糖脂水平(血清葡萄糖、胰岛素、三酰甘油、游离脂肪酸及总胆固醇)、HOMA指数以及体重增加量均高于注射等渗盐水组,而上述指标的改变在AHSG基因敲除的C57小鼠中并不出现,提示SARS-CoV N蛋白可经AHSG介导,致小鼠的胰岛素敏感性下降,清除葡萄糖能力减弱,影响糖代谢和脂代谢。
2.4使用皮质类固醇加重高血糖类固醇糖尿病是指因机体存在过多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GCS)所造成的糖代谢异常。在SARS、MERS流行期间,皮质类固醇是主要的免疫调节药物,多用于重型或者危重型患者。研究发现,患者在冠状病毒感染期间使用GCS治疗可引起血糖增高,且血糖增高水平与GCS治疗的疗程和剂量相关。一项纳入132例SARS患者的试验,记录患者使用GCS的日最大剂量、平均日剂量、治疗时间和空腹血糖水平(FPG),发现95例(71.9%)使用GCS患者中33例(36.3%)被诊断为GCS诱导型糖尿病,GCS日最大剂量、平均日剂量、总剂量和治疗时间与新发糖尿病正相关[31]。另一项研究对1291例SARS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GCS起始剂量、累积剂量以及日最大剂量进行分组,所有类型的GCS兑换成甲泼尼龙(methyl-prednisolone, MP)剂量,结果显示GCS组病程中最高血糖比未用GCS组更高[(8.68±4.80)mmol/Lvs(6.39±3.71)mmol/L,(P<0.001)];使用GCS的各组平均血糖均明显升高,在使用GCS后第1~2周,血糖水平上升最明显,而后逐渐下降,其中,MP累积≥3000 mg组比其他组的血糖增加更多高且持续时间更长(P<0.05)[32]。
3 糖尿病患者是冠状病毒感染和死亡的高危人群
3.1 糖尿病患者合并冠状病毒感染更危重对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发现,与非糖尿病者相比,糖尿病患者更易发生重症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率更高。Wang等[3]分析了138例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发现14例(10.1%)患者合并糖尿病,需要收入ICU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人数是不需要收入ICU治疗者的3.8倍。Booth等[8]对144例确诊或疑似的SARS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144例SARS患中有8例死亡病例,死亡病例中合并糖尿病者有6例;多变量相关分析提示糖尿病与死亡独立相关。Yang等[33]将SARS患者分为死亡组(135例)、存活组(385例)与非SARS患者(19例)进行对照,死亡组使用类固醇治疗前的FBG最高,死亡组伴糖尿病病史的例数明显高于存活组;相关性分析发现,糖尿病史和FPG≥7.0 mmol/L是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
3.2糖尿病患者病毒易感性增加糖尿病患者因蛋白质分解速度较快,白细胞吞噬功能减弱及细胞生成H2O2能力下降等,故此类患者产生免疫球蛋白、补体的能力不足,杀菌的能力较弱,病毒易感性增加,易罹患冠状病毒感染。有研究将SARS患者分为高血糖组(A组,40例)和正常血糖组(B组,40例),用流式细胞术测定SARS患者的T淋巴细胞亚群并进行比较,发现A组CD3+、CD4+、CD8+显著低于B组,A组82.5%(33/40)患者CD4+< 400/μL,65%(26/40)患者CD4+<200/μL;B组37.5%(15/40)患者CD4+<400/μL,15%(6/40)患者CD4+<200/μL;直线相关分析显示所有SARS患者的血糖与CD3+、CD4+、CD8+计数呈负相关,此外,A组合并二重感染率(20%)高于B组(5%),差异有显著性(P<0.05),提示高血糖的SARS患者T细胞亚群计数降低更显著[34]。
4 结 语
针对COVID-19的多项研究均发现,糖尿病患者为其易感人群,且糖尿病合并COVID-19患者病情更加危重,预后不佳,提示冠状病毒感染与糖尿病之间关系密切。冠状病毒感染主要通过识别ACE2入侵并损伤胰岛细胞,并通过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诱发糖耐量正常者出现血糖升高,同时,GCS的使用可致继发性高血糖,进一步加重血糖紊乱。糖尿病患者免疫球蛋白、补体下降,病毒易感性增加,感染冠状病毒后重症率、死亡率高。但冠状病毒感染与糖尿病的研究甚少,可能是突发疫情缺乏防护设备和研究环境以致于临床标本难获取,动物造模难完全模拟等原因造成。如何在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中更好的保护患者胰岛功能和糖尿病人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