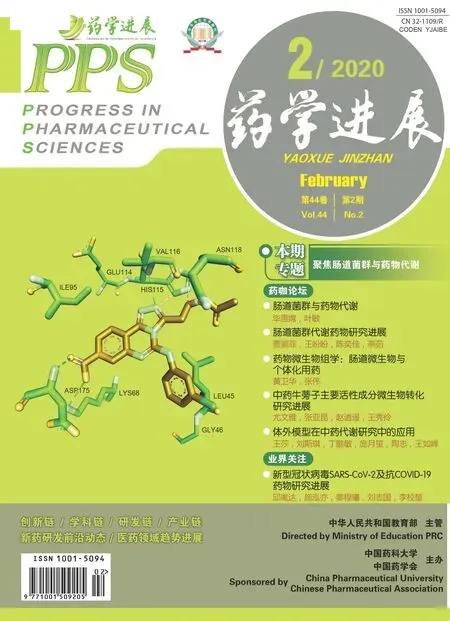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及抗COVID-19 药物研究进展
邱胤达,施泓亦,姜程曦,刘志国,2,李校堃,2*
(1.温州医科大学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2. 温州医科大学病毒与诊疗研究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病毒是一种寄生在活细胞内进行生长繁殖的非细胞形态的微生物,全世界已发现的病毒超过3 000种,其中约1/3 的病毒感染人后会引发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1-3]。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因在电镜下该病毒形态类似王冠而得名,在系统分类上属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4]。21 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先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引起的新发和烈性传染病不断出现,如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病毒和2012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分别在中国和中东地区流行,造成的死亡率分别高达约10%和36%[5-6]。当前,由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2019 年12 月以来,我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多起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立即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武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与湖北省、武汉市共同研究落实疫情防控措施。2020年1 月8 日初步确认了此次肺炎疫情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1 月12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引发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nCoV”[7]。2020 年 2 月 11 日 WHO 将 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命名为“COVID-19”,当天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新型冠状病毒再次命名为SARS-CoV-2[8]。多位中国专家认为新病毒是一种天然病毒,不同于所有其他SARS 样或SARS 相关冠状病毒,将新病毒命名为SARS-CoV-2 不仅会对病毒学知识不足的人群产生误导,也与疾病名称COVID-19不一致,因此呼吁将病毒命名为“2019 年人冠状病毒”(HCoV-19)[9]。截至 2020 年 2 月 2 日,国内确诊的COVID-19 患者为14 423 例,死亡病例为304例,病毒传播速度和确诊病例人数均已超过2003 年的SARS 事件。由于对COVID-19 的治疗至今仍缺乏特效药物,国内外医药界科学家们已经纷纷投入到抗COVID-19 新药的研发中。本文搜集整理了新型冠状病毒及其感染肺炎疫情的有关特征,并针对目前COVID-19 主要治疗药物的研发进展情况进行总结和展望。
1 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
自COVID-19 疫情暴发后,探索病毒的起源及其从天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类的传播路径,是科研人员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高福研究团队通过对早期发现的3 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样本全基因组测序,从感染者气道上皮细胞中发现了一种以前未知的β 冠状病毒属(β-coronavirus)病毒,将其命名为2019-nCoV[8,10]。该病毒归属于Sarbe病毒亚属、正冠状病毒亚科,虽然与先前报道的SARS 和MERS 病毒均属于冠状病毒,但其形成了另外一簇的进化分枝,因此被认为是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科中的第7 个新成员[11]。自发现SARSCoV-2 以来,科研工作者对该病毒的来源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郝沛研究团队率先采用遗传进化分析方法,发现SARS-CoV-2 所属的β 冠状病毒属在进化树的位置上,与SARS 和类SARS 病毒的类群相邻,而且这些病毒的共同祖先是和一个寄生于果蝠的HKU9-1 类似的冠状病毒,因此推测SARSCoV-2 的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12]。
石正丽研究团队进一步证实了SARS-CoV-2 进入细胞的受体与SARS 一样,均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并与一种蝙蝠的冠状病毒的序列一致性高达96%,为SARS-CoV-2 可能来源于蝙蝠宿主论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10]。虽然大量证据表明蝙蝠可能是SARS-CoV-2 的原始宿主,但尚不清楚任何有助于转移给人类的中间宿主的身份。朱怀球研究团队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开发的病毒宿主预测(VHP)方法,发现水貂病毒的传染性模式更接近SARS-CoV-2,从而推测SARS-CoV-2 可能在水貂体内大量扩增,使之更易于传播给人类,认为水貂可能是将病毒从蝙蝠传播给人的中间宿主[13]。随着COVID-19 疫情的进一步发展,SARS-CoV-2 的病毒起源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美国著名病毒进化学家Andersen 从病毒结构性和功能性2 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SARS-CoV-2 病毒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非实验室制造[14]。我国科学家通过对四大洲12 个国家的93 个新型冠状病毒样本全基因组数据解析发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的[15]。Science杂志专职作家Cohen 通过分析 41名COVID-19 患者临床病例后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能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源头[16]。目前,关于SARS-CoV-2 溯源工作仍在进行中,科学家和医学界均尚无定论。
管轶和胡艳玲联合团队研究发现,从广东等地截获的走私穿山甲中的冠状病毒与SARS-CoV-2 的多个谱系相似度在85.5% ~ 92.4%之间,推测穿山甲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17]。沈永义和肖立华科研团队进一步通过对蝙蝠 Bat-Cov-RaTG13冠状病毒、穿山甲相关冠状病毒和SARS-CoV-2 序列进行进化树分析发现,Bat-Cov-RaTG13 冠状病毒与SARS-CoV-2 序列一致性高达96%;而分离自穿山甲的病毒株与感染人的SARS-CoV-2 病毒株序列相似度高达99%。据此认为穿山甲是新型冠状病毒潜在的中间宿主,而SARS-CoV-2 可能进化于穿山甲相关冠状病毒和蝙蝠Bat-Cov-RaTG13 冠状病毒[18]。最近,我国学者周烨真等[19]运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分析后认为,SARS-CoV-2 病毒可能出现在2019 年11 月左右,与基因序列最为相似的蝙蝠Bat-Cov-RaTG13 冠状病毒不存在时间进化关系,不太可能由Bat-Cov-RaTG13 演化而来。目前,科学家们仍然继续对SARS-CoV-2 的来源和中间宿主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2 传播途径和临床症状
根据目前的证据,可以确定新型冠状病毒可以持续性人传人。SARS-CoV-2 感染引发的肺炎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有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2 种,特别在家庭成员、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尤其在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时候往往出现集群性的传播。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3 ~ 7 天,最长不超过14 天,但也有潜伏期达到24 天的个例[20]。易感人群普遍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腹泻等症状,甚至无明显的临床症状[21]。老年人及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力低的人群很容易被感染,并有较高的几率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凝血功能障碍以及死亡等严重后果[7,22]。也有部分感染病例为儿童和婴幼儿,目前发现的最小患者不足1 月周龄。
此外,值得警惕的是COVID-19 通常还具有无症状高效传播、治愈后还可以排出病毒、戴口罩难以防护等特点,明显增加了临床的诊断难度和病毒传播速度[23]。包括武汉和深圳等地医院的医生在临床上还观察到部分COVID-19 患者首发症状仅为腹泻,进一步对这些患者的大便和肛拭子进行检测也发现了病毒核酸,因此推测新型冠状病毒除了密切接触和飞沫传播途径外,还存在一定的粪-口传播途径[24]。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增加了“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25]。
3 防控及治疗措施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是目前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管好易感人群的有效措施。易感人群应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接触病原风险,同时注意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开窗通风,环境清洁。另外,注意手卫生也可以防止病毒的交叉感染。由于病毒普遍具有较高的基因组重组和突变率,可以感染人与多种动物[26]。因此,易感人群也应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接触野生或养殖动物。对于已确诊病例,一般患者一线临床上使用的药物以抗病毒药物为主,包括生物药物α-干扰素(雾化吸入)和化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磷酸氯喹、阿比多尔(口服)以及利巴韦林(静脉输注)。对于重型、危重型患者也会根据病情程度,酌情短期(3 ~ 5 天)使用糖皮质激素和血必净(1日2 次)。也可根据病情使用肠道微生物调节剂等,以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继发细菌感染。总之,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的特性了解还不够,临床尚无特效治疗药物。
4 药物研发进展
一般而言,防治病毒感染主要依靠疫苗和药物,由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感染的肺炎传播性强、传染速度快、致死率高,针对性的疫苗与药物研发显得尤为迫切。当前,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疫情,我国科研人员正在全力奋战推动药物研发,全球大量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也相继投入资金和人员进行相关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究与开发。
4.1 SARS-CoV-2 及受体ACE2 结构研究
本次疫情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内,我国科研人员通过对SARS-CoV-2 病毒外层包被蛋白-刺突糖蛋白(spike-蛋白,又称S-蛋白,冠状病毒依靠其刺突蛋白与宿主细胞表面受体结合而入侵细胞)结构进行模拟计算,发现SARS-CoV-2 的S-蛋白宿主受体互作区(RBD 区)与SARS 病毒的RBD 区结构具有73.5%的相同序列。虽然与SARS 相比,SARS-CoV-2 中S-蛋白RBD 的4 个用于与宿主细胞ACE2 蛋白结合的关键氨基酸发生了改变,但与ACE2 蛋白仍然具备很强的结合自由能(-50.6 kcal · mol-1)[12]。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根据我国研究人员先前提供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在原子尺度上重建了SARS-CoV-2表面S-蛋白的3D 构造[27]。近期,国内多支研究团队先后解析了ACE2全长蛋白与SARS-CoV-2病毒S-蛋白受体结合结构域的复合物结构,明确了ACE2的全貌及ACE2 与SARS-CoV-2 病毒S-蛋白RBD的相互作用模式和位点,阐明了SARS-CoV-2 病毒S-蛋白介导细胞侵染的结构基础及分子机制,为设计针对S-蛋白或ACE2 蛋白的药物和抗体提供了前期实验基础[28-30]。
冠状病毒基因组编码的主要蛋白酶[(mainprotease,Mpro),又称 3C 样蛋白酶(3C-likeprotease,3CLpro)]和木瓜蛋白酶样蛋白酶(papainlike protease,PLpro)是2 个参与多肽翻译的蛋白酶,负责将宿主细胞内的病毒RNA 翻译成蛋白以产生新一代病毒[31]。RNA 依赖的RNA 聚合酶(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RdRp)是除逆转录病毒外的其他RNA 病毒复制所必须的酶,由于这3 种蛋白酶对病毒复制和控制宿主细胞至关重要,因此也成为抗病毒药物研发的重要靶点[32-33]。饶子和与杨海涛团队在疫情发生后快速表达了SARS-CoV-2 的Mpro蛋白并获得了高分辨率晶体结构,为COVID-19 治疗性抗体药物、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开发提供了关键的药物靶点[34]。
4.2 疫苗
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最先确定SARSCoV-2 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实现全球共享后不久,又成功分离到了病毒毒株,为相关疫苗研究单位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随后,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转化医学平台与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大学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 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美国强生公司等全球国家医药机构和公司均启动了COVID-19 疫苗的研发工作。截至目前,在抗病毒疫苗研发方面,国内已有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在内的5 条疫苗研发技术路线正同步开展。疫苗研发过程涉及病毒毒株分离、细胞株培养、动物实验和行政审批等多项程序,部分疫苗最快也需要在2020 年4 ~ 5 月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35]。
4.3 化学药物
化学药物以其见效快、治疗效果好、药理机制明确等优点在防治病毒感染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36]。饶子和与杨海涛团队综合利用计算机虚拟筛选和酶学测试技术,重点针对已上市药物和自建的多种实体“化合物数据库”进行药物筛选,首次发现了包括HIV 治疗药物茚地那韦、沙奎那韦、洛匹那韦等在内的30 种可能对COVID-19 有效的治疗药物,为肺炎感染患者临床治疗提供了用药参考[34]。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联合团队发现了3 种“老药物”瑞德西韦、氯喹、利托那韦在细胞水平上可以有效抑制SARS-CoV-2活性[37]。德克萨斯A&M 大学刘文设研究团队发表文章认为,SARS-CoV-2 病毒的 3CLpro、PLpro 和RdRp 蛋白酶与SARS 病毒高度同源,以这些蛋白酶为靶点的多个抑制剂如瑞德西韦和3CLpro-1 等有潜力用于此次肺炎疫情的治疗[38]。我国学者发现瑞德西韦和磷酸氯喹在猴肾细胞Vero E6 模型上可有效抑制SARS-CoV-2,半数有效浓度EC50分别为0.77和 1.13 μmol · L-1,表明 2 种药物在细胞水平上均能有效抑制SARS-CoV-2 的感染[39]。
部分医药企业也积极参与到抗COVID-19 新药开发中,截至目前包括利巴韦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瑞德西韦、法匹拉韦、磷酸氯喹在内的多个药物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下文将分别对上述药物进行简要分析,以了解抗COVID-19 新药研发的动向与趋势。
利巴韦林:一种由ICN 制药公司开发的核苷类抗病毒药物,具有广谱抗病毒活性。该药物进入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后发生磷酸化,其产物作为病毒合成酶的竞争性抑制剂,干扰病毒早期转录事件,并且阻碍核糖核蛋白的合成,从而抑制病毒的复制与传播[40]。作为经典抗病毒药物,该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被推荐为抗COVID-19 试用药物,并在第六版诊疗方案中延续试用。
瑞德西韦:由Gilead 公司开发的另一种核苷酸类似物前药,属于第二代病毒RdRp 抑制剂。作为COVID-19 的潜在有效药物,瑞德西韦曾在美国、法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治疗中,发挥出较好的疗效。在权衡风险和获益后,我国目前已经在武汉10 家医院启动了比较大规模的瑞德西韦Ⅲ期临床试验[41]。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由Abbott 公司开发的HIV 一线治疗药物,可能通过抑制SARS-CoV-2 的Mpro 蛋白酶而发挥抗病毒作用。洛匹那韦是细胞色素CYP3A4 和P-糖蛋白的敏感底物,在血浆中具有较高的蛋白结合率。利托那韦作为CYP3A4、P-糖蛋白和CYP2D6 的底物,可抑制CYP3A 介导的洛匹那韦代谢,有助于产生更高的洛匹那韦浓度[42]。值得一提的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也是此次疫情暴发后,从首版至第六版诊疗方案中,一直被推荐的抗病毒试用药物。
阿比多尔:由Pharmstandard 公司生产的一种非核苷类抗病毒药物,具有广谱抗病毒活性,对各型流感病毒均有明显抑制作用。阿比多尔抗病毒环节主要定位于病毒复制周期的早期——病毒与细胞相互作用阶段[43-44]。李兰娟团队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阿比多尔在 10 ~ 30 μmol · L-1浓度下,与药物空白组比较,能有效抑制SARS-CoV-2 达到60 倍,并且显著抑制病毒对细胞的病变效应[45]。目前,在最新发布的第六版诊疗方案中,阿比多尔被推荐为抗COVID-19 试用药物。但是,卢洪洲团队近期对临床收治的134 例确诊COVID-19 患者的临床资料回顾性研究中发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在改善临床症状和加快病毒清除方面均未优于对照组,认为上述药物的有效性仍有待临床研究进一步确认[46]。
法匹拉韦:一种由Toyama Chemical 公司研制的新型RdRp 抑制剂,可以通过阻断病毒核酸复制的方法来抑制病毒增殖[47]。最近,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了法匹拉韦用于治疗COVID-19 的初步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服用法匹拉韦后,发热患者2 天内退热率达72%,3 天内肺部影像学好转率为38%,6 天内肺部影像学好转率为70%,并且尚未发现明显的副作用[48]。法匹拉韦治疗COVID-19 的临床试验目前已在全国多家临床中心启动,治疗效果还需等待进一步的试验验证。
磷酸氯喹:病毒感染细胞要经过病毒脱壳、释放等过程,需要适宜的酸碱度(pH 值)。磷酸氯喹作为一种上市的抗疟药物,不仅能改变细胞的pH 值来阻断病毒感染和细胞融合,还可以通过干扰冠状病毒受体ACE2 糖基化而影响病毒和受体的结合[49-50]。先前已有128 例COVID-19 病例接受磷酸氯喹治疗,其中93 例已转阴,在临床试验中已经初步显示出一定疗效,并且治疗过程中未见与药物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磷酸氯喹被正式纳入抗COVID-19 治疗[25]。由于磷酸氯喹在成人中的致死剂量为2 ~ 4 g,湖北省卫健委通知各定点医疗机构在使用该药物过程中需进行严密观察该药的不良反应[51]。
4.4 中药
我国是中草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传统中药在治疗病毒感染方面具有耐药性低和多靶点作用机制等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52]。中药应用以复方为主,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协同发挥作用,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菌、调节免疫等整体综合调节作用。应用中药治疗SARS 和MERS 疾病时,往往具有早期干预、阻断病程、减轻症状、副作用小和病死率低等多种优势,这些积极作用得到了政府和WHO的肯定[53]。针对此次COVID-19 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专家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在确诊患者临床治疗期的不同阶段提供了不同的中药处方和中成药等用于选择。例如在医学观察期乏力伴有发热患者,可使用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和防风通圣丸(颗粒)等中药制剂;对乏力伴有胃肠不适患者可使用中成药藿香正气胶囊(丸、水、口服液)等。
5 结语与展望
目前,SARS-CoV-2 感染肺炎疫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给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逐步攀升,疫情不断扩散的关键时刻,最短时间内研发可用于抗COVID-19药物已经成为广大医药科研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已经积极投入到抗病毒疫苗的研发中,相关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化学药物由于存在研发周期长、风险高、投资大等特点,借鉴SARS、MERS 的治疗方案,从已上市药物中寻找潜在药物是重要策略之一。SARS-CoV-2 的Mpro 水解酶高分率晶体结构的快速解析,以及ACE2 全长结构、ACE2 与新冠病毒S-蛋白RBD 的相互作用模式和位点的确定,为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及虚拟筛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SARS-CoV-2 与SARS 病毒的3 种蛋白酶3CLpro、PLpro 和RdRp 序列高度相似性,为开发选择性或广谱抗病毒药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验基础。总之,无论是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还是目前报道的多个在酶学或细胞上对SARS-CoV-2 有抑制潜力的候选药物,仍需要通过人体临床试验才能最终服务于患者。不过笔者相信凭借科研人员的努力,集中各方科技资源和科技界的智慧,有希望研发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的治疗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