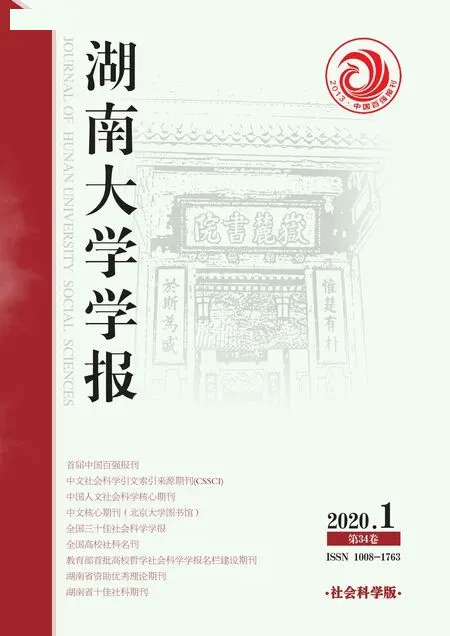底本之信:《周易》在西方传播评要 *
禹 菲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自17世纪以来,《周易》不单是中国的经典,而且逐步向外传播,成为世界各国都重视的经典,各种语言和风格的《周易》译本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中国近代翻译家严复在其《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原则:信、达、雅。信谓忠实原文,达谓译文畅达,雅谓文辞优雅。这是译本对应其翻译文本而言的。但若翻译中国古籍《周易》,便迎面遇到一个难题:《周易》经文古奥,若无注解,根本无法读懂。自古以来,中国关于《周易》的注本数百千种,所作解释千差万别。究竟哪一种注本可信度更高?因此,西方人要想有一个好的《周易》译本,首先须有一个好的中国《周易》注本作为底本。只有选择了好的《周易》注本,才有翻译上的“信”的基础,而后才是翻译水平的“达”与“雅”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注本,便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理解,这便提出了一个“底本之信”的问题。
《周易》自利玛窦来华被欧洲人认知并向西方传播,至今已接近四百年。这期间西方研究《周易》的论著已有数千种之多,翻译文本多达数十种。而从现代易学研究的步调而言,西方易学研究已经与中国易学研究渐趋同步。
历史上对于《周易》的解读,主要有两大派:象数派和义理派。魏晋以后义理派逐渐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综观《周易》在西方的传播,也主要是以义理派为主,并且主要是以宋代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以及清代李光地的《御纂周易折中》为底本的。这三个注本都称得上好的注本,但其间也有是非利钝的差别。李光地的《御纂周易折中》代表清初官学的立场,“折中”(实为依违两可)程、朱两家易学,而以朱子易学为本。然黄宗羲、顾炎武、皮锡瑞等清代大儒都认为《周易》最好的注本是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则存在严重的迷思,特别是关于易图学(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的迷思。从客观的角度看,黄宗羲等清代大学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官学的巨大影响力以及西方传教士更看重当时官学的意见,《周易》在西方的传播基本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的。正因为如此,朱熹易学关于《周易》的迷思便也不知不觉地传播到了西方。
一 中国本土易学研究的纷乱性
《周易》作为中华元典之一,被称为六经之首、“三玄”之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另一方面,对于研究者而言,《周易》千百年来又一直是一部扑朔迷离的书。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周易》理解的分歧程度远甚于此。所以,在讨论和评估《周易》在西方传播的成绩之前,须先对中国易学研究历史状况与所存在的问题作简要的介绍。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西方易学传播与中国本土易学的关联性及其问题所在。
古来中国学者对于《周易》的解读五花八门,大多数著作价值不大,这种现象很早就有。北宋学者杨时曾说:“自汉魏以来,以《易》名家者殆数千百人,观其用力之勤,盖自谓能窥天人之奥,著为成书,足以师后世。然其书具在,不为士大夫议评讪笑、用覆酱瓿者,无几矣。”[1] 489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面对成百上千的《周易》注本,如何加以选择,才能找到研习《周易》经典的正确途径?清代四库馆臣曾说: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礻几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相互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一·易类一》)
四库馆臣高屋建瓴地概括清代乾隆以前的易学发展历史,并指出《周易》的真正精神所在,可将它分作三层意思来理解:
第一层意思讲易学内部的研究。易学内部可略分“两派六宗”。“两派”指象数派和义理派;六宗指象占宗、礻几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前三宗属于象数派,后三宗属于义理派。这“两派六宗”虽然也“相互攻驳”,但属于易学内部的门派之争。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论“两派六宗”,全不提及朱熹。从这点看,乾隆时期四库馆臣的易学观念已与康熙皇帝、李光地等儒者的尊朱理念有很大不同。
第二层意思讲易学外部的研究。易学“旁及”其他学术体系,“旁及”的范围可以包罗万象,如天文学、地理学、数学、乐律、兵法、音韵,乃至炼丹术等,这些“旁及”的学术领域原本与《周易》并无关系,属于易学外部的学术体系“援易以为说”。
第三层意思讲《周易》的真正精神。《周易》的真正精神体现在《大象传》“君子以”的语言形式中,如《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大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屯》卦大象传“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等等。这是说作为中华元典的《周易》,其创作者的本意在于塑造“君子”人格,提高其境界智慧。循此精神以解读《周易》,方是正途。
四库馆臣这一论述实为《周易》解读的指路明灯,可惜历史上的《周易》解读者很少有此认识,中国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关于《周易》正确解读的某种共识。在中国,对于《周易》的认识尚且五花八门,当《周易》传播到西方后,由于西方学者从他们各自的学术立场对之加以解读,不免更增添异彩缤纷的特色。
有鉴于此,笔者下文拟从易学内部研究和易学外部研究两个方面来对《周易》在西方的传播作一分析评估,意在引起一种关注和讨论:《周易》的真正精神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研习、认识和传播《周易》。
二 《周易》在西方传播所选底本并非最优
从宋代开始,易学已由儒理派易学占据主导地位,其代表性著作为胡瑗的《周易口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等。与此同时,易图学也裒然崛起,其代表性学术便是刘牧的《河图》《洛书》、邵雍的《先天图》、周敦颐的《太极图》等。朱熹综合诸家之学而成《周易本义》。自元仁宗恢复科举考试,《周易》考试以程颐、朱熹两家易学为主,明、清两代基本延续这一定式。起初,程颐、朱熹两家易学并重,但科举考试喜简厌繁,朱熹《周易本义》因其简明,更为学人所看重,因而朱熹《周易本义》逐渐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明末以降西方传教士接触并翻译《周易》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展的。
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华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此后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华传教,促进了西学东渐,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明代朱谋垔《续书史会要》谓:“外夷利玛窦,号西泰,大西洋人。万历时入中国。侨寓江西,后入两京,卒葬应天。其教宗天主,性聪敏,读中国经书,数年略遍。”[2] 373所谓“读中国经书,数年略遍”,当然也包括《易经》在内,并且他可能是最早接触中国经书(包括《易经》)的西方人。林金水就认为西方传教士最早学习《易经》者,可能要推利玛窦。利玛窦多次谈到《易经》的内容,如他说: “《易》曰:‘帝出乎震。’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3] 367利玛窦坚持西方天主教信仰,以为中国经典如《诗经》《尚书》中的“上帝”即是天主教的“天主”,是宇宙的主宰者。上帝不等于天,而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中国人常常将“上帝”与“天”混为一谈是不对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援引《周易》“帝出乎震”的话,认为上帝是“出于一”的存在,而不是“抱四方”的存在。又,利玛窦曾说:“自伏羲画《易》以后,文王图位已错综互异矣。”[4] 533这足以表明利玛窦是曾仔细研读过《周易》的。
利玛窦去世之后不久,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来华,他曾在杭州组织刻书,其中有他所译《中国五经》一卷的拉丁文译本(Pen tab ilion Sinen se) ,五经当然包括《易经》。《中国五经》一书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出版。此译本后来下落不明。从文献的角度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实际见到清代以前的西方《周易》译本。西方《周易》译本的大量涌现,是在入清以后。
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曾于公元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在巴黎出版拉丁文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此书共412页,第一部分是柏应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献辞》,第二部分是106页的《导言》,其中13页介绍《周易》的八卦、六十四卦,并配有《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此二图属于“先天图”)及《文王六十四卦图》(此图属于“后天图”)。此外《导言》还介绍了宋代朱熹的理学和易学。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得到三点认识:第一,柏应理对于《周易》的介绍,是基于对朱熹《周易本义》的研究和理解,因为在宋代易学家中朱熹是最早将“先天图”和“后天图”同时并列于《周易》注本中的。第二,柏应理在《周易》注本的选择上,部分采用了朱熹的理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周易本义》载有《伏羲四图》(或称《先天四图》),除了上述《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之外,还有《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柏应理并没有介绍后两图。就此点而言,柏应理坚持了传统意见,伏羲只作八卦,并未作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为周文王所作,所以只收入了《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和《文王六十四卦图》。第三,柏应理介绍《周易》只用了很少的篇幅,严格地说,这只是一种对《周易》的概略性介绍,这种介绍还不能算是《周易》的译本。
欧洲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由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1663-1738)完成的,译本为拉丁文,其书竣稿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但直到一百年后才分为两册于1834年和1839年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出版,书名为《易经——中国最古之书》(Y-King,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 Quem Ex Latina Interpretatione)。实际上这个译本是在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和汤尚贤( Pierre-Vincent de Tartre, 1669-1724)不完整翻译的基础上完成的。法国学者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评论说:“是为中国诸经中之最古、最珍、最不明确和最难解者。雷孝思神甫利用冯秉正神甫之译文并用满文译本对照,参以汤尚贤神甫之解释,由是其义较明。”雷孝思译本中讨论了《性理大全》以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张载的《西铭》和《正蒙》, 邵雍的《皇极经世》等。[5] 123从其所讨论的内容看,雷孝思是从宋代易学的大背景来译介《周易》的,并且从其特别对《性理大全》等书的关注看,雷孝思是以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刊行的《御纂周易折中》为底本的。李光地的《御纂周易折中》又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吸纳了周敦颐《太极图》、邵雍的先天图的易学思想,而清代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皮锡瑞等大儒已经通过他们的著述批驳朱熹等人易图学的迷思。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39-1867)在1854年和1855年分别完成《易经》和《易传》英译初稿,因没有把握是否理解《易经》原意,在搁置译稿二十多年后,重新加以研究整理,直到1882年才在牛津出版,收入东方学家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主编的《东方圣书》第十六卷。[6] 923理雅各的《易经》英译本成为一个里程碑,在卫礼贤译本问世之前,它是西方研读《易经》的理想蓝本。李伟荣提出:“理氏翻译《易经》时采用的底本为朱熹的《周易本义》……通过通读理氏《易经》英译本,可以梳理出理氏在翻译《易经》时主要中文参考书目有:《御制周易折中》(李光地撰,1715年刻本)、《御制日讲易经解》(牛钮撰,1682年刻本)和朱熹等宋代理学家所著的易学著作。”[7] 126
李伟荣强调理雅各的《周易》译本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而以李光地主编的《御纂周易折中》为主要参考书。事实上《御纂周易折中》也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编纂底本,其中的区别在于,《御纂周易折中》是以朱熹《周易本义》为本来折中程颐、朱熹两家易学。虽然二程、朱熹的理学合称“程朱理学”,但在易学观点上,程颐、朱熹两家易学却有根本性的冲突,这一点恰是“底本之信”的关键处,且待后文解释。
西方人最好的《周易》译本是由德国人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1873-1930)所完成的。[5]128卫礼贤在晚清学者劳乃宣帮助下花了十年时间最终推出德文版《易经》,并于1924年在德国耶拿出版。此书克服了理雅各译文冗长、呆板、平淡的缺点,而呈现出简明和富有洞察力、表现力的特点,更好地把握了原著的精神实质。在德译本的“导论”中,卫礼贤特别谈到了清代的重要版本:“在康熙年间组织编纂了一个非常好的版本:《周易折中》,《经》和《十翼》是分开来处理的,并且包括了所有时代最好的注疏。德译本就是以这一版本为基础翻译的。”卫礼贤的中国老师劳乃宣基本上将《易经》看作“占筮之书”,卫礼贤也继承了劳乃宣使用《易经》占卜的做法。
以上简要介绍了西方有代表性的《周易》译本及其底本问题。当然,西方关于《周易》的译本远远不止这些。但笔者之意并不在于全面罗列《周易》西方译本的书单,而是要通过西方有代表性的《周易》译本来谈底本选择的问题。通过上述论述,亦可知道西方关于《周易》译作的底本选择基本是以朱熹《周易本义》或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为底本。李光地的《御纂周易折中》是以朱熹《周易本义》为编纂底本,而以程颐《周易程氏传》为最重要的参考本的。这里有必要讨论程、朱两家易学孰为优秀的问题。
从学术角度说,程颐、朱熹两家易学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程颐易学认为《周易》是“说理之书”,遵循了孔子、王弼、胡瑗以来的学术传承,完全不接受《先天图》一类内容;朱熹认为《周易》是“占筮之书”,其书首列有《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等九图,杂糅了陈抟、邵雍一系的易学。对于程颐的《周易程氏注》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两部书,当时学术界的评价是不同的。李光地奉诏主持编纂《周易折中》,以朱熹《周易本义》为本,这反映了康熙皇帝尊崇朱子的立场。与此立场不同,清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皮锡瑞等大儒皆推崇程颐的《周易程氏传》,而贬抑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周易本义》吸纳了宋代易图学的成果,将易图学九个图置于《周易本义》一书卷首。但他这样做,真的就符合《周易》本义吗?[8] 479
顾炎武批评说:
昔之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见及写录唐宋人之书亦有十数家,有明之人之书不与焉。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9]42
黄宗羲也说:
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于是而大定矣。其时,康节(指邵雍)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庵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官,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晦翁曰:“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10]2
皮锡瑞则说:
综上所述,学校管理成败与否的重要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因此对于学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要充分重视。学校领导要制定出适合本校发展的规章制度,全面地评价每一位教师,建立完善的人才考评机制,把经过实践考验证明合理的各类优秀人才及时选用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来,让他们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朱子以《程传》不合本义,故作《本义》以补《程传》,而必兼言数。既知《龙图》是伪书,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真图,既知邵子是《易》外别传,又使蔡季通作《启蒙》,以九图冠《本义》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粪佛头。[11]50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前的九图,其中有四图是伏羲《先天图》,因称《先天四图》。伏羲氏本是中国远古的传说人物,“伏羲画八卦”本是一种缪悠无凭的传说,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其图卦序与后来西方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相吻合),即托名伏羲自我作古而已。朱熹将之冠于《周易本义》卷首,这本是一种迷思,却因朱熹的崇高学术地位,影响其后几个世纪,甚至影响了包括西方如白晋、莱布尼茨那样的大学者。
朱熹的另一个迷思就是将《周易》看作“占筮之书”。《周易》可以用于占筮,但《周易》从根本上说是一部关于哲学智慧的“说理之书”,孔子、王弼、胡瑗、程颐等儒者皆如此对待。在“占筮之书”与“说理之书”两者之间,谁更符合圣人本意呢?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要》篇记载孔子之言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义而已。”[12] 279这清楚表明,孔子的易学传承乃是“观其德义”的“说理”之学。而在这方面,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做得最好的。正如前面所引黄宗羲所说:“逮伊川(程颐)作《易传》……《易》于是而大定矣。”
“底本之信”,当信何书?这对于中外易学家而言,都是应该认真思考的。
三 易学外部研究:以耶解《易》与以二进制解《易》
如上文所说,历史上易学发展可以略分为“两派六宗”,此“两派六宗”可以视为易学的内部研究。“两派六宗”之外旁及三教九流的学术,“旁及”的学术领域原本与《周易》无关,属于易学外部的学术体系“援易以为说”。这种情况在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西方学者解读《周易》,虽然自有其各自的学术立场,但也间接受到《周易》译本所依据的底本的影响,下面列举两例:
(一)白晋的以耶解《易》
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受过神学、语言学、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5年)来华,后被康熙留京供职,并成为康熙皇帝的宠臣之一。白晋对于中国古籍的熟悉程度,远超同时在华的其他传教士,康熙对他有许多期许。康熙曾说:“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通中国文理者,唯白晋一人稍通中国书义,亦尚未通。”[13] 173康熙曾传诏让白晋将《易经》翻译成西文,并多次关心此事,梵蒂冈图书馆中还留有康熙督促白晋的圣谕:“上谕。七月初五日。上问,白晋所译《易经》如何了?”“奏稿。初六日。奉旨问:白晋尔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化……臣白晋同付圣泽详细加研究。”后来传教士纷纷翻译中国经典,与当时的中国统治者鼓励传教士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政策有关。
白晋毕竟是天主教徒,他在研究《易经》时,时刻不忘其天主教徒的宗教立场。他把《易经》与基督教《圣经》相附会,创造了一种以《圣经》故事来解读《易经》的所谓“耶易”。将“先天”解释为造物主创造万物,将“后天”解释为救世主降生为人;将“伏”字解释为“人”合“犬”,伏羲乃是“犬首人身”的智慧之人;将《易经》八卦乾、坤、震、坎、艮、巽、离、兑解释为乘方舟逃难的诺亚一家八口(父母加三子三女);将《屯》六二爻辞“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解释为圣母玛利亚与上帝婚媾以生圣子;将《坤》卦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解释为圣子为拯救万民与邪魔相抗;将《需》卦九五爻辞“需于酒食”,解释为救世主行救赎之功等。[14] 59
(二)莱布尼茨以二进制解《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谈易学上的一个概念:“卦序”。所谓卦序,就是《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传统的《周易》卦序,首乾坤,终《既济》《未济》。而北宋邵雍发明了一种新的六十四卦排列顺序,首《坤》卦,终《乾》。他称传统的卦序为文王后天卦序,而称自己发明的卦序为伏羲先天卦序,他将这种卦序的排列画出来,称为《先天图》。而如果将《先天图》六十四卦中的阴爻和阳爻皆用“0”和“1”来表示的话,正好合于后来西方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的0—63的排列顺序。
德国大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于1701年2月26日向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交二进制论文,4月25日宣读。但4月30日科学院秘书长封丹内(De Fontenlle)给莱布尼茨回信对此文婉言谢绝,因为看不出二进制算术有什么用。(此信现存莱布尼茨档案馆)与此同时,莱布尼茨将他发明的二进制论文寄给远在中国的朋友白晋分享。白晋遂于1701年11月4日将《伏羲六十卦方位图》自北京随信寄出,莱布尼茨于1703年4月1日在柏林收到。(现存汉诺威莱布尼茨档案馆)
莱布尼茨看出图中六十四卦与其二进制数(0-63)的一致,认为他和白晋解开了伏羲图之谜,于是他立即用法文对其论文加以修改和补充,以《只用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阐释——和对它的用途以及它所给出的中国古代伏羲图的意义的评述》为题,于1703年5月在法国皇家科学院杂志上发表。[15] 133
莱布尼茨与白晋都认为中国在上古的伏羲时代已经有了二进制算术,后来失传。其实这个所谓的伏羲六十四卦图(即先天图)根本是由北宋邵雍所创,与先秦以来所传《周易》并没有什么关系。白晋、莱布尼茨所传播的都是朱熹一系的底本。朱熹不仅误信《先天图》传自上古伏羲,还将自己的迷思误导了后世学者,包括西方学者。

……
由此看来,邵雍《先天图》的卦序排列,的确非常奇妙。而这个奇妙之处,却是被莱布尼茨和白晋揭示的。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是一段美丽的佳话,然而这只是宋代邵雍的发明,与真正的《周易》无关。打一个比喻说,虽然十五的月亮非常明亮美丽,但月亮本身并不发光,那光亮是太阳投射给它的。虽然围绕《周易》有无数光环,但并非《周易》的本来面貌,那光环是外部投射给它的。
《周易》在跨文化传播交流中,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通过《周易》在西方传播的底本研究考察,可以看到《周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试借此文加以沟通,以期中、西方学者对此问题加以关注、思考和调整,进一步推动《周易》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