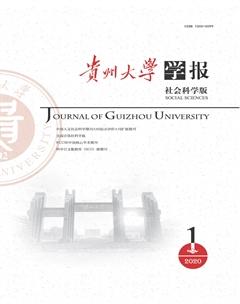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
摘 要:
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马克思超越了政治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方法,将正义的“价值”评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的考察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批判。马克思正义观的这一方法论基础决定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不是抽象的“形式”规范,而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总体”规范。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不是超然于生产方式之外的“自然正义”,而是在变革生产方式过程中将正义的价值理想内化于社会现实的“社会正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正义理论;辩证法;规范性;社会正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1-0019-07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s Justice Theory
in the Cr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GAO Guangxu
(College of Humanity,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211189)
Abstract:
Cr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provides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s justice theory. Based on the dialectics of “Changing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in political economics, Marx transcended the dichotomy of facts and values of political rationalism and incorporated the judgement of “value” in justice in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us to achieve the critics of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is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Marxs view of justice determines that the normative nature of Marxs theory of justice is not an abstract “formative”norm, but an “overall” norm that unifies facts and values.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Marxs theory of justice is not “natural justice”beyo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but “social justice”that internalizes the ideal of justice in social real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Key words:
cr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s justice theory; dialectics; norm; social justice
当前,隨着学界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深入,基于马克思正义观进一步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
尽管在如何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问题上学者们路径各异、观点不同,但是大都不否认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这固然是因为马克思有关正义的关键性论断大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展开,更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充分汲取并自觉运用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契合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内在逻辑,也是深入推进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内在要求。为此,本文从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可能涉及的三个基本层面,即方法论基础、规范性特质和理论形态入手,尝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为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做一些清理地基的工作。
一、“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
正义是一个古老且常谈常新的政治哲学概念。纵观西方政治哲学史,政治哲学家们虽然大都关注正义问题,但对于正义的理解却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我们看到,古典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对正义的理解不同,古典政治视域中的正义是“自然正当”和“先天德性”,近代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正义是基于社会制度安排形成的“权益之计”和“后天契约”。即使是古典政治哲学视域内部的正义理解也不尽相同,柏拉图的正义观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洛克的正义理解与卢梭也存在差别。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多少政治哲学家便有多少种正义理论。正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姆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罗米修斯似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
政治哲学家们的正义理论为何差异如此巨大?其中原因固然与不同时代的正义问题发生的背景紧密相关,但不同正义理论背后的不同建构方法更值得关注。正是由于政治哲学家们建构正义理论的方法不同,正义的理论形态才迥然有别。在这个意义,我们当前探讨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建构问题,就必须要对马克思理解正义的方法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
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方法论自觉,需要反思的前提性问题是: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是否必须在马克思持有积极和建构性的方法论立场,进而持有一种绝对的正义立场和原则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换言之,如果马克思不持有积极和明确的正义观点,或者说马克思认识和理解正义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支持一种绝对的正义原则,那么我们是否就无法建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对此,有观点认为,如果马克思在对待正义的问题只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那么建构建设性的马克思正义理论便不可能也不必要。也有观点认为,马克思虽然在正义问题上持有消极的或批判性的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建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马克思正义理论。
毋庸置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关正义问题的直接论述并不多,也没有著作专门探讨正义问题,而且,在仅有的几处关于正义的论断中,也大多呈现为论战性和批判性的话语形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正义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是一个可有可无或者只具有批判和否定意义的问题呢?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以重新还原马克思正义观点的论域为前提。实际上,马克思正是在与庸俗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围绕分配正义的论战中,提出了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截然不同的正义论域,而相关论域集中体现在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价值论语境中。[2]
马克思之所以总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探讨正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消极的或批判的层面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形式的辩护总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展开,强调商品交换的一般形式以及这一形式中的劳资交换符合平等自由的分配正义原则。同时,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们也总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合理性的质疑。而马克思的正义观正是在对以上两者的批判性分析中确立起来的。
另一方面,从积极的或建构的层面来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庸俗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正义的批判,总是基于对流通领域之外的生产领域分析,进而强调正义的支点不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不是劳动者对自身劳动的所有权,而是具体的物质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也构成马克思正义观的积极语境。
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正义观点的基本语境首先构成我们透视马克思正义观思想方法的载体。众所周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既不满足于表象的杂多,也不停留对表象的抽象概括,而是在对表象的抽象形式的自我运动的总体把握中,实现对对象的具体再现。“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
因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既不停留于事物自身呈现的混沌表象,也不是从抽象的形式方面把握事物。而是蕴含着两个环节,一是“从具体到抽象”,即从繁杂的表象中抽离出表象所具有的共同规定;二是“从抽象到具体”,即从关于表象的抽象规定出发,实现对事物自身发展逻辑和规律的具体性“再现”,这时所得到的“具体”与表象的具体不同,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在对于事物从“存在”(表象)到“本质”(规定)再到“概念”(具体)的总体把握中,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既不是一种科学实证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哲学思辨的方法,而是将对于事物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结合起来的总体性方法。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性辩证法,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考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统一起来,既实现了对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本质再现,也实现对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所支撑的正义观念的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個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4]
关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否表明马克思基于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国内外学界仍存在争议,我们这里暂且不介入这一争论,而仅从方法论层面来看马克思如何理解正义。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明确强调了交易过程中所遵循的正义原则实质是一种法权正义,这种正义实质是一种关于正当的形式确定性,也就是说它只就其自身保证交易形式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不能超出去决定交易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决定交易内容正当性的是生产方式。
这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为马克思正义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马克思对于正义的理解既不是从正义的表象出发,也不是从正义的形式规定出发,而是将在关于正义的形式规定与其内容的辩证关系中,再现正义与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换言之,马克思是在辩证法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总体性视角中把握正义,这就是,正义不是抽象的法权形式,而是内在于物质生产方式中的社会现实。也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马克思超越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方法论前提,将正义的“价值”评判纳入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的考察之中,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把握。
因此,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决定了,我们只有对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的总体性视角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才能既避免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阉割为一种非规范的描述性理论,又避免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玄思为一种与分配正义无涉的绝对价值。建构马克思的理论必须结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社会历史考察,即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撑的资产阶级分配正义的限度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限度。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构成明晰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特质的方法论前提。
二、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特质
如果说很难设想一种没有规范性功能的正义理论,任何的正义理论总是蕴含相应的价值规范,那么在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规范性的过程中,就需要对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法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对于马克思而言,如果基于正义去规范一种事物是可能的,这种规范并不是基于独立于事物之外的价值原则展开,而是内在于事物自身的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之中,探寻其自身的总体发展逻辑及其内在限度。对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这一规范性特质的理解,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
从一般意义而言,建构一种正义理论就以该正义理论对社会现实作为规范性的判断,因为正义尽管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但究其根本而言是一种价值观念,其理论功能在于对现实发挥规范作用。结合前文所述,马克思关于正义的基本观点是,不存在绝对和永恒的“自然正义”,正义的形态总是由相应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因而,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理论旨趣界定为建构一种规范性理论,那么这里就存在着这一理论旨趣与马克思正义观点相矛盾的问题。换言之,建构一种规范性的正义理论必须以绝对的正义观点为前提,而马克思探讨正义的思想方法决定了其拒绝将正义绝对化。结果,我们在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何认识和走出这一困境是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我们先来看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剩余价值虽然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秘密所在,也表明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但是却并不违反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原则。换言之,剩余价值仅仅是生产过程中的经济事实,其与分配过程中的正义观念无涉。如果把剩余价值与正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此建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这恰恰与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的相对性考察正义的思想逻辑相背离。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根本没有依靠某种正义概念,那些试图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诸多谴责中重构‘马克思正义理念的人,顶多只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换成被马克思本人一贯视为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或‘神秘的形式。”[5]29
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包含解释和评价两个层面,因此,应当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和运行机制的解释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区分开来。换言之,尽管马克思在解释的层面并没有对资本主义是否正义做出评判,但在评价层面则对资本主义做出道德层面的批判。所以,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配不公的道德批判和控诉。“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没有按劳分配,而且因为它没有在生产的可能性范围内满足人类的需要,更不用说满足生产者的所有需要。资本主义的分配安排,对于归属不同社会阶级的个人给予区别对待,这在道德上是应该遭到谴责的。” [5]76-77
不难看到,这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马克思是否基于正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造成对这一问题迥异解答的关键又在于如何认识和理解剥削或剩余价值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正是由于对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在能否建构积极的和明确的马克思正义理论问题上才产生了巨大分歧。如果剩余价值与正义无关,那么建构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就是虚假的,如果剩余价值本身意味着对工人有违道义的剥削,那么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必然诉诸道德立场。可见,英美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探讨,最终要么走向质疑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要么走向马克思道德正义理论的建构。
因此,澄清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理论旨趣,必须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剩余价值与正义关系的探讨。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是否持有积极的和明确的正义观点问题的全部复杂性都蕴含在这一问题中,而且这一问题成为决定我们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关键。
剩余价值是否正义既是探讨马克思正义观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也是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必须直面的基本问题。如果说马克思正义观的思想特质在于以唯物辩证法揭示了正义与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那么这一思想特质在具体层面就表现在回应和破解剩余价值与资产阶级正义观念的辩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过程中,应当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这一思想特质及其具体表现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必須直面剩余价值之于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意义,因为这一问题关涉我们究竟如何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怎样的马克思正义理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最为重大的思想发现便是剩余价值理论。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的社会主义者要么从事实层面只关注剩余价值所蕴含的价值量的比例关系,要么从道德层面只是谴责剩余价值有违道义和公平,马克思既不把剩余价值看作是一种经济学的事实比例关系,也不以抽象的道德标准对其作价值评判,而是从商品的价值形式剖析入手,基于商品价值二重性揭示商品内蕴的劳动二重性,进而资本生产过程内部剖析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机制,实现了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再发现,并由此推动了“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剩余价值理论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理论,它实际上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
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所追问的:“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作用呢?”这是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6]
可见,马克思对全部经济范畴研究的旨趣就是要推动全部经济学的革命,而马克思推动这一革命的钥匙正是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再发现。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再发现决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所实现的“经济学革命”,并在“经济学革命”的理论高度上实现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剩余价值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推动“经济学革命”的根本旨趣在于推动“社会革命”。因此,对于以“术语革命”为前提的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经济层面,因为经济层面的公平正义问题并不能完整呈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进而,剩余价值是不是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应得利益的道义层面的不满,是不是基于劳动所有权对资本剥削不公平性的谴责等问题,也不能完整呈现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旨趣。以剩余价值的再发现为基础,实现对资本主义作为剥削和奴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体现的总体批判,才是马克思正义理论规范性建构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表明,在剩余价值与正义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既不囿于经济学的实证视域关注剩余价值所蕴含的比例关系,也不囿于抽象的道德批判视域关注剩余价值在何种意义上违背伦理道义,而是深入到剩余价值作为资本逻辑的生产和再生产动力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与其分配正义之间相互支撑和相互否定的辩证关系,以此实现对资产阶级法权正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这一规范性特质决定了,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应当立足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建构一种超越“自然正义”的正义理论形态。
三、“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社会正义: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以辩证法探讨正义的方法论自觉,不仅为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提供方法指引,
而且为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奠定基础。马克思对于正义的理解始终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结合起来,强调正义总是相应生产方式中的正义,不存在脱离生产方式的“自然正义”。换言之,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视域中,正义总是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相一致,不同形态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具有不同形态的正义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建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形态必须紧密结合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
结合生产方式概念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需要明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众所周知,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政治生活是自由公民关于公共生活方式的言谈和行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始终被排除在政治哲学话语之外。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主要关涉的是人类的劳动,而劳动是满足人类私人生命需要的活动,与公共生活并不直接相关。所以,当阿伦特提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反传统在于“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以哲学的用语叙说“劳动解放”的思想家时[7],
她虽然是在强调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断裂,但是也确实切中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特质。这就是,劳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不仅是满足自身生命需要的经济意义,而且是人作为类的存在者创造自身类本质的政治意义。换言之,人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不仅创造了人的满足自身生命需要的物质资料,而且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人与他人、个人与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基于生产方式概念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不仅不能囿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而且恰恰要在重新理解生产方式概念的基础上重塑正义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形态。
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总是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排除在政治哲学语境之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注重对人类劳动生产活动的考察,但是这种考察却只是在特殊性的层面考察人类劳动生产活动的某一种方式,尤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既没有超越特殊生产方式以发现生产方式的一般概念,更没有基于生产方式的一般概念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因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于生产方式的关注实质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这种研究只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且将这种比例关系看作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内在机制,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而无法揭示这种生产方式所内蕴的矛盾,更无法揭示这种生产方式所支撑的价值观念的限度。
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传统均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而言,生产方式是表征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概念。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活动不仅为人类共同生存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这种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由于采取的生产方式不同,也构成认识和理解人类不同的共同生活方式的重要参照。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人们就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因为人们是什么样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也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8]
可见,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不仅构成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视角,而且构成认识和理解人以及人所创造的人类世界的解释原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明确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哲学意义的强调并非偶然,因为生产方式作为哲学概念的自觉运用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展开。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自觉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基本解释原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一般形式,在对“人体解剖”的过程中实现了“猴体解剖”。诚如列宁所指出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0]
由此可见,马克思之所以总是在政治经濟学批判语境下探讨正义问题,不仅仅是由于理论应对的需要,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解释原则所决定的。换言之,正是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包括正义在内的社会意识,所以对于正义观念的考察必然要立足正义所奠基其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进而,马克思对正义的考察始终与对相应生产方式的考察联系起来,也就是自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域考察正义的社会历史形态。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城邦时代,正义是社会的首要美德,是人类应当具有的“自然秉性”,换言之,正义是先天的德性而不是后天的制度,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和一项制度是否正义,就是判断这种行为和制度是否符合先天设定的公共善。随着古希腊城邦的没落和瓦解,经由中世纪政治生活的世俗化改造,尤其是近代以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取代公共善成为政治生活的首要价值,正义的形态也由“自然秉性”转变为社会为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权益之计”。正义不再是先天的德性,而是人们后天的约定,进而,正义的理论形态完成了从先验形态向经验形态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作为解释原则理解正义,意味着超越以生产方式的某一个环节尤其是分配环节理解正义的狭隘性,转而关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与正义观念的联系。因此,马克思基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理解正义,不仅在消极的意义上颠覆了古典政治哲学关于正义作为“自然秉性”的形而上学设定,而且在积极的意义上深化了近代政治哲学对于正义作为社会“权宜之计”的政治定位。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正义观念只有在商品流通领域内有效,一旦跳出流通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这种正义观念的“先天正确”背后的剥削和奴役实质就会暴露出来。因为流通领域所遵循的只是资本生产的一个环节即商品交换环节,在这个环节的交换价值的形式合理性保证了交换双方的形式正义。而在生产领域,资本生产的秘密即剥削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本质暴露出来,流通领域的形式正义幻相将被生产领域的实质不正义所击破。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过程来看,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不仅是一种物质财富的生产逻辑,也是一种生产资料与劳动相分离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逻辑,而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逻辑对生产逻辑所创造价值的持续占有,进一步强化了价值创造者与价值的分离,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撑的正义实质是一种为资本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自然正义”。
这种为资本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自然正义”的“伪善”之处在于,将本来奠基于相应生产方式的正义观念塑造成脱离一切生产方式的正义法则,将本来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权宜之计”的正义塑造为永恒的、绝对的公平正义原则。进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语境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建构了作为“公平”的正义、作为“平等”的正义和作为“德性”的正义等正义理论形态。这些正义理论形态尽管拥有相应的社会现实基础,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由于它们总是脱离其真正诞生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考察正义,在将自身包装成为先天的和永恒的正义的同时,也不过是在描绘“普罗米修斯经常变化的脸”的意义上塑造正义的抽象形态,而正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真实关系却始终被遮蔽。
由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于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意义体现在,既然政治经济学批判总是在揭示资本生产的内在矛盾过程中,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逻辑所支撑的法权正义视为“自然正义”的虚假本质,那么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就不仅需要直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危机,认清现代政治所秉持的“自然正义”的内在限度,更需要在重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将正义从一种应然的法权形式沉降为一种实然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不是超然于物质生产方式之外的“自然正义”,而是在相应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将正义的价值理想内化于社会现实之中的“社会正义”。
参考文献:
[1]博登海姆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2]高广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中的正义问题[J]. 哲学动态,2018(7).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9
[5]李惠斌,李義天马克思与正义理论[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0
[7]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2
[8]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68
[9]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10]列宁.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责任编辑:张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