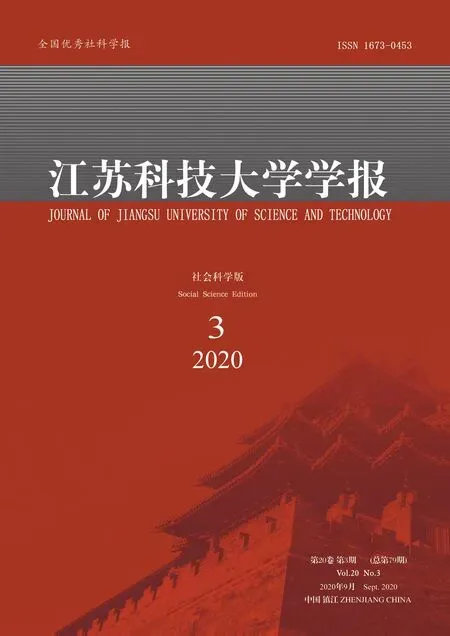浅析《南京条约》马儒翰译本的翻译对等性
郑观文, 刘梦晗
(宁德师范学院 语言与文化学院,福建 宁德355200)
《南京条约》是近代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割地赔款,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负担,破坏了领土完整。此后,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南京条约》展开了研究。国内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主要从国际法、中国的近代化、政治角度等对其进行研究。戚其章(1997)认为,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但没有促进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发展,反而将中国的近代化扼杀在摇篮里”[1];董临瑞(2014)认为《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晚清国人对国际法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靠近,体现出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西方国际法”时的“主权”意识[2];李育民(2016)探讨了晚清中外条约产生、条约实施和整体结构等外在形式,他认为这些“基本形态呈现了晚清中外关系的各种面相,既具有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属性,又引入了国际交往的近代模式”[3]。此外,学者们还从语言学和翻译学角度研究《南京条约》的中文译本。在专题论文方面,屈文生(2014)逐条考证了《南京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深入探讨了部分法律词语的翻译问题,重新为《南京条约》提供了一个白话文译本;邓文婷和张凌(2015)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即以翻译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承诺伦理的视角分析了《南京条约》的误译;陈顺意和马萧(2017)运用面子理论研究《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天津条约》以及《望厦条约》的翻译现象。他们认为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误译是英美译者有意为之,目的是使侵犯我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看起来“友好”,这样既照顾了清政府的“面子”,又掩饰了其豪取强夺的本质[4];刘霞(2018)从马建忠的“善译”理论出发,对《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中英文版本进行对比,探析其是否可以称得上“善译”,并探究其缘由[5]。在专著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季压西和陈伟民合著的《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2007)以及《中国近代通事》(2007)。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对于晚清不平等条约的研究成果不及国内显著。颇具代表性的论著有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TradeandDiplomacyontheChinaCoast(1969),书中对《南京条约》的形成、内容及实施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国外著作虽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行了辩护。
《南京条约》的中文译文有两个版本,第一版是1842年英国外交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负责起草和确定的,是中英双方使用的官方版本;另一版本则是由2014年华东政法大学屈文生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白话文译文。笔者以马儒翰的译文为研究基础,探讨其翻译对等性。
《南京条约》中英双语官本皆由英国外交官马儒翰为首的翻译团队主导,中方在译本翻译期间和翻译后,充当着文字上有限的共同商定者和条约批准者的角色[6]。马儒翰的父亲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英国来华传教士,他“精通中国语言和政治”,曾任“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兼译员”一职[7]。他去世后,儿子马儒翰子承父业,凭借着语言优势深受历任英国驻华都督的信任,协助他们在对华事务上出谋划策。与英方相比,时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到达广东后虽有一个语言服务团队,但团队中的成员要么师从于传教士,要么留洋于国外,林则徐不敢对他们委以重任。琦善继任钦差大臣之位后,干脆将这支翻译团队遣散,转而重用英语水平不合格且与洋商有密切往来的汉奸,造成中英交往的信息滞后。琦善获罪后,接任的官员们为避免犯相同错误而对本国翻译干脆一概不用,转而信任英方翻译,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的翻译们“通晓汉文,兼习汉语,勿须通事传话”[7]。至此,马儒翰顺理成章地成为中英双方的居中翻译。他的译文在风格上能够达到与源语的对等,但作为英国公民,他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并将自己的政治立场代入到译文当中,有意省译或误译部分词义,导致译本无法忠实于源文本,进而使目的语读者无法真实地了解源文本的意义和意图。
在古今翻译史上,翻译学家们对于“何为好的翻译”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不同的翻译学家提出了各自标准。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中给好翻译下的定义是:“原作品的价值要完全传输到目标语中去,使得目标语读者能够如同源语读者一样,清楚明白源文,产生强烈共鸣。”[8]37同时他还提出了三条通用的翻译法则:译文应完全再现源文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写作方式应与源文的特点相同,译文的行文应与源文一样流畅[8]37。根据泰特勒的三条法则,在翻译时,译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忠实于源文;若内容和形式无法兼顾,可以为了使表意准确牺牲译文的风格。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认为,在翻译领域夸大作者原意和译者主体性都是错误的,要从文本出发,强化文本在理解中的中心地位[9]。有鉴于此,笔者将以《南京条约》源文本为中心,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探讨马儒翰的中译本的对等性,借此为法律语言的翻译提供参考。
一、词汇对等性分析
秦秀白在《文体学概论》中指出,“法律条款,历史文献,议会以及重大的国际会议文件属庄严的冷冻文体(the frozen style),读者须经过反复琢磨方能领悟蕴藏在词句之中的层层含义”[10]。为了达到庄严的效果,法律英语常常使用古体词。古体词是法律英语的语言特色,其语义流传至今相对固定,可避免误解和歧义的产生,使行文更加准确、简洁。最常见的古体词是“here-”“there-”和“where-”三个前缀构成的古体复合词。《南京条约》签订于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该时期的英语词汇和语法特点与现代英语基本一致,都属于后期现代英语时期(1700—至今)。《南京条约》属正式的法律语言,源文本共使用了四个古体词(whereas、hereunto、hereafter、whereat)。“whereas”的本意是“鉴于”,一般出现在句首,作为正式文件的介绍性陈述,“hereunto”的本意是“在此”,这两个古体词出现在条约前言处,衔接条约签订的时间和地点。译者在翻译时将其省译了,没有忠实于源文。“hereafter”和“whereat”则出现在条款中,译者将其直译了。如第二项条款和第十项条款的“hereafter”被分别直译为“自今以后”“今又”;第三项条款中的whereat被译为“以便”。
除了古体词外,词汇重复是法律英语的另一大词汇特点。如“subject”一词,在源文重复使用11次,牛津字典将其定义成“a citizen or member of a state other than its supreme ruler”[11]。陈忠诚指出,“法律语言强调词汇的指称意义,为了实现法律译文语内连贯,避免歧义,译者须采用译名同一律原则,即词语一经选定就必须前后统一”[12]。但是《南京条约》的翻译马儒翰在翻译“subject”一词时,八次将其译为“国人”或“民人”或“人民”,三次译为“商”。如第五项条款出现了两次“subjects”,皆译为“商”。“国人”和“商”属上下义,译者将上义译成下义,可能使读者误认为清政府只需偿还欠英商的债款,而不是英国国人的债款。译者此处没有遵守“同一律原则”,不但使法律语言失去了严谨性,而且曲解了源文的意思,误导了目的语读者。
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是法律英语的另一大特色。由于英语单词具有一词多义的特点,为避免歧义,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可确保法律语言的准确性和庄重感,从而维护法律文件的权威和规范。《南京条约》源文本同义或近义词连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动词连用,如“careen and refit”(修补)、“demand and obtain(redress)”[讨求伸(理)],“publish and promulgate”(誊录)、“molest or stop”(拦阻);第二类是名词连用,“security and protection”(全安)、“(without)molestation or restraint”[(无)碍],“heirs and Successors”(世袭主位者)、“laws and Regulations”(法),“dealings and intercourse”(来往)、“provisions and arrangements”(和约开载之条);第三类是形容词连用,violent and unjust(proceedings)[不公强(办)]、“full and entire”(全然)。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使文本表达更加严谨,同时扩大了文本的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在翻译时只保留其中一个词的意思或者概括两个词同义的部分,避免语义的重复和累赘,体现中文法律文本的简洁性。
词汇特征的另一个体现是法律术语的使用。江丹指出,“法律术语是法律制度中核心的部分,是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析出并固定下来的,体现了人类法律文化的传承。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使用频繁,地位稳定,具有法律语言的特征”[13]。《南京条约》运用了许多法律术语,比如discharge(交纳)、perpetuity(常远)、successor(世袭主位者)、abolish(不必仍照)、insolvent(无措清还)、redress(伸理)、ransom(赎……银两之数)、confinement(被禁)、amnesty(免罪),这些术语在法律英语中语义相对固定,避免歧义,减少了法律适用上的任意性,体现了法律语言书面性强、正式化程度高以及形式确定性的特点。在翻译这几个术语时,译者采用直译法,忠实于源文的意思。此外,第八项条款中的“unconditionally”也是常见的法律术语,本意是“无条件地”,译者在翻译时理应保留原意,将英方要求清政府无条件释放英国人的强硬态度准确转达给目的语读者。但是译者轻描淡写有意省译,曲解了原意,违背了译者的职业道德。
除了上述词汇对等性差异外,译者在日期的翻译上摒弃了国际通用的新历,而是采用中国传统历法,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清朝的日期表述方式是帝王的年号及在位时间及农历的月份和日期,而英国日期的表达方式是公历的日期加上月份和年份。译者在翻译时,将英国的日期表达法转译成清朝的日期表达法。如“the month of March 1839”(道光十九年二月)、“the 1st day of August 1841”(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43”(癸卯年)、“1844”(甲辰年)、“1845”(乙巳年)。
二、句法对等性分析
从句子结构上看,法律英语所陈述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语言结构严谨周密,逻辑性强,使得法律英语的语句中长句多,且语句程式化,因此句子长度远高于英语句子的平均长度”[14]。王佐良和丁往道在《英语文体学引论》中指出,英语句子的平均长度为17个词[14]。《南京条约》十三项条款的句子平均长度为60个单词,最长的句子达到129个单词(第十条),每个句子包含了多个从句和平行结构,使用最频繁的从句是定语从句,十三项条款中共有16个定语从句,不但丰富了句子的内容,而且增加其逻辑性和严谨性。如第四项条款“……as the value of Opiumwhich was delivered up at Canton in the month of March 1839, as a Ransom for……Superintendent and Subjects,who had been imprisoned and threatened with death by the Chinese High Officers.(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1)参见Treaty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signed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t Nanking, August 29th, 1842。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关系代词“which”和“who”引导的两个定语从句分别紧跟着“opium”和“superintendent and subjects”两组先行词,限定了“opium”和“superintendent and subjects”两组事件,增加了句子的复杂性和长度。一般而言,汉语中定语的位置在所修饰的名词前面,但是由于此条款相对复杂的逻辑关系,若将其直译,会使得中文句子过于冗长,造成语义混乱,影响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将其转化成原因状语从句(因……)。然而译者在从句转换过程中有意张冠李戴,造成了读者对源文的误解。第一个定语从句本意是“道光十九年二月间被(英人)运送到粤省的(鸦片)”,但译者有意省略从句中的谓语,将其译成“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索出鸦片以为赎命)”,此译文并未交代英人在粤省贩卖鸦片毒害大清百姓的非法勾当,反而突出大清钦差大宪无理拘留并恫吓英人,逼迫他们交出鸦片以赎命,将事件的责任方推脱给清政府,译者有意颠倒黑白,以偏概全,极大地造成了源文和译文内容的不对等。
除了最显著的定语从句以外,《南京条约》十三项英文条款中还多次使用动词不定式的平行结构,它们前后衔接、相互照应,增加了句子的长度,丰富了句子的内容,使句子富有节奏感。如第二项条款“to reside at……, to be…… and to see……”,第三项条款“to be possessed……, and to be governed by……”,第五项条款“to abolish……, and to permit……”等,这些平行结构作宾语补足语,使句子更凝练简洁,富有层次。翻译时若保留平行风格,则会给目的语读者带来咄咄逼人的压迫感,因此译者摒弃了平行结构,将其译为普通的动词。
除了长句外,情态动词的广泛使用是法律英语另一大特色,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情态动词“广泛出现在国际法律文件中,如公约,协议,条约和合约等,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明确双方对于责任和义务的要求程度”[15]。《南京条约》源文中共使用了三个情态动词:shall,may和should。首先,shall在条款中的出现频率最高,共使用了14次,其中,第一项条款两次。第一个“shall”被省译了,第二个“shall”被直译为“必”,强调了和平共处是中英两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苏小妹指出,“shall”的使用指明了“条约规定性”的特点,并在法律语篇的概念性结构中强化了“义务”的概念性角色[16]。“may”在条款中的使用频率仅次于“shall”,共出现了六次。如第九项条款“……to release all Chinese subjects whomaybe at this moment in confinement for similar reasons.(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2)参见Treaty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signed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t Nanking, August 29th, 1842。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此条款中的情态动词“may”被省译了。按照法律文本中规定的情况或条件,may表达了履行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在此条款中,这种可能性指的是须释放与英国人来往而“可能”受监禁的中国公民。译者将其省译,将可能性变成一种肯定的语气,间接突出了英政府的强权本质。“should”在条款中出现了一次。“should”的原意为“应(该)”,在意思上与“shall”意思相近,在第三项条款“British subjectsshouldhave some Port whereat they may careen and refit their Ships(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3)同上。中,“should”一词表达了清朝作为战败国,向英方割地是其应尽的“义务”。译者在翻译时有意增加了“自”字,将其译为“自应”,目的是为了强调割地行为是清政府的“义务”。此处译文说明了译者虽作为中英双方的居中翻译,但并未保持中立的立场,而是带有明显的民族意识。
与英语中的情态动词相比,汉语的情态动词较少得到学者的关注。尽管如此,情态动词在法律语言中依然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刘红婴在《法律语言学》中指出,“应该”“可以”“不得”是立法的核心词汇,是“表述法律规范最为重要的语言材料,支撑着法律文本构架的主脉”[17]。《南京条约》译文中也使用了四个情态动词:“必”(第一、五、十一项条款), “应”(第三、七、十、十三项条款),“未能”(第七项条款)和“只可”(第十项条款),规定了英方要求清政府承担责任以及须履行的义务。
《南京条约》属法律语言,张长明和仲伟合指出法律语言的文本特点是“缺少情感、评论、讽刺等主观情绪,语言具有较强的程式性,以此达到规范功能的目的”[18]。被动句的使用正是法律英语客观性的另一个体现。当无需明确施事者时,法律英语常使用被动语态。但由于语言习惯不同,翻译时英语的被动句式常转化成中文的主动句,如:第二项条款“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shall be allowed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4)参见Treaty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signed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t Nanking, August 29th, 1842。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被动句的使用规定了英国人民有权居住在大清沿海的五处通商口岸。译者考虑到汉英句式使用的差异,将原意“英国人民被允许居住”转译为“大皇帝恩准……寄居”。通过语态转换,句子的主语变成“大皇帝”,而英国则“屈居”清政府之下,沦为施事动词的承受者;谓语动词由“被允许”转译为“恩准”。此处语态的转译没有传达出源文的意思,译者在翻译时有意添加了自己的政治意图,其目的是希望避免清政府在阅读此项条款时产生逆反情绪,潜移默化地使他们接受此项内容,从而达到英政府豪夺的目的。再比如,第七项条款“It is agreed that……; and it is further stipulated, that……”(酌定……则酌定……)(5)同上。。两个“it”引导的被动句构成了平行结构,并显示了法律英语的客观性。译者将“It is agreed that”(原意:经双方同意)和“it is further stipulated that”(原意:经进一步规定)两个被动句译成主动句,且保留了平行的结构,有意将其译成“酌定”,缓和了语气,使目的语读者认为此条款的内容是双方经过仔细斟酌后共同决定的。而事实是双方并没有商量的余地,所有内容都是英国政府单方面强加给清政府的。因此,虽然译者做到了忠实于源文风格,但是在内容上没有忠实于源文。
三、语篇对等性分析
从1844年《中国丛报》刊登的《南京条约》双语官方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中英双语版本在语篇格式上有较大差别:中文译本按照清朝奏折的书写习惯,采用从右到左的竖排书写方式;而英文源文则与现代英语书写习惯一致,采用从左往右横排书写方式。此外,中文文本在提及“大皇帝”和“君主”时,顶两格书写,以示对清朝皇帝和英国女王同等尊敬,屈文生指出文中的“大清”和“大英”空一格书写,“表示两国地位平等,无尊卑之分”[19]。相比较而言,英文源文则无此方面的考量,采用的是每一段空两格的常规书写方式。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中文版本与清朝奏折相同,不使用标点;英文文本标点符号使用频繁,语义划分更清晰,避免歧义的产生。在语篇格式上,译者考虑到了目的语的书写习惯,达到了风格上的对等。
在语篇衔接上,译者也考虑到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即英语注重形合,常用衔接词表明句子的逻辑关系;汉语注重意合,衔接词常常被省略,语义的表达也不会受影响。但在法律语言中,为了强化语篇的衔接,汉语和英语都会使用衔接词连接上下文。《南京条约》源文使用连词如“and”“when”,或者介词短语,如“for the purpose of”“on account of”等衔接上下文,译文常以“因……,今……”,或“凡……,今……”,“倘有……,则……”等词表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实现了内容和风格的忠实。
四、结语
鸦片战争期间,译才奇缺,清政府闭关锁国,“不知外国之政事,不询问考求,不知西洋”,愚昧地接受以马儒翰为首的英方翻译作为“居中翻译”[20]。译者马儒翰具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其“单向思考”性造成了《南京条约》的不对等翻译,尔后在条约解读上引起了国际纠纷[7]。译者,尤其是法律语言的译者,在翻译时应该以源文为中心,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尽可能地忠实于源文,若二者有冲突,则须舍弃译文的风格,保留原意,在词汇选择、句子铺排、篇章表述上尽可能地再现源文的真实意义和意图,因为“法律文本具有权威性和庄严性,只有译文实现了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才能使译文具有源文的规范功能和信息功能,才能使译文的接受者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避免对译文产生歧义和费解,保证译文的准确性交际目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