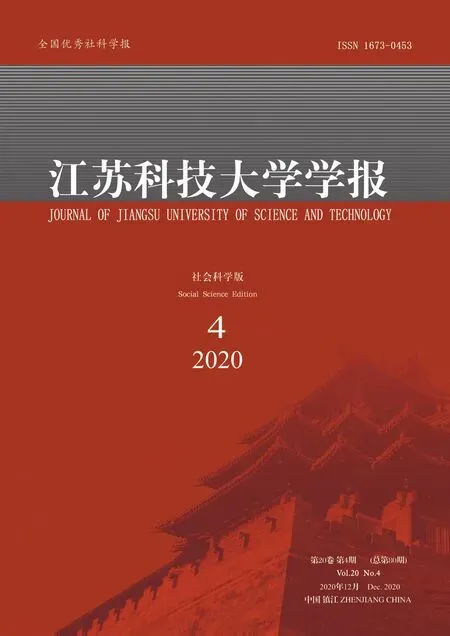从《甲行日注》中的死亡书写看叶绍袁的遗民心境与生死观
王萧依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明末苏州府(今江苏苏州)文人叶绍袁(1589—1648)的日记《甲行日注》详细记载了其于乙酉(1645)至戊子(1648)年间流亡途中的见闻经历与所思所感。目前研究者对这部日记的关注多集中于其遗民文学的特色与思想价值方面:如严迪昌《“长明灯作守岁烛”之遗民心谱——叶绍袁〈甲行日注〉》探讨了作者代表的东南遗民人文生态及日记独特的文学价值[1];陈雪《叶绍袁〈甲行日注〉的思想意蕴与艺术特征》从其家世、生平切入,分析日记所体现的爱国忧生之情及其简丽文风、优美意境[2];彭娟《从叶绍袁的〈甲行日注〉看明遗民心态》分析其选择逃禅的独立意志以及在怀古、吊古中的精神追求[3];李秉星《叶绍袁〈甲行日注〉的风景书写与抒情表达》通过剖析日记中写景抒情的深层内涵,揭示寄身山水作为一种“延宕帝国覆灭的时空策略”所承载的情感创伤和遗民体认[4]。事实上,《甲行日注》还存在尚未被关注的重要精神内涵,即其传达出的作者在遗民身份下独特的生命价值判断。“死亡”是这部日记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叙述情境和对象,家族成员的接连病故和抗清义士、无辜百姓的殉难死节都对叶绍袁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持续的、巨大的冲击。在对死亡事件的延续书写中,关于逝者的梦境是他缅怀、沟通死者的重要方式,鬼神传说则往往寄托着生者于现实中无力完成的心愿。值得注意的是,叶绍袁并没有选择成为他感佩、赞叹的殉节烈士,而是选择了隐匿于私人生活、江南湖山乃至佛禅之中,试图在私人语境中为自我生命和精神世界寻找最后的救赎。然而,因为其个人生死观与充斥着殉难死节的主流价值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痕,因而他短暂逃离死亡阴影的自我救赎愿望注定是要失败的,日记中的死亡书写也因此承载了明清之际士大夫个体悲剧命运背后独特的心灵史和思想史内涵。
一、 亲人之死与悼亡之梦——家国倾覆的双重伤痛与曲折表现
亲情是叶绍袁个人生命中极其宝贵的情感体验,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他晚年对至深亲情的书写几乎都是建立在亲人不断逝去的痛苦之上。在《叶天寥自撰年谱》中,他称自己“为子则藐而哭父,晚而哭母,为父则哭将嫁之女,将婚之子,为夫则哭妇”[5]821。这些死亡事件构成了他重要的书写对象。崇祯十三年(1640),其爱子世傛于变卖田产、求医问道无果后与世长辞,只留给叶绍袁那年冬天“大雪弥漫,松摧柏折,积地盈数尺,自望至晦,阴冻不开,冷亦异常”[5]859的刻骨记忆。三年之后,年仅四岁的孙女宝珠夭亡,五子世儋亦因科举失意而缠绵病榻,叶绍袁为其四处寻医问药,最终竟因医治不当导致病情急剧恶化,“语言即不能清楚,目不识人,惟呻吟呼痛,痛馀或呼母,或呼观音大士”[5]866。世儋于病痛中撒手人寰后,叶绍袁恸哭“虽欲以白发衰翁,代换儿命,何可得哉”,“死固无恨,得见先太宜人、亡妇、亡儿”[5]866。这种百身何赎的负罪感和无能为力的绝望在叶绍袁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伤痕。如果说王朝覆灭导致叶绍袁及许多文人流离失所,那么他个人的窘迫则直接导致了其他家庭成员得不到妥善的安顿与照料甚至失去生命。根据《甲行日注》的记述,自幼长于叶家并跟随叶绍袁流亡的小童张辰于乙酉年患病,作为家主的叶绍袁无力为其寻药,最终不治身亡。这件事极大地加重了叶绍袁的自责和痛苦,他坦言,“死生固亦大数,然使安然在家,即死,我亦不恨。患难追随,流离山谷,倘或故园可返,归计有期,亦何以为情乎?我悲与之同出,而不与之同入也”[6]924。家庭破碎、王朝覆灭的新愁旧恨不断叠加,构成了叶绍袁晚年情感世界及其文学写作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乙酉年末,叶绍袁“追溯平生所过除夕”所记,称庚午(1630)退休还家那年与老母妻儿团聚的除夕最为快乐,但随后就是不断降临的悲痛:
癸未,迁葬百福……幸两人得安吉地,足慰风木。而亡儋之痛,方新不能已。
最惨莫乙亥为尤甚,一岁三丧,泪痕相续……
又次则壬申,琼章脱屣尘世,又遭昭齐之戚,然同伤共悲,犹有亡荆在也。
又次则己卯,亡傛病深,就疗武唐,佺留视之。侗赘妇家,余与佺、倌、倕三幼儿,一盏黄昏,含愁卒岁。
在外度除夕者三,其一则甲子,公车是夕至任邱,同家廷尉、陆任吾、黄孺完、侄叔秀,高歌快饮……其二则己巳,皇华报命,虏薄都城,不能进矣……其三则今夕矣。国破家亡,衣冠扫地,故国极目,楸陇无依。行年五十余七,同刘彦和慧地之称,萧然僧舍,长明灯作守岁烛,亦可叹也。所幸父子相聚,兵燹暂远,但求不愧天地,不辱父母,不负二祖列宗,虽不能死,稍以自尽心亦此已矣。[6]933-934
作者回忆了他从享受天伦之乐到接连失去至亲至爱、从同年举子高歌痛饮到国破家亡知交零落的“痛”“泪”“愁”“悲”。在风雨飘摇之中,尚在人世的亲友越来越少,他的侥幸和希望则越来越卑微。
对死者的强烈怀念化为了频繁出现的梦境,这是生者与死者沟通的唯一渠道,而短暂虚幻的重逢最终留下了更为深重的寂寞和失落。在叶绍袁的笔下,与爱女小鸾有关的梦是最为凄美悲哀的。小鸾病故于崇祯五年(1632),叶绍袁于次年的年谱中记述了他于七夕之夜梦入仙境、偶遇小鸾,却于悲喜交加中发现她“迭呼不应,珊珊响佩环去矣”[5]849。随后他从镇江一僧人处听说此梦预示着小鸾已成仙,这一说法此后成为叶绍袁坚定不移但实际上又苍白无力的心灵安慰。在他人生最后一年的八月二十日,叶绍袁又梦到了小鸾,她留下了半阕《浣溪沙》词。词云:“愁绪懒拈残画叶,病怀新著怨秋辞,断肠花落梦相思。”叶绍袁不禁叹问:“仙人亦有愁病耶?抑为我慨也?”[6]1031亡者在梦中的情感表达实际上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叶绍袁自己的愁病感慨。叶绍袁曾于丙戌年(1646)六月初四梦到妻子为侍儿银针作挽诗云:“为雨为云事已休,楚台空结雨中愁。生怜丽玉随黄土,自怨明珠堕翠楼。仙去夫人方士帐,魂来倩女使君舟。谢娘泣断金娥冷,一任椒华镜黛收。”[6]950诗中有颇多“使事不伦”之处,而现实中其妻已亡故十二年,年方十六的银针则娟然在世。梦中生者和死者的错位实际上是叶绍袁对亡妻的思念在侍女身上的曲折投射。
家人的死亡以及相关的梦境是叶绍袁日记中最为私人化的情感表达场合。“梦”对于叶绍袁来说,大抵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字眼,而满载他美好回忆的午梦堂则无疑是亲情体验最核心的依托。被传为佳话的《午梦堂集》是叶绍袁家庭生活的美好回忆和家族创作的结晶,但其整理刊刻却直接源于妻女的逝去,因而其本身更是成为了世事无常的见证者。在乙酉年的流亡开始前,叶绍袁于仓促之中对无法带走的家人与财产作出了若干安排,其中就包括“《午梦堂集》六本授达元,为护藏之”[6]919。而在丙戌年四月十六日,叶绍袁收到家人来信,得知清兵闯入家中,“将书橱悉毁,简帙抛零满地,《午梦堂集》板碎以供爨,愤余贫而无物,以逞恨也”[6]945。这个“梦”从诞生到破碎的经过实际上是叶绍袁个人命运与明王朝存亡的缩影,那些细碎而凄婉的个人悲剧书写或许并不具备慷慨悲壮的史诗效果,但依然可从中感受到一个对家国倾覆无能为力的文人在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体验,这是无比宝贵且鲜活的个人化的历史。
二、 殉难死节与鬼神传说——复杂遗民心境的投射与表达
不同于私人语境中书写至亲至爱离世的巨大悲痛和失落寂寥,当对死亡的书写转向公共社会、文化语境,同僚旧友、素昧平生之人或是距离他相当遥远的古人的遭际和生死抉择都带给了叶绍袁另一种意义的冲击,使其遗民心境的内涵更加复杂。叶绍袁似乎从这些死难者的精神中看到了最后一丝人心可救、故国可复、故园可返的希望,但当惨痛的现实一次次将他淹没,他的焦虑、绝望乃至走向狭隘的报复情绪都在其对死亡的记述中浮现出来。在叶绍袁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的同僚、同年、挚友接连殉难:
(乙酉九月)三十日,戊寅,晴。客有谈王孝廉昭平、陆大行鲲庭俱殉节死。陆郎北府之年,尤为难耳。山阴刘、祁二中丞,则先于七月间,一谢孤竹之粟,一捐沅江之袂矣。[6]923
(丙戌)十二月初二日,甲戌,晴……武进乡同年韩不挟嗣子公严亦僧服同谐孟在,言江东事,极推重余武贞经世之略,有道之品也。城破,自投水死,不愧第一人矣。金华被祸最惨,张玉笥阖门死之,虏车裂马士英以殉,快哉![6]967
(丁亥八月)二十二日,庚寅,晓雨,晴,晡又大雨。侗来云:“顾大鸿、仲熊云间被害,时兄弟争死,辨海上诸札,皆出己手,与父无与也。虏酋亦相顾咋指叹。”机云河桥之后,又有此二隽。[6]1003
(戊子闰三月)二十九日,甲午,晴……云华超凤以族中起义,虏执之不屈,被害。伤哉![6]1021
在这些文字中,叶绍袁毫不掩饰他对于殉国义士的感佩痛惜之情,对同样作为汉人而惨死的马士英则怀有类似报仇雪恨的快感。然而他所恨和所惜之人的死亡实际上是由同样的现实所导致的。这不得不说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日记中还记载了大量在国破家亡之际沦为牺牲品的无辜女性。她们中有的是遁入空门的名门闺秀,也有许多人仅仅是普通百姓,如在清兵来犯时投水而死、年仅二十岁的侄孙元丰之妇钱氏,被丈夫锁闭家中一同自焚的吴山郡吴某之妻,以及在乙酉年集体投水殉节的400余名昆山妇女。对于她们,叶绍袁的态度大抵还是赞叹多于同情。日记中还记述过清军劫掠官宦家孙女打算贩卖却被地方武装势力半途劫走的事件,并认为这一命运“犹胜于北行”[6]982。尽管叶绍袁对自己的妻子、女儿充满了疼惜、爱护和尊重,但他对女性整体生存状态和个人价值的评判依然无法摆脱将其视为男权社会依附品的根本原则。我们很难想象,倘若宛君、小鸾等人活到明亡之后,处于与这些无辜女子同样的境地时,他又会进行怎样的抉择和书写。
丙戌年五月,叶绍袁听说“金阊有商航,载大松木,皆是孝陵园中物”,痛惜“谁无心胸,其能忍此”[6]948。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心之变对于叶绍袁来说是比个人苦难更加绝望的事,他对此非常敏感、警惕且焦虑。在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他清晰地记录了民风之变:
……仲日言:“郡中骄淫之习,殆不可言。闺阁具用貂鼠襭额,以效虏风。洒线绣衫,不但女子服也,丈夫奇锦,作小袖衣,必加半臂,制纫精工,花鸟炫艳之极。戏剧较前益多,画船箫歌,外室无虚夕,饮食若流,非盈方丈,不御匕箸矣。”噫!风俗由人心而成,人心已死,杀气安得不生!虏未足以厌之,而又恃虏以恣其毒欤?且若有朝不及夕之意焉。[6]966
戊子年二月十一日叶绍袁又记:“平湖郊外,盛作神戏,戏钱十二两一本,国难未纾,居然忘用夷之变,人心尽亡,岂止贾太傅之哭哉!”[6]1015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希望通过对义士烈女的表彰来激励遗民的反清恢复之心。如丙戌十二月十一日记载钱其若、黄蜚、顾子凝、王畹仲等人皆于战争中壮烈殉难之事,他认为,“中兴茂典,似当首加崇恤,阐既往之幽贞,励将来之臣节”,否则“人心士风,至今日顽钝无耻已甚,何以障狂波而反正欤”[6]968-969。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新王朝统治下的民众逐渐恢复了原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活动,甚至奢华更胜往日,叶绍袁所亲历、亲睹、亲闻的义士烈女的悲壮经历也必将逐渐淡化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文学作品中的故事。
当重振人心、恢复故国的愿望最终落空,古往今来的殉国死难者便化为传说中的鬼神,这也成为叶绍袁最后的精神寄托。在流亡之初的乙酉年九月十四日,叶绍袁记述过一个关于钱江畔神女庙的传说:
……神女,倪氏处子也。宋高宗初,兀术追至临安,女避乱出奔,旋死,埋半山下,即托梦诸将帅:“必速决战,我以阴兵助汝。”诸将异之,遂战,果以神助获胜,共为立祠。至今庙貌不毁,然香火冷落甚矣。余谓正当葺其土木,冀明鉴于神焉可也。[6]1014
在与北宋覆亡相似的社会环境中,作者将破碎殆尽的希望托付给了虚幻的神女之梦,希望通过修葺她的祠庙来重获庇护、再图恢复。丙戌年十月初七日,叶绍袁记载了他从流亡故友处听闻的一则鬼魂于酒宴间告诫诸人“此犹明朝故恩也,诸君岂无念哉”的传说,实际上是借此来谴责“今之鲜衣美食者,皆自以为人也,乃良心死尽,不如鬼欤”[5]960的社会现实。次年六月,叶绍袁记述了另一个鬼魂的故事:
二十三日,壬辰,微雨……当湖胡伯时,纂辑死难诸臣事,忽其兄子患病,有鬼附之,自称李乾德,欲见伯时而来。伯时至,则病者起而揖,分宾主坐云:“受命任偏沅巡抚,渡江则胡骑躏金陵矣。有二十二姬侍及二子,俱沉江中,以孤身督兵决战,将士溃散,亦投江死。乃有加以李陵之辱,此何可忍!偶过槜李烟雨楼,见有人言,公辑死事传,故来悉之,幸白此情事也。”仍揖而别,病者如故。夫人臣忠义,碧血千古,自不甘猥流污蔑。但伯时何人,岂湘东金管,遂能感动幽冥,至今范蠡湖边,英魂相告耶?[6]998
在这段记述中,叶绍袁有意突出了李乾德生前孤军奋战、携家殉难的悲壮,更强调了“纂辑死难诸臣事”这一举措对于延续生者和死者存在价值的重要意义。有时,鬼神传说甚至成为帮助复国无望的遗民发泄仇恨的工具,他们以极具戏剧性又颇为扭曲的方式兑换短暂的心理安慰。如,他在戊子年闰三月初六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昆山顾宗伯殉难后其子降清为官一事,宗伯鬼魂“责其隳节义、忘忠孝,立击而死”,作者感叹“忠魂英爽,耿耿不湮如此”[6]1019。尽管这样的行为对于挽救王朝危亡、解除民生苦难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但对于饱尝痛苦的个人来说,它所蕴涵的精神力量不可小觑。这种报复性情绪也是明末遗民心境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三、 “死亦难言之,姑从其易者”——个人价值抉择与明末士人生死观的矛盾
尽管《甲行日注》中充斥着如此多的死亡记述,但叶绍袁从未流露过放弃生命的念头。这在明亡之际的士风环境下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一章“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的“生死”一节中专门讨论了明末从崇祯皇帝到匹夫匹妇的生死观念和现实处境。作者认为,他们无不处于道义、道德重负与舆论压力之下,皇帝的“死社稷”或许还有几分主动权,而人臣无可选择的“死封疆”“死城守”实际上是对明初文人高压政策和严苛政治环境的一种延续,所有的政治、军事、社会、民族问题都被简化为道义层面上的生死抉择,死亡成为在这一时期具有高度笼盖性的核心话题,大批“可不死而死”的文人集体自杀以赴义,这实际上是明代士人轻死重节的普遍思想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这大语境被宋明儒学亦为明儒、明代士人的常谈营造已久,作为道德律令亦作为士人的世界观,在明亡之际‘规定’了士人的行为方式”[7]。不难想象,像叶绍袁这样曾浸润于晚明士风与文化氛围中的文人变成“不即死”的遗民后会承受怎样沉重的精神压力。
当然,没有选择死亡的遗民绝不止叶绍袁一人,他们各自也都有其种种原因或借口,如赡养父母、抚恤孤幼、存续文运、再图中兴等。这些话题在《甲行日注》中也有过不同程度的表达,但这些都不是叶绍袁不赴死的真实动机。在《甲行日注》的开篇,叶绍袁对自己在国破家亡之际选择剃发出家、遁入山林的原因有过这样的剖白:
……是臣子分,固当死;世受国家恩,当死;读圣贤书,又当死。虽然,死亦难言之,姑从其易者,续骆丞“楼观沧海”句耳……于是决计游方外亦遁,时八月二十四日。[6]918
我们虽然不能肯定叶绍袁究竟是出于恐惧还是仍心怀希冀才没有一死了之,但可以确定的是,他选择剃发出家实际上是作为一种逃离世俗的仪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皈依。他遁入山林,也不同于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归隐,而是流亡于那些在战乱中侥幸逃过一劫的山林湖泽之地,和与他同样流亡于草泽中剃发为僧或暗谋反抗的文士一起交游唱和,以此作为延缓个人生命和群体精神终结的暂时性手段。然而这一切的最终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这一充满矛盾和纠结的选择本身具有深刻的悲剧根源,也就注定了这条道路无法为他带来精神解脱,只能将他引向更加痛苦的窘境。正如彭娟在《从叶绍袁的〈甲行日注〉看明遗民心态》中所说:“选择全身而遁成为遗民,这事实的本身又让敏感的他们感到了自身存在的无力。他们的孤愤对于改变现实没有意义,他们的存在与才智未能形成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国家的危机,始终有着悲剧意义。”[3]
既然选择了生,叶绍袁就要为其生的方式和结果作出尽可能完善的规划,以免枉费他付出的精神道德层面的代价。他在离家前作出了一系列安排:“三幼孙藏之他所,冀存一线……以两先人及亡妇子女遗像七轴、家谱一帙、诰敕六轴、余诗文杂著八本、《午梦堂集》六本授达元,为护藏之。顾夫人与公子……当令善返昆山耳。诸妇女可寄西方尼庵。不腆数亩与环堵之室,不暇计矣。”[6]918-919而对于归隐之地的选择,他也有过一番纠结,最终表示“我吴人也,不可更入矣。其湖与杭乎”[6]920。叶绍袁委托家族文献的场景也许会令人想起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所记的赵明诚在分别之际的嘱托,但叶绍袁带不走又放不下的东西并没有那么沉重或昂贵,它们的珍贵几乎只存在于叶绍袁的私人及家庭世界中。这实际上也暗示了叶绍袁没有选择殉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家庭情感和个人生命在叶绍袁的考量中至少不低于礼、义、节、忠等儒家道德守则的地位。他最终选择了一种看似折中的道路来尽可能保全其所爱、所念与其无法搁置的士人操守。在这样的心境和现实状况下,归隐山林只能充当暂时缓解焦虑和绝望的安慰剂,而不能提供自我救赎的最终归宿。叶绍袁对此心知肚明,尽管友人劝说他“泉石自娱,毋久陨忧时之泪”[6]924,但在日记中他对所到之地风景的描写却总是萦绕着其对个人遭遇的伤怀、家庭破碎的悲痛和国家覆灭的黍离之悲。与此同时,现实中的危险信号也持续刺激着叶绍袁的神经,如丁亥年四月二十五日“闻虏于山中索九人焉,杨维斗、薛谐孟、姚文初、陆履常、顾端木、吴茂申、包朗威、惊几及余”[6]992,次日得知实乃谣言,却仍担忧“人言籍籍,山中不可以久留”[6]992。这段记述从侧面表现了他恐惧死亡、尽力保全生命的真实心态。
曹淑娟在《孤光自照——晚明文士的言说与实践》一书中曾通过分析众多晚明士人的日记、年谱、自传、自作墓志铭等自叙传文来解读他们的生死观,其中的刘忠、胡应麟、张自烈、杨涟、杨继盛等人在不同的生命困境中展现了直面死亡的姿态,代表了当时重节、重道而轻死的思想潮流,这与随后的陈函辉、瞿式耜等遗民毅然选择殉难来确认社会身份有密切关系[8]。但易代之际社会急剧变动造成的生死二元的极端思维方式并不能统摄每个文人个体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虽然不论逃禅还是逃生,其在明亡之后的士人舆论中都遭到了相当程度的批判,但仍然有许多遗民选择了这一道路,他们基于个人价值抉择而体现出的对生的渴望并没有完全让位给大环境对死的号召和导向。就遗民生存价值评判来说,全祖望曾表示“使必以一死一生遂歧其人而二之,是论世者之无见也”[9],王夫之则借由对宋代四隐士的 “时”“志”“行”“品”[10]的评价来揭示当下隐逸一途的价值之所在。就个人出处抉择来说,当时亦有如陈确拒绝标榜自己放弃举业、皮熊祝发为僧暗图恢复等并未选择以死明志的士人案例。他们并不宣扬死亡的道德性,而是在探寻每一种生存方式中的个人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在对自我生命价值进行界定和说明。在士人个体生命价值逐渐从主流舆论中浮出的过程中,叶绍袁的纠结与矛盾颇具时代性和典型性。
邓实在为《叶天寥自撰年谱》所作的跋中这样总结叶绍袁晚年的写作和生存状态:“先生以憔悴幽伤之思,自述其琐尾流离之况,所载园亭花木、文酒唱和、门庭琐故,皆不胜盛衰兴废之感。亡国诗人,伤心秀麦,盖莫不有深意存乎其间。至其触境寓愁,移情仙佛渺茫之事,则固有讬而逃,读者略跡而原心可也。”[5]916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甲行日注》。日记中大量的死亡书写,当然存在迎合大环境下重节轻死的主流价值观的态度,但回到个人语境中,比起考虑“死”或“怎样死”,叶绍袁恐怕更愿意考虑带着对“生”的美好回忆和微弱的希冀,尽可能久地逃离死亡。对死的书写实际上强化了对生的珍视。这可以视为士人个体价值话语在大环境下的思想世界中挣扎的信号,《甲行日注》也恰恰因此可以作为研究明遗民复杂心境的一个独特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