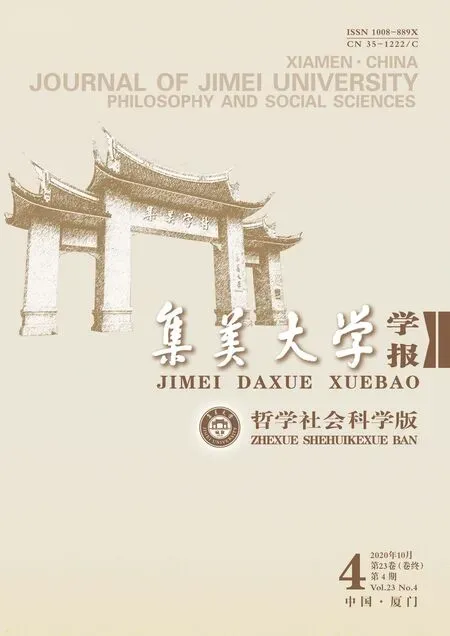论弗洛姆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及意义
郑清清,唐 瑭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弗洛姆综合精神分析法和社会历史研究法这一方法论创新本身就是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冲击。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过度维护“唯物主义”的原则,忽视甚至排斥对精神领域的关注,以至于将对精神领域的关注直接等同于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立场。但是,通过回到弗洛姆的“社会性格”与“社会无意识”等具体理论,我们就会发现弗洛姆的社会性格是连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媒介,而社会无意识理论中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无意识”这一基本原则的坚持也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关系的补充与发展。可见,弗洛姆对精神领域的关注并没有动摇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与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的确证。
一、精神分析的视角不等同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
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继承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精神分析法的运用给弗洛姆招致了一些误解。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固守“唯物主义”原则的学者认为弗洛姆对精神领域的关注就意味着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忽视,必然会导致对社会研究的片面性。具体到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上,这些学者对弗洛姆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社会性格的立足点是抽象的人性,即以心理需求为根本动力的人性而不是根植于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人性,这就直接导致社会性格作为一种精神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去影响社会发展,于是,他们就断定弗洛姆忽视了社会基本矛盾对社会发展的客观影响。换言之,他们认为,将社会性格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除此以外,学界对弗洛姆的批判还集中在他的社会改革理论,弗洛姆认可弗洛伊德对整体的重视,于是在社会改革上主张整体改革:经济、政治、文化并举。一些学者认为弗洛姆主张采取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就表明了他的思想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残余,具体考察他的改革举措,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不可行的,因而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
但是,精神分析的视角以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甚至于社会改革措施的不合理性,都不足以构成判定弗洛姆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充要条件,而这些学者对弗洛姆的误解,实际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解读。这一点弗洛姆其实早有提及,他指出,西方社会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对物质的推崇与追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动力,实际上这也就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学界对弗洛姆的误解的基本逻辑实际上就是这种观点的变体,因为只有将物质因素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才会将对意识形态的关注直接等同于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
实际上,当弗洛姆跨越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意识到精神分析法的局限性,并吸收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意味着弗洛姆对精神领域的关注不是以忽视物质领域为代价的,实际上,他试图从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出发来解释精神领域的现象。弗洛姆从弗洛伊德向马克思的跨越在他的社会性格理论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他批判弗洛伊德对性格形成的研究并没有将人置于社会历史的条件之中,而是置于家庭这一背景中,并且弗洛伊德也没有将家庭视为社会的缩影。弗洛姆吸收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法,认为人的性格的形成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同时也认可家庭的中介作用,并将家庭定位为社会向个人传递影响的媒介,正如他所说,“家庭本身也是由阶级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它只是一个社会代理处,其职能是将社会性格传送给婴儿——即使是在婴儿与社会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之前。”[1]66由此可见,弗洛姆在对人的性格的研究中,就已经超越了弗洛伊德将个人置于家庭中的静态研究法,将性格的形成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也就表明弗洛姆意识到弗洛伊德研究的局限性,并开始向马克思跨越。换言之,弗洛姆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的跨越就表明固守“唯物主义”原则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者将其划为历史唯心主义者是不合理的。
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歧表明弗洛姆与其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么排除形式上的差异,弗洛姆的思想能否被划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呢?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通过回到弗洛姆自身的思想,我们发现他的核心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大体一致,这些观点也就成为了确立弗洛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有力论据。
具体说来,弗洛姆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首先体现在他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解读上。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文中,弗洛姆在回应“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涵”这一问题时说道:“它的确意味着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地生活着的人——不是由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历史规律这一观念的主题”。[2]30在此,弗洛姆虽然没有指明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仍徘徊在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但是在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时明确了意识形态的附属地位。同样是在这一篇文章中,弗洛姆指出:“某些经济条件,像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对金钱和财产的欲望,这种欲望成为人的主要动因;其他的经济条件可能产生恰恰相反的欲望,如禁欲主义和对世俗财富的轻视,正像我们在许多东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所发现的那样。”[2]29这里弗洛姆就明确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明确表达了不是思想观念决定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具体的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思想观念。至此,弗洛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得到较为明确的体现。
在社会性格理论中,弗洛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得到了更具体的阐释。弗洛姆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经济制度是决定社会性格的主要因素,社会的经济制度不同,它所形成的社会性格就不一样。譬如,19世纪的社会性格是竞争、贮藏、获取、权威、侵略和自私;20世纪接受型和市场型的社会性格取代了19世纪获取型和贮藏型的社会性格,这是因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激增、资本日益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升,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性格的改变。由此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在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中得到了体现。
虽然弗洛姆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都坚持唯物主义,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经济决定论”的嫌疑,它看到了生产力对经济结构的决定性作用,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形态及其运动,忽视了生产力与人的关系,甚至为了坚持“唯物主义”原则,将复杂的社会运动还原为单向的经济运动。而弗洛姆则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上将经济以外的的因素吸纳进来,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体现出来,这就赋予历史唯物主义更丰富的内容,使其更接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二、社会性格理论: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发展
弗洛姆所提出的社会性格之所以具有联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可能就在于它的形成过程。弗洛姆认为,社会性格是个人心理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具有不同的社会需要,社会需要借助于社会性格向社会个体传递,从而使得个体具备使社会有效运行所应该具备的性格特征。
具体而言,社会性格作为某一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的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是作为一个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的结构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连接社会经济结构与个人心理结构的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经济结构通过社会性格向个人传递社会需要。在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了维持该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发展,需要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具备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征,这就是弗洛姆所提出的社会性格。社会性格相比于社会经济结构而言,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更为直接,它将社会需要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心理需要,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个人性格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促进个人行动的内驱力。当社会个体遵循社会性格所显示的社会要求行动时,社会会给予积极的回应——物质方面的回报或者精神领域的鼓励,这就使社会成员进一步坚定社会要求的合理性,从而对社会的经济结构起到巩固的作用。(2)个人的心理结构也要通过社会性格才能发挥作用。社会性格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引导作用,并使人依据社会性格行事时心灵能够得到慰藉,认为按照社会性格行动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行动。换言之,个人借助于社会性格完成了个人的社会化,当个体按照社会性格行动时,并非有意识地遵循社会要求,因为社会性格已经将社会要求内化为个人的心理需要了。
综上,社会性格的存在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个体的心理结构与社会的经济结构之间无法实现直接的沟通,而社会性格既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宏观的客观物质需要,又反映了个体心理结构的微观的主观精神需要,这就使得社会性格能够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与个人心理结构之间的中介。
社会性格形成于个人心理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成为两者之间得以互动的中介,这就为社会性格成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桥梁奠定了基础。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承认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论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们更侧重于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坚守。弗洛姆则在他们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如对“经济基础如何能够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弗洛姆认为社会性格理论可以起到联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他提出:“社会性格是社会经济结构和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各种观念、理想目标之间的中介。它既是从经济基础过渡到各种观念形态的中介,也是从各种观念形态过渡到经济基础的中介。”[3]换言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性格,并借助于社会性格对经济基础产生客观的作用,因为社会性格既体现了个人的本质需求又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经济基础也需要借助于社会性格对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发生作用,因为经济基础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维度,它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没有客观形态的维度——相对平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是天然成立的,需要社会性格这样兼具客观与主观属性的中介参与其中。由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社会性格的沟通下才成为可能。
对于社会性格沟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过程,弗洛姆阐述道:“变化中的社会条件导致了社会性格的变化,即因此而产生了新的需求和忧虑,这些新的需求又引起新的观念,并且可以说,又使人格接受了这些新的观念;而这些新的观念反过来倾向于稳定和加强新的社会性格,倾向于决定人的行动。”[1]382在此,弗洛姆更加清晰地揭示了经济基础、社会性格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的改变引起社会性格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社会性格吸收并传递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性格特征,社会性格的变化引起了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改变也必然会对社会性格产生反作用,从而借助于社会性格对社会成员的行为造成影响,并借助于更广范围的社会成员的生产活动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
综上,弗洛姆通过社会性格理论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完善为“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同时也表明了,弗洛姆的思想非但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还批判了固守这一单向原则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其批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过度关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2)即使承认两者之间的作用具有相互性,但对于这种相互作用何以可能没有提出现实可行的理论构想。而弗洛姆在这两方面的理论工作就表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态更成熟、更完善,更多的具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因素。
三、社会无意识理论: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补充
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们认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但却将这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原则视为唯一,从而陷入独断论和教条主义的泥潭。弗洛姆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无意识”不仅坚持而且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他还主张社会无意识具备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可能性,并对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这就使得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近了。
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的理论来源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无意识范畴,弗洛姆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上,借鉴了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法,将无意识这一范畴的适用范围从个人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形成“社会无意识”,并对社会无意识作了进一步解释:“我所说的社会无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4]弗洛姆认为社会无意识理论的提出既克服了弗洛伊德局限于个体无意识的不足,又规避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意识压抑是一种社会现象,却无法在个体层面去科学地认识无意识领域的问题。
对于社会无意识理论,弗洛姆进一步提出社会无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社会意识,而决定哪些意识可以成为社会显意识,而哪些意识只能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是弗洛姆所提出的“社会过滤器”,他认为不同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不同的社会过滤器,未通过社会过滤器的意识就成为了社会无意识。换言之,社会过滤器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的,而社会显意识与社会无意识的界限又是由社会过滤器划定的,所以,当决定社会过滤器的社会结构变化时,社会显意识与社会无意识也会随之改变。由此,弗洛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也就显示出来了,同时也表明对个体进行分析并不直接意味着对社会客观发展状况的决定地位的违背。
弗洛姆在对社会无意识理论进行基础的研究后,对于社会无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也做出了明确的回应。他认为,不仅社会意识,社会无意识也被社会存在所决定。具体说来,一定历史阶段中都会形成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定的经济结构就决定了哪些社会意识成为社会无意识,这些社会无意识使社会成员在没有外在力量的推动下貌似自觉地按照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结构稳定的方式行动。因此,社会无意识看似游走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之外,实际上同社会意识一样,被社会存在决定并且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弗洛姆借助于社会无意识不仅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到了更加深刻的揭示,还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无意识领域中的客观作用,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提出过社会无意识这一概念,但他所理解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无意识有很多相关性。(1)弗洛姆与马克思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无论是社会无意识还是社会心理都被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5]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也是在回应“社会力量如何决定人的意识”这一问题时提出的。(2)弗洛姆与马克思都强调社会无意识与社会心理的形成受到社会与个人两方面力量的影响,正如社会心理是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综合一样,社会无意识也是在社会与个人的无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3)弗洛姆与马克思还主张社会无意识与社会心理的整体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并且共同构成社会意识;相应地,弗洛姆认为社会无意识与社会显意识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没有绝对的社会无意识,两者之间可以通过社会过滤器转化。由此可见,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心理的观点具有一致性,这表明弗洛姆跳出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将心理学的理论切实地吸纳进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补充
通过对弗洛姆的具体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在基本立场上,弗洛姆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但通过他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譬如过于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而轻视人的地位、重视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地位而忽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等,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被束缚在“唯物主义”这一原则之内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弗洛姆企图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恢复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给予意识形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有的位置。弗洛姆的这一立场也就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理论立场在他与阿尔都塞的争论中得到比较明显的体现。阿尔都塞以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将其之前的思想定位为意识形态,之后的思想定位为科学,并主张后者才是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形态,历史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生产方式,历史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并认为人本主义的价值只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人道主义的口号没有理论价值,但有实际指示价值。”[6]弗洛姆则认为阿尔都塞低估了人本主义的客观影响,他将阿尔都塞削弱甚至取缔的人这一历史主体彰显出来,并进一步指出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将历史唯物主义误读为经济决定论,这样的解读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批判的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弗洛姆认为人作为实践的主体,自然也就是历史的主体,主体向度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至此,弗洛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确立起来。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确定何以就意味着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补充?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历史与社会。正是因为弗洛姆对人的关注一方面是在历史维度中,以生产性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强调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现实的人;另一方面是在社会维度中,将社会性作为个人存在的重要前提,强调一定社会条件、社会关系中的有限的个人,才使得弗洛姆对人的关注没有脱离社会历史这一客观背景,没有违背社会历史研究法这一方法论,即没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立场,由此可以将他的理论定位为是在此前提下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补充。
在历史维度上,弗洛姆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定位为现实的、具体的人。而现实的、具体的历史主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受制于自然的被动状态逐渐转化为创造自然的积极状态,由历史的产物变为历史的创造者。而这样的转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就在于人是进行劳动生产的实践主体,人总是不满足于他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实然状态,借助于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实践活动将其本质外在化,创造出他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应然状态。但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对外在客观界限的无视,人对其与外在世界关系的构想不可能脱离一定历史阶段提供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弗洛姆是在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的基础上来强调人作为历史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
在社会维度上,弗洛姆在解读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时将社会主义等同于人回归到他自身,这就导致一些极端主观主义者借机夸大个人对于社会的作用,将弗洛姆对个人的关注独断地解读为对社会前提的抛弃。而一些批判者因急于反驳这些主观主义者的观点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过度强调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而忽视了个人对社会的反作用。因此,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取平衡就是弗洛姆理论工作的重要目标,当然,这也是他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之处。弗洛姆认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只能在社会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会上升到改变社会进程的程度但也不能忽视。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历史维度还是在社会维度,弗洛姆对个人的强调,甚至于对的人精神领域的重视,都在社会研究法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都未曾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是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的补充。换言之,在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虽然可以看出“人”的中心地位,但弗洛姆所强调的人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生产的具体的人,因而,他对人的强调就是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补充。实际上,学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的挖掘相对比较充分,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关注相对较少,部分原因在于对其关注存在巨大的风险,会引发将其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的可能性,这也是学界对弗洛姆社会思想的主要误解。但实际上,仅仅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并无法展示其完整的理论形态,只有科学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添加进去,既坚持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基础和客观必然性,又尊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历史主体地位,才能构建科学而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更接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正是弗洛姆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展开批判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