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壁画看“水墨山水”图像之变
于安记
(南京农业大学 工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1)
一、“水墨山水之变”溯源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山水树石》中有言:“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李将军、李中书)。树石之状,妙于韦偃,穷于张通(张璪也)。”(1)[唐]张彦远著,俞建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26页。如果说山水画之变始于吴的话,那么这次山水之变影响了两次山水变革:南北宗山水之变。在董其昌看来,南宗王维和北宗李思训固然分别是唐代水墨山水和青绿山水的代表人物,而人物画大家二阎和盛唐吴道子则在唐初就开始了山水画的变革新探索,虽其艺术成就不及人物画,但也对山水画的革新起到关键作用。其贡献之大,述说一二。山水一变,一般认为与唐代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有关,山水依附于宫观楼。“国初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2)[唐]张彦远著,俞建华注释《历代名画记》,第26页。阎立本、阎立德善于绘制精美的宫观楼台,但又尝试性地改变了山水依附宫观楼的状况,虽不成熟,也能“功倍愈拙,不胜其色”。(3)[唐]张彦远著,俞建华注释《历代名画记》,第26页。吴道子作为传统山水画变革的先驱人物,也以人物画之法来绘制山水,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亦曰:“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4)陈高华《隋唐五代画家史料》,北京:中国书店,2015年,第132页。;《太平广记》中则有“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5)陈高华《隋唐五代画家史料》,第133页。的记载,可见其水墨功力之大。吴道子在人物、山水、飞禽走兽、建筑台殿等方面无不精通,史称“国朝第一”。其作为山水之变的探索者,画法既有概括,又有壮气,对后世影响巨大。其作画以墨线“豪气”挥毫,“不加丹青,已极形似”(6)[宋]黄庭坚著,宋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51页。,富有“纵以怪石崩滩”(7)[唐]张彦远著,俞建华注释《历代名画记》,第26页。的山水画气势。
北宗李思训发展了展子虔“稚拙”的画风,以“金碧辉映,为一家法”的山水之法改变了六朝以来的山水画停滞状态,形成技法上用笔“细密”、着色丰富,风格上有装饰意味、工整艳丽,青绿山水具有“皇家”风格。其子李昭道继承了吴道子的“山水之体”“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取吴、父之所长,完成了青绿山水画历时性的变革。二李把青绿山水艺术推到一个时代的里程碑,史称“国朝山水第一,故思训神品、昭道之上品也”。(8)陈高华《隋唐五代画家史料》,第67页。而南宗水墨画之变则以王维、张璪为代表,他们“另辟蹊径,开始了对水墨画山水画的新探索,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完成了山水画的重大变革,奠定了中国一千多年水墨山水画发展的基础。”(9)赵声良《敦煌壁画风景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3页。王维早年学画师法李思训,又学吴道子,“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10)陈高华《隋唐五代画家史料》,第186页。因“安史之乱”仕途受挫,王维“以禅诵为事”(11)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92页。,归隐辋川,信仰佛法,主张“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12)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上),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462页。,以“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尝试以浓淡墨进行不同层次水墨的新探索,这一画法与李思训所主张“笔格遒劲”相悖,他的画“笔墨宛丽,气韵高清”,成为独立意义上的水墨山水画。当然,这一水墨技法也影响并流行在敦煌的莫高窟壁画中。
一般认为,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是两个不同的山水画表现方式。敦煌壁画早期的山水画多以“勾勒赋色”的青绿山水为表现形式;隋唐以降,山水画依附于宫观楼画中,“严格地说,壁画中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水墨画,因为所有的壁画都需要色彩染出。”(13)赵声良《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1页。在以盛唐长安为中心的水墨画的影响下,敦煌壁画自盛唐、中唐以后便出现了“用色较少,用墨较多”“水墨晕染和皴法”等水墨画的典型技法。需要说明的是,在敦煌壁画中山水作为故事画、叙事性经变画等佛教绘画的一部分,并不是独立意义上的山水画,但却可以称得上是水墨山水。因此,“水墨山水”之变,是以实物图像为研究基础,以墓室壁画、卷画与敦煌壁画为实物映证,并以对比分析的方法考察水墨山水在用墨、皴法、图式和风格特征等方面的变化。在经变画、故事画中具有“水墨山水”特征的图像都将纳入研究范畴。
二、墨色之变:“勾勒赋色”至“水墨晕染”
在传统水墨山水中,“墨分五色”,即以黑、浓、湿、干、淡来区分用墨的变化。在墨中加水把原来的浓墨破分成不同层次,来代替青绿颜料以渲染山峦树木,这就是南宗王维所宣扬的“渲淡”一法。在敦煌唐代壁画中水墨画用墨技法之变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汉代以来传统的水墨影响,二是以南宗王维为代表的中原水墨山水影响,其主要表现在浓淡墨线勾勒技之皴法、渲染之变。

图1 渠树壕1号新莽墓后壁壁画

图2 凤凰山1号东汉墓西壁北段壁画(采自《看见美好:文物与人物》)
赵声良认为“中国佛教绘画中的山水画并非传自西域,而是来自汉代以来传统的山水表现风格”。(14)赵声良《敦煌壁画风景研究》,第155页。先不说汉代书画,最早山水卷画之一——隋展子虔的《游春图》据傅熹年考证是北宋的复制品,也可能就是徽宗画院的复制品(15)傅熹年《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文物》1978年第11期,第52页。。所以汉代以来至隋唐以前的山水未有卷画传世,只有“唐人张彦远还见过,留有记载”(16)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5页。,如想了解早期山水的特色,需根据其它艺术形式,如墓室壁画、漆器、画像石或者敦煌壁画加上文献以了解其真实情况。从目前发现的实物作品来看,不仅在墓室壁画中出现了水墨画,而且在陕西富平吕村乡朱家道村唐墓壁画六曲屏风中也出现了独立意义上的水墨山水画,这个独立山水的出现与盛唐王维所宣扬的“水墨最为上”的时间较为相近,为更深入了解“汉代以来的传统山水”对敦煌壁画中水墨山水的影响提供有力佐证。在两汉时期发现的墓室壁画中具有“用色较少,用墨较多”的水墨技法,如在西汉后期墓室壁画中有洛阳卜千秋墓的“墓主夫妇升仙壁画”,运用浓淡墨直接勾勒白虎、青龙、朱雀、日阳神等外轮廓墨线,尤其白虎的四爪、青龙的头上部以及部分白虎前爪下部云纹用淡墨勾勒,并没有“随类赋色”,这应该是水墨在墓室壁画中的早期雏形之一。在西汉之后新莽时期,陕西靖边杨桥畔二村渠树壕1、2号墓墓室后壁壁画出现了早期水墨山水形态,画面以极其概括的手法绘制了二条弓形三重山,山体以淡墨粗墨线直接绘制,下面逐渐变淡,山间穿插了浓淡墨,以平涂绘制似“蘑菇状”的树木及各类飞禽走兽。“尤为重要的是,整个画面中山峦成为主体,并无人物的活动。换言之,此图是以山峦为主题的独立画面。”(17)郑岩《看见美好:文物与人物》,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111页。因其技法、风格特征较为“幼稚”,这个所谓“独立画面”也有可能是“史前水平”的水墨山水之一。类似水墨画法已在两汉、新莽多座墓室壁画中被较为广泛运用。随着“水墨”技法的渐趋成熟和运用,在内蒙古鄂托克旗米兰壕1号所发现的东汉墓墓室北壁中出现了水墨山水,以浓、淡粗墨线勾画出概念化三重山峦轮廓,左右两边墨色较淡,中间两座尤深,树木形态手法颇为相似,有浓淡墨变化,山峦从上至下以淡墨皴擦山体,山头重以下轻,有明显的“渐变”效果。显然,这个时期水墨山水已经“初步掌握”墨色的变化,墨线勾勒,分层晕染,四周深墨色山体与淡墨色山体形成对比。

图3 莫高窟第112窟局部 金刚山

图4 莫高窟第112窟局部 山泉芭蕉(采自《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
相较而言,水墨山水在唐代敦煌壁画中已发现既有墨法的变化,如莫高窟第112窟中也有类似渐趋“成熟水墨”的特征。南壁“金刚经变”与北壁“报恩经变”两壁经变中绘有山水图像,如金刚经变中的金刚山,中景中山的轮廓以重墨直接勾勒,两边泉水都用淡墨直接描绘,尤其左边山石下部的外轮廓至泉水的描绘,出现分层晕染,墙壁上出现了通透的淡墨效果。“山泉芭蕉”远景右上部的山石从内轮廓至里水墨出现了“淡墨晕开”的渐变效果,“山间瀑布”中的左部也有类似的用墨画法。赵声良则认为其“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水墨山水画了”,(18)赵声良《敦煌壁画风景研究》,第156页。虽离独立意义上的水墨山水尚有一定距离,但在同时期的榆林窟第25窟中水墨技法则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也印证了赵声良对水墨山水的论断,这一点对于水墨画的蜕变,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通过以上比较,两汉以及新莽墓室水墨壁画在水墨技法和皴法的运用上虽相对较“简单”,但从这些古老而传统的图像中可以窥见水墨在墨法层面上的演变和积累过程。受其影响,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青绿山水开始有意识地以水墨山水为点缀,墨法上运用黑、浓、淡的墨色变化来表现山体的阴阳相背,出现了形似劈斧的“简单”皴法,可以认为莫高窟第112窟应是敦煌中期水墨山水画发展的早期形态之一。换言之,水墨山水在中唐莫高窟第112窟得到了有力的实物映证,并体现出汉以来的传统水墨图式和技法。

图5 榆林窟第25窟局部 山中修行

图6 榆林窟第25窟局部(采自《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
在榆林第25窟,有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一铺和北壁弥勒经变一铺,两壁西边都绘有水墨山水,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北壁《山中修行》一景。画面描绘了佛弟子迦叶正在洞中禅修的场景,近景有青树山石,墨线勾勒赋色的木桥穿插在近景和中景之间,通向迦叶所在的山洞;中景左边有群山结构,以淡墨线直接中锋勾勒,用墨有粗细、浓淡变化,迦叶打坐山洞以及上部山崖有多处淡墨晕开的效果,层次十分分明;远景中有淡墨直接描绘的三角形山峦,其画面空间由平面装饰性向“纵深幽远”转变。通过图像分析发现,无论是用墨还是光影的处理,比莫高窟第112窟的山水技法都有明显的发展,尤其在色彩、水墨晕开的光色效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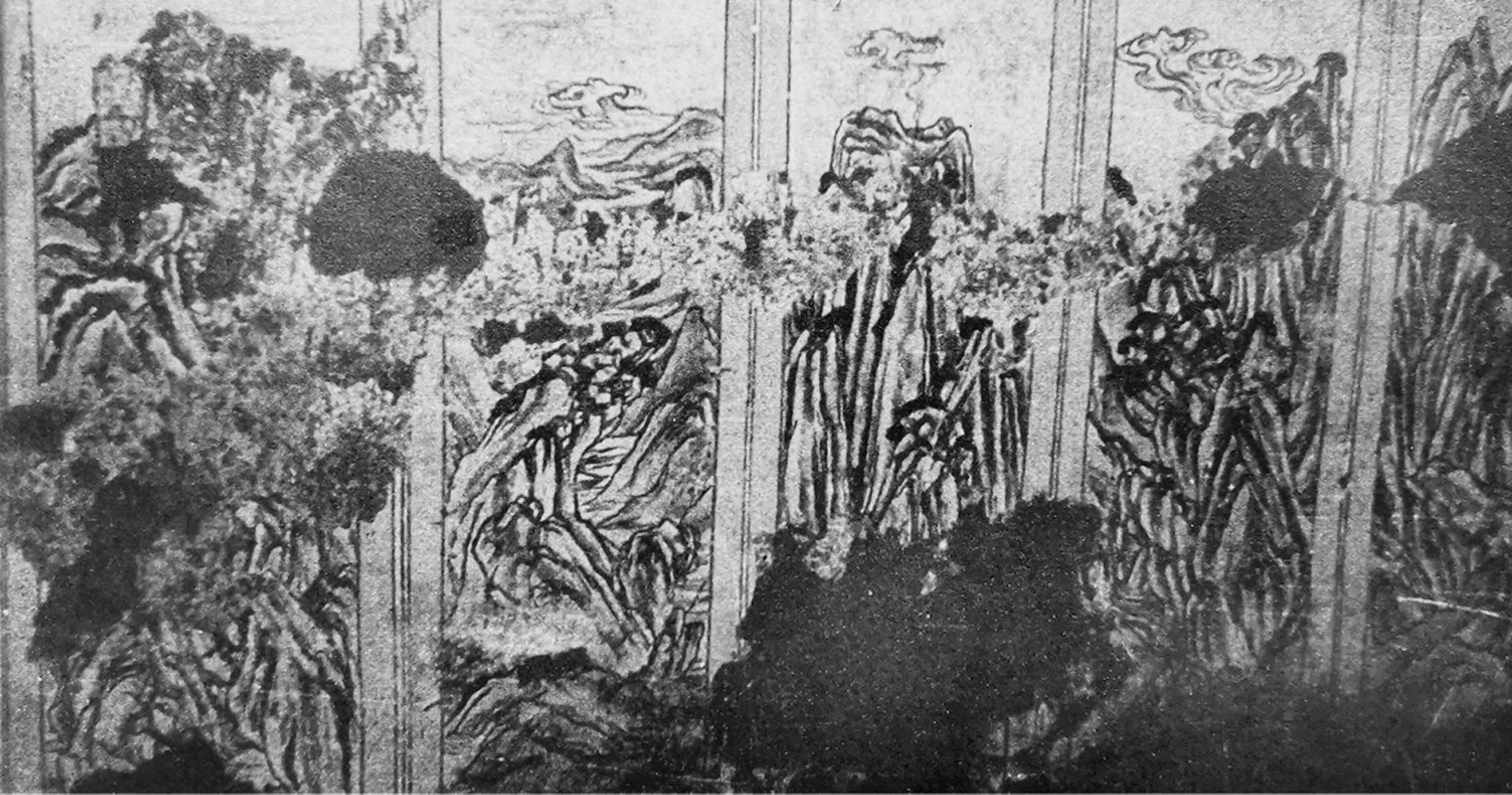
图7 六屏式水墨山水壁画 (采自《中国墓室壁画史》)
我们再来对比分析同时期陕西富平吕村乡朱家道村发现所发现的唐代墓,从壁画内容、布局、风格推测,可能是盛唐时期的墓葬(19)贺西林、李清泉《中国墓室壁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本座墓所发现的西壁连屏式六屏独立水墨山水,为唐代盛行的殿堂装饰形式,也反映了“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这种绘画形式的出现对考察王维水墨山水、盛唐时期墓室壁画、敦煌壁画水墨特征的演变以及唐代绘画对于日本山水影响具有重大意义,在山水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6幅壁画山水全部采用水墨画法,笔试粗狂豪放,构图紧凑,山势雄强”(20)贺西林、李清泉《中国墓室壁画史》,第192页。。从图像的水墨特征看,画面以取近景构图,浓墨点染树木,淡墨晕染,既有钩斫法,又有渲淡或擦皴山体,所运用的皴法为颇似披麻皴和斧劈皴,画论称之“钩斫之法”。贺士林、李清泉认为“这组壁画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独立水墨山水画,为探索盛唐山水画之变,尤其是认识王维一派水墨画的面貌提供了可靠依据”(21)贺西林、李清泉《中国墓室壁画史》,第192页。。因此,从传为王维山水作品《雪溪图》和《江山霁雪图》与六屏山水第二幅对比分析来看,王维的线条易于启发”披麻皴”,不似李将军“春蚕吐丝”式的刚性,也不似吴带当风式的壮气,而是形成了“曲折自然、变化随意、漫不经心式的”,且“如自然披挂着的长麻皮,”(22)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96页。这种画法与六屏山水第二幅山峦、榆林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中的水墨山水渐趋一致,这也是盛唐比较流行的“阙形山水构图”(23)赵声良《敦煌壁画风景研究》,第159页。。另外,六幅山水画有四幅出现了分层墨线勾勒形似的流云,隋展子虔《游春图》和传为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中都绘有多处穿插在山间的流云,虽王维的绘画没有相关流云的画法和可见图像映证,但南宗山水主要继承者北宋画家王诜的《烟江叠嶂图》中景、远景均出现了多朵这类云的画法,不难看出,这些云纹的处理方式与6幅壁画中的流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到敦煌元代壁画,水墨山水进入一个极盛的时代,而西夏榆林窟第3窟西壁门两侧的文殊变与普贤变更是走向成熟并达到高潮,其水墨濡染效果和皴法都可以代表敦煌水墨的最高成就,作品水墨层次分明自然,皴法十分丰富,主流青绿山水几乎为水墨取代,只有树木是青色点染,水、山、云、雾都以水墨尽染,一直占据中心画面的“主尊”地位被削弱,整个山体位于经变画上部的核心位置,尽显“敦煌本土化”的水墨奇观,唐至两宋以降卷画水墨山水的特征继承和变革在这里得到有力的图像映证,丰富诠释了青绿山水至独立水墨山水在敦煌壁画的演变历程。
因此,王维“渲淡一变钩斫之法”的技法告诉我们,所谓“渲淡一变”改变的不仅是青绿山水在士大夫阶层即文人层面的审美趣尚,也是宋人对唐画技法的传承和革新,这种追求水墨独立性的审美趣味已经在盛唐墓室壁画中出现。而王维的山水技法不仅影响了敦煌壁画水墨画的发展,也影响着日本绘画的发展。
综上可知,卷画、墓室、敦煌壁画水墨山水的特征由于墨色晕染和材质不同,主要以“五色”分层晕染效果来表现山体、树木、人物以及飞禽走兽的凸凹立体感。正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谈到,魏晋以降的山水“群峰之势”,虽“若钿饰犀栉”(24)[唐]张彦远著,俞建华注释《历代名画记》,第26页。有所欠缺,但有“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25)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上),第462页。。可见,由于材质的差异,加之墨加水后,其晕染技法在不同材质上会出现明显差异化的表现效果,但从其水墨属性看,与“墨分五色”较为契合,既有“得意”之处,又有形似之妙,其“气韵生动”的技法日臻完善,在唐代后期则进入“水墨晕章”兴盛的新时代。敦煌壁画自西夏至元这段时间完成了“水墨山水蜕变”,实现了从经变山水至文人山水的转变,并开创了水墨发展的新时代。
三、图式之变:从“平面装饰”至“平远之法”
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晋是山水画兴起之初,因构图缺少纵深空间感,以画面左右横向分布来表现远近关系,山水画构图出现了“咫尺千里”(26)王去非《试谈山水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问题——从“咫尺千里”到“咫尺重深”》,《文物》1980年第12期,第76页。的形式,盛唐以后构图方式向“咫尺重深”转变。“咫尺千里”颇似于敦煌建窟的早期——北魏至北周时期山水画的特征,具有装饰性“图案效果”,这种装饰性图案效果可以追溯到两汉以来的墓室壁画的水墨山水。渠树壕1号墓墓室二条弓形的三重山几乎上下平行分布,形似“蘑菇状”的树木无明显的大小变化,画匠画树虽根据山体结构有意识而画之,但树木在二条弓形空白处被“任意”摆放,各个元素之间呼应关系和穿插关系并不是很明显,这些纹样图案虽具有一定内在的形式意义,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却能体现出古人对孔子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自然山水观的向往与热爱。而凤凰山1号东汉墓墓室西壁北段壁画多重山峦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尤其是近处的农夫形体较大,远处的牧民形体较小,显示出画工已初步掌握了近大远小的透视法则,虽说不上气韵生动,却也拙朴可爱。”(27)郑岩《看见美好:文物与人物》,第111页。显然,人、动物、山和树木之间运用了合理穿插、疏密、对比关系以及“留白”等构成法则,分割成二段式的“图式单元”叙述两个场景画面,近似六朝谢赫所说的“经营位置”。清代王昱更一步强调构图的重要性,即“作画先定位置,次讲笔墨”(28)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上),第377页。,虽说山水画位置得到初步掌握并运用,但从画面构成特征看,这个时期画匠开始使用所谓的“初步掌握”透视法,具有平面装饰的特征,有“咫尺千里”而无明显的“咫尺重深”的效果,但“人大于山”的远近关系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由横向分布转变为上下分布,“平远”之法和“纵深幽远”的意念特征渐趋出现。
虽说敦煌壁画中早期的青绿山水依附于宫观,但到盛唐时期这种情况出现了改变。“盛唐第103窟、172窟、217窟、320窟等都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山水画。”(29)赵声良《从敦煌壁画看唐代青绿山水》,《故宮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5期,第6页。空间构图上也开始由“平面装饰”转变为“咫尺重深”,如在103窟和217窟两窟南壁中都有化城喻品之山水,320窟北壁日想观前景山水,172窟未生怨远景山水,这四窟都具有“平远”的特征。通过对比分析,前两窟山水图式虽有多段式“叙事空间”,但还未表现出较强的平面装饰性,后两窟的“纵深幽远”空间特质则渐趋明显。“咫尺重深”能够展示深邃的山水意境,多见于盛唐敦煌青绿山水和卷画、墓室壁画,与郭熙所说的“平远”之法颇为相似,“‘平远’的用墨一般较淡,其在平和中把人引向‘远’‘淡’的境地”,(30)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233页。又有“渐远渐淡”之意,“平远”与“咫尺重深”之意较为契合,又有透视法中“近大远小”之妙,这种用“平远之法”来表现山水“渐远渐淡”的淡墨意境在水墨山水中尤为多见。
从传为王维的《雪溪图》和《江山霁雪图》来看,两幅作品在构图上都运用了平远法。《唐国史补》记载“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唐书·王维传》所云“山水平远,绝迹天机”(31)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97页。。这两幅画都接近于王维画风,董其昌也认可南宗画中,多属平远构图,这种构图方式与陕西富平吕村乡朱家道村六屏山水第二幅的远景平远法近乎一致。平远之法在荆浩《匡庐图》的近景和中景中,李成的《秋岭遥山图》《岚烟清晓图》《雾披遥山图》《雪山行旅图轴》以及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画中均出现山峦的平远幽深和远阔之境。李成师承荆浩,王诜又是李成的传人。因此,这种水墨山水图式的传承关系已很清晰。另外,五代河北曲阳后唐王处直墓也有两处平远法水墨山水,前室北壁画远景中的山峦,以及水墨山水与器具一壁中的山水,与同时期董源的《龙宿郊民图》远景和《夏景山口待渡图》近景都采用了类似的图式方法。从目前的图像材料看,卷画和墓室壁画多取景自然山水,画面平远开阔,图式多为中远景,青绿山水“敦煌本土化”特征较为明显。
相较而言,敦煌壁画水墨山水画的平远之法出现较晚。中唐时期敦煌水墨山水虽依附于青绿山水,成为青绿山水一个“附属”部分,但这个部分有从青绿山水“渐变所附”的情况出现。从中唐第112窟北壁西起画报恩经变图形看,中景上部宝盖中部、右边形成一个“对比构成”的样式;用独立的墨线勾勒出两处山峦,形成左右对比的形式,虽无用墨色表现的树木和水景,却形成“近大远小”的空间关系。榆林窟第25窟“平远”之法则有所发展,南壁右侧屏风山水上部的远景山峦与王维、董源以及王处直墓水墨山水都有类似的构图特征,此壁“三山”表现为前景山、中景山与远景山相互穿插的远近层次关系,既有以“柔软、悠淡”的三山,也有以“刚硬、概括”的两山为一组进行绘制,与下部左边颇似“三山”形成对比关系,平远之法的表现技法已近于成熟,追求“自近山而望远山”、有“平远旷荡”(32)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232页。之感的审美意趣在敦煌壁画中唐时期开始蜕变。而敦煌水墨山水在西夏榆林窟第3窟则完成了最后的探索和变革,并生动诠释了郭熙的“三远”之法,其“咫尺重深”“深远”“平远”意境尤为凸显。
如上分析,敦煌壁画中的水墨山水绘画在空间关系上继承并革新了传统山水水墨图式,一方面运用绘画纵深、近大远小、透视法和“三远”等绘画中常见表现手法;另一方面,以强化中心“主尊”地位的构图方式在历时性的演变过程逐渐分化并减弱,由“满画面”为“平面装饰”的构图方式转变为“渐远渐淡”的审美境界,这是一种异于卷画、墓室壁画的水墨图式构成。
四、余论
敦煌壁画水墨山水从中唐至元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虽说只有以上几个洞窟具有水墨山水图像的特征,却也能够清晰梳理敦煌壁画与卷画、墓室壁画中的水墨山水发展脉络。通过图像佐证深度剖析了水墨山水的技法特征,由此阐释中国水墨山水画的演变路径。敦煌水墨山水直至元代虽没有完全脱离佛教美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但在敦煌后期山水成份被逐渐加大,敦煌画匠兼容并蓄地吸收了汉代以来的传统水墨山水和以王维为代表的中原山水“敦煌式”画法,形成具有“敦煌本土化”的独特风格图式,成为中国水墨画史的经典艺术范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然,王维水墨所代表的是苏轼所说的士人画即文人之画,而敦煌壁画、墓室壁画所代表的是工匠之画,诚如马德所认为的那样:“敦煌古代的画工画匠是敦煌艺术的创造者。”(33)马德《敦煌画匠称谓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第1页。这些“良工”“巧匠”创作的水墨山水具有文人画意味的倾向,既有佛教美术的“神圣性”,又有士人画的“秀润天成”,同时又区别于文人之画,两者之间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水墨特质,他们所创立的墨法和图式风格都是中国山水画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