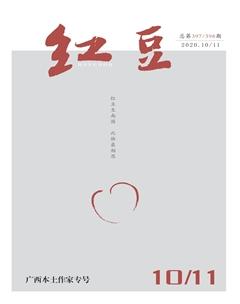砍柴的年少时光
陆寿青
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不用教,天生就会砍柴。谁要是笨手笨脚把柴捆得不像样,都会被笑:“连捆柴也不会,将来还讨得上老婆?”
过去在我们那里,男耕女织,砍柴这些粗活都是男人干的,挑水这类简单活儿则由女人负责,分工明确。所以哪家媳妇生孩子,人们不会问生男还是生女,而是问:“是砍柴的,还是挑水的?”有了砍柴的希望添个挑水的,有了挑水的希望添个砍柴的,这样农活才样样有人做,日子才和谐美满。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有的人家明明生了四五个男孩仍拼命要生一个女孩的缘故。
印象中,我小学二年级起就跟人家上山砍柴了。当时人小、力小,刀柄难以把控,安全事故屡屡发生。记不清多少次,举着柴刀砍着砍着,白晃晃的刀刃直接就砍伤手指,当场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疼得我哇哇大哭……一听见有人哭,伙伴们便从四处跑来,乱扯一些树叶,含在嘴里嚼碎,然后涂敷到伤口上,或者翻出口袋缝里的细碎棉絮充当创口贴,胡乱止血。意外的是,血居然真的给止住了,而且屡试不爽。如今回想,年少的自己还真是勇敢。
因为砍柴,仅仅我的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就留下了大大小小近10处刀疤。这些疤痕,或长或短,或浅或深,或清晰或模糊。每每看着它们,仿佛就看到山坡上有一群熟悉的砍柴少年,扛着柴火往家里奔走……
念小学的时候,没有什么课外作业,我们的课外作业就是傍晚放学到山上砍柴或找牛。那时候的山,夏天有很多野果,我们边砍柴边摘着野果吃,运气好的话,还能从树上掏到鸟蛋,甚至一整窝雏鸟。
野外劳作难免有意外发生。有一次跟两个堂哥去砍柴,我刚踮起脚跟伸手去扯一根干枯倒伏的栎树,突然,树根处传来一阵嗡嗡声。糟糕,撞上马蜂窝了!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一群马蜂便朝我四处袭来,我顿时丢盔弃甲,砍柴刀也不要了,哭喊着往山下亡命地逃跑。不过百来米,便倒在草丛中。那一天,我的脸部、头部、颈部被马蜂蜇了七八处,鼻青脸肿,眼睛肿痛得几乎看不见路。见我动弹不得,两个堂哥吓得魂飞魄散,柴火也不要了,赶紧轮流将我背回家。
那一次,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因为马蜂太毒,至今我的后脑勺仍有好几个小凹印。大人们后来告诉我,那是一种奇毒无比的地蜂,要是再被蜇上那么几下,生命都有危险。前几年看到一些报道,说哪个地方发生毒蜂蜇死人事件,边看边联想自己的年少际遇,不免心有余悸。想想真是后怕,为了砍柴,自己竟在阎王地府边走了一趟,要不是亲身经历,说起来谁信啊。
砍柴时偷黄瓜的经历至今久久不忘。年少时期,村里到处开荒,哪里开荒砍树,哪里自然就有柴火,这些新开荒的坡地里,人们常常种有黄瓜。因为饿,口又渴,我们也不管是自家的瓜,还是别人家的瓜,只要看到瓜,我们就鬼鬼祟祟地匍匐进地里,偷得黄瓜就拿到草丛中美美地分享……饥饿的年代,我们这些砍柴少年郎,谁都有偷瓜的经历,所以大人们也不怎么计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人家被偷会生气咒骂,也就随便骂那么几句,说哪个缺德鬼偷吃了他(她)家的瓜不得好死云云,也没有谁真的去追究。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苦涩的岁月,反成了一份甜蜜的回忆,让人回味无穷。
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从小时候起,砍柴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到假期,不用父母催促,我们就会自觉担负起家里砍柴烧火的责任。农历七月十四或春节前,为了储备过节的柴火,我们每天上山两三趟,把一捆捆柴火满满地堆在自家的墙根屋檐下。大人们看着我们砍的柴火一捆比一捆大,一捆比一捆捆得结实利索,他们就笑眯眯地自言自语:“嘿,我的孩子真的长大了,可以娶媳妇了。”
那时候,我们那一带都习惯订娃娃亲,我记得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些家里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同学,都陆续订有娃娃亲了。我虽然比别人勤奋,砍的柴火也一捆比一捆大,但因为家里穷,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同伴们将附近村屯的俊俏小姑娘一个个相走。
那时候,我们村里的同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大多数男孩小学毕业因为考不上初中就不得不辍学回家“修理地球”了。假期的时候,白天我就跟这些不上学的“闰土”一起砍柴、放牛,晚上偶尔跑到七八公里外的村部(那时候叫大队)去看电影。农村的孩子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学,学喝酒、学抽烟,有时候还三五成群地故意找其他村的小姑娘逗着玩,那种单纯的快乐,简单,无拘无束。
初三的暑假,因为等候录取通知书,日子漫长而煎熬。附近的村屯有人买了一艘铁皮船,专门在灵歧河来回收购柴火之类的东西。为了赚点钱用,我和同伴们决定上山砍柴卖。印象中,那个暑期,我砍了近20天的柴火,冒着酷暑将一根比一根重的木头从山上扛到河边,肩膀都磨破了几层皮,赤裸的脚丫更不知被草丛中各种尖利的东西割破了多少道伤口。
我记得我把那一堆高高的柴堆卖后得了12元。那是我生平唯一一次砍柴賣钱,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靠自己的力气换来收入。我拿着这笔钱,上街一连吃了两碗肉粉,美美地犒劳自己,然后买了一双鞋。那是一双皮凉鞋,我穿着它,配着喇叭裤,走起路来,得意扬扬,那份满足感,是我后来穿的任何一双皮鞋都比不上的。
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我干了一件让父亲刮目相看的大事,凭一己之力新建了家里的晒坪!
我家门前地势高,起架晒坪最困难,因为修理困难,旧晒坪的木架子朽了很久了,父亲也迟迟没有重修的念头。
晒坪就是农家人的前台后院和小广场,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场所。人们不仅要在那里晒东西,平时劳动回来也要在那休息,夏天晚上我们还可以躺在晒坪上乘凉、看星星、赏月亮,谈天论地……
从学校回来,看见母亲一边提心吊胆一边骂骂咧咧在上面晒东西,我实在于心不忍,气愤地对父亲说:“你不修晒坪我来修!”父亲也不看我,就扔了一句话:“你厉害你修啊!”
我和父亲赌上气了,第二天就约着同伴提着柴刀上山找修建晒坪的条木、横条和柱子。晒坪的竖板条很讲究,必须选取那些长得又直又长正好够手臂般粗大的木头。这些木头,都要到距离很远的深山老林里找。那个夏天,我和隔壁的“闰土”为了修建自家的晒坪,整天早出晚归,晒得就像根黑木炭似的。我记得除了晒坪最高大的那3根柱子是父亲和我一起抬回来之外,其余的柱子包括十几根大横条,都是我一个人去山上砍并自己扛回来的。
把旧晒坪拆除翻新的那一天,大家一边帮忙,还对我称赞不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居然一个人完成了这么大的一项工程。父亲欣喜之余,似乎有些惭愧,反反复复就一句话:“想不到,想不到,这小子真的长大了……”
那时我18岁多还没满19岁,新建的晒坪就是我的成年礼,是我献给家里人的一份礼物。看着母亲笑靥如花安然地在晒坪上晒米晒衣服,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那时候我就有种强烈的意识,我不仅可以打柴放牛,还可以像大人那样做一些大事了。
过去春节,大年初一天还没亮,我们这些孩子就争相到河边祈福。大人们说,谁第一个喝上新年的第一口水,谁就会变得比别人聪明。我们一边舀水喝一边许愿,口中念念有词:“喝了聪明水,就会修犁耙;懂得犁田会耙地,就不愁娶上俏媳妇。”喝完聪明水,我们还郑重其事地用绳子绑着一块石头,当着牛马一路牵回,拿到牛栏里放着,以此祝愿家里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虽然我不会修犁也不会修耙,但在同龄人中已算是劳动的一把好手。看我能里能外,乡亲们就说,大概我是把村里的聪明水都喝走了。
喝了聪明水,就会修犁修耙?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农家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祈愿。19岁那年夏天,我就是带着这份朴素而美好的愿望,放下了曾经陪伴我多年的柴刀,告别了家里那头与我心有灵犀的水牛,带上劳动带给我的坚韧和磨炼,离开了那个叫那兰屯的山沟沟,到远方去求学。
此去经年,光阴似水。蓦然回首,如今青山依旧在,但远方成了故乡,故乡成了远方,而当年的那个砍柴少年,再也看不到自己原来的模样……
责任编辑 练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