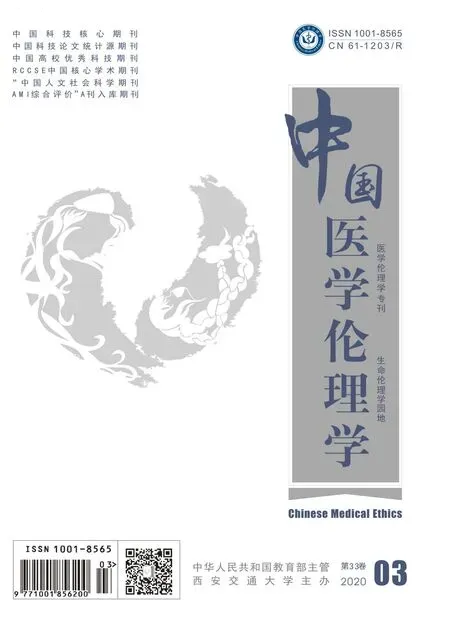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文化性格
高翠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 100730,happybjcf@sina.com)
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重要机构,也是我国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典范,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通过研究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文化性格,总结其培养模式中的文化因素。
1 对“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的定位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6年建立的教会学校协和医学堂,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协和医学堂并于1917年正式成立时沿用了“协和”的名字。自建校起至1942年协和因日军占领被迫关闭。这一时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得到平稳发展,从外部环境来说,协和独立办学尚未被动荡的政治局势、侵华战争大范围影响,还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和文化精英的支持;从内部发展来说,经过几年的积累探索,协和的建筑建设、设备储备和教职员工队伍建设已经完成,学科设置不断趋于完善;从人员储备来说,现代化的设备,先进的教学理念,吸引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一流医学科学家来协和任教,并开展不同领域的医学科研工作;招生培养来说,经过不断摸索已经初步成熟的严格招生制度和培养模式也严选出许多优秀学子来协和求学,协和优秀毕业生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协和医学院以可以比肩欧美先进医学院校的姿态,不断成长并走向成熟。
本文选取1917年建校到1942年这一时期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文化性格作为研究对象。协和经历了迅速壮大发展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前的“黄金年代”,取得了医学教育史上的跨越性进步,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将聚焦协和平稳发展时期的宗教氛围与科学人文将神的此消彼长,探讨这一时期协和迅速发展的性格特征的影响。
2 医学传教与协和的基督教色彩
早期的协和医学院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1914年12月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第一次会议中宣读了《关于医学传教和耶稣精神的几点想法》,自那时起便确定了协和文化性格中的基督教基调,早年的学院管理者们一直反复强调保留协和的基督教特征。
2.1 协和医学院与医学传教的关系
北京协和医学院与医学传教颇有渊源。自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1835年在广州建立以来,至1914年传教士医生在华开设医院达59所,占当时中国医院总数的三分之二。教会坚信自己代表新的文明,中国的当务之急不仅是发展医学科学,而是人素质的提升,于是医学院校就成了传教的理想场所。在传教士们看来,将道德约束的基督教精神与作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的理性与科学结合,可以全方位变革提升贫穷落后的古老中国。诸多教会医疗机构就是这样的理念的产物,北京协和医学院因其宗教机构的背景也受到了一脉相承的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是一所六家教会合办的协和医学堂,在被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时,教会同意出售并给予了很大的优惠,教会的力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决策中发挥着影响力。小洛克菲勒曾在1915年3月致信各教会强调了对继续弘扬基督教精神的目标和态度,这些信函一直被教会视为一种契约。小洛克菲勒还在1925年明确作出承诺,要与教会进行诚挚默契的合作,希望对传教事业作出贡献。在七年后的开业典礼中,他再次重申,要对教会的精神和目的完全赞同并尽可能贯彻下去,体现在服务和自我牺牲中。
2.2 医学院中的基督教传教士与教徒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产物,与洛克菲勒父子的信仰息息相关。洛克菲勒本人在1857年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而他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一直致力于传播“福音”,投资慈善事业,这也是洛克菲勒家族设想建立协和的初衷之一。
而协和的管理和教师群体当中,不乏基督教徒或者传教士出身的医学科学家。初创时期的校董事会13位成员中就有6位各自来自于创办协和医学堂的六家教会,在学校决策中发挥作用。在教学科研人员中,也存在大量基督教背景人员,以医院妇产科为例,妇产科教授兼主任马士敦是一位医学传教士家庭出身的虔诚基督教徒,他的助手王国栋(Jordon King)本身就是一位传教士,而后来的第一位中国妇产科主任、素有“万婴之母”之称的妇产科学家林巧稚,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这种情况在协和的各个科室很普遍。
2.3 宗教事务机构——宗教与社会服务部
协和医学堂医院一直雇用“福音传播者”,在医院病房和门诊向患者传播福音,还聘任一位“宗教主任”,承担有关社会服务工作。协和医学院沿用了协和医学堂关于宗教主任的设置和做法,成立“宗教与社会服务部”,并全额提供该项活动的经费支出。1918年夏,斯瓦尔兹神父成为该部门第一任负责人,并于1920年增加了一名雇员,该部门的工作范畴包括学生工作、医院福音传播、学校周日礼拜活动以及学生体育课和各项文娱活动,协和的周日礼拜日活动经常吸引许多协和之外的人参加,第二任主任朱友渔在中国宗教界颇有影响,极大的提升了这一部门在学校内的地位。
2.4 宗教色彩逐渐淡化
20世纪30年代,协和的基督教色彩经历了一个逐渐淡化的过程。一是随着国民政府教育管理政策的调整,协和校董事会进行了改组,6位代表教会的董事会成员退出,与教会的联系没有先前紧密。二是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协和的管理者们也多次试图调整预算,由于宗教与社会服务部由学校全额出资未受教会资助,被认为可以调整用于专业科室的发展。三是朱友渔离职后合适的社会服务部负责人又很难及时到位。协和内部对于在一所教学教育机构中是否保留社会与宗教服务部产生了分歧,有部分管理者一直主张解散宗教与社会服务部。由于小洛克菲勒二世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和对教会机构承诺的坚守,甚至不惜迁怒于为协和早期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校长顾林,并在1934年将其解聘。在小洛克菲勒的坚持下,宗教和社会服务部一直得以保留。但是随着学校的教育事业的扩大,宗教工作与教学的融合愈发变得艰难,宗教工作逐步让位于现代医学教育理念,逐渐在现代教育理念指导办学的协和边缘化。
3 科学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
3.1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彰显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互相渗透的关系,前者是医务人员应具有的物质基础,后者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主要表现为人道主义,是支撑医务人员的精神支柱。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的校训是“科学济人道(science for humanity)”。科学,指以实验或数学方法为主认识的系统知识。人道,指关爱生命、维护自尊、尊重人性的道德观念。济,帮助、救助。“科学济人道”将科学作为手段,人道为目的,强调科学的价值导向。这个校训体现了早期的协和教育者将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开展医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内核,成为协和师生共同的精神准则。
3.2 对科学精神的推崇和对科研工作的支持
一是强调科学精神。从建院时方针和指导思想中可以窥见其对科学精神的推崇,小洛克菲勒在开幕典礼的讲话中提出,他相信有科学精神的教师不仅能传授知识,而且应能进行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对医学科学发展作出贡献。作为一家医学教育机构,“科学”精神深深地融入协和的血脉,北京协和医学院一贯重视实验室和临床实践。首任校长麦克林在给他的顾问的信件中,曾经透露出对繁重的临床工作占用员工精力而冲击教学、科研工作的担忧。从侧面反映了协和的管理者为坚持将工作重心放在科研教学上的努力。
二是支持科研工作。协和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吸引了诸多醉心科研的科学家,许多教师也是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协和的教授斯美唐纳曾经表示“(协和)是科学家的天堂……极多的科研机会……任何设备,只要证明对我们有用,就不会因为太贵而不去购买”[1]。1930年秋天,哥本哈根著名的医学教授、医学教育项目观察家纳德·法伯尔调查了中国当时22所医学院校的情况,给予了最高的赞誉:“真正的科学精神统治着整所学校”,他认为这所学校可以和美国和欧洲最先进的医学院校相媲美。
三是建立现代医学科学体系。早期协和建设者们建立了完备的实验室和浓厚的科学研究风气,秉承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理念,将现代化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开展诊疗技术和医学科学研究,早期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包括关于“北京人”的发现和研究、麻黄素的发现和研究、《本草纲目》的翻译介绍、血液的生物化学研究、神经生理学研究、乙酰胆碱的研究、中国常见寄生虫病、传染病的调查研究、软骨病及钙磷代谢病的研究、梅毒的研究等,当时我国主要的医学杂志学术论著主要来自协和[2]。协和为中国建立了临床医学和实验医学为基础的“科学医学”体系,完成了一系列与当时社会需求紧密相连的科研成果,契合了当时古老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对科学精神的渴望和中国人健康的内在需求。
3.3 对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视
医学人文精神的价值存在于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临床实践中。医学是济世救人之术,医学教育培养的是具有人文品格和悲天悯人情怀的医学工作者。人文教育是医学教育的灵魂和根基,北京协和医学院强调的“专业”精神、科学精神的教育模式,却没有将学生局限于繁重的医学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坚持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对学生加强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熏陶培养,表现如下:
一是医预科阶段的语言学习。作为中国第一个医学预科与医学本科教育相结合的八年一贯制医学教育,北京协和医学院非常重视学生预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尽可能按照美国一流医学院校的要求录取学生、设置课程。由于将英文作为主要授课语言,所以非常重视语言教育,教师主要由外国人担当,实行全英文教学。在学生大多来自教会学校的情况下,无论是自办医学预科教育,还是资助全国综合性大学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南大学等,对学生语言的教学均作了详细规定,包括: 英语20学分、中文20学分、英语和中文以外的其他一种语言10学分。
二是建立医学人文教学机构。随着中国教授和职员的加入,学生们开始考虑在中国行医的语言需求和中国本土医学科学体系发展的需要,主张用中文授课和开展中文教学的呼声越来越大。1925 年3 月,校学生会同意增加一门医学汉语课程。同年6月,协和医学院成立中文部( Division of Chinese) ,一直持续到日军侵占协和停办。中文部的职能在教学、出版、事务管理、医学人文研究等方面全面发展。教学方面,通过中文教学提升学生以中文写作科学文章、翻译西方医学著作和论文的能力,开设医学伦理、社会和专业精神、医学史等方面的讲座。在出版方面,协助编辑出版中文医学著作与论文,出版中文著作和论文、翻译英文文献。管理工作则是协助医学院和医院处理各类中文官方文稿以及事务工作。中文部另一项值得提及的工作是,为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收集了一批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在医学人文教学方面,协和医学院在20世纪20年代,开设了医学伦理与法律、医学史、护理学史的讲座课程,展示最新的研究方向与成果,除了给医学生开课之外,对学生的医学职业素养培育影响巨大。
三是注重医学人文研究与医学科普。在医学史与医学伦理学研究方面,1937年4月,中文部教师李涛带领学生编写了《医史大纲》,是我国医学史界出版的第一部正式的医学史教科书。1943年在美国《医学史通报》(BulletinofHistoryofMedicine) 上发表“中国古代医学伦理学”(MedicalEthicsinAncientChina) 的英文稿,最早向西方医学界介绍中国古代医学伦理学的文献资料,对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古代的医学伦理传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五卅运动后,杨济时、朱章庚、贾魁、褚福棠、胡传揆、陈志潜等学生共同成立社团“丙寅医学社”,旨在“向民众普及卫生科学知识,评论社会医事、提倡新医学,增强民族健康”[3],他们创办一种通俗医学读物,向民众普及卫生知识,稿件还被发表在李涛任主编的《大公报·医学周刊》,极大扩大了社会影响。
4 对当前医学教育的启示
经过了早期的沉淀与积累,北京协和医学院探索出了一整套与世界先进医学机构比肩而立的培养模式,而蕴含其中的文化因素更是推进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以史为鉴,对于今天医学教育中的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4.1 发挥创新文化的创新驱动作用,培养医学生的“科学脑”
文化是一种基本、深沉、持久的精神力量。创新文化鼓励、崇尚创新,有利于培育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当前医学教育要重视创新文化的引领作用,坚持弘扬创新价值(精神文化)、塑造创新规范(制度文化)、优化创新环境(环境文化)等文化创新的“软”手法,不断提升创新活力和动能,为高素质人才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提供核心驱动力,增强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4.2 不断丰富发展高校文化,滋养医学生的“人文心”
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只有当医学科学素质与医学人文素质相互促进、和谐发展,达到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融通与共建,才能真正实现医学的目的。在医学教育中,要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育人。要处理好传统文化和创新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不断凝练总结高等医学教育机构的文化精髓,丰富精神文化的内容,提升精神文化的层次,传播和继承那些能够推崇崇高理想、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大众需要的内容,将精神文化深深地融入医学生的成长过程,为医学生的成长成才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成为培养医学生高尚医德的精神源泉。
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医学实践中,在基督教医学传教的科学启蒙与精神教化基础上,秉承着现代教育模式将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念,培养了诸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优秀人才,这一时期的毕业生中涌现出了我国现代医学诸多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对于推动我国现代医学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协和医学院历经三次停办三次复校的曲折历程,但是建校早期确定的优良传统却一直传承下来,并推动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发展,成为我国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