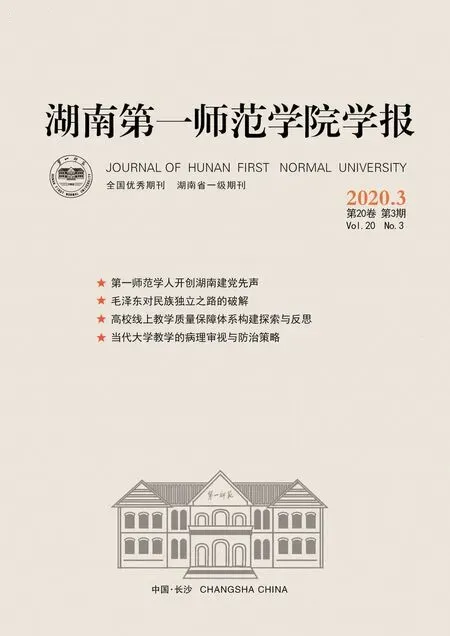卢梭的人学理论探析
刘黎明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引言
在西方人学思想史上,卢梭并非人学理论的首创者。在卢梭之前,就有很多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早在古希腊,智者派、苏格拉底等哲学家都对“人”的问题展开过深刻的探讨,把哲学的目光从天上拉到地上,实现了哲学的重要转向——由自然哲学向伦理哲学转变,人成为宇宙万物的中心和存在的尺度。智者派的创始人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人的感觉、思想、理性在认识活动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苏格拉底进一步探讨了人的问题,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使哲学的人文意蕴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这两个命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使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人学开始出现,开启了哲学人学化的先河。而“人学”作为一个概念是由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出来的。他们肯定人的价值、力量和尊严,并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著作中看到人性的光辉、美好的智慧、高尚的品德以及个性的解放和自由,提出“让死去的东西复活”的口号,致力于人的问题的探讨,建构了颇具人文意蕴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建立“人学”的思想诉求,使“人”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卢梭批判地继承了前辈的人学思想,建构了既与前辈人学思想不同,又与其他启蒙思想有别的人学思想。他认为,前辈对“人”的学说和知识的探讨是“最不完备”的,而这种“人”学说和知识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中又是“最有用的”。“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胜过伦理学家的一切巨著。在他看来,认识人类本身,确立人学思想是真正解决一切政治、道德和教育问题的前提和条件。因而,他无论是对科学与艺术问题的论述,还是对人类不平等起源问题和社会契约的问题的探讨,抑或是他对自然教育人学思想的建构,都是以他的人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内在地蕴含着人学理念。
一、“自然状态”中的人比“社会状态”中的人更优越
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是对立,前者优于后者,与此相适应,自然人比文明人更优越。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野蛮人(也称自然人)把身体视为用于各种用途唯一工具,尽管野蛮人分散生活在丛林的野兽之中,但自然状态使地面上不会有某种突然的、经常性的冲突和事变,即使他遇到需要与野兽进行争斗的情况,野蛮人也会将自己的力量与它们比较,如果他在力量和敏捷上超过动物,他就不会感到害怕;反之,如果野兽的力量和敏捷超过自己,他的处境就与弱小的动物相似,还是能够活下去。因为人具有野兽所没有的优势,即他不仅比野兽跑得快,而且能在树上寻找到自己的安全的庇护所。虽然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本能,但野蛮人能够学会这些特殊本能并为己所用,尤其是能比任何动物更能找到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必需品。与其他动物相比较,尽管他没有某些动物强悍凶猛或灵巧敏捷,但它的身体构造比所有其他动物更合理。不仅如此,他还从童年时代就得到了父辈的吃苦耐劳的训练,造就了强壮结实的体格,学会了赤手空拳地保卫自己,获得了人类所能拥有的全部力量和能力。然而,人类永远不可能停留于原初的自然状态,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社会状态之中,人的灵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面目全非。人不再是按照自身固定不变的本性行事,造物主赋予人的神圣庄重的淳朴也不复存在,在人身上只剩下自以为合理的情感和走火入魔的悟性之间的可憎对立。这是因为不断产生的种种原因,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谬误,人的体质的变异以及情感的持续的冲击导致的。更不幸的是,人类在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所有进步更加远离原始状态。人类的新知识积累得越多,对人的研究越深入,越不能抓住其中最重要的东西,越不能认识人。
与野蛮人相比,我们文明人的身体难以胜任野蛮人所使用的的各种用途,因为其身体缺乏锻炼。“正是我们所拥有的技能,使得野蛮人在生存需要的迫使下所获得的那种力量和灵敏在我们身上不复存在。”[1]88我们不具有野蛮人所具有的优势和状态。两者对比,我们会发现文明人的悲哀。
首先,人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而非大自然。尽管我们在科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丰功伟绩,在征服大自然中也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填平了沟壑,削平了山峰,砸碎了岩石;江河可通航,土地被开垦,湖泊被疏浚,沼泽被排干;陆地上矗立起座座高楼,大海上船只编队航行。”[1]177然而,它们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我们稍稍加以思索并仔细探究一下所有这些为人类幸福带来的实在利益,就会对幸福与痛苦的比例严重失调而感到震惊,并且就会悲叹人类的轻率行为。人类为了滋长自己的愚蠢的骄傲情绪和虚浮的自我智慧,狂热地追求可以承受的一切苦难,而这苦难都是仁慈的大自然着意要人类避免的。”[1]177
其次,人际关系变坏。人类社会在科学知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人们有理由去赞美它,“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愈加紧密,这个社会就必然使人们愈加相互仇恨。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表面上看人们总在相互帮助,实际上都在互相算计。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每个人的理性为他自己确立的准则,都与公共理性向全社会说教的法则截然相反,每个人都从他人的不幸中谋得好处,想一想这是一种何种方式的交往!”[1]178因此,“我们要透过人们的浅薄的仁慈的外表,深入了解人的内心深处。我们要想一想,人人被迫相互亲近,又相互争斗,出于责任而结仇,又由于利益而互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事态。”[1]178
再次,人的某些生存能力的退化。当野蛮人步入社会状态后,人原有某些生存能力退化。文明人不再具有野蛮人那种强健的身体和敏捷的四肢,野蛮人的强壮机灵、勇敢善战的力量和勇气在文明人身上不复存在。人类随着知识和技巧的获得以及自身的不断进化,人的生理器官及能力随之退化。卢梭指出,一般说来,森林里的马、猫、牛甚至驴,比家养的牲畜身材更高大,体格更强健,而且更有力,凶猛。但经过对它们的驯化,精心的喂养和细心的照料,它们的优势不复存在,会丧失掉一半。人也是如此,当野蛮人步入社会后,其优势如力量和勇气也随之丧失。卢梭分析了人的某些生存能力退化的原因,指出:“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别必定比野生动物与驯养动物之间的差别大,因为兽类和人类是受大自然同等对待的,而人的舒适生活条件比人所驯的动物多,这就是人的退化更为显著的具体原因。”[1]93
卢梭之所以要讴歌“自然状态”和“自然人”,其意图是反思以往的各种学说,反思文明社会中的种种罪恶,揭示人的进化是造成人的痛苦的根源。尽管在卢梭的思想体系中“自然状态”只是一种观念的假设,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不会存在,但它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自我,观照社会,“说明现实社会状态中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幻想,什么是有道德约束力的法律。”[2]
二、自由、平等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权利
自由和平等是卢梭十分向往和憧憬的境界,他曾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中称:“我愿意自由地生,也自由地死”[1]62。按照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解,卢梭之所以热爱自由,是因为他把自由看作是比生命更高尚的善,甚至把自由等同于德性和善。自由就是服从于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对德性来说还是对善来说,“自由就是善;自由,或者说成为一个人自己,就是成为善——这是他关于人天性善良的论点的一个含义。尤其要紧的是,他提出要以一种新的对人的意义来取代传统的定义,在新的定义看来,不是理性而是自由成为了人的特质。可以说卢梭开创了‘自由的哲学’”[3]自由是人的特质,因而,自由平等构成了卢梭人学思想的重要部分。
卢梭尽管继承了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观点,也从假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论述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和天赋权利,但提出了与他们不同的新观点。
卢梭认为在人类发展的最新阶段“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4]5-6除了自然所造成的年龄、健康、体力、智力、心灵等差异外,其他一切方面都是自由平等的。就人的自由而言,野蛮人自由自在地漂泊游荡于丛林中,过着与世无争自食其力的生活。他们没有栖所,没有语言,也没有技艺,没有战争,也没有联络。对于自己的同类没有任何需要,也无害人的欲望,甚至对人也难以辨认。他们很少动感情,满足于自身的各种真实的需要。他的悟性和智力发展不出他的妄想范围。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一切事物似乎都在阻碍野蛮人拥有摆脱其所处状态的愿望和手段。“例如,他的想象力产生不了图画,他的头脑提不出问题,他那一点儿需要随手即可满足,他还远没有那种驱使他需要更多需要所必备的知识。所以,他既不可能深谋远虑,也不可能有好奇心。大自然的景象总是那种秩序,总是那种轮回,他已经视若无睹。他没有很强的悟性,不会对自然奇观感到惊异。他的头脑中没有那种能促使他观察常见的哲学思想。他的思想受不到任何刺激,完全沉湎于对他当前存在的感觉之中,没有任何关于未来的概念。”[1]99这表明野蛮人对这种自由自在,只注意当下事物的感觉的质朴生活是相当满意的。这种自由植根于人性的法则。因为“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4]5可见,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造物主赋予人的天赋人格,人应该珍视这种权利,不能放弃它。因为它是人所拥有的做人的资格和权利。如果放弃这种权利和资格,无疑既不合人性,也不合道德。
与自由密切相关的是人的平等。卢梭指出:“人与人原本是平等的,就像其他各类动物,在种种自然因素使他们身上发生我们目前尚能观察到的变异之前,同类的动物生来都平等一样。”[1]75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缺乏明确的义务、好坏和善恶的区别。他们与其说是邪恶的,不如说是野性的。由于那时的人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不知什么是虚荣、尊敬,也不知什么是敬意和蔑视,绝少有你的、我的之分,缺失关于公正的正确观念[1]116。正是由于人们生活在既缺乏相互联系,又缺乏互相依赖的自然状态之下,因而他们是自由、平等的。即使有人用暴力夺取另一个人捡到的果实,也不妨碍他们的自由平等。因为这种偶然的行为不构成奴隶与被奴隶,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他们仍然是互不依赖和独立生活的,也是没有私有财产的。
上述观点表明,卢梭的观念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人对人的战争状况的观点和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人们具有天赋的财产权迥然不同。针对霍布斯之言,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不是战争状态,而是恬静、安宁、幸福的和平状态,每个人虽然专注自我保存,但并不损害他人的保存。由于人性是善的,而不是恶的,因而不出现“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战争状态,霍布斯所描绘的战争状态,不会在自然状态中出现,它反映的是“文明状态”的真实画面。针对洛克之言,卢梭认为,洛克所主张的“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自然人在丛林之中散居,缺失社会关系,因而不存在“属于”这种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他们的需要是很有限的生理需要。“看和摸是他的最初状态,这种状态是他与一切动物共有的。肯与不肯,要求与害怕则是他们心灵的最初的活动,也几乎是唯一的活动,这种情形一直维系到新情况使他发生新的发展为止”[5]可见,私有财产权不是“自然状态”的产物,而是随私有制而出现的“文明状态”的产物。
三、人以自我完善者和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参与自身活动
人不仅拥有自由、平等的天性和权利,而且具有拥有自我完善恶化的能力和自由施动者的身份,正是后两者使人能够参与自身的活动,促进人的不断进化、完善和发展,从而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何为自我完善化能力?卢梭认为,“自我完善化是一种需要借助外界因素而实现的潜在能力。这种能力借助于环境渐渐开发的其他一切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现存于个体身上,也存在于全人类。”[1]96自然人显然离不开大自然,大自然为他们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但对自然人的理性、语言、智力和可完善的影响并不大,他们的自身活动和发展依赖于自身的可完善性能力。这种自我完善化能力显然不是固定的,而是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离不开外在因素的影响。正如卢梭所说:“完善化能力、社会美德以及自然人的其他潜在能力,根本不会自发产生的,而是需要许多可能从未有过的外界原因的偶然协同作用才会产生,如果没有这些协同作用,他可能永久的停留在原始状态。”[1]112这些外界的偶然因素和事件如洪水、火山、地震、雷电等改变了自然人散居的生活状态,而是集体聚集起来,克服面临的困难。“这些偶然事件在使人类堕落的同时,又使人的理性臻于完善,在使人变成爱交际的同时,又使他变坏,最终把那个遥远时代的人和世界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幅模样。”[1]123偶然事件的爆发促进了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人越来越高于理性和智慧。换言之,人的自我完善能力在外在偶然事件的推动下不断提升。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人的这种特殊而且几乎无限的能力成了人的一切不幸的根源,正是这种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使人脱离了原本可以安宁淳朴过日子的原始状态;正是这种能力,千百年来启发了人的智慧,也引发了人的谬误,萌生了人的善恶,最终使人成为他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1]96因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既要看到它的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有害的一面。在这里,我们不难知道,正是外界的偶然事件和人的自我完善能力的协同作用,推动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使它由自然状态步入社会状态。
除了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外,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因素是人的自由施动者的身份,这是参与人自身活动最为重要因素。“人与动物是受大自然平等对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残酷又公平的天道法则。动物毫无怨言地绝对服从大自然的法则,动物从不违背大自然为它制定的规则,死在眼前也在所不惜。就这样生生死死,一代代繁衍生息,亿万年始终如此,没有大的更改变化。在此,动物在大自然始终是以被动身份参与自己的活动,受大自然规律支配,大自然是唯一的施动者。人类就不同,大自然赋予人类自我完善化能力,从而在大自然的活动中,人类能以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参与自己活动,不完全屈从大自然使唤,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6]这也就是说,动物的活动受大自然的支配,是被动的,它依附本能决定取舍;而人的活动是主动的,自由的,受自己的独立意志支配。因此。人是以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参与自身活动的。正因为如此,卢梭指出:“构成人类与兽类之间的种类的不是人的悟性,而是人的自由施动者身份。大自然支配所有动物,兽类服从支配,人同样也感受到大自然的影响,但人自认为有服从或不服从的自由,而主要就是由这种自由的意识显出人的灵魂的灵性。”[1]95
综上所述,人的自我完善能力和自由施动者身份,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也是人参与自身活动,促使自己的理性、思维、情感和语言等能力不断完善的根本力量。它们表明,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不断进化,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是精神世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它,人的精神发展可能性难以成为现实性;而人的自由施动者的身份为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保障,显示人的灵魂的灵性。
四、自我保存和怜悯心构成了人的本性
如前所述,人拥有自我完善化能力和自由施动的能力,能够主动地参与自身的活动,这彰显了人的主体性。这里蕴含了两种本性,它们先于理性而存在,其中“一种本性使人对自己的福利和自我保护极为关切,另一种本性使人本能地不愿目睹有感觉力的生灵(主要是人的同类)受难和死亡。”[1]79前者指的是“自我保存”,后者指的是“怜悯心”,它们都体现了人的本性。
卢梭认为,人的自我保存同人的欲望密切相关。欲望是造物主赋予人的生存所必须的情感,它构成了人的自我保存的基本内容。“人们的自然欲望是非常有限的,它们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工具,它们能使我们达到维持生存的目的。”[7]268-269这些基本限度的欲望是保存个体生命和自由所必需的。如果一个人的欲望超过了自我保存的限度,就会奴役甚至毁灭自己,因为人的欲望与能力的不平衡,是造成不幸和痛苦的根源。“所有那些试图征服或摧毁我们的欲望都来自其他方面;大自然并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欲望,是我们违背了大自然的本意,擅自把别的东西当作我们的欲望。”[7]269
在卢梭看来,维持我们最重要的欲望是自爱。“人类与生俱来的唯一激情,也就是自爱,是一种本身并不在乎善恶区别的激情。”[8]因为人生来是善的,热爱正义和秩序。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人具有只是保存自己的原始欲望,人心没有丝毫败坏,没有嫉妒、愤恨、骄傲、仇恨等一系列负面情绪。自爱是我们各种欲望的根源,是体现人终生不弃不离的唯一欲望,也是所有欲望的发端和本原。它们是原始的,与生俱来的先于其他欲望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他所有的欲望都只不过是自爱的演变。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认为一切欲望都是自然的。”[7]269人最初的生活和动物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纯感觉的生物,大自然赋予了人的资质没有被利用,大自然的东西也很少去索取。但后来,遇到了困难,就会克服它们。例如,其他动物与人争夺食物;树太高果子够不着;还有觊觎人性命的猛兽。所有这些困难都必须努力去锻炼身体,必须锻炼得精力充沛、斗志顽强,灵活机敏,奔跑迅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实现自我保存。
自爱本身始终是好的,始终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这决定了每个人的自爱特质,就是要始终关爱生命,对自己的生命有极大兴致。这是我们首要和最重要的责任。因此,为了我们的自我保存,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生命关爱,甚至胜过爱其他一切东西。从这种自我保护的情感中直接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同时也会对那些维护我们生存的人加以关爱。“最初,这种爱纯粹是无意识的,有谁给我们带来幸福,我们就喜欢谁;有谁给我们造成伤害,我们就痛恨谁:这完全是一种盲目的本能所致。”[7]269受人的本能影响,儿童的第一感情就是爱自己。由此引发的他也爱那些亲近他的人,如奶妈和保姆。“对他来说,奶妈和保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也是愿意帮助他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孩子才会开始对他们产生爱的情感。”[7]270随着儿童人际交往的扩大,儿童的自爱就会发展为自私。尽管儿童在观察亲近的人中养成了对他的同类抱有好感的习性,但随着人际关系的复杂体验,产生蛮横、爱嫉妒、喜欢骗人和报复人等毛病,自私心随之产生。它涉及的是自己和别人的比较,在比较中只顾自己的满足而不顾及别人。它与自爱不同,自爱满足的是自己,当真正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儿童会心满意足。由此可见,“温和而忠厚的性情可以萌生自爱,而偏激和易怒的性情只会引发自私。”[7]271在这里,卢梭区分了自爱和自私的差异,由此导出了善恶观念,要求人们从善抑恶,因此蕴含了一些合理的内核。
为了增进自爱欲望的健康发展,卢梭建构了自爱与他爱相结合的原则,即“爱应该是相互的。为了得到别人的爱,就要使自己成为可爱的人;为了得到别人的喜欢,就要使自己变得比别人更可爱,而且要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加可爱,至少在他所爱的对象里应该是这样的。……当一个人想到被爱有一种甜蜜的感觉时,该多么希望所有的人来爱他。”[7]272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人,是人学研究的重要路径。正如卢梭所说:“对人的研究,就是研究与他相关的各种关系。当只能凭借身体进行自我认识时,他应该通过他与事物的关系来研究自己,他要利用他的童年开展这样的研究:当开始感觉到精神存在的时候,他就应该通过他和别人的关系来研究自己,他应当利用一生来进行这样的研究。”[7]271
卢梭认为,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除了拥有与生俱来的“自我保存”的能力——自爱外,还拥有“怜悯心”。怜悯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感,它的重要作用在于,能使自身强烈的自爱情绪得到克服,促进人类的相互保护。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怜悯对人类是有益的,适合于那些较弱并且容易遭受不幸的生灵,而且由于它是很天然的,就连动物身上有时也有很明显的怜悯情感。为了让儿童具有情感和怜悯之心,我们必须让他不仅要懂得他的同类会遭受到的痛苦和悲伤,而且还必须让他懂得其他人还有另外的悲伤和苦楚。这是儿童怜悯心产生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能激发他身上的那种善良、仁慈、博爱、怜悯等愉悦和温暖的情感,并阻止贪婪、仇恨等恶习的萌生,那么,这些恶习既会使人的情感化为乌有,而且还会出现负面作用。卢梭将以上思考归纳为三条原则:(1)在人的心灵中占有位置并更应关注的,是那些比我们更值得同情的人,而不应该是那些更幸福的人;(2)在别人的痛苦中,我们只是同情我们认为无法免除的那些痛苦;(3)我们对别人痛苦同情的程度,不取决于别人痛苦的多少,而取决于我们对于遭受这种痛苦的人的感受[7]285-288。
卢梭对人的自我保存和怜悯心的论述,进一步论证了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这既是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人对人的战争状态的有力反驳,又是对私有制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批驳和揭露。
五、人的自由、平等的本性随“文明社会”的产生而不复存在
卢梭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命题:“人是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4]4“一切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旦落到人的手中,就全破坏了。”[7]7“自然使人幸福和善良,而社会使人堕落和不幸。”[1]116这三句话尽管对人的善良、自由、幸福与不自由、堕落和不幸的论述侧重点有差异,但它们表达的共同意思是:自然与文明是对立的。在自然状态下,人是善良的,天生拥有自由、平等和幸福,是社会状态导致人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丧失,人性和道德的堕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拥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正是这种自我完善化能力,为人类的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提供了可能性,而外在的因素如生产力的发展、语言的出现、人类的繁衍、家庭的形成、人际交往的增多、尤其是私有制的出现等,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人天生地拥有自由平等,自我保护是人类首要关心的事情。本能使他们去利用大地为他提供的一切生活必需的东西,饥饿和其他种种改变使他相继采取各种生存方式。人口的增长,土地、气候和季节的差异,造成了人的生活方式的不同,由于大地上的一切被荒年、漫长的寒冬、酷热的炎夏毁掉,他们必须学会新的谋生手段。例如,在海溪河畔,他们发明了钓线和鱼钩,成为渔民和以鱼为主食的人。森林里的人创造了刀箭,成为猎人和尚武之士。居住在寒冷地区的人,他们披上了兽皮。他们还因闪电、火山喷发、或者某次幸运的机会,认识了火,学会了保存火种。“最初取得的这些进步,终于使人类在其他方面加快了进步的速度。”[1]129例如,人的头脑日益开化,人的本领日趋完善。人们不再睡在原始的森林里,也不再栖身于洞窟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坚硬锋利的石块用来伐林,挖土地,建起了树枝搭的小屋,后来又想到在墙上糊上泥。这些事情引发了人类的第一次变革,随之带来的是家庭的确立,私有财产以及纠纷和斗殴的出现。人类的面貌有了改观。由于气候的共同影响,同类生活和食物的需要,他们聚集起来形成了部落。最后在每个地区形成了习俗与信仰一致的“国家”。随着人们各种观念和情感的相继产生,头脑和心的相互作用,人的交往日益增多,关系日益密切。这时候人们把唱歌和跳舞当成娱乐,相互之间的关注日益增多。“这就向不平等迈出了第一步,同时也向堕落迈出了第一步。这些最初的偏爱情绪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鄙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耻心和仰慕之情,由这些新的酵母引起的发酵,最终产生了危及幸福和天真的致命毒素。”[1]132-133
私有制的出现,文明的发展,尽管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如人的能力得到了开发,记忆力和想象力也在发挥作用,自尊心得到了关注,推理能力日趋活跃,头脑都开发到了最佳状态。但这种自我完善化能力,更多是给人类带来了痛苦和不幸,人的天然自由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统治、奴役、暴力和掠夺等。野蛮人生活在自我之中,能够根据自我意愿而生活;社会人始终超越自身,依据别人的看法而生活,活在他人的评价之中。不仅如此,这一过程还使人类日益走向不平等,人性的败坏和道德堕落势在必然。卢梭认为,人类存在着两类不平等,它们是自然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和伦理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前一种不平等是自然所造成的,是“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人和动物都具备的不平等,而后一种不平等是人类进入社会状态,由私有制所引起的不平等。换言之。它是私有制的产物。它使所有的人产生一种损人利己的卑鄙的癖好和隐藏的嫉妒心理。“一面是相互竞争,一面是利益冲突,两者都带有秘而不宣的损人利己的欲望。所有这些都是私有制最初产生的后果,都是新产生的不平等的不可分离的伴生物。”[1]140
卢梭通过对人类不平等的演变考察,指出人类的不平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法律和所有权的制定阶段,表现为贫与富的对立。根据富人和穷人的性格的差异,人类开始产生支配和奴役与暴力及盗窃,平等随之打破。“富人们巧取豪夺,穷人们盗窃抢劫,双方都怀有非常强烈的偏见,窒息了人们的天然的怜悯,压抑了很微弱的正义的呼声。人就这样变得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凶狠毒辣了。”[1]140-141穷人和富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安全也无法保证,整个人类被推向劳作、奴役、苦难的深渊。第二个阶段是行政官职位的设立,认可强与弱的分野。行政官要篡夺非法权力,就难免要培植一些亲信来分享,公民们也因怀有盲目的野心甘当奴才听凭他人的压迫,眼睛不是盯着上面,而是盯着下面,目的不是独立自由,而是支配他人、奴役他人。第三个阶段是合法权利向专制权力的转变,认可奴隶主与奴隶的分野。这应是最大程度的不平等。“历史的逻辑是物极必反,这种极度不平等、不自由又成为新的平等和自由的起因。这就是卢梭探索社会不平等根源和发展所得出的最终结论。”[9]这也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带给我们的启示。
六、人的道德随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而堕落
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与德行是不相容的,科学和艺术越进步,人的道德越堕落。它们“给人们身上的枷锁装点许多花环,从而泯灭了人们对他们为之而生的天然的自由的爱,使他们喜欢他们的奴隶状态,使他们变成了所谓的‘文明人’”[10]10然而,他们从外表上看一身都是美德,而实际上一种美德都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变坏。真诚的友谊,真心的敬爱、深厚的信任感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的猜疑、彼此的冷漠、互存戒心、互相仇恨和背信弃义。
就科学而言,它的所有学科都是虚幻的,它产生于坏的思想。“无论是查遍世界的编年史,还是通过哲学的理论研究来推论难以确定的史事,都找不到人类的知识有一个表明人类喜欢研究科学的起因。天文学诞生于人的迷信,雄辩术是由于人们的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产生的,数学产生于人们的贪心,物理学是由于某种好奇心引发的。所有这一切,甚至连道德本身,都是由人的骄傲心产生的。”[10]25由此可见,科学产生于虚伪、贪婪、骄傲等坏思想,但它们的发展又使闲逸、虚荣奢侈和拜金主义得到滋长。卢梭还专门阐述了科学和艺术与奢侈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科学和艺术,奢侈之风就难以盛行,没有奢侈之风,科学和艺术也无由之发展。”[10]28奢侈之风的盛行,败坏了风尚和人们的审美力。“如果在才俊之士中间有一个心灵坚毅的人拒不趋时媚俗,不愿制造无聊的作品来玷污他自己,那他就必然会遭到不幸!”[10]31
就哲学而言,尽管有一些哲学家奔走呼号,想唤醒人们美德和人类天经地义法则的爱,但哲学家奢谈理论的各家学说却深深地轻视了如何做人和做公民。按照卢梭的理解,尽管哲学家对人类的命运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思考和观察,并按照人的价值来评判人,然而,由于他傲气十足地轻视别人,因而不可能对人产生深厚的爱;由于他十分自私,把一切利益都捞归自己,因而他只爱自己,爱自己的心增一分,对别人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就增一分;由于他是哲学家,而不是任何人的亲友和公民,他也不会热爱家庭和祖国。
就文学而言,由于文学爱好者做学问存在贪图安逸和爱出风头习气,随学问的增多,这两种坏习气愈发严重,因而,“对文学的爱好,预示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中间已经开始的腐败现象将加速发展”[10]52,最终将使他们为了获得成功而不择手段,道德受到损害。文学家一方面追求生活情趣的高雅,喜欢繁文缛节的礼仪与低三下四的吹捧,时时渴望别人对他备献殷勤,时间一久,他会变得心胸狭窄,灵魂卑鄙;另一方面他对别人事事嫉妒,争强好胜,对同行如同冤家,造谣中伤,欺骗和背叛朋友,无恶不作。“如果说哲学家轻视别人的话,文学家则是招人家轻视他自己,而这两种人都在争相使他们最后成为被人轻视的人。”[10]56
就艺术而言,它削弱了人的勇敢精神,瓦解了人的士气。他举例说,当罗马人“随着他们开始喜爱绘画、雕刻和金银器与精工艺之时,他们骁勇善战的气概便逐渐消失。这个泱泱大国似乎注定要成为其他民族的前车之鉴。”[10]33
根据以上论述,卢梭得出结论,“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日趋完美,我们的心灵便日益腐败。……随着科学的光辉升起在地平线上,我们的道德便黯然失色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看到。”[10]14尽管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科学与艺术的进步给人类的身体和精神尤其是道德带来恶果,但卢梭认为他的目的是捍卫美德,而不是谴责科学的本身,要论述的是“事关人类幸福的真理之一。”[10]5
结语
卢梭的人学理论是在深刻批判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等哲学家的人学理论,吸收他们人学思想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得以建构的。它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其内容包括“自然状态”中的人比“社会状态”中的人优越;自由、平等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权利;人以自我完善和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参与自身活动;自我保存和怜悯心构成了人的本性;人的自由平等本性随“文明社会”的产生而不复存在;人的道德随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而堕落。它们构成了卢梭思想大厦的基石。卢梭无论是对科学和艺术的论述,还是对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探讨,抑或是对教育哲学的研究,都是以其人学理论为支撑的,后者构成了前者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彰显了卢梭的人学理论在他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卢梭的人学理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首先卢梭的人学理论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成分,对后世哲学家和教育家对“人”的问题的探讨和人学思想的建构有借鉴价值。后世学者在回答何谓人性、自然人与文明人的关系、人的自由天性和权利、文明社会与人的自由本性的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上,仍然可以回溯卢梭的人学理论,并从卢梭的人学理论中获得借鉴和教益。其次,卢梭的人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体反主体的效应,从总体上刻画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全面冲突的社会图景,体现出的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关怀,对理性和文明的怀疑和反思,客观上要求人们对文明进化的代价进行痛苦的反思。”[11]再次,卢梭的人学理论对后世人学理论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吸引了康德、歌德、杜威、卡西尔、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施特劳特等哲学家、文学家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和人学理论的建构。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康德,他认为卢梭的地位堪与牛顿的地位媲美,牛顿发现了宇宙的规律,而卢梭发现了人性的规律。正是卢梭启发了他尊重人,他把卢梭的思想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康德称赞卢梭是这样一位道德哲学家,他在种种的畸变和遮蔽之下,在人类与其历史进程中自我打造和蒙罩的一切假面之下,探悉到‘本真的人’,这也就是说,康德之所以尊敬卢梭,乃是因为他省察并高扬了人类的卓然超拔和不变鹄的。而他本人正是要沿着卢梭所开辟的这条道路向前突破,并竭力继续走向那个目标。”[12]第四,卢梭的人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卢梭的人学理论构成了文明社会发展的尺度、建立平等社会的尺度、人的自由、平等本性发展的尺度和人的道德发展的尺度,它像一面镜子,既可以观照社会,也可以观照个人,促使我们对文明社会和个人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互联网化、科技生活化的时代,它既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舒适、便利的一面,又给我们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拜金主义、人性能力弱化、社交方式的改变、情感冷漠等。这些负面的影响使人不断的远离原初的自然状态,成为被科技和文明奴役的存在。卢梭对文明社会的批判和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反思,无疑对当今社会和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警示意味。“卢梭式”的反思和批判,可以使我们对当今文明社会的进步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恶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给予我们解决人性异化问题的方法论的启示。总之,卢梭的人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回归人性的本真,有助于解决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人性异化问题。我们要努力学习“卢梭式”的反思和批判,从对人性异化的批判中,寻找一条切合人性发展之路,让人不断地走向自由、幸福之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