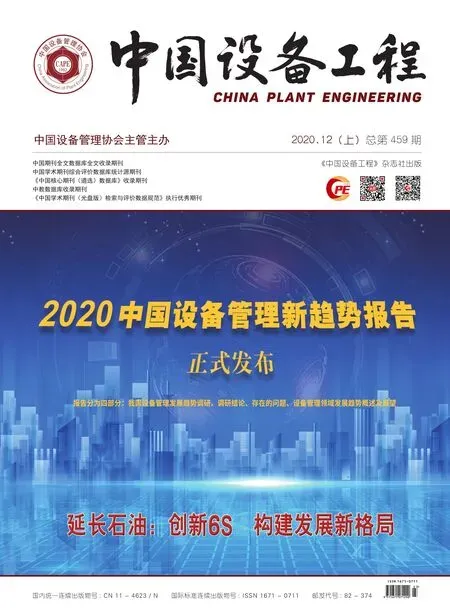论跨境油气管道运输中的过境自由原则
张颖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回顾人类开展活动和交往的过程,“过境”行为可谓如影随形。自20 世纪30 年代与能源过境有关的政府间合作开始出现,2006 ~2014 年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不断发生的天然气过境争端,能源过境运输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其恰如一道桥梁,连接着能源产业链条从上游的勘探开发向下游的炼化销售之间的转化。然而,不同于非歧视原则已经成为过境领域和国际法上一项普遍适用的原则,能源管道的过境自由尚缺乏广泛的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支持,对于国际法上是否已经存在“过境自由原则”还未有定论。通过追溯和探讨过境自由原则的国际法理论基础,尤其是在能源管道过境领域的条约实践和国家实践,全面清晰的认识过境自由原则,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和加强能源管道合作地理论前提和制度基础。
1 过境自由原则的内涵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以及国际法作为一门专门调整国家间法律关系的法律制度的出现,国际法意义的“过境”(transit)有了其专门的定义,即指“货物或人员至少在两个国家的边境通过”,过境自由原则是指货物或人员有在至少两个国家的边境通过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国际法中的过境总是与至少一个国家(过境国)的领土主权相关。过境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利益给予过境,也有权否认或限制通过其境内的任何运输,甚至中断以前允许的过境。在能源管道过境领域,虽然迄今国际社会还未有一部统一的国际能源管道运输条约的出现,但是,随着相关国际条约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过境自由原则已被普遍认为是过境运输领域一条具有基础意义的原则,该原则的外延和内涵也在不断拓展并日渐明晰。
2 过境自由原则的实效分析
2.1 过境自由原则的法律实践
(1)一般性国际条约中的过境自由原则。第一部分是过境制度在国际条约上的早期出现和发展。包括1919 年国际联盟时代的《国际联盟盟约》首次提出与过境制度相关的过境自由和平等待遇原则1921 年《巴赛罗那过境自由协定规约》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中对过境权做出明确规定。第二部分是随着海洋法的发展和公海自由原则的确立,联合国主持制定有关公约。包括1958 年《日内瓦海洋公约》确认所有国家有权在公海和大陆架上铺设海底管道;1965 年《内陆国过境贸易公约》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中对内陆国过境问题进行专门规定;尤其是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了海底管道的法律制度和内陆国过境规则。第三部分是WTO 主持的与国际贸易制度相关的GATT、TRIPS 和《贸易便利化协议》。GATT1947 第5 条“过境自由”对适用于所有货物的一般过境权做出了规定并被其后的GATT1994 全部接受,而《贸易便利化协定》则进一步澄清和细化了GATT1994 有关过境自由的规定。
(2)《能源宪章条约》中的能源管道过境自由。除了上述国际公约外,1994 年《能源宪章条约》是一项专门针对国际能源问题的国际公约,涵盖能源合作(贸易,投资,过境,能源效率,争端解决)所有方面,也是第一个阐述能源过境详细原则的多边文书。《能源宪章条约》第7 条第1、4 款的规定涉及能源过境的过境自由原则。规定每个缔约方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过境运输”,不得“在起运地,目的地或所有权方面进行歧视,以及由这些差异而产生价格歧视”,不能“无理由的拖延、限制或增加过境费用”且过境请求受跨国管道的国民待遇要求的限制。第7 条第5 款的规定还涉及能源过境自由的例外。
2.2 国家间有关能源管道过境自由原则的条约实践
有关能源管道过境的政府间协议为所有协议缔约方规定了确保管道流量过境的义务,通常包含为实现该项目所必需的授予土地权利的义务,确保缔约方不干扰或便利项目的建设和运行的义务,以及要求缔约国不要征收(附加)税的义务,这些条约义务的规定和履行都体现出过境自由原则的重要地位。具体来说,其中有一些属于结果义务(obligation of result),如“不允许或要求中断或限制天然气运输自由”(“纳布科协定”第7.2 条);保证通过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能源充分和不受限制地过境(俄罗斯-希腊南溪协议第9 条;俄罗斯-保加利亚南溪协议第10 条;俄罗斯-匈牙利南溪协议第8 条)。有一些属于行为义务(obligation of means),如对在其领土内的项目部分的运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义务,以及“确保天然气不间断流通”(ITGI 协定第2 条);承诺尽一切努力确保通过石油管道不间断运输石油(布尔加斯-亚历山大波利斯协定第1 条)。如果过境国中断或减少过境,将会违反所有这些过境义务,也会违背过境自由原则的要求。
3 对过境自由原则的评价
过境自由从来不是一项绝对权利,该权利的获得和行使更多的基于各国在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中做出的承诺以及在条约项下履行的义务,是基于国家主权权利的行使而进行的权利让渡。在《能源宪章条约》制度内,过境自由被认为是缔约方集体能源安全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能源资源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路径需要越来越多地跨越多个国家边界。随着国家主权观念从绝对向相对转变,过境自由权利也在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条约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承认,能源过境自由的基本原则地位日益清晰。
自格老秀斯于国际法的形成年代提出“海洋自由原则”以来,国际法上关于“过境自由”的国际习惯的最后一项一般性研究是1957 年劳特派特的《国际法中的过境自由》一文,该文将过境权称为“不完美的权利”,在充分认可“过境自由是群体间最基本的需要之一”的同时,对于“过境自由”能否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上的规则,并未给出肯定的回答。换言之,过境自由原则还没有达到像“公海自由原则”这样的习惯国际法的地位和效力,其是能源过境合作各方追求并希望达到的目标。
4 过境自由原则对我国开展能源管道合作的启示
4.1 考虑接受《能源宪章条约》对中国的临时适用
目前,与中国已经签署了管道过境合作协议的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属于《能源宪章条约》缔约方而非WTO 成员方,接受《能源宪章条约》一方面可将以“过境自由原则”为基础的过境规则纳入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的能源贸易和运输合作中,可以确保对中国供应的油气资源不会半路被拦截,使中国成为比俄罗斯更安全的油气资源输送目的地,且条约项下的能源投资保护、非歧视待遇等都将对中国和中国的投资者适用;另一方面,加入《能源宪章条约》也会使中国承担遵守过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承担环境安全标准的要求等义务。从给予中国的跨国能源企业更大的安全感,鼓励能源投资与合作有序进行的角度出发,中国可以采用过渡式地加入程序,接受《能源宪章条约》对中国的临时适用,并在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决定是否最终批准加入。
4.2 签署更多的诸边、多边能源过境协议
由于过境自由的国际习惯法尚未形成,各个国家都是基于双边或多边条约下的授权而享有过境权利。迄今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缅甸分别签订了多项油气管道合作项目协议,随着能源合作的深入开展,中国也面临协调不同国家之间利益和矛盾的局面。因此,中国尚需签署更多的诸边、多边能源过境协议,发挥过境自由原则的条约法规则效力,通过更多有关过境自由的条约实践更好的建立和维护能源过境运输的纽带,明确丝绸之路能源带所覆盖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过境国对长期能源供应、需求和过境运输的承诺,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能源合作的网络走向明朗和清晰。
4.3 切实履行已加入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便利过境责任
中国是WTO 成员国,且已于2015 年9 月完成接受《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国内核准程序。随着《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在即,履行协定下的责任近在咫尺,通过全面审查与过境相关的海关监管措施,做好协定项下免征税费、不歧视、手续简化、协调成员方合作等各项承诺,清理阻碍过境自由的边境执法措施,既是履行已加入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便利过境承诺的体现,也是谋求“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区域能源合作与发展的有效路径。
4.4 把握在能源宪章进程以及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
2015 年5 月在海牙举办的能源宪章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新的《国际能源宪章》,中国在会议上签署了该文件。新的《国际能源宪章》体现出“去欧洲化”的发展倾向,旨在构建以国际能源合作和监管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框架,这与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不谋而合。中国应把握能源宪章现代化进程的权利困境所提供的机遇,着力提供和建立起相应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在制定有关能源过境的规则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国开展多边能源合作,解决能源过境争端,实现能源安全和全球能源治理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