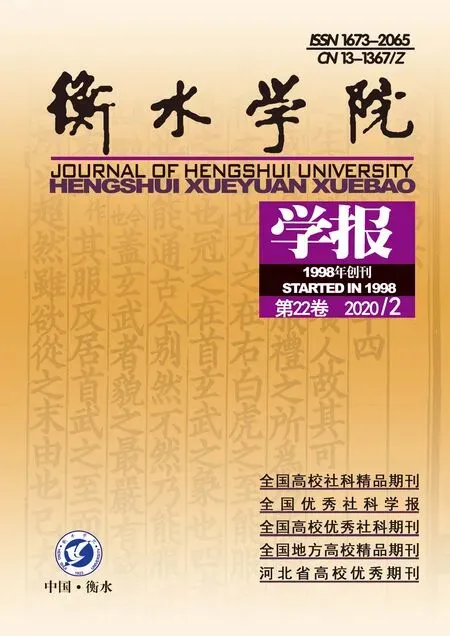有效辩护辨析
(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550000)
当下,有效辩护问题是理论界、司法实务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这个问题,探寻掣肘有效辩护目标实现之因;运用不同的理论检视这个问题,指出有效辩护不能实现之恶果;结合司法实践研判这个问题,提出实现有效辩护之路径。但是,这些意见或者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下面,笔者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有效辩护之界定
要研究有效辩护,首先要明确其内涵,这是开展此项工作的内在的基本要求,也只有如此,研究才具有价值。
目前,理论界对“有效辩护”概念尚未做出定论。陈瑞华指出:“按照一般的职业标准,有效辩护是指律师为被告人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法律帮助。”[1]贺江华等认为:“有效辩护更多强调刑事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包括案件实体部分的意见以及程序部分的异议)能够被办案机关接受并获得有利结果,对办案机关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不仅仅流于形式上的辩护。”[2]熊秋红从狭义层面对有效辩护进行界定,认为有效辩护是指“律师在刑事案件中认真的、有意义的代理,包括律师要就所有权利对被告人提出建议,律师要根据流行的职业标准合理履行所要求的任务”[3]。这些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如果孤立地仅是从律师角度依据律师职业标准研究、分析有效辩护问题,而不将其置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论证,是很难对其做出相对精准而科学定义的。
欲论“有效辩护”,先要明确“有效”之义。有效,即为有成效、有效果。同时,也应看到,在有效辩护这一词组中,“有效”是用来限制、修饰“辩护”一词的。如此,从字面理解便知,有效辩护强调的是因律师辩护而取得的最终成效,关注的不是律师辩护的过程而是辩护意见对案件处理结果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在美国,“判断有效与否的基本点必须是,律师的行为是否损害了对抗制诉讼的基本功能,以至于难以通过审判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4]。他们将律师辩护行为与公正结果之关联关系作为判定有效辩护的标准。然而在我国,辩护效果究竟怎样,律师是无法对此做出预判的,因为辩护意见对案件处理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律师的辩护质量,还要受案件承办者的个人好恶、政治与业务素养、对社会的担当、对法律的敬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轻视律师辩护意见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痼疾。有学者对33 起公开报道的冤案进行了实证考察,其中有32件案子存在轻视律师辩护意见的情况,占比高达97%[5]。那么律师纵然使出浑身解数,提出既有事实根据也有法律依据的辩护意见,如果得不到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的认可和接受,这一切皆会是徒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维护也不会产生实质性效用。只能是辩而无果,又何谈有效辩护呢?
由此可见,若单纯从律师辩护工作的角度,依据律师职业标准来讨论有效辩护从而对其进行界定,并据此检讨律师辩护水平及其辩护工作质量,有失偏颇也有失公允。既然有效辩护注重的是结果而非纯粹的辩护过程,考量的是通过律师辩护所达到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效果,那么,就不能忽略甚至舍弃对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办案行为的关注。因此从结果论,才能对有效辩护做出契合实际的概念阐释。依据这样的思维逻辑,笔者认为,所谓有效辩护,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同时,针对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对此做出中肯评价并予以采信,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二、有效辩护之困境
有效辩护目标之实现,既需要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引,也离不开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保障。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在其境内并受其管辖的所有的人……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捷有效的程序和机制。”提出了实现辩护权的制度性保障体系的构建要求。反观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基本司法理念,是难以实现有效辩护的。
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始终被打上“罪犯”的标签,这从法庭位置的设置就可见一斑。在法庭上,被告人的位置是在审判员席位的正前方,而代表被告单位出庭参与诉讼活动的诉讼代表人席位却不在此①《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1条规定:“……开庭时,诉讼代表人席位置于审判台前左侧,与辩护人席并列。”。可以说,这样的位置设计是非常微妙的,也透显出司法机关的一种心态:被告人是犯罪者,需要接受国家和人民的审判,只能坐在被告人席;诉讼代表人不是罪犯,不需要接受国家和人民的审判,可以远离被告人席就座。
这样的位置设计,势必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第一,虽然“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确定有罪”作为一项原则已在法律中有所规定,但因位置设计易误导人们对被告人身份的判断,使人们从骨子里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正因如此,许多法官在法庭上对待被告人的态度往往简单粗暴,缺乏应有的尊重。第二,会让人误判审理内容。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法庭审理的对象应该是案件事实,而不是被告人——此时只是涉嫌犯罪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罪犯。现实是,基于这样的位置设计,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审人。在一次庭审中,面对律师提出诉讼代表人应坐在律师席旁之要求时,审判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不坐在被告人席,我审谁?“我审谁”,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啊!而在韩国,朴槿惠与律师坐在一起,法庭的审理工作不也是正常进行吗?第三,被告人远离自己的辩护人,不能及时进行事实、法律层面的沟通,无论是被告人自行辩护还是律师辩护,其效果都将大打折扣。正因为不能正确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画上等号,那么在疾恶如仇的心理驱使下,轻视辩护意见甚至是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辩护意见,似乎成了一种惯常性的思维取向。
其次,律师的辩护作用常被错误定位,这既有社会认识方面的原因,也与国家对律师的评价有关。“反映在传统观念上,犯罪嫌疑人的辩护行为不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利行为,而被视为与侦查权力相对抗的行径,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律师容易背上为‘坏人’说话的社会恶名”[6]。故而,长久以来,人们总是用“讼棍”这样的贬义之词形容律师。社会的负面评价,将在一定程度上挫伤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积极性,影响到律师开展辩护工作之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当然,社会的负面评价虽对律师辩护工作开展有影响,但这样的影响总是有限的。
如同社会评价一样,国家对律师的评价也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律师伪证罪”就是最好的明证。“‘律师伪证罪’的单列,容易产生误导作用,产生负面影响。让人错误认为,律师是造成伪证之罪魁,是干扰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大敌,从而破坏律师队伍形象,破坏尚还十分脆弱的律师制度”[7]。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一罪名的设立颇有微词,不断有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提案的形式,呼吁取消此罪名,但“律师伪证罪”犹似磐石,始终无法撼动。“律师伪证罪”如同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严重束缚了律师的手脚,令律师们不敢创造性地开展辩护工作。特别是在证据收集过程中,面对证人证言,基于证言的可变性,律师们总是望而却步,唯恐触碰了“律师伪证罪”这颗雷而身陷囹圄。这种带有“敌视性”的立法规定,也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律师的接纳程度,影响到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对律师辩护意见的态度。如此,律师辩护意见被轻视,也就不难理解了。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是社会共知的司法怪象。如此一来,遑论辩护质量、辩护效果。
再次,公、检、法三机关具有天然的亲密关系,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使得律师辩护权的有效实现成为难题。有人将公检法机关这种关系比喻为:公安机关生产产品,检察机关对产品进行质检,人民法院最后进行产品销售。虽然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甚至存在调侃之意,但也揭示出公、检、法三机关实践中相互配合的关系和利益共同体的实质。前述33个冤案中,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的案件占比为97%,非法证据不能有效排除,疑罪从无原则不能得以充分实现,无疑是三机关重配合轻制约的关系使然。笔者在参与公安机关处理某团伙诈骗案件时,其他被告人均被法院定罪量刑并已交付执行,本案卢姓被告人因另案处理,滞后于其他同案被告人开庭。辩护人提出证据不足、疑罪从无的无罪辩护意见,承办法官却意图通过已入监被告人收集卢姓被告人“有罪”证据,丧失其中立地位,代行指控职能。在此类情况下,律师辩护效果能有几何,已不言自明。
最后,先天不足的庭审结构关系,已然成为律师开展有效辩护工作的又一障碍。科学的庭审结构关系,应该是等腰三角形式的,法官居于等腰三角形的顶角,控、辩双方分列两底角。不偏不倚超然于外的居中裁判,是法官居于等腰三角形顶角之基本要义。然而,控方的特殊身份,完全打破了这一应有的平衡。“受×××检察院指派出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这是每位检察员发表公诉词时都需要讲的一段公式化语言。这一语言清楚表明,在法庭审理中,控方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一是诉讼参与者,接受法庭指挥;二是法律监督者,具有凌驾于法官之上的权威。如此,要想法官真正处于超然状态,对被告人而言,很可能成为一种奢望。不能实质性居中,法官的裁判或将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实践中,面对存疑案件,法官可能会根据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长短,做出适当的量刑处理。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中,律师辩护又如何能取得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效果?
三、有效辩护之路径
虽然面对诸般制约律师辩护工作有效开展、影响律师辩护工作积极性的问题,我们仍不能舍弃对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梦想。
首先,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制度之建构与司法之改革,离不开人,特别是法律人的参与。法律的制定与推行,也必须仰仗法律专业人士和法律专业队伍。具体到律师有效辩护问题,也不能忽略了人的因素的影响作用。如前述,律师辩护的有效性,非律师一方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就能达此目标,这需要刑事诉讼参与各方共同合力而为,所以,首先应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这是本。舍本逐末,自不可取。培养一支敬畏法律、崇尚正义的司法队伍,才能排除一切世俗干扰,也才能真正实现其独立办案之法律目标。有了这样一支司法队伍,律师辩护之意见也才有了真诚的倾听者、理性的分析者、秉公的取舍者。如此,律师的辩护才不再虚化,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但是,要培养并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实非易事,需要循序渐进。
其次,客观公正地评价律师工作。思想支配行动,任何制度建设或改革,只有全社会对此形成主流认识或者制度建设者基本统一了思想,才能提到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若国家不能对律师在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做出客观评价,不能改变对律师的歧视性态度,社会公众仍然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律师和律师群体,仍然会对律师工作给予负面评价。在这样的思想导向和舆论氛围之下,围绕如何实现律师有效辩护,是很难开展有建设性的工作的。一种思想的产生、一种思维定式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几十年甚至成百上千年的积淀而成。同样,思想的改变、思维方式的转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再次,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革命性重建。制度建设或者司法改革,不能是零敲碎打式的修补性工作,应该是具有颠覆性的系统工程,因为,律师辩护工作贯穿于刑事诉讼过程始终。也就是说,在每一个诉讼阶段,均应关注如何从制度建设上为律师辩护工作打开方便之门,如何从制度层面确保律师辩护意见得到最起码的尊重。简言之,实现有效辩护价值目标,需要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革命性重建,而非部分学者所倡导的制度修补。面对如此恢宏巨大的工程,必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前期调研、分析论证、工程设计等等工作,然后再进行落实并着手建设。
一言以蔽之,在掣肘律师辩护功能有效发挥的种种问题消除之前,在律师辩护严重虚化的现实背景下,是很难提出一些中肯的有效辩护实现路径的。
论及此,笔者撰写此文,并非传递在困难面前消极无为的思想,而是希望人们能正视现实,从提高律师自身辩护质量入手,多作有益探讨。司法部门、司法人员也应密切关注律师辩护观点,愿意接纳律师的辩护意见。同时,也希望人们能意识到孤立、片面地研究有效辩护之弊,拓展思路,全面、客观审视制度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今后的制度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