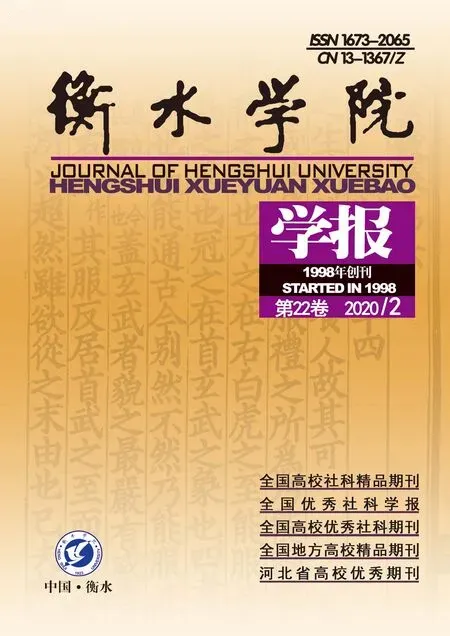张岱年先生的董仲舒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最早见于1932年在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的《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一文,其中发掘了董子的“一些近乎辩证法的思想”①张岱年说:“董仲舒认为天地间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的作用,阴阳是相反的二物。”“阴阳二气虽然相反,但又‘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董仲舒将‘物莫无合’的原则运用于许多问题上,如在人性论上,他便主张性情二元,在伦理上他便主张仁义的对立以及仁智的对立。”(《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页。)。1933年,总结“本根”或“元”的含义时,张岱年指出董仲舒的“元”乃“统摄义”[1]168。1935年,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书评里,张岱年赞同冯氏“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很客观的看法”[2]。但较为系统的董仲舒研究则集中在1935年至1937年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一书中。《大纲》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也多次谈到董仲舒,然而除却研究方法有所变化和增加少数新问题外,所论大都不出该书。故而,我们以《大纲》为讨论的中心。
一、《大纲》前的董仲舒研究
考察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的意义,诉诸史学史的脉络无疑是一个可行的路径。换句话说,即从董仲舒的研究史中去分析其研究的价值。
对于董仲舒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关注,可以上溯至其后约二百年的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王充屡屡提及董仲舒,其中多是谈论其“雩祭”“策文”等问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探讨则至少有二:第一,指出董仲舒情性说的思想渊源在孟、荀,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评判②“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也。’若仲舒之言,谓孟子见其阳,孙卿见其阴也。处二家各有见,可也;不处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恶,未也。夫人情性,同生于阴阳,其生于阴阳,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纯有驳。性情〔生〕于阴阳,安能纯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实”。(黄晖:《论衡校释》卷第三《本性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9-140页。);第二,认为董仲舒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完善者③“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黄晖:《论衡校释》卷第十三《超奇篇》,第614页。)“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黄晖:《论衡校释》卷第二十九《案书篇》,第1171页。)。当然,王充的结论乃基于他自身的理论立场而为,然而却不失参考价值。后世的宋明理学家对董仲舒的整体评价不高,例外的是,《汉书》所引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却格外被他们推崇,程颢甚至认为“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3]324,二程弟子游酢也盛赞董子此句“善乎其言,始可与言仁也已矣”[4],朱熹亦云:“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5]这两句话之所以受到理学家的青睐,在于他们“惟义所在”[6]的价值取向与董子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晚清的董仲舒研究,春秋学是重点,且笼罩在经学研究模式之下。廖平反对“始于董子,成于何君”的“王鲁之说”,认为“董子立义依违,首改‘素王’之义,以为托鲁之言,此董子之误,后贤当急正之者也。且其说以王意不可见,乃托之‘王鲁’;托者假托,实以‘素王’为本根,‘王鲁’为枝叶,因王意不见,乃假‘王鲁’以见‘素王’之义。是董子之言‘王鲁’者,意仍主‘素王’也”[7]。康有为更是借助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而宣扬以公羊三世为核心内容的托古改制说:“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变周制,以殷、周为王者之后。大言炎炎,直著宗旨。孔门微言口说,于是大著。孔子为改制教主,赖董生大明。”[8]“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9]众所周知,康氏的观念直接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政治目标。皮锡瑞则认为:“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10]立足于客观的立场反观清代之前的董仲舒研究,毋宁说宋代的程朱和晚清经学家反倒不如东汉王充的深刻,程朱在整体上蔑视董子思想而独取其义利观,晚清经学家则带有更多的“成见”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民国时期,这一情况有所改观,这一时期的董仲舒研究多了一层近代意义的学术成分。
事实上,1904年《中国白话报》即刊登《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学术》一文,其中介绍董子的性善说、仁义和忠恕说等“学理”内容。此文虽刊发于民国建立前,但已经具备民国学术的某些特点,故而纳入我们的介绍范围。张岱年《大纲》撰写之前或与之基本同时,还有金搏《孟荀贾谊董仲舒性说》(《新教育》1923年第16期)、甘蛰仙《董仲舒之名学》(《晨报副刊》1924年8月5日、6日、7日、8日)①此文虽名为“名学”,但所讲却是董仲舒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人生论等哲学内容。以“名学”为名,或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名学方法”作为古今思想沿革变迁之线索的枢纽的影响。、周谷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民铎》1928年第3号)、蔡尚思《董仲舒之儒家宗教》(《大夏季刊》1929年第2期)、秩素《董仲舒对于天治主义的贡献》(《清华周刊》1933年第1期)、朱显庄《董仲舒之政治哲学》(《清华周刊》1934年第2期)、徐瑞麟《孟子与董仲舒人性论述评》(《正论》1935年第36-37期合刊)、顾颉刚《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文澜学报》1937年第1期)等文章问世,内容涉及董仲舒的人性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论、政治哲学和思想特质等,这些无疑都是《大纲》写作的重要参照。此外,中国哲学史方面著作的相关章节也有值得注意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和钟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都简略介绍了董子的天人合一说和人性论,后者则比前者多写“仁义”一节,但在研究方法上皆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且其所论也都缺乏哲学味道。事实上,查看日本学者渡边秀方的《支那哲学史概论》(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4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加之谢、钟二人都有留日经历,可知他们的研究套路取自日本②谢无量1903年至1904年在日本游学,钟泰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至1911年,其《中国哲学史》乃任教之江大学期间用三年时间撰就,1929年首刊于商务印书馆。二人尤其是钟泰《中国哲学史》之前,日本已有内田周平《支那哲学史》(哲学馆,1888年)、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学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898年)和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金港堂书籍,1900年)、中内义一《支那哲学史》(博文馆,1903年)、高濑武次郎《支那哲学史》(文盛堂,1910年)、宇野哲人《支那哲学概论》(中文馆书店,1926年),这些著作深深影响了二人的研究。。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确立的标志,但因只完成了上卷,没有涉及董仲舒。“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11]的是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③1931年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1934年9月该书两卷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它的相关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大纲》之前从哲学视角分析董仲舒的典范。该书专设“董仲舒与今文经学”一章,从“董仲舒在西汉儒者中之地位”“元,天,阴阳,五行”“四时”“人副天数”“性情”“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灾异”“历史哲学”“春秋大义”等多个方面叙述董仲舒哲学,可谓全面而系统,但也的确存在“选录”多“叙述”少(亦即史料多、评论少)的缺点。我们知道,冯友兰深受西方新实在论的影响,因而他在写作公孙龙和朱熹两位在思想上与新实在论有一定相通性的哲学家时,分析得就比较充分,而董仲舒的思想却与新实在论相去甚远,故而他采取了“选录”多“叙述”少的处理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评论的深度上,可以认为,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比冯氏更进一步。
二、张岱年基于新唯物论的董仲舒哲学思想述评
撰写《大纲》时,张岱年已经确立了新唯物论的理论立场,认为相较于其他学派的哲学,它是“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1]132。因而,张氏对董仲舒的研判,乃是在新唯物论的视域下。
(一)总体概括
张岱年曾数次总括董仲舒的思想。早在1932年即说:“董仲舒是第一个中古哲学家,他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混合起来,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系统。在他的学说中有许多部分可以说不够算作哲学的理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1]32此中有三个关键词,“中古”确定其历史阶段,“混合”“不够算作哲学”指出其思想特征。《中国哲学大纲·序论》里,张岱年讲:“汉代思潮的权威,即是建议罢黜百家的董仲舒。董仲舒虽然主张独尊孔氏,但他的思想却是儒家与阴阳家的混合。他好讲阴阳五行,及天象人事的相应。他的思想中杂有许多迷信,不尽是纯粹哲学理论。董子的影响甚大,以后中国的社会伦理如三纲等,便是他确定的。”并接着评论道:“儒家与阴阳家之混合,是西汉思想的特色,当时人都好谈灾异,好谈天人相应。这实乃是思想低落的表征。”[12]17-18与几年前相比,多出的说法有“汉代思潮的权威”“主张独尊孔氏”“好讲阴阳五行,及天象人事的相应”“杂有许多迷信”“影响甚大,以后中国的社会伦理如三纲等,便是他确定的”“思想低落的表征”等,内容更加详尽,评判兼顾优劣,但总体评价不高。
20世纪50-70年代,张岱年对董仲舒的定位则明显带有时代的痕迹,受到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①1947年,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著《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李立三译:《苏联哲学问题》,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页),对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较大影响。1956年完成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张氏认为“董仲舒是汉代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目的主义。他承认天是有意志的上帝,是世界的最高主宰”“这种荒谬的学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力作辩护的”[13]38,39。20世纪70年代末的观点则有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如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张岱年说:“董仲舒代表地主阶级,从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他的哲学学说和政治主张。董仲舒宣扬唯心论,在哲学上是倒退,但他的体系中也采纳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材料。政治上与汉武帝的政策呼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3]369-370指出董子体系中也采纳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材料,乃是看到学界把日丹诺夫的定义简单化、公式化的不足,而真实情况是:“在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有对立斗争的关系,也有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关系,更有相互包含、相互联结的关系”“有些哲学家,总的倾向是唯心主义,而在个别问题上也同意唯物主义的观点。”[14]291
(二)宇宙论
1919年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人生切要的问题”为标准将哲学分为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六大门类,但这种分类显然失于混乱,前两者属于哲学问题,后四者则属于领域哲学,不能简单地与前两者并为一个系列。冯友兰30年代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借鉴西方,认为哲学的内容包括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分类科学,但忽略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张岱年于《大纲》中主张“中国哲学家对于其所讲的学问,未尝分别部门。现在从其内容来看,可以约略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政治论五部分”[12]3。他认为,前三部分是主干,相当于西方的一般哲学,而修养论、政治论则属于特殊哲学。因此,张岱年对中国哲学的架构只取前三部分。比胡适和冯友兰更进一步,他又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将各部分细化,分宇宙论为本根论和大化论,分人生论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分致知论为知论和方法论,从而给中国哲学穿上了系统的外衣。针对董仲舒的研究,张岱年也是从这个分类出发的。
在宇宙论之本根论和大化论两个部分,张岱年都揭示了董仲舒的学术贡献。张氏将董仲舒的本根论归入其中的太极阴阳论这一类①张岱年把本根论分成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理气论、唯心论和多元论六类。。阴阳观念比太极观念产生得早,但它以物有二本,所以《易传》之《系辞传》就用太极来统摄阴阳,作为阴阳之所从出者,亦即宇宙的究竟本根,而成一元论。在张岱年看来,董仲舒以元为一切之究竟根源,其所谓元“实即《易传》之太极”,且董子是“《易传》之后,论阴阳最详者”[12]63;可董仲舒虽然认为元在天地之前,而又强调天是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万物的创造者和人世治乱的最高决定者,“天主发施,地主化成”“如不加分别,则天地之间,惟一气而已。如加以区分,则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虽相反,但“阳乃所以生物,阴乃所以成物”;不止于此,董仲舒又兼言五行,与《洪范》的水火木金土的五行次序不同,他以木火土金水为“天次之序”。张岱年就此断言,“儒家之中,就现在可考见者而言,首先兼言阴阳五行者,似是董仲舒”[12]64,65。在1987年完成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张岱年又特别说明“董仲舒将阴阳家的一些观点纳入儒学体系中,建立了自己的阴阳学说”,同时指出董子之五行乃“比相生而间相胜”的关系,而他将五行配四时,则是“非常勉强的”[13]540,546。
大化指“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变易历程”。张岱年认为,大化论能够展示中国哲学的“殊异面目”:“西洋哲学中有认动是假相者,印度哲学家更多认变化为虚幻,在中国固有哲学中则认为变动是实在的”[12]192。大化论部分中有“两一”一章。在张岱年心目中,“两者,对待或对立;一者,合一或统一。两一者,对待而合一,即对立而统一”[1]374“中国哲学中两一的观念可以说与西洋哲学之辩证法中所谓对立统一原则,极相类似”[12]157。前文已示,1932年张氏即已注意到董仲舒的辩证法思想。《大纲》中,他又从“两一”的角度进一步总结说:“董仲舒很注重两极现象,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偶的,都是成对的;阴阳之对待,遍于一切。”[12]149用董仲舒自己的话讲,即“凡物必有合”(《春秋繁露·基义》)。既然宇宙是一个大化,就引发了“一个根本问题”——“大化性质”,即“大化是有目的的呢,抑并无目的?有主使之者呢,抑并无主使之者?即大化之动力是内在的呢,抑还有外在的主宰?”[12]149关涉董仲舒对大化性质的叙述,张岱年说,董氏讲天意,以为天生万物是爱利人,天象变化是谴告人。换言之,大化的动力不是内在的,而是有外在的高高在上的主宰之天。因之,在理论深度上,“董仲舒的天意说只是墨子天志论的复述”[12]161。如上判断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张氏多次给董仲舒“唯心主义的目的主义”的标签的依据所在。
(三)人生论
人生论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部分,上文已示,张岱年析之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
1.天人相类
在张岱年那里,天人关系论是人生论的开端,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问题则是天人关系论的开端。中国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两类回答:第一类认为人是藐小的,在宇宙中实无重要地位,这种观念主要见于《庄子》的《外篇》及《杂篇》,势力不大;第二类主张人身体虽然藐小,但有优异的性质,在天地间实有卓越的位置,这是多数哲学家的看法,董仲舒就在其中。他之前,老子、荀子、《礼运》都曾不同程度地表达这种观点。“董仲舒更极言人之卓越,认为人在宇宙中,实有很崇高很重要的地位”。根据《汉书·董仲舒传》所引董子“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的话,张岱年提出“人有道德有智慧,是人之所以贵之理由,此与荀子以有义为人之特殊优点,意思相近”[12]198,199。除《大纲》外,张氏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1987)、《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1982)、《中国古代的人学思想》(1991)、《论价值与价值观》(1992)等论著中一直坚持30年代的观点。
谈论人在宇宙中之位置的开端问题后,张岱年进而归纳说,中国哲学家论天人关系“较简”,然“有一特异的学说,即天人合一论”[12]202。天人合一论有两种:一是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代道学的“天人相通;一是董仲舒的“天人相类”。进言之,天人相类“亦可析为两方面。一,天人形体相类,此实附会之谈。二,天人性质相类,此义与天人相通论之天道人性为一之说相似,实际上亦是将人伦道德说为天道”[12]210。董仲舒的天人相类属于第一种。张氏强调,“‘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是董子天人关系论之宗旨”[12]204。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也多次提到董子此说,并与其“天人感应”关联起来,如说“在董氏的系统中,天人感应与‘天人一也’是密切联系的,因为他所谓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但张氏认为“在理论逻辑上,天人感应思想与天人合一观点并无必然的联系”[14]615-616。总体来说,张岱年对于董仲舒天人相类说的评价是不高的,“牵强附会”是评价它的高频词,另,还说它“内容粗浅而烦琐,理论价值不高”[14]615,“是天人合一的粗陋形式”[15]35,最好的评价也就是说“他肯定人道与天道的联系还是具有哲学意义的”[16]441。
2.性有善有恶
载抗肿瘤药物的壳聚糖纳米粒氨基化靶向修饰物的研究进展 ……………………………………………… 陈雨晴等(13):1850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中得到普遍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历来争论不休,派别纷呈,关注度非其他人生问题所能比。在张岱年,人性论是人生论的基础。他认为,“中国性论有一个特点,即以善恶论性”[12]279。从此一角度,张氏将董仲舒的人性论归入性有善有恶论,认为他是调和性善论与性恶论者。
张岱年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分析,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性的含义。董仲舒所谓性“是生而有之质”,这是“以生说性,颇近于告子”[12]229。第二,性的属性,即善或恶。此“生而有之质”中有善的要素,也有恶的要素,不是“纯粹的善”“完全的善”①1998年,在坚持性有善有恶论的基础上,张岱年对于董仲舒的人性论多了一个定位:“区别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可以说是后来性三品论的先驱。”(张岱年:《天人合一评议》,《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原因在于,性作为自然之资“乃天之所为”,而“天之所为有其限度”,需要得到教导才能成为完全的善,这就是董子所云“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所要表达的意思。第三,与孟子性论比较。首先,“善之表准”不同。孟子的善指善于禽兽,而董仲舒“视善甚高,所以认为善字不可以轻许”;其次,“性”的含义不同。“孟所谓性,专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要素”“董所谓性,非专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所以孟子说性已善[12]230,“董仲舒所谓性则指人的自然本性”[15]98。第四,性何以有不善?董仲舒提出两点理由:1)性中有情,情是性的一部分。性中的非情的要素是仁的,情则是贪的,“人之性与天之道也是相应的,……天有阴有阳,人性之中也有贪有仁”“仁是善性,贪是恶性”[16]441“贪性指情欲,仁性即道德意识”[15]98,因而性是兼含善恶的;2)人性不能全善,与环境有关。张岱年发挥道:“在此世界之中,生活之竞争甚烈。故人之争夺之心,常胜过其辞让之心;占有之心,常胜过其施予之心。求生则必相争,故人性无由全善。”[12]231第五,心的作用。根据董子的“心有哀乐喜怒,……心有计虑”(《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张岱年说:“哀乐喜怒是情,计虑是知。心兼含情知。”进而认为,与荀子一样,董仲舒所谓心具有宰制情欲之力[12]265。换句话说,心能制恶。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发现。遗憾的是,张氏此说并未受到当今学界的重视。
3.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人生理想论是人生论的中心部分,指关于人生最高准则的理论。中国哲人关于人生最高准则的理论可谓丰富、精深。
在人生理想方面,孔子讲仁,欲通过行仁而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不玄远,也不神秘;孟子“亦以仁为人生之第一原则;而又极注重义,仁义并举,以为生活行为之基本准衡”,希冀由此达到神秘性的生活之最高境界——“浩然之气”[12]291,294。张岱年认为,董仲舒是孟子之后“论仁义最晰者”,他“以对人对我分别仁义,爱人为仁,正我为义”,详细地说,即“仁为爱,而仅自爱,非是仁;爱人方足为仁。义为正,而仅正人,非是义;能正己方足为义”;此外,董子还仁智并举,“认为都是极必需者”[12]296,297。此中,分别仁义主要是对孔孟仁义观念的阐释,而仁智并举也是对孔子思想的推衍。对于董仲舒这两种观念,张岱年始终持肯定的态度,1986年完成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仍说“董仲舒的伦理学说中,关于‘仁义’关系、‘仁智’关系的议论颇有精彩之处”[17]642。《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则有更明晰、深入的分析:“仁是爱人,这是孔子所说;义是正我,这是董氏的创见,与《易传》《荀子》关于义的解说正相反。董子所谓‘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从文字学来说是错误的,但他所谓‘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却有精湛的含义。”[13]621该书中,张岱年不仅指出董子思想的继承及创新,并与《易传》《荀子》的相关观点进行比较,而且对董子不拘泥于文字训诂的解释表示称赞。
4.人生问题论
人生问题由人生中的矛盾引起。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学说即是人生问题论。天人关系论与人生论指向人生的自然状态,人生理想论确定人生当然的总原则,人生问题论则是研讨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张岱年认为,董仲舒讨论了人生的三个问题,包括义与利、自然与人为以及情的问题。
首先,义与利的问题。张岱年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1)董仲舒义利观的基本倾向是义重于利或义大于利。这是由于,在董子那里,“义乃所以养心,利乃所以养身。心贵于身,故义大于利”。张氏强调说:“此所谓利,指个人之利,即私利。”[12]4202)董子颇重公利,以“兴天下之利”为要务,又认为人君应该以“爱利天下”为意,以求天下之公利为目的。3)对比《春秋繁露》和《汉书》所引董仲舒语,判断正误。《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曰:“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则记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张岱年断言,这两个记载必有一误,因为“不急其功”与“不计其功”语意轻重相去甚远。他还从董子所说的“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等话推断其未尝不重功,因而“疑《春秋繁露》所载,乃董子原语;而《汉书》所记,乃经班固修润者”[12]422。4)《汉书》所记董子义利观二句“简括地将孔孟关于义利的思想完全表出了”,虽不是董子的原话,但对后世影响很大。张岱年发现,“董子所以能获得宋儒之相当景仰,全由此二语”[12]422。1986年,《试谈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变革》一文梳理了后世对这两句话的反应:“宋代理学家大多赞同董仲舒的观点,强调所谓‘义利之辨’。事功学派叶适对董仲舒的命题提出批评,认为道义脱离了功利就成为‘无用之虚语’了。到清代,颜元讨论义利问题,提出对董仲舒命题的修改意见。颜元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15]174三年后张氏写作的《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学说》一文则针对颜元的观点进一步评论道:“应该承认这是比较全面的观点。道义是不能脱离功利的,也不能专求功利不顾道义。”[15]477不难看到,这种评价与其30年代的生活理想论是一致的,张岱年倡导理生合一,认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便充分地表现出重理派的态度:凡做事只问于理应该不应该,不管生活的实际”。其实,理想的生活应该理生并重:离开了生,就无所谓理,离开了理,也会毁坏了生;“生的圆满,即是理的实现;理的实现,就是生的圆满”[1]281,283。
其次,自然与人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张岱年的理解里也是天与人的问题,但所论与天人关系论中不同,它侧重解答的是:“人类的生活,应该因任自然,无所作为呢;还是应该改变自然,注重创造?”[12]447董仲舒宣扬天人合一,则“自然与人为,可以说根本不成问题”。张岱年以为,董仲舒是提倡“继天”的。具体而言,就是“既非任天,亦非制天,而乃顺天之道而有所创作”。顺天道,则会好善、恶不善,但人未必能不动摇,故而需要人道。就此,张氏发挥说:“董子讲天人相类,而又重天人之分,似以为人固当知天人之合一,而亦不当忘天人之区别。”[12]455
再次,情与无情的问题。张岱年区分欲与情,认为前者指向饮食男女声色货利,而后者指向喜怒哀乐爱恶惧。每个人都有情,发而不当,常至害事,所以情的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在张氏看来,这是一种“关于消除苦恼获得至乐之方法的理论”,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统御情绪的艺术”[12]495。他把中国哲学中关于情的思想分成节情说、无情说、有情而无情说三种,主张董子的有关思想属于节情说。依张岱年之见,董子不赞成无情,以为喜怒哀乐当发之时不可不发,而期望人在有喜怒哀乐之情时返于“中”,由此便能得到“和”。一句话,“董子论情,以‘中和’为要义”[12]500。张氏还特别提到,“董子所谓中,指无过无不及,非《中庸》未发之意”[12]501。
从上可以看到,张岱年从宇宙论和人生论两个视角对董仲舒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评价。这些总结和评价不仅独到,而且深刻。
三、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的特征
纵观董仲舒研究史可知,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民国时期,他率先发掘董子的辩证法思想,更在《大纲》一书中系统呈现其整体思想面貌,进而立足新唯物论的立场加以评析,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研究虽带有时代烙印,但在有些问题上也不乏值得回顾的见解。
总体观之,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坚定的理论立场。自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就确立了为其一生所坚守的新唯物论的思想信仰,并将此立场贯穿于其中国哲学史研究之中,董仲舒研究也不例外。新唯物论视域中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非史学式的,而是哲学式的。然而,任何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都是带有“成见”的。所以,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某些哲学家如张载的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提出了影响很大的“一家之言”①宋明理学分系中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的三系说即本于张岱年的《大纲》。这种说法得到普遍认可。,但他对从唯物论视角看归入唯心主义的哲学家的评判则未必公允。董仲舒思想在张岱年那里总体评价不高的原因就在这里。第二,明确的哲学史方法论。哲学史方法论是张岱年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30年代他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两篇书评里就渗透着鲜明的哲学史方法论[18]。《大纲》更是提出并应用“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和“辨其发展源流”[12]“自序”的四种研究方法。在董仲舒研究上,张岱年注重对其基本概念的解释,如对“元”“性”“仁”“义”等概念的界定,就是“析其辞命意谓”之方法论的使用,亦即对西方哲学的“解析法”的汲取;从宇宙论和人生论两个方面阐发董仲舒思想,即是“察其条理系统”的贯彻。第三,精湛的文本校勘。这一点体现在张氏对董仲舒义利观的两种记载的分析上。他不仅使用“对校法”②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一书中总结了“校法四例”,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堪称经典。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也吸收陈氏之说。,指出《春秋繁露》与《汉书》所记的文字差异,而且综合运用“本校法”“理校法”,从董仲舒相关文字的思想倾向判断孰是孰非,展现了深厚的学术根基。
毋庸讳言,基于张岱年新唯物论与董仲舒唯心主义③目前,学界已不太使用这个术语来评价董仲舒,但在张岱年的新唯物论的视域下,董子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故而我们仍沿用旧说。的理论冲突,他在董子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是需要商榷的。如,被他多次判定为“牵强附会”“理论价值不高”的董子的“天人合一”说,如果放在政治哲学的视角下,就显得格外具有意义。因为“天”经过荀子的描绘,神秘、主宰的成分被剔除,成为自然的、客观的存在,而其神秘、主宰的成分曾经是对君这个无限体的制约力量。此种意义的天的消解,无疑会使古代君王成为没有任何约束的政治主体。秦王朝的短命警告世人,这是极端危险的。故而,到了董仲舒,重新恢复天的权威、天对君王的谴告功能,就成为维护其提倡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必需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董子的理论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和政治哲学价值,而非只是“牵强附会”。在这一点上,张岱年的研究就缺少了一种“用各家本来的观点来讲”[19]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