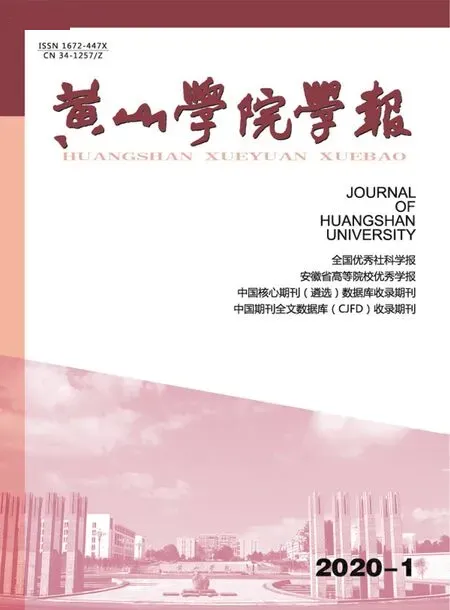传统而新锐 宏阔而细微
——李时人先生治学思想管窥
李玉栓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李时人先生(1949—2018)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40年来夙夜祗勤,兢兢治学,终成一代名家。据统计,先生生前共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出版专著20余种,至若《中国禁毁小说大全》《明清小说鉴赏辞典》《全唐五代小说》《崔致远全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以及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等,皇皇巨著,嘉惠学林。仔细研读先生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先生有着一套自己的学术思想,诸如“文人是靠笔说话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补空白、攀高峰、立异端”的三种研究范式等,传统而新锐,宏阔而细微。从中选择三点,结合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就予以阐述,或许可以从中窥见先生独具特色的治学思想。
一、“工夫在诗外”的治学理念
“工夫在诗外”,本是宋代诗人陆游向其子传授写诗经验的一句话,意思是要想把诗写好,不能只注重磨炼诗歌本身的辞藻、技巧、形式等,而应该走出诗歌,向生活、向社会、向自然去寻找源泉,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正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李时人先生经常借用这句话来形容如何才能做好学问,他的意思有这样两层。
从宏观上看,做学问不能仅仅着眼于学问本身,而应当多读书,甚至是不作辨别地去读书。先生在中学时代就酷爱读书,“近乎狂热地找各种‘课外书’来读,从来不考虑这些书与功课有没有关系”[1]。当时流行的《红岩》《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自不必说,国内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的小说他几乎全部读遍,国外的如法、英、德、意的小说也都阅读,对中国古代小说更是痴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他都读过不止一遍。当后来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时,他首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与这一时期的大量阅读密不可分。“文革”期间,先生继续坚持读书,《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列著作读,《赤脚医生手册》也读,“家里的书读完了,就千方百计到外边去找”[2]。正因为这种坚持,当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之后,他便有机会走上大学的讲台,而这种“无书不读”“无时不读”的积累也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做足了储备。读先生的文章,除了雄浑的论述、明晰的思辨、个性鲜明的语言外,文中旁征博引而似信手拈来的渊博学识既令人叹服,也让人着迷。先生在近40年的治学经历中也不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曾先后编纂过《古训新编》《中国旅游文学大观·诗词卷》(上下册)《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等,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工夫在诗外”的理念。
从微观上看,做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本身,而应当从具体问题生发开去联系问题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观照。这种观照,既包括精神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也包括物质层面的,这在今天叫做“文化学”研究方法。1985年,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和杂剧的繁盛》一文,提出以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视角去阐释元代杂剧兴盛的原因,引起学者共鸣。1986年,在第二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一文,引起热烈反响,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视角,后来又发表《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金瓶梅〉》再次强调这一观点。此后,他相继发表《出入乾嘉:李汝珍及其〈镜花缘〉创作》《〈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等论文。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中国古代发生的一种文化和文学事象”[3],“作为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和人类成年的艺术,小说具有包罗万象的气魄,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可以说是用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俗史’和‘心灵史’”[4],并明确指出:“我总觉得,从社会思想文化的角度,包括从社会思潮的角度研究古代小说,不仅有利于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对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建设来说,也是有一定意义的。”[5]先生还持着这样一种理念去指导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如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王言锋《中国16—18世纪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余丹《宋代文言小说的文化阐释》、聂春艳《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与实学思潮》等。这种治学理念又由小说推广至戏曲:“真正的中国文化其实并不全在孔孟程朱、庄老佛禅的典籍之中,不经的小说戏曲之类也常常凝聚、积淀着民族的精神文化。”[6]再由小说、戏曲扩展到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如在阐述明代文学特点时,“各种文学创作突出表现出与时代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社会心理同步的态势,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所占份额增大,成为时代‘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地体现出了文学的职能、价值和意义。”[7]在剖析地域文学的生成机制时,“就中国古代而言,一个地区文学繁荣的沃土实际是‘文化’——或者说文学之树总是植根于‘文化土壤’之上。”[8]当这种理念发展成熟以后,他提出了更为铿锵的论断,“即使是那些艺术上几乎毫无可取的小说作品,作为一种文化遗存,也可能因其具有一定的文化内容而成为人们认识历史文化甚或探索民族心灵历程的资料。”[3]除小说以外,先生自己也曾尝试运用这种理念去观照其他文学名著,例如他曾旗帜鲜明地提出应当“以‘文化学’的眼光对《文心雕龙》加以审视”,因为《文心雕龙》“并非纯文学理论著作,它的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比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要宽泛得多”,“《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刘勰较之一般谈文说艺者有着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作者的文化通观,许多问题,甚至范畴、概念的使用都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关”[9]。
二、“求实、创新、循序渐进”的治学原则
李时人先生曾多次公开地表述这一治学原则,如在《〈江苏明代作家文集述考〉序言》中,“对于治学,我从来主张求实、创新、循序渐进。”[10]在这三个词语中,“求实”是基础,“创新”是目的,“循序渐进”则是方式。《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的编纂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治学原则。
七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是中华书局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1996年先生接受《明代卷》的编纂任务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尽可能先搞清楚明代到底有多少文学作品存世?有作品存世的作家到底有多少?各人情况如何?”[10]4只有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弄清楚,然后才能从中遴选出一定数量的作家进行编撰。由于明代诗文作家的历史文献数量惊人,搜寻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明代诗文研究在资料整理方面长期滞后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为此,先生本着“求全”“求实”的原则,遍览明人总集、别集、笔记、方志、金石、正史《文苑传》《艺文志》以及各种目录类书籍,历经十余年时间最终考索出明代作家20000多人、存世诗文集近5000种,这是对长期以来困扰和阻碍明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数据问题的有力回答,是继明末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以来,在明代诗文研究资料上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在如此近似“海选”的基础上,再从中遴选出3046人入编《明代卷》,对他们生平经历、文学活动、著述情况、成就评价以及生平事迹的资料来源等一一进行述介。
与此同时,先生还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合作的博士后进行有关明代文学的学位论文和出站报告的撰写,从2003年至2018年,已有60多篇通过答辩,如马汉钦《明代诗歌总集与选集研究》、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芦宇苗《江苏明代作家诗论研究》、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刘坡《李梦阳与明代诗坛》、周潇《明代山东文学史》、张慧琼《唐顺之研究》、鲁茜《李维桢研究》、马兴波《明代笔记考述》等,这些出站报告和学位论文涉及明代的地域作家研究、个案作家研究、家族作家研究、女性作家研究、名作名著研究、诗文总集(选集)研究、诗文理论研究、结社交游研究、笔记史料研究等,可以说是覆盖了明代文学的方方面面。自1996年接受编写邀请至2018年正式出版,前后经历了20余年,时间不可谓不长。
除此以外,《全唐五代小说》,从1987年开始到1998年出版,用了10余年时间,到2013年再版又用了15年时间。《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从2000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成书与渊源》,至2011年完成初稿,获批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后继续撰写,最终完成约170万字的成果,前后花了18年时间。《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2003年左右制订研究规划,至2018年也已经过15年时间,但也只是基本完成初稿,离最后定稿、出版应该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其他成果或许花费的时间并没有这么长,但所用时间与成果规模之比也多超出常规,都是遵循着“求实、创新、循序渐进”这一原则展开研究的。
三、“靠材料说话”的治学方法
“研究问题要靠材料说话”是李时人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所谓“靠材料”就是要有文献考证;“说话”就是能够理论阐述。两者结合实际就是说研究问题要能考论并用、考论相长,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谓也。学界也普遍认为李时人先生“长于传统的文献考据学,又认真学习科学理论及各种研究方法”,“考论兼长是李时人同志治学的特点”[11]。
李时人先生治学向来注重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读。他在编纂《全唐五代小说》时就说:“我觉得,搞古代文史研究,首先应该是对对象的全面了解和正确把握,否则其他一切都谈不上。”[12]在谈到明代文学的研究现状时又说:“20世纪以来的明代文学研究存在不少问题……相对于其他朝代的诗歌文献整理,明代可能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13]他特别反对那些轻视文献、游谈无根的治学行为,“不注重第一手史料,连最基本的史实都没有搞清楚就妄发议论”,是一种“以哗众取宠骗取高名令誉的做法”[10]6。正因为如此,先生早期的很多文章都是从考证入手的,仅以“考”字命名的就不下10篇。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文献的编选、辑校、评注,《古训新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国旅游文学大观·诗词卷》《全唐五代小说》《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游仙窟校注》《崔致远全集》等,莫不如是,直到离世时还在编注《唐人小说选》。先生在文献考订方面的特色和成就早已为学界所公认和赞誉,原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陈毓罴就对他早期的学术研究作出“材料翔实、考证周密、眼光明锐”的鉴定[2]37,原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魏崇新则评价他的《金瓶梅》研究是“论据充分,论证严密,考订精慎”“考论兼长”[14]。
但仅仅进行文献考订还是不够的,“考”只是手段、工具,“论”才是目的、旨归,任何“以繁琐考证、放弃思想创造”来做学问,都是“‘现代’学术基础理论薄弱的表现”[15]。李时人先生学识渊博、才力雄厚,所以论述起来常常大开大合、不拘一格。这里不妨略举几个“中西结合”的例子。比如,在阐释“文化”一词的内涵时,一方面引用《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和《说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进行解释,另一方面也指出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进行的定义[8]41。在论述科举制度发展时,不仅认为“‘科举制度’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中国特有文化下产生的特有制度,而且依据西方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1577—1628)等人的介绍,认为19世纪西方各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首先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但与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肯定不无关系”[16]。在论述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时,既会关注朱熹《诗集传》、魏征《隋书·文学传序》、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相关观点,也会联系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19世纪法国的丹纳以及20世纪瑞士的让·皮亚杰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域的影响,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的观点[8]39。在谈论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时,会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文学”谈起,尤其是“骑士文学”中的叙事作品——韵文体和散文体的“骑士传奇”(romance),并通过对“骑士”阶层、“骑士”的爱情婚姻以及“骑士文学”的细致梳理,指出“骑士传奇”所描绘的种种爱情故事“究其底里,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17]。类似的例子在先生的文章中比比皆是,而像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丹纳等人的名字和言论更是可以经常见到,甚至于像“哥德巴赫猜想”这种跨学科的术语也会被拿来使用。
“考”,考证、考据、考订;“论”,评论、论析、阐述,两者结合,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方法,李时人先生也继承了这一治学路数,主张实证与评释不可偏废。他曾专门撰文讨论乾嘉汉学的得与失,认为“乾嘉学派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和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学术研究为形式的思想文化潮流”,在实实在在的考据之中是蕴藏着理论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实际上就是说乾嘉学派是有考有论、考论结合,而并非有些人所说的“为考据而考据”[15]。在坚持考论并用的治学方法的同时,先生还特别强调由文献考证到结论推导的科学合理性,强调研究问题不能依靠表面考证、实则索隐的“主观想象”,更不能用“拼凑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观想象”,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根据材料得出结论”。他因此发出呼吁:“衷心希望搞考据工作的同志能尽可能依据可靠的材料和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少走一些弯路”[18]。
了解李时人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求学、治学经历极富“传奇”色彩。198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授先生以“国家自学成才”奖章,在表彰大会上,先生曾引用刘禹锡“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作为发言题目,这是先生对之前生活、学习经历的总结,也成为日后他在学术研究中孜孜以求的真实写照。先生一生著作宏富,学术思想自成一体,不是一两篇文章即可概而述之,加之个人学殖与才力有限,实难尽窥先生学术之全貌,遑论治学思想之奥义,仅撰此短文以为引玉。